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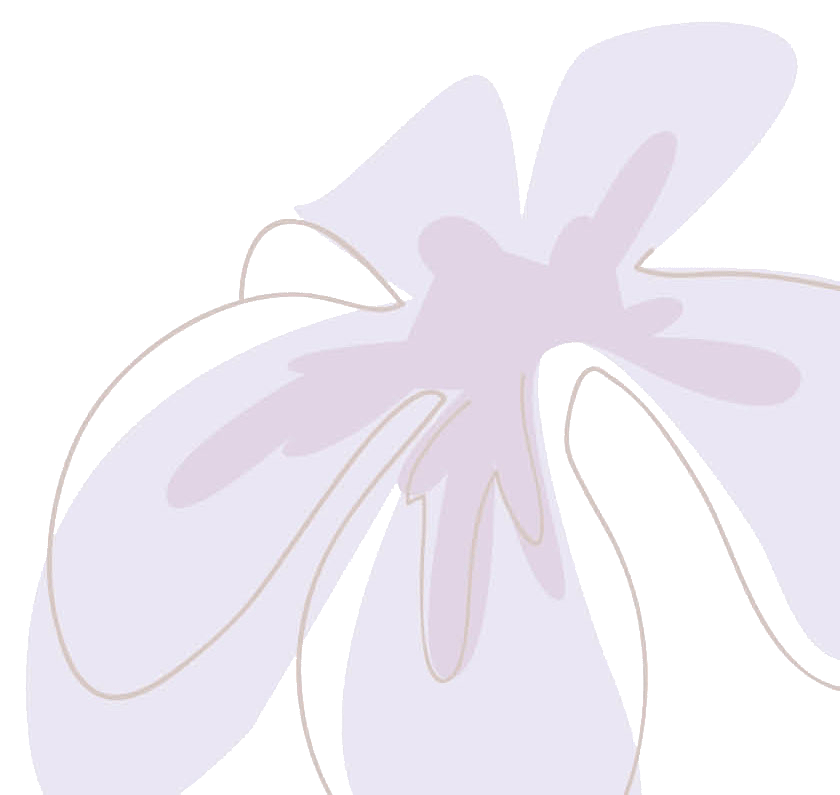
冯友兰先生——我的父亲,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四日来到人世,又于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毁去了皮囊,只剩下一抔寒灰。在八天前,十一月二十六日二十时四十五分,他的灵魂已经离去。
近年来,随着父亲身体日渐衰弱,我日益明白永远分离的日子在迫近,也知道必须接受这不可避免的现实。虽然明白,却免不了紧张恐惧。在轮椅旁,在病榻侧,一阵阵呛咳使人恨不能以身代。在清晨,在黄昏,凄厉的电话铃声会使我从头到脚抖个不停。那是人生的必然阶段,但总是希望它不会来,千万不要来。
直到亲眼见着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血压下降,身体逐渐冷了下来,直到亲耳听见医生的宣布,还是觉得这简直不可能,简直不可思议。我用热毛巾拭过他安详的紧闭了双目的脸庞,真的听到了一声叹息,那是多年来回响在耳边的。我们把他抬上平车,枕头还温热。然而我们已经处于两个世界了。再无需我操心侍候,再得不到他的关心和荫庇。这几年他坐在轮椅上,不时会提醒我一些极细微的事,总是使我泪下。我的烦恼,他无需耳和目便能了解。现在再也无法交流。天下耳聪目明的人很多,却再也没有人懂得我的有些话。
这些年,住医院是家常便饭。这一年尤其频繁。每次去时,年轻的女医生总是说要有心理准备。每次出院,我都有骄傲之感。这一次,是《中国哲学史新编》完成后的第一次住院,孰料就没有回来。
七月十六日,我到人民出版社交《新编》第七册稿。走上楼梯时,觉得很轻快,真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父亲更是高兴,他终于写完了。直到最后一个字,都是他自己的,无需他人续补。同时他也感到长途跋涉后的疲倦。他的力气已经用尽,再无力抵抗三次肺炎的打击。他太累了,要休息了。
“存,吾顺事;殁,吾宁也。”父亲很赞赏张载《西铭》中的这最后两句,曾不止一次讲解:活着,要在自己恰当的位置上发挥作用;死亡则是彻底的安息。对生和死,他都处之泰然。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的老助手、八十八岁的李濂先生来信说:“十一月十四日夜梦恩师伏案作书,写至最后一页,灯火忽然熄灭,黑暗之中,似闻恩师与师母说话。”正是那天下午,父亲病情恶化。夜晚我在病榻边侍候,父亲还能继续说几个字:“是璞么?是璞么?”“我在这儿。是璞在这儿。”我大声叫他,抚摩他,他似乎很安心。我们还以为这一次他又能闯过去。
从二十五日上午,除了断续的呻吟,父亲没有再说话。他无需再说什么,他的嘱托,已浸透在我六十二年的生命里;他的嘱托,已贯穿在众多爱他、敬他的弟子们的事业中;他的嘱托,在他的心血铸成的书页间,使全世界发出回响。
父亲是走了,走向安息,走向永恒。
十二月一日兄长钟辽从美国回来。原来是来祝寿的,现在却变为奔丧。和母亲去世时一样,他又没有赶上;但也和母亲去世一样,有了他,办事才有主心骨。我们秉承父亲平常流露的意思,原打算只用亲人的热泪和几朵鲜花,送他西往。北大校方对我们是体贴尊重的。后来知道,这根本行不通。
络绎不绝的亲友都想再见上一面,不停的电话询问告别日期。四川来的老学生自戴黑纱,进门便长跪不起。南朝鲜学人宋兢燮先生数年前便联系来华,目的是拜见老人。现在只能赶上无言的诀别。总不能太不近人情,这毕竟是最后一面。于是我们决定不发讣告,自来告别。
柴可夫斯基哽咽着的音乐伴随告别人的行列回绕在遗体边,真情写在每一个人脸上。最后我们跪在父亲的脚前时,我几乎想就这样跪下去,大声哭出来,让眼泪把自己浸透。从母亲和小弟离去,我就没有痛快地哭一场。但是我不能,我受到许多真诚的心的簇拥和嘱托,还有许多许多事要做,我必须站起来。
载灵的大轿车前有一个大花圈,饰有黑黄两色的绸带。我们随着灵车,驶过天安门。世界依然存在,人们照旧生活,一切都在正常运行。
我们一直把父亲送到炉边。暮色深重,走出来再回头,只看见那黄色的盖单,它将陪同父亲到最后的刹那。
两天后,我们迎回了父亲的骨灰,放在他生前的卧室里。母亲的遗骨已在这里放了十三年。现在二老又并肩而坐,只是在条几上。明春将合葬于北京万安公墓。侧面是那张两人同行的照片。母亲撑着伞,父亲的一脚举起,尚未落下。那是六十年代初一位不知姓名的人在香山偷拍的。当时二老并不知道。摄影者拿这张照片在香港出售,父亲的老学生加籍学人余景山先生恰巧看见,遂将它买下。七十年代末方有机会送来。母亲也见到了这帧照片。
亲爱的双亲,你们的生命的辉煌乐章已经终止,但那向前行走的画面是永恒的。
借此小文之末,谨向所有关心三松堂的亲友致谢。关系有千百种不同,真情的分量都不同寻常。踵吊和唁文未能一一答谢,心灵的慰藉和嘱托永远铭记不忘。
1990年12月17—19日 距曲终已三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