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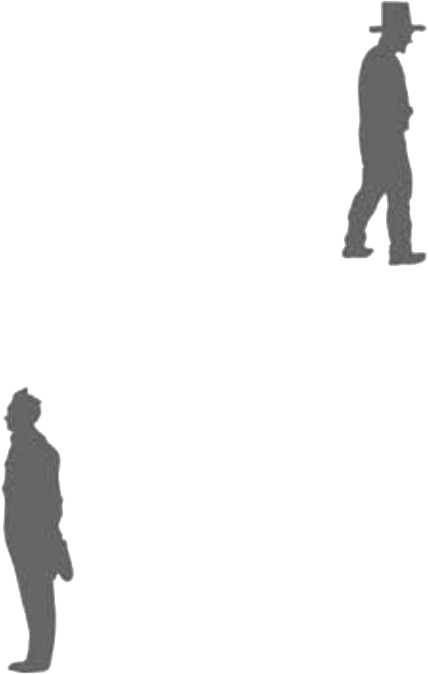
一八二八年九月,全德国最伟大的数学家高斯多年来第一次离开故乡,前往柏林出席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他当然不愿意动身。在获邀后的几个月里,一直都在拒绝,却敌不过亚历山大·冯·洪堡的顽固和坚持,最终心软答应下来。即便这样,他也仍希望动身的那一天永远都不要到来。
现在,高斯教授躲在床上。明娜正催他起床,马车已经备好,何况路途遥远。他紧紧抓住枕头,闭上双眼,试图让妻子就此消失。再次睁开眼睛时,明娜仍然站在床前,他便开始骂她难缠、专制,是自己余生的不幸。当然,骂也没用,到头来,他只好掀起被单下床。
他带着怒气草草洗漱完走下楼,儿子欧根正在客厅等着,行李已经装好。一见到儿子,高斯的怒火喷发了,他抓起窗台上的一只罐子,用力摔了个粉碎,然后跺着脚,继续砸东西。欧根和明娜一左一右用手摁着他的肩膀,向他保证人们会好好照顾他,他不久就能回到家里,这一切就像一场很快结束的噩梦,但高斯仍不能平静下来。直到他年事已高的母亲被外面的闹声惊扰,从房间里走出来,捏着他的脸问她那个勇敢的儿子哪儿去了,他才多少收敛了一些,非常不情愿地辞别明娜,心不在焉地摸了摸女儿和小儿子的脑袋,由人搀扶着上了马车。
旅途十分艰苦。高斯骂欧根是个失败者,顺手拿起木头拐杖,用力去捅儿子的脚。然后,他皱紧眉头盯着窗外看了好一阵子,喃喃问道,女儿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出嫁,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娶她,问题究竟出在哪儿?
欧根向后拢好长发,两手捏捏头上的红帽子,似乎不想回答。
说话,高斯冲他嚷道。
说实话,欧根应道,姐姐不是美人儿。
高斯点了点头,这个回答不假。便打住话题,问欧根要本书看。
欧根把自己刚翻开的书递给他:弗里德里希·扬
 的《德意志体操艺术》。这是欧根最喜欢的书之一。
的《德意志体操艺术》。这是欧根最喜欢的书之一。
高斯看了不过几秒钟就抬起头来,转而抱怨车轮上的新式皮弹簧减震装置,这东西让人们坐车时比以前更难受了。接着他说,不久的将来会有一种机器,以子弹的速度搭载人们往返于城市之间,到了那个时候,从哥廷根到柏林,只需要半个小时。
欧根摇摇头,一脸不相信。
这既古怪又不公平,高斯说,生活充满了可鄙的专制,一个真实的例子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会在某个特定的时代出生,然后被束缚其中。它使你在面对过去时,有一种天然的优势,而在面对未来时,又与小丑无异。
欧根困倦地点了点头。
即便拥有他这样的头脑,高斯接着说,身在人类文明早期或者奥里诺科河
 畔,也无能为力;而两百年后的任何一个蠢蛋,都会以他为消遣,杜撰各种关于他的谬见。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突然又愤恨地骂欧根是个失败者,然后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本书上。欧根凝视着窗外,以此来掩藏他那张因为受了羞辱和伤害而扭曲的脸。
畔,也无能为力;而两百年后的任何一个蠢蛋,都会以他为消遣,杜撰各种关于他的谬见。他停下来想了一会儿,突然又愤恨地骂欧根是个失败者,然后才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那本书上。欧根凝视着窗外,以此来掩藏他那张因为受了羞辱和伤害而扭曲的脸。
《德意志体操艺术》是一本介绍体操器材的书。作者详细地讲解了由他亲自设计的、可以让人们在上面翻转跳跃的运动设备,还给它们取了名字:鞍马、平衡木、跳马。
这家伙简直疯了!高斯说着,一把打开车窗,将书扔了出去。
欧根喊着,那可是他的书。
就是这样才要把它扔掉,高斯说完就闭上眼睛睡着了,直到傍晚在边境驿站换马时才醒来。
在套换马匹的空当,他们坐在驿站的餐厅里喝土豆汤。客人很少,店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个蓄长须、两颊深陷的瘦男人。那人坐在邻桌,偷偷地打量着他们。高斯因梦见各种体操器材而恼怒不已,愤懑地说身体简直是一切耻辱的根源,上帝真会恶作剧,像他这种了不起的灵魂,竟被困在一个孱弱的躯体里;而欧根那样的庸人,却几乎从不生病。
欧根回应说他小时候得过天花,差点儿送了命,如今还能看到疤痕。
哦,是的,高斯说他都忘了那件事。他指指窗外的驿马,说这真是个笑话,同样的路程,富人花费的时间是穷人的两倍—租驿站马匹的人,每站都可以更换新马;骑自己马的人,得等着它恢复精力才能继续上路。
那又怎么样?欧根说。
啧啧,对于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这似乎是理所当然,高斯说,就好比年轻男人会随身带手杖,老年人反而不带。
大学生持节杖,欧根说,一向如此,这习惯还会延续下去。
或许吧,高斯笑了笑。
他们不再说话,只是默默转动着汤匙,直到边境宪兵进了餐厅,命令他们出示通行证。欧根递给他自己的通行证,那是一张官方证书,上面写着:“此人是学生,无须怀疑,获准随他父亲一道踏上普鲁士的土地。”宪兵怀疑地看着欧根,又仔细检查了一遍通行证,终于对他点了点头。接下来是高斯—而他,身上什么凭证都没有。
没有任何证明吗,宪兵吃惊地问道,没有邀请函,没有官印,什么都没有?
高斯说他从来都不需要这些,上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还是在二十年前,那时就没有任何问题。
欧根试着向宪兵解释他们是谁,要去哪儿,是应谁的邀请。自然科学研究者会议,是受国王的恩泽而召开。作为荣誉嘉宾,他的父亲可以说是—直接受到了国王的邀请!
宪兵执意要看通行证。
欧根接着对宪兵说他可能有所不知,自己的父亲声名远扬,是所有的研究学会的会员,少年时就已被称作“数学王子”。
高斯点了点头:人们说拿破仑就是为了我,才放弃炮轰哥廷根的。
欧根听了脸刷地变白了。
噢,拿破仑啊,宪兵重复了一遍这名字。
没错儿。高斯答得很干脆。
宪兵提高声音再一次命令道:出示通行证!
高斯干脆把脑袋枕在胳膊上,懒得动了。欧根用胳膊肘捅他,也没有用。随便啦,高斯喃喃自语,反正他也想回家,这根本就无所谓。
宪兵摆弄着自己的军帽。
就在这时,邻桌那男人掺和进来了:这一切都将结束!德意志将获自由,良善的公民将自在地生活、旅行—身体健康、灵魂饱满,纸上公文之类的,他们再也不会需要。
宪兵满脸怀疑,径直走过去,请他出示证件。
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男人一边嚷着,一边翻腾口袋。突然他跳起来,撞翻椅子,飞奔了出去。宪兵盯着大开的餐厅门,几秒钟后才回过神来,追赶而去。
高斯慢悠悠地抬起头。欧根提议:立即起程。高斯点了点头,默默喝完剩下的土豆汤。岗哨里空无一人,两个宪兵都去追捕那个蓄长须的男人了。欧根和马车夫一起挪开道上的横栏木,踏上了普鲁士的土地。
现在,高斯心中的阴霾一扫而空,轻松愉快地谈起了微分几何:人们几乎无从推测弯曲空间中的路径究竟指向何方,就连他自己对此了解得也很粗浅—欧根真该庆幸自己的凡庸!因为懂得这些有时反而让人感到焦虑和恐惧。接着他开始回忆年轻时的苦难。他有个冷酷无情、不负责任的父亲—在这一点上,欧根应该是要谢天谢地了吧。高斯说,他在会说话之前,就已经能心算了。有一次他的父亲在算工资时出了错,他立刻哭起来。父亲刚把错误更改过来,他就变得安安静静了。
欧根一副入神倾听的样子,尽管他十分清楚这个故事纯属杜撰,是他哥哥约瑟夫编造、四处宣传的。父亲一定是听了太多次,以至于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高斯又说起了“巧合”:“巧合”是一切知识的敌人,而他一直想要战胜这个敌人。靠近去观察,可以窥知藏在每处表象之下的无穷因果。退远了看,又可获知整体全貌。所谓自由和巧合,不过是观察距离上的问题。听懂了吗?
多多少少吧,欧根疲惫地回答,一边瞅了瞅自己的怀表。它走得不怎么准,但是现在一定是在凌晨四点半到五点之间。
至于那些概率的规则,高斯揉着发痛的背脊,接着说道,却并不严格。它们不是自然法则,出现例外也是可能的。就拿赌博来说,像他这种天才可能会赢,十足的傻瓜也可能会赢。有时他甚至推断,即便那些物理定律,也是循了统计学的规则,因此也允许有例外:幽灵的存在、思想的传承。
这算不算是玩笑话?欧根问道。
高斯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罢便闭上眼睛,又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傍晚时分,他们到达柏林。数以千计的矮小民居,既无中心又无秩序,堆建在欧洲最泥泞之处、一片正在扩展的聚居地。一些恢宏雄伟的地标建筑正在兴建:一座大教堂、几处宫殿,还有一座用来展示洪堡那些伟大考察发现的博物馆。
几年之后,欧根说道,这里将变成一座像罗马、巴黎或者圣彼得堡那样的大都会。
全无可能,高斯反驳道,城市通通讨人厌!
马车在路面很差的石板路上颠簸,马匹被狂吠的路犬惊吓了两次,车轮也几乎要陷入小巷中的湿沙地里。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街四号,在市中心,新博物馆工地的后面—为了避免走错路,高斯用细羽毛笔绘制了一张非常精准的方位图。一定是有人老远就看见了他们并且通报了洪堡,他们刚刚驶进院子,屋门便打开了,四个男子径直向他们跑过来。
亚历山大·冯·洪堡是个头发斑白、身形矮小的老先生。跟在他后面的,是一位秘书—手里拿着已经打开的记事本,一个身着制服的仆人,还有一个长着络腮胡的年轻人,他带着连有木箱的支架。四个人像是预先排演过一样,摆好姿势各就各位。站在最前面的是洪堡,他朝着就要开启的马车门,张开了双臂。
马车门全无动静。
马车里传来激烈的争论声。不要,有个声音在喊,不要!之后是一记沉闷的敲击声,又是第三声不要!之后便好一阵子都没有半点儿声响了。
车门终于开了,高斯小心翼翼地迈出来,脚踏在柏林的街道上。洪堡一把抓住他的肩膀,高喊对于科学,对于他自己而言,这是一个多么伟大和荣幸的时刻!吓得高斯直往后退。
秘书忙着做记录,木箱后面的年轻人则轻声说道:准备!
洪堡僵住了。他不动嘴唇地低声向高斯介绍:那个年轻人是达盖尔
 先生,正在他的资助下研制一种设备,将生命中的各种瞬间拓印在一层光敏碘化银薄膜上—连流逝不停的时间,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劫持。无论如何,请别动!
先生,正在他的资助下研制一种设备,将生命中的各种瞬间拓印在一层光敏碘化银薄膜上—连流逝不停的时间,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劫持。无论如何,请别动!
高斯对洪堡说他想回家。
马上就好了,洪堡仍旧低声说,十五分钟左右吧—这算相当进步了。不久前还要比这长得多呢!第一次试验时,他甚至觉得自己的背会撑不住。高斯想要逃走,但那个小老头儿却用令人吃惊的力道抓紧他,压低声音向侍立一旁的仆人下了命令,快去通报国王!仆人飞奔而去。然后,显然是因为脑袋里面突然蹦出了个什么念头,洪堡又对秘书说:记下来,调查在瓦尔内明德
 养殖海豹的可能性,各项指标看起来都挺合适,明天向我汇报!秘书记了下来。
养殖海豹的可能性,各项指标看起来都挺合适,明天向我汇报!秘书记了下来。
直到这时,欧根才一瘸一拐慢腾腾地下了马车走过来,并为他们的迟到表示歉意。
这里没有什么早晚的问题,洪堡小声说,只有要做的事情,而且迟早都会干完的。谢天谢地,银片应该还可以继续感光,别动!
正说着,一名警察走进院子,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晚点再说。洪堡紧抿双唇,轻言细语。
这算是一场非法集会了吧,警察说道,马上散开,否则就要公事公办了。
洪堡嘟哝着说他可是宫廷大臣。
什么?警察凑近了身问。
宫廷大臣,洪堡的秘书复述了一遍,宫廷成员。
达盖尔要求警察从他的取景框中走开。
警察皱起眉头,后退了两步说道:首先,如今人人都说自己是宫廷大臣;其次,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那位,他指了指欧根,明显是个大学生,这事可不好办。
他要是不立刻溜走,秘书说,就会遇上连他自己都料想不到的麻烦事。
哪有这样同警察讲话的呢,警察犹疑地应道,他给了他们五分钟时间。
高斯抱怨了两声,挣脱了洪堡。
噢,不!洪堡叫道。
达盖尔气得直跺脚:这么难得的历史瞬间,算是永远失去了。
就跟其他所有的历史瞬间一样,高斯面容平静地应道,全都一样。
的确如此。那天晚上,洪堡拿着放大镜仔细检查了曝光用的铜版。彼时,隔壁房间的高斯鼾声大作,整座宅子里的人都能听见。洪堡没有辨认出什么来。盯着瞧了好半天,版子上才隐隐约约浮现出一团混乱难辨的鬼影:某种像是水下风景的模糊图样。其中有一个手掌、三只鞋子、一截肩膀、一件制服的袖口和某只耳朵的下部。或者,又不是?他叹了口气,把那块铜版扔出窗外,听到院子里传来一声钝响。不过几秒钟之后,他就忘了那玩意儿,就像忘了那些他没能完成的事情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