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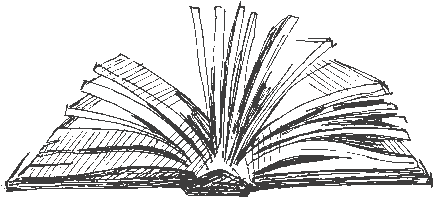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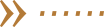
接到李薇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大学门口晃荡着。头顶火热的骄阳,手里拖着一个大大的行李箱,我像个傻瓜似的,仰着头,木讷地盯着眼前的宏伟建筑。
“盛世大学”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被阳光照得格外刺眼,我有种眼睛要被戳瞎的感觉。擦了擦汗,我对着手机吼道:“李薇啊,看着眼前这四个钛合金大字,还有跟古代土财主娶媳妇似的挂满一条街的红灯笼,我怎么感觉天雷滚滚啊!我真恨不得抽自己一个耳光。你说我高考到底是怎么考的?每次模拟考试全校排名不落前十的人怎么堕落到这么一所学校来了?”
“得了吧!就你这德行,去一流大学还不是混二流专业,做三流学生,出来找四流工作啊!”在家吹着空调的李薇咬着薯片回吼道。
我苦着脸望着直通校园的石道上熙攘的人群,感觉鼻子有些酸涩。
“李薇,你说我回去复读高三怎么样?”
“呸!”话还没说完,我就听到电话那头李薇的吐槽声,我的太阳穴涨疼了。
“你脑袋被高温烧残了吧?复读?你干吗不回你妈肚子里回炉重造啊!你改个德行,别一天到晚想象力丰富地写小说,说不定高考时就不会在发呆中过去了。”
我要哭了,对着手机吸了吸鼻涕:“李薇啊,别人可以回炉,我不成啊!你让我去哪儿找我亲爸啊?要找不到,回炉不出我啊!”
“你就贫吧!再怎么乐观也没你那样的。你爸自己在外面有人还有脸说你?他和你妈离了也就算了,干吗还扯出这么多事来!算了,我不跟你废话了,你赶紧报到去,大热天的你一个人拖着那么多东西在太阳底下暴晒,还真不是开玩笑的。也不是我说你妈,再怎么怨你爸,开学也不能让你一个人去啊!对了,你东南西北都搞不清,绝顶路痴一个,你们学校有没有给新生服务的志愿者啊?找不着地方就找小红帽去!”李薇喋喋不休地数落完我爸妈后,又来数落我。
我放眼望了一下四周,戴小红帽的志愿者挺多的,就是不知道该去找哪一个。
远远地看见有几个人站在街道的一处,手里举着一块“外语系”的牌子,我那被太阳灼得视线模糊的眼睛霎时亮了起来。
“李薇,我看到我们外语系的牌子了!我先去了,挂了!”
“外语系!艾叶你真是脑残啊!你一个学理科的、英语烂得一塌糊涂的人怎么好意思读外语系?”
手机里传来李薇无休止的骂声,我手指一抖,挂断了电话,脑袋一扬,眼泪又要下来了。阳光下,我明媚而又忧伤。
谁想填外语系啊?当初高考考砸了,爸爸妈妈又在闹离婚,家里天天闹腾不休,吵得我简直想一头从六楼栽下去,谁还有心思填志愿啊?那天去学校填志愿时,才到半路就有人嚷嚷着告诉我,说我妈在闹上吊。有时候我想,我妈也真够有魄力的,死这回事,我也就想想,她却果断地来真的了,一边往门框上挂绳子,一边冲着奔回去的我惨笑道:“都是你这个野种害的!”
我脑袋一片空白,瞪大眼看着准备把脖子往绳圈儿里套的女人。
一连几天被曾经最亲近的人叫“野种”,可到底是谁“野”了才会有我,他们自己不知道吗?为什么明明自己犯了错,却还要怪罪在我的身上?
李薇说“回炉重造”,有时候我真想回去,但不要再被造出来了。因为太作孽了!填志愿的时候,我心不在焉地随便勾了几个,没想到我勾的第一专业就是那该死的“外语”。命运就是这么作弄人,我从出生的第一秒就是个笑话,一直活在玩弄与被玩弄中,上大学选专业这种被命运玩弄的事,实在是太轻微了。
李薇说的没错,我就是待哪儿都是一样混的人。外语系也罢,只要能躲开家里人,一个人生存就是好的。
大中午的,我热得涨红了脸,满头大汗地拖着行李箱朝外语系的人群跑去。
没走几步,一个女高音破空而来——
“学长,这儿有一个新生不舒服!”
我这人很懒,更懒得管人家的闲事。
事不关己,我拖着箱子就要走,谁知道那个不舒服的新生站哪儿不好,偏偏站在我身旁,是谁不好,偏偏又是我认识的。
“蓓蓓,你怎么了?你忍着点,妈已经叫司机去给你买饮料了。瞧你这小脸,苍白得真让妈心疼。”
几步之外,外语系的志愿者站在那儿,一个浓妆艳抹的阿姨正拍着干呕的女生的背,心疼地说着。
那个戴小红帽的女志愿者继续扯着女高音喊:“学长,这儿有人中暑了!拿一瓶绿茶给我!”
我的神经本能地绷紧,眼睛死死地盯着扶着梧桐树、面色苍白的女生,那娇柔的身子、梨花带雨的小脸委屈的神情,不就是不久前在KTV扇我巴掌、嚣张得跟女王似的莫蓓蓓吗?我艾叶活了十八年,很少会发自内心地厌恶一个人,莫蓓蓓就是那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从高一到高三,我跟那丫头做了三年的同桌。我就搞不懂,我哪里吸引莫大千金了,什么都跟我比,例如:比身高。
高一的时候,我只有一米五,她比我高,于是她嘲笑了我整整一年。这大小姐吃饱了闲得没事干,爱怎么说,我无所谓。可谁知我的青春期来得太晚,本以为不会长个了,哪知道高二的时候一个劲疯长,我一下子蹿到一米六五,赶超了莫大美女。她恨恨地瞪了我大半年,天天当着我的面吃增高药,高跟鞋踩得那叫一个得瑟啊!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莫蓓蓓在花了三万块钱增高了三厘米后,终于跟我一般高了,外加她又爱上了踩“高跷”,这下能高出我一个头,莫大美女不跟我比身高了。
那比什么?
比身材!
她是魔鬼身材,我呢,身材就跟搓衣板一样,整个就一平原。
莫大美女又得意了,天天穿着低领的衣服在我眼前晃。其实我很想告诉她,我不是男的,她没必要花这么多心思,天天变着法儿地“勾引”我。
想让我自惭形秽?我早就残了,连胡乱写的小说里都无一例外地带个大胸大屁股、绝色倾城的女配角,芳名蓓蓓。
可命运就是这么无常,李薇她老妈给她买了好几箱木瓜,天天给她补胸。李薇不爱吃,就全扔给了我。我爱吃木瓜吗?不,我只是不爱浪费食物罢了,更何况还是免费的食物。于是,在我吃掉李薇家几箱木瓜又恰好高二体育课学了瑜伽后,我的平原成了小山丘。
莫蓓蓓又不爽了,校服下的衣服越穿越露,恨不得不穿了,只要老师没在,她就恨不得把校服全脱掉,露出里面可怜的几块布。几乎所有男生的眼光都被她吸引了,可即便是这样,她还是看我不顺眼。
除了比身高、身材外,莫蓓蓓几乎能比的都跟我比了。成绩、家境……甚至男朋友。
高三毕业之前,我依旧是大多数人羡慕的商业大亨的女儿,当时爸爸还没破产,妈妈也还不知道他外面有人,他们还没有吵起来,我还没被叫作“野种”。
那时的我又会学又会玩,家境又好,还有个让人羡慕的男朋友林枫。
一想到那个人的名字,我又开始疼了——脸蛋疼。
因为他,我被莫蓓蓓打了。
高中三年,莫蓓蓓什么也没有比过我,不过她最在意的还是林枫。
莫蓓蓓喜欢林枫,不,不仅是她,当时高中的大部分女生应该都喜欢他。
其实我从未想跟莫蓓蓓比什么,但有林枫这个男朋友,在当时着实让我觉得欣慰。我一直以为,我跟林枫会好好的,一起毕业,上一样的大学,最后结婚。直到后来家里出事,我仍然以为什么都会变,但我跟林枫的感情不会变。
年纪小就会胡思乱想,特别是我这种天生想象力丰富的人,浮想联翩的本事比别人更高一筹。那时候我的想法真单纯,用李薇后来骂我的话来说,就是你小说写多了,分不清现实与梦幻了。最后,我被莫蓓蓓一巴掌打醒了。
她说:“艾叶,我跟林枫好了。”
我当场震惊了,捂着被打肿的脸,推了推李薇,呆呆地问:“什么叫你跟林枫好了?”
李薇说:“叶子,你别傻了,林枫半年前就跟莫蓓蓓有一腿了,就你傻,被蒙在鼓里。我上次就告诉过你我看到林枫和莫蓓蓓接吻,你偏不信。”
“那不是同学间纯洁的友谊吗?你也知道林枫家跟莫蓓蓓家是世交啊!”我瞪大眼睛,有些愤怒地朝李薇喊道。
“世交需要那么热烈地接吻吗?你这傻瓜!”
李薇扇了我另一巴掌,将傻乎乎地要向莫蓓蓓问个清楚的我拖出了KTV。
天真够热的,汗水流进眼睛里了,我胡乱擦了一下眼睛,捂着发疼的小腹,低着头想走。回忆太长,想得发慌,现在一想到林枫跟莫蓓蓓,我的眼前就浮现出他们亲昵的情景,胃里一阵阵抽疼、恶心。
想象力太丰富就是不好!
那个女高音还在“学长学长”地喊,不一会儿,传来一个清冷的声音,夹杂着些许不耐烦。
“拿着!”
有人把冰冻的绿茶扔了过来,我敢说那人绝对是青光眼加白内障,往哪儿扔不好,偏偏对着我这么个大活人扔。毫无意外地,我被扔给莫蓓蓓的绿茶砸了,砸中的部位偏偏又是我这会儿不断抽疼的小腹。
自从莫蓓蓓告诉我她和林枫好了之后,我每次听到那两人的名字或者看到他们,小腹就会神经性抽疼。
这是干吗?鬼上身了?
我捂着小腹,咬着嘴唇,额头冒冷汗,眼睁睁地看着那瓶绿茶掉在地上,里面的饮料流了一地。然后我感觉下腹一热,有什么东西流了下来。
“大姨妈”被砸出来了!
“学长!”那女高音又是一声叫喊,带着震惊、恐慌与急促。
“我说我又不是你们外语系的,你老叫我干吗?”男生不耐烦地回问道。
脚步声朝我们这边走过来了。
“不是把饮料给你了吗?还有什么事?”一个男生越过我,径直走到“女高音”的面前,冷冷地说道。
那男生身材修长,黑色短发,肤色白皙,侧脸很漂亮,轮廓精致,鼻子英挺,下颚性感。初步鉴定,帅哥一个。
我的目光毫无顾忌地从那人脸上落到身上,当看到他穿的那件蓝白色格子衬衫时,我的小腹疼得更厉害了。
眼前晃过一道身影,蓝白色的格子衬衫,阳光下的温柔浅笑……然后温柔亲吻莫蓓蓓的林枫。
又来了!想象力太好就是折腾人的神经。
这男生穿什么不好,非穿一件跟林枫一样的衣服。
人们说,穿着体现一个人的品位,看来这男生一定也跟林枫一个德行。
“学长,你饮料扔错方向了,你……把人家砸出血了!”女高音讪讪地指着我,咧着嘴朝侧对着我的清俊男生说道。
男生转过身来看着我,眸子深邃,冷意慑人,他将我从上望到下,一脸的淡定从容,目光最后落在我黏血的腿上,唇角一勾,嘲讽地笑:“喂!你‘大姨妈’来了!”
此话一出,女高音当场怔住。
那男生嗓音不高,却足以让方圆十米之内的人都听清。整个林荫道宽不到十米,附近所有人都望向了我。
我“哦”了一声,当场放倒手中的拉杆箱,蹲下身子,麻利地打开,在众目睽睽之下,将上面的内衣、内裤、睡衣拨到一边,从箱底拿了一条浴巾出来,在自己腰上裹了一圈。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淡定得让所有人震惊。
我一向没皮没脸,只做最直接的事。
我曾在整个小区住户的围观下,被无数曾经的亲人喷着口水叫“野种”,最终丢下长长一句“谢谢你们当了这么久的野种她爸、她妈、她叔、她伯、她爷……”后扬长而去。
相比之下,现在这事实在是微不足道。
周围一片欷歔,我瞥了一眼身旁目光冷淡的男生,从容地朝女高音走了过去。
“我是你们系的新生,来报到,不认识路,有人带路吗?”我满脸真挚地问道。
女高音的脸很僵硬,抽搐了几下后,朝我僵笑道:“有。不过你先等等,另外几个志愿者都带人走了还没回来,我这又有个新生身体不舒服,你等他们来了再走吧!”
女高音说着,指了指身旁脸色惨白的莫蓓蓓。
莫蓓蓓看着我,脸色更加难看了,她用大眼睛瞪着我,眼里全是震惊。
说实话,之前我看到她的那一秒,比现在的她还震惊——我们是不是太有缘分了,同桌三年,现在又念一个学校一个系。
我们前世到底回眸了多少次,恐怕是脖子都扭断了才这么有缘吧?
从震惊到惊悚再到激动,结果“大姨妈”都提前了。
“艾……艾叶!”莫蓓蓓难以置信地叫我。
我看着她,笑得比见了亲人还灿烂:“哟!同学,我们认识?”
莫蓓蓓的脸当场僵住了,惊恐地望着我:“你……不记得我?怎么可能!”
“哦!我想起来了,你不是莫蓓蓓吗?唉,你也知道,我脑袋被人打过,现在不太好使!”我话中有话地拉着莫蓓蓓的手惊叫道。
莫蓓蓓看着我,神色慌乱,一把甩开我的手,躲进了她妈的怀里,不再看我。
这是什么状况?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现在假装懊悔吗?
不,不需要。
这不是她的错,一切都是命运。
我艾叶天生就是悲剧命。除了我的出生,我不能控制外,认错爸,爱错人,交错朋友,都是我自找的,怨不得他人。
命运啊,真是个奇怪的东西!
下腹越来越疼,我捂着肚子站在树荫下不再说话。
身旁的女高音忙着给莫蓓蓓扇风。莫蓓蓓她妈神色哀戚,从跑过来的司机手里接过柠檬水喂莫蓓蓓。
我站在一旁看着这几个手忙脚乱的人,额头上的热汗又流进了眼里,胃里一阵泛酸,有些想吐。我干呕了几下没吐成。
“走吧!我带路!”
突然一只冰凉的手落在了我肩上,清冷的嗓音随之传来。我抬起头就看到了皱着眉的那个“学长”。
“你不是说不是我们系的吗,带我干吗?”我别扭地甩开他的手,没好气地开口。
我真心觉得他那件蓝白格子的衬衫刺眼。
“你不是快要倒了吗?脸色惨白,嘴唇发紫,身体颤抖,浴袍裹身,小腿上还黏着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影响学校新生形象。”
那人边说边拿起我的拉杆箱,回头冷眼看着我。
“什么叫还以为,我本来就出事了!被不长眼的整瓶饮料砸到,这还算没事吗?”我狠狠地回瞪他一眼,提了提快要掉下去的浴巾,骂骂咧咧地跟了上去。
跟那家伙走,总比待在太阳底下干等好。站久了,我腿都酸了,外加“大姨妈”来了,连脑袋都晕。最关键的是就算垫了护垫,也阻挡不住奔涌不止的“大姨妈”啊!
“同学,你怎么称呼?”走过林荫道,拐上了山路,一路上两个人都沉默着,我终于有些忍不住了。
“你不累吗?还有力气说话!”那人回头瞄了我一眼,满头大汗地说道。
我看了一眼他手中我的行李箱,一连跳了好几级台阶追上了他。
“你似乎也不累啊!还有力气说废话!”我冷嘲道,目光一直紧紧地盯着那男生的脸。刚才只看到侧脸,很惊艳,这会儿看到正脸了,我只能说,还是侧脸比较好看。
他长得不丑,算好看的那种,比起那精致的侧脸,他正脸的整体轮廓不算突出,但很干净、清俊,比较顺眼。只是眉宇间透着一股深沉,眼眸深邃,神情高傲、冷漠。
他不如林枫帅气,看上去也没林枫温柔,但他们都一样,是“蓝白格子控”。
以前我特别喜欢穿格子衬衫、皮肤白皙的男生,因为看上去很干净。后来我发现,一个人干不干净,不能光看外表,当年林枫把格子衬衫穿得出神入化、帅至骨髓,还不是照样背叛我。
我的目光一直追随着那件淡蓝色的格子衬衫,小腹抽疼得更厉害了。
“冷子沫!”清冷的声音突然再度响起。
“呃?”我茫然地回应道。
男生白眼一翻,一副想撞死的样子,嘴角抽搐地看了我一眼,别过头去。
“冷子沫,我的名字,记得以后叫学长!”那人头也不回地拎着箱子继续爬石阶,我恍然大悟,才意识到他是在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冷子沫!
我咕哝了一声他的名字,又望了望那清冷的背影,耸了耸肩。
这名字倒还蛮配他的。
“我叫艾叶!”
“我知道,刚那中暑的女生叫了!”冷子沫冷冷地说,突然停了下来。
我疑惑地抬头一看,才发现我们已经到了一幢建筑楼前。
“这是你们外语系的新生宿舍楼,光急着带你来宿舍,忘了带你去报到处看分班情况。算了,外语系今年就招两个班,你名字怎么写的,我去宿管那儿问问看你住哪间宿舍,然后去领钥匙跟床上用品。”
“你急什么啊,哪有新生报到连自己分到哪个班都不知道的?你快先带我去报到处,我查查我是哪个班的。”
我不爽地拉住冷子沫的衣服就要走,冷子沫皱着眉头甩开了。
“查什么,你把名字写给我,就两个班,在宿管那儿一查就知道了。再说,你现在这个样子,还想跑哪儿丢脸去,拿到钥匙后快点去宿舍洗个澡!”
冷子沫对我一顿乱吼,我下意识地垂头看看自己满是血污的斑驳的腿,自己都觉得恶心起来。
宿管处人很多,围着宿管阿姨忙着领钥匙跟宿舍用品的全是家长们。
我愣愣地看着那群争着拿东西的阿姨,心里有些发苦,抽了一下酸疼的鼻子,将咸咸的汗水吃进了嘴里。
要是我妈在,她肯定不会跟那群阿姨一起抢,她是多优雅的女人啊!挤进人群里的肯定是我。
当然她不可能来,我这会儿也没力气去抢。
痛经,难受。
一旁站着众多看着自己家长抢东西的新生,陆陆续续地有人把目光朝我投过来。
不用想,我现在这样子的确怪异,丢脸得很。
没事,爱看就让她们看去吧!人活着不就是给人家看的吗?
“哭什么?”
脸上突然一凉,冷子沫的脸突然在我眼前放大,冰凉的手指笨拙而不耐烦地擦着我的脸,随后快速地脱下他那件刺眼的蓝白格子衬衫,阴沉着脸套在了我身上。
冷子沫很高,比我高一个脑袋,我琢磨着他应该有一米八。那衬衫穿在我身上,遮住我的腿,正好把我的热裤跟浴巾全挡住,连带着盖住了我那污血淋淋的腿。
虽然讨厌蓝白格子衬衫,但这会儿这衣服还挺遮羞的。
“谁哭了?汗水流进眼睛了,不懂别瞎说!”我擦了一把脸,望着只穿一件深蓝耐克背心的冷子沫,狡辩道。
冷子沫不置可否,将箱子往我身旁一放,居高临下地说:“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拿东西。”
“喂!我名字……”
我想起还没告诉那家伙我的名字怎么写,冷子沫已经挤进了家长中间,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
周围吵闹声不断,学生家长都在不停地嚷嚷,我的话早就被淹没了。
算了,也不一定要找名字,读音相同就是我了。“艾”这姓,姓的人本来就不多,跟我名字一样的人,两个班应该没有吧!
“英语一班,六〇一宿舍二室,走吧!”
没等多久,冷子沫从人群里钻了出来,手里拿着把钥匙,拎着个大塑料包。
“你就送到这里吧!剩下的我自己来好了。”
我伸手作势要拿冷子沫手中的塑料包,他却一闪身躲过了。
“还有个行李箱,你一个人怎么拿?你先拿钥匙上去,在宿舍坐会儿,我一会儿就把东西拿上来,然后你就去洗个澡。”
冷子沫鄙夷地朝我说道,然后将钥匙扔给我,把塑料包往肩上一甩,转身去拎一旁的行李箱。
我手里握着钥匙,望着表情难看、动作吃力的冷子沫,心里很不是滋味。
其实我跟他不熟,他没必要为我做这些,看他的样子,也不像是个热情的人。
“你还杵着干吗?走吧!”冷子沫再次皱起眉头,用脚踢了我一下,冷冷地说。
我捂着被踢疼的脚,嘴里那句“回头请你吃饭”顿时被咽回了肚子里。
先是用饮料砸我,这会儿又用脚踢我,跟他对我的帮助算扯平了。
冷子沫拿着一大堆东西走得比较慢,我想帮他拿那个塑料包,却被他一口拒绝了。
最终在他的催促下,我拿着钥匙一个人先跑上了楼。
虽然“大姨妈”刚来,量不算很多,但天气太热,身体的粘腻感着实让我感到难受。再加上痛经,我这会儿也没多少力气,要不是有冷子沫帮忙,估计我早就坐在地上歇菜了。
宿舍的门已经打开了,我直接跑进二室,按照钥匙上连着的床卡找到了自己的床位,将肩上的背包往床上一放,急忙掏了片卫生棉,拿了包纸巾,将腰部的浴巾一扯,不顾房间里其他人惊愕的目光,就朝厕所跑去。
垫完卫生棉出来,冷子沫已经到了,正站在我床边放东西。一见我出来,那个依旧摆着张千年不变的冰山脸的家伙,没经我同意,竟然从我的箱子里拿出了一套衣服,塞进我怀里,然后又从塑料包里拿出各种型号的盆递给我。
“先去洗个澡!”
我拿着东西,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
冷子沫拽着我的手臂,将我拉到宿舍浴室的门前,二话不说将我推了进去。
莲蓬头的水温正好,不冷不烫,浇在身上温温的。浇了许久的热水,隐隐作痛的小腹终于舒服了很多。望着被踩在脚下湿透的蓝白格子衬衫,我的脑袋有些混乱。
现在是什么状况?那个叫冷子沫的是不是做得有些多了?
这衬衫怎么办?全湿了怎么还他?
他走了没有?
我有些失神地站在莲蓬头下浇着水,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脚下的衬衫,正琢磨着怎么处置这碍眼的衣服时,突然听到有人在敲浴室的门。
“同学,你男朋友让我把浴巾递给你!”
温润的女声传来,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似的,全身一颤。
我男朋友?
谁啊?
我拧开了浴室门,露出一条缝,从一只白嫩的小手里接过了那条深蓝色的浴巾。
不是我之前围的那条,而是我放在箱子里的另一条。不用想,肯定是冷子沫擅做主张又翻了我的东西。
我那突然冒出的“男朋友”估计就是还没走的冷子沫了。
也对,那家伙那么堂而皇之地给我拿衣服又推我去洗澡,任谁看了都会误会。
我一开始就觉得哪里不对劲,压根儿没想到我在这事上吃亏了,我一黄花大闺女,莫名其妙地就成了人家的女朋友。
我在浴室里穿衣服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吃了亏,等我进宿舍看到忙着给我整理床铺、背上湿透的冷子沫时,就觉得人家似乎比我还吃亏。
六〇一是个大宿舍,有三个小室,每个室里住四个人。
宿舍里除了我已经来了两个人。洗澡前,我顺势瞟了一眼,那两人都跟爸妈忙着整理东西。帮我送浴巾的是其中的一个,矮矮胖胖,脸很白。等我出来,那两张床铺都已经整理好。那小胖女孩跟她的爸妈站在一起,正准备出门,另一个女生估计早就出去了,这会儿根本看不到人影。
那一家三口一走,宿舍只剩下我跟冷子沫两个人。
我出来站了有一会儿了,冷子沫像没看到我似的,依旧冷着脸一丝不苟地给我铺床弄被子。
我站在一旁,总觉得哪里不对劲,等我意识到哪里出了问题时,冷子沫已经帮我把床铺好了。
“那个……你干吗帮我做这些?”
对,这就是问题。
我跟他不熟,他干吗跟老妈子似的,又帮我挂蚊帐又给我铺床的。
冷子沫依旧是那副冷傲的样子,瞥了我一眼,然后朝我伸出手。
“我的衣服呢?”
“弄湿了,我泡在水里准备洗呢!你要吗?那我去拿。”
我转头就要往洗漱间跑,却被冷子沫叫住了。
“湿了就算了,别给我了,反正那衣服不值钱,而且又不是我的。”冷子沫大度地说道,从我的纸巾盒里抽了几张纸巾,擦擦手就要出门。
“不是你的?”我震住了。
原来那家伙跟林枫品位不同啊!很好很好,世界上又少了个“渣男”。我正为社会多出一抹光亮而激动万分,一抬头又对上了冷子沫的冷眼。
“大惊小怪什么?前阵子我住在朋友家里,衣服带少了才穿了朋友的,很正常的事!”
“那别人的衣服就可以不要了吗?真是没礼貌的家伙!”我在心里暗暗嘀咕。
不对,等等……朋友?我又一次感到不对劲,想想那件跟林枫的一模一样的衬衫,我的心里猛然起疑。
“别告诉我你那个朋友叫林枫!”我惊叫道,手指颤抖。
这事情也太烂俗了,李薇当初告诉我林枫也在这所学校,我还不信,这下看来八九不离十了。
冷子沫紧紧地盯着我,表情严肃。
看,我猜对了吧!
我就是一个倒霉蛋,专遇到这些倒霉的事!
“我朋友是谁关你什么事?还有,林枫是谁?我们学校的吗?你朋友?你有朋友在这所学校,干吗不让人家接你?你一个女生独自来学校还搞成这副德行,我真不知道该说你什么!”冷子沫冷哼一声,甩手道。
我愣愣地看着他,他朋友不是林枫啊!害我白激动一场。
“那不谈你朋友了,你还没说你干吗帮我铺床。难不成你对我一见钟情,或者想泡我?现在不是流行学长泡学妹吗?难道你也想追赶潮流?”言归正传,我还没弄清楚冷子沫干吗帮我做那么多事呢!
我的话一出口,冷子沫脸上的鄙夷更深了,他一脸无奈地望着我,怅然道:“厚脸皮的女生我见多了,没见过你这样没皮没脸的。你以为我闲得没事干,帮你做这些?还不是看你可怜,一个人,身体又不舒服才帮忙的。怎么说我也砸到你了,算补偿吧。要知道你会这么想,我压根儿就不会帮你。”
他毫不留情地摧毁了我的幻想。
我理解地点点头,继续追问:“那你是不是随便砸到谁都帮她带路拎东西还铺床?”
冷子沫翻了个白眼,冷哼道:“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一砸就砸出‘大姨妈’来。”
我满头黑线——这人嘴真毒。
“我没工夫跟你瞎扯,走了。”
见我发愣,冷子沫高傲地丢下这么一句,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也懒得追。
小腹又开始隐隐发疼,我随手抓了个枕头就躺到了床上。
天气很热,宿舍也热得够呛,我赤着胳膊躺在床上,肚子上盖着条夏被,身体还是感到有些冷。
看来,有些冷意是发自身体里的,无关天气。比如冷子沫那双冰冷的手,也比如我此刻疼痛的腹部。
有人打来电话的时候,我还在睡觉。要不是被人推醒,我根本就感觉不到自己的手机铃声在响。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宿舍里开着灯,多了三个女生,忙着各自的事。
不用说,她们应该就是我的新室友。
推我的那个女生就是给我送浴巾的人,宿舍里另一个女生叫她“安佳”,说的是她们的方言,两人应该是老乡,所以刚认识就特别熟稔。
安佳叫另一个女生“陈怡珊”,我拿着手机去阳台的时候,瞥了那女生一眼,秀发乌黑,气质优雅,明眸皓齿,一个典型的古典美女。
另一个坐在上铺玩电脑的女生,我还没来得及知道她叫什么,一个低柔的女声就从手机里传了过来。
“到了没?”我那悲剧的老妈打了个酒嗝问我,旁边还萦绕着酒吧的喧嚣。
毫无意外,她又去喝酒了。
离婚后,她就从来没离开过酒。
她有时间去酒吧唱歌、跳舞,就是没时间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没时间在大学开学时送我过来。
怨吗?
我站在阳台上问自己,抬头望着群星璀璨的夜空。
有什么好怨的,最起码她还记得有我这么个女儿。
“中午就到了。”我淡然回答,天知道我为什么要把“中午”这个词咬得那么重,明知道她根本不会在乎。
“学费、生活费,我一次性全汇到你卡上了。假期没事的话就别回来了。”
听听,这就是我妈,一句话就能把人堵死。
“嗯,不回来。我懒,不爱动,回来太麻烦了。寒暑假我会去打工,钱我会自己赚的。”
昼夜温差真大,阳台上的风真冷,我吸了口冷气说着我妈爱听的话。
“能自己赚钱最好!你也知道你那不要脸的爸爸留给我们的钱不多。”
妈妈又打了个酒嗝,电话里传来她清脆的响指声。
“再来杯威士忌。”
我握着手机发笑,的确,钱不够多,连她的酒钱都不够,哪够养我。
也对,我过了十八岁,成年了,即便那个人是我爸,离婚后也没义务养我,更何况他根本不是我爸。
“你别喝太多,早点回去。我挂了,长途话费贵。”
“嗯。”妈妈咕哝了一声。
我挂断了电话。
宿舍其他三个人都不是我老乡,出来时我看过那个玩电脑的女生的床卡,她是广东的,安佳她们说的是北京话。我们的方言都不同,所以根本不怕她们听到什么。
就算她们真听懂了,又能怎样?
艾叶是野种,她爸妈离婚了,这事我们那儿整个市的人都知道,我也不在乎多几个人知道。
阳台风景不错,冷风吹得也够凄凉,感怀伤情最适合了,但我这会儿痛经,难受,没那闲工夫忧伤,再忧伤我还是野种,爸妈还是离婚,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眼泪浪费了还得买水补呢!钱不够,得省着点花。
我缩了缩脖子,握着手机从阳台回到了宿舍,一骨碌又爬上了床。
那边,三个女孩子已经聊开了,小胖妹安佳一个劲地拉着玩电脑的女生“菜苗菜苗”地叫着,旁边的陈怡珊笑得花枝乱颤。
“嘿!我是蔡淼,你叫艾叶吧?”
听到有人叫我,我从被子里露出脑袋,眼睛眯成一条缝,打量着突然在我眼前放大的瓜子脸。
对方眨巴着眼睛,让我感觉有些惊悚。
“嗯,艾叶!叫我叶子就行了!”
宿舍有床卡挂在各自床头,上面写着名字。我一点儿都不好奇蔡淼怎么知道我的名字,让我惊奇的是,我前一秒还看她坐在床上捧着电脑,下一秒她就站我床前了。
“你们一个菜苗,一个叶子,真有意思。我是安佳,她是陈怡珊。”安佳拉着陈怡珊也凑了过来,晃着圆脑袋说。
我朝她们点头微笑,然后闭眼又想睡。
“艾叶,你怎么了,不舒服吗?”靠我最近的蔡淼第一个发现我不对劲,紧张地睁大眼睛问道。
我朝她们摆手苦笑:“‘大姨妈’拜访,痛经,睡会儿就好了!”
“我有红糖。”
“我有速溶姜粉。”
“可是,不知道去哪里打热水啊!”
蔡淼发话,安佳紧跟,陈怡珊哀叹,耳边很是热闹。
我突然有些想李薇了,因为她也很聒噪。
有时候耳边热闹一些也是种幸福。长时间安安静静的,听不到外面的声音,就会感觉自己跟死了似的。
“艾叶!叶子!”
“她好像睡着了,还是别吵她了。”
床边的人渐渐散开,陆续传来细碎的声音,小声地闲聊、键盘的敲击声、嗑瓜子声、喝饮料声……
有些吵,我有些生气,但毕竟让我感觉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新世界里,我是活着的。
“我真是作孽,戴了这么多年绿帽子。要不是看到高考的体检单,我这会儿都不知道自己养了个野种。”
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妈妈淡妆素雅的俏脸上,爸爸一脸怒容,朝摔倒在地的妈妈唾骂。
妈妈擦了擦嘴角渗出的血丝,目光怨毒地望着爸爸的身后,艰难地爬起来,笑得歇斯底里。
“当初不是你抢着要娶我的吗?明明知道我新婚就守寡,但你看我家有钱,说什么都不在乎,要娶我。现在呢?你有钱了,瞒着我在外面有了人,这会儿却跑来说我的不是。我刚结婚,没几天又被绑着嫁给你。才隔了几天,你让我怎么知道怀的孩子是谁的!倒是你,你怎么养了这么大一个野种,竟然还敢把那女人带回家。艾胜啊,你还有没有良心!要不是我,你这会儿还在厂里做车床工。你能有今天?”
“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要不是你哥挪用公司那么大一笔资金,又把方案卖给别人,公司会破产?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既然现在话说开了,那就这样,你带你的野种走,我跟阿莫带我儿子离开,咱们离婚!”爸爸愤恨地将身边餐桌上的东西砸了,抓着身后瑟瑟发抖的年轻女人跟孩子,冷酷无情地朝面前还在微笑的妈妈说道。
“都说男人没良心,我总算是见识到了!艾胜,你就是只白眼狼啊!有钱的时候,你把钱都给了这个女人;现在没钱了,你竟然要跟我离婚跟她逍遥。你真当我傻啊?你欠那么多债,离婚我得跟你平摊,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得逞的。”妈妈吼着,伸手抓起茶几上的茶壶朝爸爸砸去。
爸爸没躲,茶壶正好砸中脑门,霎时多了块青紫的瘀伤,身旁的叫阿莫的女人急忙去帮他揉额头,表情别提多紧张了。
“是,当初是我贪钱娶了你,但这十八年来,我对你也算尽心尽力。要不是遇到阿莫,我也以为一辈子就跟你这么过了。阿莫怀了我的儿子,怕我让她打掉,偷偷走了,要不是我找到她,我艾胜这辈子就真的断子绝孙了。我对你感到愧疚,所以一直瞒着你阿莫的事,一直把阿莫置于见不得光的位置。要不是公司倒闭,要不是叶子的血型跟我不符,我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你放心,阿莫没钱,我们都没钱,钱都用来还公司欠的债了。除了你哥拿走的钱,其他的我都还清了。剩下的债他们会找你哥算,就算我们离婚,你也不用跟我一起平摊债务,更不用担心我跟阿莫两个人逍遥。我把你女儿养这么大,我儿子现在才三岁,剩下的人生,我要为我儿子奋斗。”
爸爸说完,从怀里拿出一份离婚协议书朝妈妈甩去,然后一把抱起脚边的懵懂幼儿,带着从头到尾未发一言的阿莫,毫不留情地走出门去。
妈妈没有哭,一直笑着,望着站在一旁沉默的我,咧开嘴来。
“艾叶啊,你爸说你是野种呢!以后你没爸了!知道吗?”
她说完面无表情地转过身朝洗手间走去。
“砰!”
门被关上了,洗手间里随后传来了凄厉的哭声。
“艾胜,你没良心啊!艾胜!”
我安静地扫着地上的玻璃碎屑,听着门外看热闹邻居的闲言碎语,表情漠然。
是我太淡然了吗?
不,只是习惯了。
这样的争吵已经持续好久了,自从家里公司破产,妈妈知道爸爸在外面有外遇后,我家就经常上演激烈的骂战。但这次与以往不同,以往的主控方都是我妈,艾胜除了抽烟、沉默,骂不还口打不还手。这是唯一的一次,他主动发飙,也是我第一次从这种争吵中听到一些不同的话,比如,我是野种。
打扫完大厅,我安静地关上门,将那群探头探脑的三姑六婆关在门外,然后去捡地上的体检报告单。
本来高考体检单学校是不会发下来的,而命运就是那么巧,学校组织体检的那天,我恰好发烧,没去成,于是之后跟我爸去医院补办。
我想,我去捡体检单的那一刻,心里还是觉得艾胜是我爸的。
可是,当看到单子上血型那一栏写着“B型”时,我的脑袋像是被重击了一下。我蹲在地上,感觉一阵眩晕。
我妈是A型血,艾胜是O型血,而我是B型。
毫无意外,我是个野种。
十八年来,我一直以为自己是艾胜的女儿,艾胜也这么认为,我妈也这么认为。
我知道妈嫁给艾胜之前,跟别人有过婚约。不过那人刚跟她结完婚,就出车祸死了。有人说我妈是克夫命,外公、外婆怕她嫁不出去,正巧艾胜来提亲,连那个人的丧礼都没结束,妈妈就被强迫嫁给了艾胜。
豪门之女,看似风光,可惜有个刚硬的老爸,她着实没有多少主导权。
即使起初并不相爱,但两个人相处时间久了,女人的心很快就被拴住了,一心一意地跟着她男人了。
生孩子比预产期提前几天是正常的事,谁会想到就那几天,孩子的爸就不一样了。
我是个野种,是一个连亲生爸爸是谁都不知道的野种。
这么多年,我一直过得很开心,我觉得我的生活是那么的平顺,却未曾料到,命运给你最重的打击的时候,往往是在你自以为最幸福的时候。
我紧握着体检单,眼泪一滴滴地掉在上面。
从小到大,我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孩子,记忆中好像没哭过,这天我却哭得特惨特难看,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哭。
眼角一片湿润,我把头埋在被子里,闭着眼,人睡着,可回忆还在梦里汹涌着。
是不是人大了,都会变得矫情,我想醒过来,可是妈妈那一声声凄惨的哭喊紧紧地拉扯着我。长辈们那些鄙夷的唾骂声,那一句句难听的“野种”,排山倒海般朝我扑过来。最终,我无力地瘫坐在地上,手下一摊血,是妈妈的。
她躺在浴缸里看着我,白嫩的手腕上有一道狰狞的血痕。我妈是多好看的女人啊!年近四十还漂亮得跟三十刚出头的少妇似的,气质那么高雅,那天却像朵枯败的百合,朝我艰难地咧着嘴。
“都是你这个野种害的啊!不是你,他不会走得那么干脆。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是他的孩子呢?”
是啊!要是我不是野种,她还可以继续支撑这段已经变质的婚姻,还可以自欺欺人地继续跟艾胜过下去。
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不是他的孩子,我也希望艾胜是我爸,我也希望自己爱了十八年的父亲不会改变那慈祥的脸;我也希望一直爱我如珠如宝的爸爸不会用手指着我的鼻子红着眼叫嚣着“野种”!
可是这一切我能控制吗?让谁当我的亲生父亲,我能选择吗?让我怎么办?你们让我怎么办?
如果可以,我宁愿别出生,这样也不会在茫茫然地受到那么多人的指责。
所有人都在指责我,只是因为我这个野种存活了下来。
要是当初我死了多好!
“艾叶!醒醒!快醒醒啊!艾叶!今天早上要去操场集合,我们要军训!艾叶!艾叶!”
急切的呼喊声传来,我被人推醒。
我睁开惺忪模糊的睡眼,蔡淼的脸渐渐清晰起来。
“哦!天亮了!”
我咕哝一声爬起来,揉了揉酸涩的眼睛,又变回了那个没心没肺的艾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