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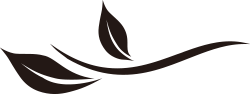
李轶南
摘要:汉代既对先秦百家思想和地域文化予以继承和兼综,又是肇启魏晋乃至其后百代思想新声的源头,其造物艺术思想主要反映在四个方面:其一为“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其二为从简朴“意真”到“纤微要妙”;其三为务以传神为胜的形神观;其四为谶纬观念的兴起与祥瑞艺术形象的滥觞。
关键词:汉代;造物艺术思想;卮议
两汉思想过去曾被误认为充斥着迷信、荒诞与浅陋 [1] ,其实细考史料,会发现它洋溢着青春活力,可谓精彩迭起、波澜壮阔。苏轼曾在《书吴道子画后》云:“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艺,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事实上,不断涌现的现代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典籍已充分证明,百工之艺,文章各体,在汉代已完成其大略。鲁迅先生曾形容汉代艺术为“深沉雄大”,徐复观先生曾说:“两汉思想,对先秦思想而言,实系学术上的巨大演变。不仅千余年来,政治社会的格局,皆由两汉所奠定。所以严格地说,不了解两汉,便不能彻底了解近代。” [2] 汉代真正结束了各国纷争、礼乐废弛、“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它既对先秦百家思想和地域文化予以继承和兼综,又是肇启魏晋乃至其后百代思想新声的源头。正是基于汉人的努力,中国作为统一国家的疆域得以稳固下来,中国传统造物艺术思想的基本特征和文化品格得以奠定。汉人的建树,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事功层面,都为后世打下了深厚的根底,具有包罗万象的集大成或百科全书式的特点,借用马克思评论培根的话来说,即是“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 [3] 。汉人兴废继绝,为其后历朝历代的开枝散叶、蓬勃发展立下万世之基。作为人类心灵真实、直观反映的汉代造物艺术及其所体现的思想,因承载时代风尚和民族文化心理而彰显其独特的历史意义和审美价值,成为把握其后我国两千年来造物历史问题的重要枢轴。
汉代造物艺术思想的汪洋繁富,得益于汉疆域内各郡国间的交流会通。汉统一帝国的形成,打破了此前各地域间鲜有交流的状态。一方面汉人对秦代焚毁的古文献典籍进行收拾补缀、整理研究,继承先秦各国地域文化,“省万邦之风”,促进了兼容并包、开放自信的文化大一统和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例如融合了荆楚、邹鲁、燕齐、吴越、巴蜀、秦晋、韩魏
 和因丝绸之路开通而传入的西域文化等,奠定了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的基本特征,促使艺术创作手法呈现多元化倾向;一方面兼综了先秦诸家学派的思想文化,例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明确提出,兼取道、儒、墨、法、名、阴阳众家思想
[4]
,并对各家思想的优劣一一进行评析;淮南王刘安召集天下“俊伟之士”著述的《淮南子》更是文宗秦汉、统合百家的集大成之作,博采黄老之学和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仁政学说、法家的历史观、阴阳家的变化理论和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等,体现了汉初学术上兼收并蓄,力求对各家各派思想吸收融会、肇启新声的发展趋势和大文化气象,即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融古今、南北于一炉而自创奇伟,有熔铸群言之妙。而观其主流是儒、道思想的融合与会通,表现为盛行于北方的儒家思想与肇源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的此消彼长,使得以“教化”为核心的儒家审美和崇尚“自然”为风旨的道家审美成为通贯两汉造物艺术思想领域的双重乐章。
和因丝绸之路开通而传入的西域文化等,奠定了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的基本特征,促使艺术创作手法呈现多元化倾向;一方面兼综了先秦诸家学派的思想文化,例如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明确提出,兼取道、儒、墨、法、名、阴阳众家思想
[4]
,并对各家思想的优劣一一进行评析;淮南王刘安召集天下“俊伟之士”著述的《淮南子》更是文宗秦汉、统合百家的集大成之作,博采黄老之学和道家的自然观、儒家的仁政学说、法家的历史观、阴阳家的变化理论和兵家的战略战术思想等,体现了汉初学术上兼收并蓄,力求对各家各派思想吸收融会、肇启新声的发展趋势和大文化气象,即在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进行综合,融古今、南北于一炉而自创奇伟,有熔铸群言之妙。而观其主流是儒、道思想的融合与会通,表现为盛行于北方的儒家思想与肇源于南方的道家思想的此消彼长,使得以“教化”为核心的儒家审美和崇尚“自然”为风旨的道家审美成为通贯两汉造物艺术思想领域的双重乐章。
儒家审美思潮是汉代强盛期推动造物艺术发展的主要精神,它以伦理的、道德的、教化的力量扣人心弦,其“儒学思想—造物”的艺术模式,是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造物艺术领域有意识遵循儒家伦理教化思想的反映,其主要表现围绕三点:以体现“仁义”观念来塑造人的性情;以体现儒家礼教色彩来选择造物艺术题材及其组合;以致用精神体现汉代天—地—人宇宙系统的思维模式和等级秩序。道家崇尚“简朴意真”的审美思潮在汉初、两汉之际和汉末的风行一时,显现其所处时代的混乱和衰颓特征,它与儒家经世致用、礼乐教化的思潮相互交织、互为矛盾、相互影响、消长绌补,反映汉人为消解乱世秩序崩弛情形下的坎坷命运,或缘情尚性,或淡泊自守,或超脱放达,追求心灵的自由。
汉代造物艺术思想的形成受到汉代“雅”“俗”层面分别代表大、小两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大传统”主要指当时知识阶层的经典思想,表现为儒道绌补,同时兼容先秦墨、名、法、阴阳等思想,完成汉代开放包容的大文化思想新建构;“小传统”指的是汉代一般思想观念和民间通俗信仰,例如阴阳五行、谶纬之说、吉祥观念、神仙方术等。“大传统”与“小传统”在互动过程中形成了文化的交融,即兼综了宫廷与民间、中央与郡国的多层次、多元性文化,形成“多元”与“一统”的辩证统一:“多元”体现为造物艺术既洋溢着想象力丰盈的奇思,又彰显了穆如清风的典雅;既有抒情言志的诗心,又有俯仰天地的胸襟;既有天人之际的哲思,又有游目骋怀的神幻,而这些“多元”的创作思想和审美观念,又集中辉映了汉代大“一统”文化的时代精神。
刘勰在《文心雕龙·文体论·诠赋第八》中总结汉赋时,指出夸张形容、比兴取义为其根本,即“情以物兴,故义必明雅;物以情观,故词必巧丽。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 [5] 。汉赋浓缩了汉代文化形态特征,以“宏衍博丽”为形式,“义尚光大”为内容,汉赋作家崇尚“博丽”“华丽”“巧丽”“朗丽”“弘丽”“巨丽”“侈丽”“绝丽”“神丽”之“丽”,无论是继承屈原抒情言志的贾谊之赋,还是继承宋玉描绘事物、衍展成篇的司马相如、扬雄之赋,都具有文采崇丽、引事繁富、描绘生动的特点。虽然汉代人对于司马相如的赋评价不高,贬低其赋为“辞人之赋丽以淫”,而赞美屈原之赋为“诗人之赋丽以则”,扬雄更进一步提出“风归丽则”的要求,即赋应“有质”“有本”“义必明雅”“词必巧丽”,就是以思想为主,辞采为副,“丽”不仅指形式的美,而且蕴含了彼时风行的包孕丰富内涵的审美范畴。由于各门类艺术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触类旁通,汉代造物艺术亦具有“情以物兴,物以情观”的特点和崇“丽”的倾向,追求兼具致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融合为一的整体表现力和强烈感染力。
汉代造物艺术思想的建树是多方面的,堪称博大、显明、绚烂和雅赡。在精神上,汉代造物艺术洋溢着不懈求索、知天日新的浪漫主义进取精神。儒家经学刻板僵化的繁缛教条,无法掩盖其生气勃勃的活力,汉代造物艺术犹如万斛泉涌般纵横变化,“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上寻九天,横廓六合,下揆三泉,揲贯万物,发扬无穷无尽的探索精神,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后出现的浮士德形象似乎是其隔世跨域的嗣响,虽然两者所处时代和文化背景迥异。汉人崇尚“驰骛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参天贰地” [6] ,其雄心“包蓄千古之材,牢笼宇宙之态。其变幻之极,如沧溟开晦;绚烂之极,如霞锦照灼,然后徐而约之,使指有所在” [7] 。汉代造物艺术门类丰繁,展现汉人宏阔志向而整体呈现结构美的特征。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下》曾提出,“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人累于天地之间,不能不受阴阳之消息;心之营构,则情之变易为之也”。造物艺术亦属“人心营构”,乃以“情之变易为之”,讨论汉代的造物艺术思想,亦可作如是观。
汉初开国君臣多为楚人,表现出对楚国故地热情缠绵、浪漫狂放、激越苍凉而富有神巫特色楚文化的追慕,这有别于北方《诗经》文化提倡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富于理性精神和功利主义的现实倾向。据《史记·叔孙通传》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这种“短衣”即为楚国衣服的旧有样式,西汉时期犹沿用。《索隐》引孔文祥曰:“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从其俗裁制。”陈直曰:“长沙战国楚墓中所出木俑,皆短衣持兵。” [4] 据《汉书·礼乐志》记载:“房中祀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 [8] 高祖好楚服、乐楚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其潜移默化之功,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世人虽将秦汉并称,但“凡秦之文献,虽至始皇力求变革,终属于周之系统也。至汉则焕然一新,迥然与周异趣者,孰使之然?吾敢断言其受楚风之影响无疑。汉赋源于楚骚,汉画亦莫不源于‘楚风’也。何谓楚风,即别于三代之严格图案式,而为气韵生动之作风也” [9] 。
楚文化艺术精神与汉初黄老思想的融合,表现为汉人一方面试图通过继承楚骚传统文化中浪漫神奇的丰盈艺术想象来理解、诠释疆域广袤、深山大泽、鸢飞鱼跃、活泼玲珑、渊然而深、万物有灵的自然世界,因而呈现瑰玮奇诡的飞动气象和力量;一方面又从继承楚人的忧患意识出发,重新审视兵戈扰攘后生灵涂炭、民生凋敝的现实社会,汉代造物艺术有了这层深沉的忧患底色而含蕴弗穷,恢拓宏肆,回肠荡气,因而在千古艺坛独领风骚。秦、汉易代之际社会变革剧烈,连年征战造成的赤地千里、哀鸿遍野,纵使“文景之治”带来一度繁荣,亦无法掩盖深刻的社会矛盾和贫富悬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10] ,如何认识“天人关系”,深通“古今之变”,反思秦勃勃而兴、忽忽而亡的教训,成为摆在汉人面前的重大时代课题。在这股思潮的激荡下,造物艺术也浸透着这种忧患意识,蕴涵着宇宙之大疑问,人生之大悲哀,直面并叩问永恒的哲思之谜,观之犹如汉代版“天问”,例如《古诗十九首》所记载的汉人心曲:“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感物怀所思,涕泣忽沾裳,伫立吐高吟,舒愤诉穹苍”,“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东汉王粲的《咏史一首》所发慨叹:“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
在这种思潮浸润下的汉画像石刻,表现为以飞动之美来承载“道的精神”和“气的生命”,作品笔力雄健、气贯虹霓,圆劲而以韵胜,沉着痛快,正如杜甫诗云:“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例如:1953年发掘的山东沂南汉墓画像石刻,模仿真实的地面建筑设计而加以缩小,内容包罗宏富,表现题材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故事、祭祀礼仪、纳租入贡、乐舞百戏、庖厨烹饪及贮藏兵器库房等,秩序井然,特别是表现乐舞百戏的画面,俨然是东汉李尤所作《平乐观赋》的生动图解,但凡赋中述及,石刻画迹无不悉备,皆笔携风涛,摇曳多姿:武士“高纵轻蹑,浮腾累跪”,舞女“罗衣从风,长袖交横”,人物形象犹如行云流水般飘逸飞动,洋溢着史诗英雄般的豪杰之气和活泼热烈的乐舞精神。1972年四川大邑出土的《弋射收获》画像砖,画中的猎人虽面目模糊,但其奋力弯弓搭箭、瞄准寥廓苍穹上展翅翱翔的一列鸿雁,仰射或斜射的矫健之姿却清晰可辨;画面右侧是一片荷塘,荷塘水面上游弋着数只悠闲凫水的野鸭,水面下是嬉戏莲叶间的游鱼;画面上猎人张满弓将射未射的瞬间姿态饱含视觉张力、紧张性和飞动的气韵,观者仿佛感到耳畔呼呼生风,听到受惊大雁慌乱中扑扇翅膀四处飞逃的悲鸣……大雁分别向画面左上方和右上方疾飞,将观者的视线顿时从有限的尺幅中引向无限的画面外,留下无穷的想象空间,味之不尽。画面人物造型孔武有力,动物形象生气勃勃,横绝千古。汉画像石的作者拥有纵览山河的胸襟,观之如登高临深,富有雄视宇宙、吞吐日月、囊括六合的气概,刻画着汉人的“实录”精神与“爱奇”梦想
 ,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强烈地激荡着读者的心弦。
汉代乐俑表现生活场景,具有非常生动而强烈的戏剧色彩,令人仿佛身临其境,可触可感,达到了绘声绘影的境地,反映了处于强盛期汉代社会生活中生动活泼的一面。从乐俑腾踔飞扬的风采和无拘无束的神态中,感受到汉人精神在蠲除烦苛之后的舒展和不受羁绊的乐趣,酣畅淋漓地塑造了乐俑活力四射的生动形象,激发人们想象汉代社会生活中种种富有乐舞精神的欢乐场面,反映汉人乐观主义精神和对此岸生活的深挚热爱,“纵声乐以娱神”。形象鲜明,朴实无华,感情激昂,气势豪放,色彩明亮。观之有若神助,一气呵成,酣畅恣肆,如高山瀑流,奔泻而出,显示出无尽的奔放力量和强烈的感情激流,“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洋溢着大河奔流般的气势和纵横捭阖的力量之美。创作者纵其浪漫主义的妙思,驰骋华赡奇伟的想象,创造出雄大壮阔、风神潇洒的境界,观之令人精神振奋,胸襟开阔。
汉赋拥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司马相如语)的雄心壮志,融贯其中的是楚骚伟大的浪漫主义激情,汉代造物艺术思想与汉赋思想在包容开放的大文化背景下,其特征其实无二。“情以物兴,物以情观”,意味着艺术创作“缘情”而发:汉墓帛画中频频出现天上的神仙珍禽、凡间的人兽虫鱼、地下的鬼怪魑魅;往古的神话人物,飘然而至,翛然而往,有天马行空不可羁勒之势,在呈现出飞动之姿和瑰奇之态。汉人善于把神话传说和夸张想象融为一体进行创意抒情,营造出宏大灏邈的艺术境界,洋溢着楚风遗韵的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广州东汉墓出土的舞俑和绍兴出土的青铜镜舞女像以及玉舞人像,显现南国娱神酬神的妍姿冶媚,轻歌曼舞,双袖飘举,随风转折,予人以飞燕惊鸿的炫目动人印象。长沙马王堆汉墓帛画透过奇丽峭拔的神话传说,“指物类象,冠剑陆离,舆旌纷错,以及灵旗星盖,鳞屋龙堂,土伯神君,壶蜂雁虺,辩名物之瑰奇”
[8]
,仿佛令人置身于惝恍迷离、奇幻多姿、参差错综、万象森罗的神话境界:飘飘高翔的凤鸟,深潜九渊的神龙,冥府的幽寂,仙界的灵秀,人间的仪式,九嶷的云烟,潇湘的浩渺,几乎把天上、人间、地下的万千气象琳琅满目地荟萃于方寸尺幅之中,令人有想落天外之感。“秦汉而还,多事四夷”
[11]
,汉人渴望奋发有为、建功立业、封侯万里、扬名后世
 和个性自由发展的迫切要求相结合,使汉代造物艺术充满着纵横八极、意致高崇、与天地同呼吸的鲜明情态,展现出俯仰宇宙、纵览古今、无所不包、穷形尽相、俯瞰万类的艺术形式,表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神欢会、死生同域的开阔视野和磅礴气势,皆殿庑阔大。荆楚文化的神巫色彩经屈骚的演绎,直接影响了汉人艺术审美心理的建构,表现为神话与现实、历史与想象相互激荡、融成一片的气概。作品充满了离奇变幻色彩,各种形象自由驰骋,腾跃有势,摇曳多姿,气势充沛,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见出庄子所推崇的“洸洋自恣”的艺术风格和特色。马王堆汉墓帛画中行人缓缓的步履,庄敬的神情,死前的仪式,离世后的“形解销化,依于鬼神”
[4]
,将汉人宇宙观念中的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
[12]
绘形绘色地铺陈壮势,“意奋而笔纵”,刻画鲜活灵动,营造一种具有神魔般魅力的强烈艺术效果。画面构图极尽变化之能事,恣肆横奇,笔力雄健。观者的思潮随着视线的迁移顾盼而跌宕起伏,激发起心灵的重重波澜,令人“情灵摇荡”。
和个性自由发展的迫切要求相结合,使汉代造物艺术充满着纵横八极、意致高崇、与天地同呼吸的鲜明情态,展现出俯仰宇宙、纵览古今、无所不包、穷形尽相、俯瞰万类的艺术形式,表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神欢会、死生同域的开阔视野和磅礴气势,皆殿庑阔大。荆楚文化的神巫色彩经屈骚的演绎,直接影响了汉人艺术审美心理的建构,表现为神话与现实、历史与想象相互激荡、融成一片的气概。作品充满了离奇变幻色彩,各种形象自由驰骋,腾跃有势,摇曳多姿,气势充沛,笔墨酣畅,气完神足,见出庄子所推崇的“洸洋自恣”的艺术风格和特色。马王堆汉墓帛画中行人缓缓的步履,庄敬的神情,死前的仪式,离世后的“形解销化,依于鬼神”
[4]
,将汉人宇宙观念中的天上世界、仙人世界、人间世界、鬼魂世界
[12]
绘形绘色地铺陈壮势,“意奋而笔纵”,刻画鲜活灵动,营造一种具有神魔般魅力的强烈艺术效果。画面构图极尽变化之能事,恣肆横奇,笔力雄健。观者的思潮随着视线的迁移顾盼而跌宕起伏,激发起心灵的重重波澜,令人“情灵摇荡”。
汉人对于自然景物不是冷漠地静观,而是热烈地赞叹,借以抒发胸臆中强烈的人文理想和雄健的精神追求,构成深邃绵邈的意境和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表面上看来,似乎信手而为,未加营构,开阖顿挫,变化万千,仔细玩味,则气象一脉贯通,表现了鲜有顾忌的直抒胸臆和开创气魄,抒情主线使得作品浑然一体,节奏鲜明,妙趣横生。
《淮南子·墬形训》记载:“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见日。其神人面龙身而无足……雷泽有神,龙身人头,鼓其腹而熙。” [13] 高诱注:“龙衔烛以照太阴,盖长千里,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汉代造物艺术中频频展现诡诞瑰玮的神话传说,表现汉人夸张雄放的浪漫主义想象,上述记载中幽奇、恢诡、谲怪的境界借助读者的联想而一跃成为真实可感的艺术形象,洋溢着浓郁热烈的抒情色彩和浓厚瑰奇的神异气氛。据《淮南子·览冥训》记载,鲁阳公与韩国交战,场面激烈,时近黄昏,鲁阳公援戈一挥,太阳竟退了三舍(古代一舍三十里),真是“出鬼入神,惝恍莫测”!西方文艺理论家在讨论浪漫主义时,常乐于用三个“大”来概括其特点:“口气大、力气大、才气大。” [14] 这种特点在汉代造物艺术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汉代造物艺术中反复出现奔虎、虬龙、朱鸟、白鹿、神祇、玉女、山神海灵、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 [6] 等灵怪而宏伟的奇思妙想,令人匪夷所思的浪漫主义艺术形象,观之惊心炫目,光耀夺人,不能不令人赞叹创作者的气魄和胆力!
如果把汉代造物艺术比作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的话,那么这些奇特浪漫、饱含激情、千容万状的形象犹如交响乐中的主旋律。黑格尔曾说:“真正的创造是艺术想象的活动”,爱迪生借《旁观者》曾言:“想象必须是热的。”毋庸置疑,汉代造物艺术中富含的想象饱蕴炽热情感是其感人至深的重要原因,其神韵飞动的作品非务胜人而务感人,无愧于真正的艺术创造精神。我们或许可以说,汉代造物艺术想象之瑰玮,出于《离骚》浪漫主义精神;汉代造物艺术意境之雄放,得于《庄子》《列子》诸家精义;汉代造物艺术之炽热情感,源于北方《诗经》的诗、乐、舞相统一的艺术精神
 。西汉初造物艺术热衷直抒胸臆、意尚慷慨、情感表现鲜明强烈,反映出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的觉醒,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明舒惨,本乎天地之心”
。西汉初造物艺术热衷直抒胸臆、意尚慷慨、情感表现鲜明强烈,反映出个性意识和主体精神的觉醒,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明舒惨,本乎天地之心”
 ,迨至西汉末,扬雄进一步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强调艺术作为创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这一重要特征,而非以充当“载道”或政治教化的工具为旨归,成为开启东汉王充“真美”观的先声,并直接影响了此后六朝时期以情感动人为美的审美倾向和抒情特征。
,迨至西汉末,扬雄进一步提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的观点,强调艺术作为创作者思想感情的表现这一重要特征,而非以充当“载道”或政治教化的工具为旨归,成为开启东汉王充“真美”观的先声,并直接影响了此后六朝时期以情感动人为美的审美倾向和抒情特征。
清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曾云:“文贵简。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理当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贵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艺术何尝不是如此?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汉代在造物艺术的创作手法、选择题材的事类富丽、工艺技术的精湛细巧等方面远胜于古代,然与今天相比,仍然显得简朴。古人造物简素而质朴,今之造物繁富而可观,并非出于偶然,而是整个社会生活踵事增华、由质趋文的体现。
明人冯时可在《雨航杂录》中曾云:“西汉简质而醇。”此论是就文风而言,造物艺术亦然。汉初造物艺术风格之“简”,主要在于追求“意真”,并与黄老之学有着渊源关系。与黄老之学同出南方的老庄哲学,提倡“见素抱朴,少思寡欲”,“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的审美追求,开启魏晋崇尚简淡、玄远、真挚的自然美风尚,是后世“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思想源头之一。《淮南子·俶真训》推崇“浑浑苍苍,纯朴未散,旁薄为一,而万物大优” [13] 的审美特征,对道家思想作出新的诠释;又因其处于儒家思想被定于一尊的前夜,部分地吸收了儒家思想,出入于儒、道之间,密切地关注着现世人生。《淮南子·说林训》提出:“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质有余也。” [13] 提出若具有优良的“质”,可不必有人工的“文”(饰),崇尚道家质朴为美的主张。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杯篇》中更是把先秦儒家“文质彬彬”的思想纳入到大文化体系的建构中,认为在“文质”不能兼备的情况下,明确倾向于选择代表内容、情志与精神之“质”,甚至“先质而后文”:“志为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质文两备,然后其礼成;文质偏行,不得有我尔之名;俱不能备而偏行之,宁有质而无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质而后文,右质而左物。”
“纤微要妙”原是东汉崔瑗《草书势》中的一句话,虽然描述总结的是汉代所创草书艺术的特点,但由于包含了与其他门类艺术相通的基本规律,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纤微要妙”包含着艺术创作既是高度自由的活动又非主观任意的率性而为,乃是合乎规律的创造,因而要求灵活地“临事从宜”,既非因袭机械教条的僵化格套,亦非仅仅关注点、线、面、色彩等方面的局部细节表现,而是着眼于艺术结构在整体上的和谐统一,同时承载了社会伦理、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内容。这与古希腊造物注重自然感性美而延伸到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例如几何学、光学、透视学、解剖学等规律的认识,存在很大的不同。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八年(前199),丞相萧何“营作未央宫,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太仓。高祖还,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悦” [4] 。所建王城,审曲面势,“瑰异谲诡,灿烂炳焕。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穆穆焉,皇皇焉,济济焉,将将焉,信天下之壮观也” [6] 。西汉中叶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和兼容并包的文化体系,决定了造物艺术显示出宏阔的胸襟、雄健的气象、磅礴的动势,展现了天人合一的宏大图景,其目的正如《诗大序》所言:“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因年代遥远,汉代的建筑今已无缘得见。汉辞赋家王延寿以其熠熠生辉的妙笔,在《鲁灵光殿赋》中展现大汉帝国辉煌灿烂、富丽堂皇的宫殿面貌,气象万千的恢宏气势宛然如在目前。从中可以想见宫室的层叠深邃,楼观的巍峨飞骞,造物的精工华美之巧,龙盘虎踞之势。作者有意将宏丽的建筑安放在广阔的背景上,借以增益壮伟雄浑之感。气宇轩昂,气象不凡,具有震古烁今的气势与力量,这与运用夸张想象的手法不无关系。造型于雄快之中,得飞动宕逸之神韵。形体以飞舞飘摇之势,运旷远奇绝之绎思,既苍凉而又极雄壮,意境浑成,其目的是起到政治的、教化的功用,“非壮丽无以重威”,通过造物艺术实现“明劝戒,著升沉,千载寂寥,披图可鉴”的功用。鲁灵光殿“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谬形;随色像类,曲得其情” [6] 。可以说奏响了后世谢赫六法的先声。
汉代艺术“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 [15] ,是故造物艺匠之思绝不厌奇,有所创获而表现自然,题材广博渊雅,文采淡泊而绝丽,情感幽隐而显明,气势正大而奇崛,意蕴细密而形体疏朗,正如《汉书·艺文志》云:“感物造端,材智深美”,灵感纷至沓来,赋像班形,志向之清峻,情感之绵邈,骨力之奇劲,充盈着纵横之气。“极开阖抑扬之变,景以寄情,文以代质,升天乘云,役使百神。” [15] 善于灵构造奇,探入雄深雅健之境,令人生出“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通过“拟诸形容”,从而“象其物宜” [15] 。史家班固所作《两都赋》具有建筑设计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描写了未央宫遵照上象天、下法地的建造原则,宫殿犹如一个微缩的宇宙,而宇宙则是放大的宫殿,“体象乎天地,经纬乎阴阳。据坤灵之正位,放太紫之圆方”。建造者把汉人所理解的宇宙模式及其运动浓缩到宫殿的架构中,从有限中窥见无限,又从无限中回归到有限。虽然眼前的物象是有限的,但却与宇宙的无限联系在一起,其宫阙楼台“焕若列宿,紫宫是环”,沟渠漕运“与海通波”,灵禽异兽来自“殊方异类”,苑囿园林皆“连乎蜀汉”,人们的引水劳作乃“决渠降雨,荷插成云”,太液池的波澜能沾溉东海神山,这里的画栋雕梁,收日月于堂奥,纳云霓于梁楣:“上反宇以盖戴,激日景而纳光”,“轶云雨于太半,虹霓回带于棼楣。” [6] 虽然有赋者夸张的成分存在,但却真切包含着汉人的宇宙空间意识和时代心理。宫室建筑的建造体现了汉人“苞括宇宙”的雄心,凭借比喻象征的手法和静中寓动的原则,彰显包容万有的崇高、宏丽和雄伟理想。宫殿的梁柱高耸犹如应龙,逶迤曲折宛若飞虹,宫阙楼阁栋椽布列,屋檐犹如鸟翼振翅高翔,屋梁之头仿佛马首萧鸣激昂,在在赋予静止的物象以飞升、腾跃、跌宕多姿的动态美,其“志在飞移,将奔未驰”,焕发“放逸生奇”的神采美,于宏大中见精细,从而昭示“纤微要妙”的审美理想。
画像砖如汉赋般追求通过铺陈排列手法营造富丽的效果,画面构图要求饱满,图像组合类似“模件化” [16] 的程式表现,即注意图像组合之间的主次关系,对称构图或连续排列,有时候这种组合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因而也往往带来出乎意料的生动表现,反映出设计者的匠心巧思。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石刻画像石,在儒家思想主导下,造物艺术的图像结构程序是谨严的,但对具体表现其宇宙观的画像石图像选择和运用却是灵活的,上与下、东与西、天与人可以通过无限变化的题材加以表现 [17] 。
汉代的织锦具有扬雄所说“雾縠之组丽”之美,远望犹如云蒸霞蔚一般,具有“五彩缤纷”“琳琅满目” [18] 的汉赋一般“奢丽”“巨丽”“侈丽”和“绝丽”“靡丽”的特点。同样内容和构图的画面首尾衔接,形成二方连续式样的重复图案,予人以数量众多、连续不断、川流不息的印象,这种起落无端、断续无际、汗漫纵横、铺排蓄势的结构,仿佛是气势恢宏、铺采摛文、明绚雅赡、瑰玮宏富、“繁类以成艳”的汉赋在造物艺术领域的映照,千态万状,层见迭出,夸张形容,体物丰繁,引人遐想,逗人情思。五色错综,成其华彩;经纬就绪,成其条理;锦绣千尺,丝理秩然,回环杂沓,观之有绵邈无际的神韵和铺张扬厉之美,可谓“以情纬艺”。例如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西汉织绣 [19] ,反映了西汉初期罗绮、纹锦、起毛锦的发展水平,为了不受当时织造方法的局限,汉人在精美的绢或罗绮上另辟蹊径增以刺绣,从而获得自由灵动的创作空间,反映了凭虚构象、以虚代实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摛锦布绣”以达到锦上添花、“晔晔猗猗”、“绮组缤纷”的艺术效果,一气观之,令人目夺神迷,既有整齐对称的结构美,又有纵横飞动之妙。
这种由简朴“意真”到“纤微要妙”的造物艺术思想变迁和艺术表现手法的渐次繁富多元,显示了艺境的扬升和审美的深层次推进。
形神关系属于中国古代造物艺术理论中的重要范畴,一般所持的观点基本为三种:重形、重神抑或形神俱重。总括而言,形神兼备是中国古典美学理论一贯关注的重要艺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中国的哲人就已提出了形神关系问题。如《周易》提出:“阴阳不测谓之神”,只有“精义入神”“穷神知化”方可“与天为一”;《庄子》所载庖丁解牛神乎其技是因为“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与”!把木匠的鬼斧神工创作艺术归功于凝神聚气,超然物外,所以能顺应天理,从而使得技进乎道;《荀子·天论》中说:“形具而神生。”
汉代造物艺术体现了天人思想,在汉代产生的形、神、气观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淮南子·原道训》曰:“形神气志,各居其宜,以随天地之所为。夫形者,生之舍也;气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则三者伤矣。”又云:“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因此:“圣人将养其神,和弱其气,平夷其形,而与道沉浮俯仰。恬然则纵之,迫则用之;其纵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发机。如是则万物之化无不遇,而百事之变无不应。” [13] 提倡艺术审美重视神采的“君形者”说:“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亡焉。” [13] 又言:“饰其外者伤其内,扶其情者害其神,见其文者蔽其质。无须臾忘为质者,必困于性;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伤骨骸,枝叶美者害根茎。能两美者,天下无之也。” [13] 主张若未表现出主宰“形”的“神”,那么西施之面虽美而无法令人喜爱;勇士孟贲的双眸画得虽大而无法使人畏惧。“心者形之主也,神者心之宝也。” [13] “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聪明虽用,必反诸神,谓之太冲。” [13]
细究其实,汉人推崇的是崇“神”、尚“质”的自然美,反对害“神”蔽“质”的虚伪文饰。汉代造物艺术正是在这一思想的引导下,发展出不事雕琢的超越于形体之上的具有恢宏雄大、瑰玮奇崛气象的神采美,因而呈现出后世难以企及、高度写意化的艺术特征。
《淮南子》高度重视“神”的作用,提出“神与化游,以抚四方” [13] ,揭示“神”在社会、艺术、人生中的重要地位和致用价值。认为只有基于“君形者”,才能“志与心变,神与形化” [13] ,臻于“神托于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总” [13] 和“身处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阙之下” [13] 的艺术境界。
从造物的自然过程到艺术创作的神采发掘再上升到对社会、人生的哲理联想,《淮南子》的形神观从主宰艺术之“神”的“君形者”着眼,提出艺术创作若有“神”,则形体生动、情真意远,具备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反映主体精神。它批评艺术追求囿于皮相酷肖的“效容”,贬其结果“必为人笑”,说明徒有“形似”以至于“使但吹竽,使氐厌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
[13]
的深刻道理。《淮南子》从探讨形神关系的辩证统一再升华到“神主形从”的艺术境界,显示出汉代“传神”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结构,它与东晋顾恺之提出的“形神论”有着必然的内在渊源关系,并直接引导出魏晋最重要的美学主张。受其影响,魏晋名士人生观“玄者玄远,宅心玄远,则重神理而遗形骸”,任情放达,重风神萧朗,不拘泥于形骸,奏响了魏晋时期中国人物画“传神写照”
 、“以形写神”、“迁想妙得”、“悟对通神”(顾恺之语)等理论的先声,成为南朝宋人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思想的嚆矢。汉人对造物艺术之美、造物艺术自身规律的自觉不倦追求,直接诱发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
[20]
之来临。
、“以形写神”、“迁想妙得”、“悟对通神”(顾恺之语)等理论的先声,成为南朝宋人宗炳在《画山水序》中提出通过写形传神而达于“畅神”思想的嚆矢。汉人对造物艺术之美、造物艺术自身规律的自觉不倦追求,直接诱发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最富有艺术精神的时代”
[20]
之来临。
汉人对于造物之美有着敏锐而独特的感触,纵其才力,别开异径,用爽朗鲜明、生动有力、毫不雕饰的语言将这种美自然而然地加以表现,从而使观者如临其境,流连不已。这些作品所体现的美学追求,与后世的意境论其实是相通的。汉人造物以简驭繁擅场,发展了古代艺术大刀阔斧的写意风格,径取对象神态最动人处“因势象形”,不汲汲于细节表现的逼真,浮雕表面常保留斧凿痕迹而有意不作磨光处理,可谓“浩浩荡荡乎,机械知巧,弗载于心” [13] ,凸显作者有意扬弃智巧刻饰,崇尚“浑浑苍苍,纯朴未散” [13] ,体现雕刻手法的豪迈不羁,别有一种苍莽泱泱的气度,追求内在神采、浑朴似拙的大巧。例如汉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伏虎” [19] ,采用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创作者于石虎背上审曲面势,刻以流转变化、朦胧缥缈的线条,宛如给伏虎平添了股股风力,“云从龙,风从虎” [21]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令人想象其一跃而起时虎虎生风的威猛气势,充满着扑朔迷离的神奇氛围,其中融贯着楚文化神思飞扬的情采,与秦始皇兵马俑理性写实的艺术风貌迥然异趣。
汉代造物艺术务以传神为胜,虽然语言浑朴自然,不事雕琢藻饰,但直抒胸臆、发自肺腑的真情流注,很好地传达了起伏跌宕的感情,擅长平中见奇,如奇峰壁立,这种以小见大、以一当十、容量宏富,具有高度概括、精炼的艺术表现力,显示出创作者杰出的匠心佳构。后世追慕、尊称为“汉魏风骨”,它不在于一点一线、一块一面的奇警、高妙,而在于整体的浑成,即整个作品为了熔铸一个完整的艺术形象或意境,风貌质朴刚健,清明爽朗,使观者可以想象和体味蕴含其中的胸襟气度和思想感情,作品擅长以神魂的律动超越形式或技巧的局限。它所独自开辟的壮美胜境,乃在于莫不因势象形,各具情态,妙诸纷披,览之兴味盎然,气度恢宏;又于严整体势之中,见气韵飞动之妙,不为形似逼真所迫,不受具象写实所限,从容中自有法度,而神明存焉。创作者往往把丰富充沛的思想感情浓缩在咫尺方寸的形象中,信手拈来,无非妙境。观之醰然有味,绝非错彩镂金、雕绘满眼之作所能比肩。
“谶”与“纬”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谶”是用神秘隐晦的语言作为神灵启示人们的预言,例如预示吉凶祸福、治乱兴衰,往往包括图像和文字,所以又称为“图谶”;“纬”是用图谶预言诠释儒家的经典 [22] ,又称为“纬书”,实质上是假托天意来解释经典。东汉的学术思想研究围绕谶纬、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展开 [23] ,但与以往解释儒家经典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汉好言灾异,而东汉则同谶纬结合紧密,通经致用无非是以经义作为政治的粉饰,烦琐神秘的谶纬其实并无多少学理可言。“谶纬的中心思想,是阴阳五行,是灾异祯祥,这正是极合汉代经学家脾胃的。” [24] “董仲舒的著作是谶纬的先导,谶纬是董仲舒思想论著的继承和发展。” [25]
中国古代的征兆思想早在《山海经》中就已有所体现,该书被堪称“一部记载奇异现象的百科全书,又是征兆图像的索引” [17] 。《山海经》中记载许多奇禽异兽、灵木嘉草,不少条目下往往在描述动植物所处地理环境、形体特征后缀以预言:“见则某事会发生”,例如:“西南三百里曰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其兽多虎、豹、犀、兕;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 [26] 鹿的题材早在周代造物艺术中就很流行,不仅因鹿的性情温和,体型美丽皆可资生,也取其与“禄”谐音,因而被视为吉祥之物,常与凤鸟或仙鹤等结合起来造型。与汉儒不断将帝王身世神话化相伴随的是,谶纬吸收了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倡扬的“天人感应”思想,从而导致大量的祥瑞现象在汉代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涌现,这些瑞兆成为汉室君权神授的有力佐证。
在汉代经董仲舒《春秋繁露》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论和《白虎通》充满宗教神学色彩的认识论强调下,征兆思想获得空前强化并引起广泛重视。《白虎通》继承了《春秋繁露》的神学目的论思想,并加以发挥和推演,把自然万物的秩序和社会政治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提出统治秩序、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天地星辰相互比附的关系,认为帝王的德行纯洽,就会阴阳相和、风调雨顺、万物有序、天地出现祥瑞;那么,用祥瑞图像装饰的造物艺术,则是带来好运的预兆。例如:山东苍山城前村画像石墓,对于墓门画像的文字说明为:“中直柱,双结龙,主守中霤辟邪殃。”“上有虎龙衔利来,百鸟共侍至钱财。” [12] 这些祥瑞形象所要表达的愿望即是避开邪殃和多利多财。1972年发现的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后室北壁左方所画琼楼双阙,中有一株枝繁叶茂的高大桂树,左右各一弯弓射箭之士(射箭象征猎取富贵功名),榜题所注:“立官桂树”,所取“桂”与“贵”谐音,表达了“为官显贵”之意 [27] 。
描述吉祥征兆的“瑞图”可以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据载公元前109年,玉芝生于甘泉宫齐房,汉武帝为此特赋诗一首:“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28] 西汉文献较少提及此诗中所说的“图”,然迨至东汉,文献中开始频频出现,例如班固所作的《白雉诗》:“启灵篇兮披瑞图,获白雉兮效素乌。” [29]
又据《汉书·武帝纪》记载:“(武帝)行幸雍,获白麟,作白麟之歌”,“行幸东海,获赤雁,作朱雁之歌”,“得宝鼎后土祠旁,作宝鼎之歌”。汉宣帝时代又获得神雀、五凤、甘露、黄龙的祥瑞征应,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造物艺术服务于政治教化,载道、明道、“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的特点鲜明。例如山东嘉祥武梁祠房脊两侧的大石板上即刻画了几十幅祥瑞图,与之相配的文字榜题说明其名称和作用,这些祥瑞图像包括神鼎(不炊自熟,五味自生)、麒麟(动静有仪)、黄龙(德至渊泉)、白虎(不暴虐)、比翼鸟(德及高远)、六足兽(谋及众庶)、比目鱼(德及幽隐)等。从《宋书·符瑞志》可以发现,自东汉至南朝的几百年间,见于“祥瑞”最多的当属元和二年至章和元年的三四年之间,仅麒麟就出现过51次,凤凰出现过139次,黄龙出现过44次;其他各种祥瑞形象也不胜枚举。汉章帝不去考察这些祥瑞是否真实,倒以为是其德被天下的必然结果而沾沾自喜。“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上行下效,随着祥瑞理论在汉代建立后近三百年的发展和风靡,直接影响了人们的观念,构成了后世造物艺术中包含吉祥观念的滥觞。
汉代基本的哲学问题是天人关系问题,思维基本形态呈现为阴阳五行模式,以及与之相关的天人同类、天人相与、天人相副、以类合之、同类相动的思想,体现了经验主义与方法论层面的重视整体、系统和结构的特征。祥瑞艺术形象的频频出现,以期达到“众庶悦豫,福应尤盛” [6] 的目的。
汉代造物艺术以神韵胜,故浑然天成,情味醇厚,非饾饤堆砌、雕缋满眼、刻意求工之作所能望其项背。欲对某时代之造物艺术得最透彻之了解,亦须研究该造物艺术所处时代之独特精神,即黑格尔所称化身为“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绝对精神”(Zeitgeist)。各时代人们的心理和社会生活之不同,造就了迥然相异的造物艺术风格和面貌。汉代国势强盛,汉武帝提倡尚武之风,开疆拓土,“从西北边境到东北边疆,都是新开辟的土地” [30] ,戍守边疆,消弭边患,积极参与构建国力雄张、物阜民丰的社会,使得上自公卿贵胄,下至布衣百姓,均拥有强烈的事功精神,儒家“外王”思想掩盖了“内圣”倾向,虽外患频仍,但汉人意气风发,胸怀开拓进取之宏志,渴望匡时济世,垂名青史,其雄强的心态向外扩发。汉《古诗十九首》中所咏“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守贫贱,轗轲长苦辛” [6] 正是这种心态的生动写照。审美观念受其浸染亦然,其所好之美在于崇尚神韵气象之高华而非拘泥形貌细节之琐碎,情思贵壮阔而非纤微,气力尚发扬而非内敛,格调重宏亮而非清幽,造物艺术尚朴澹古雅而非新艳雕琢,其美不在形貌而在意境,味尚刚健隽永而非肥醲纤弱,寓神奇于温和醇厚,寄感怆于中和平易,形简意深,神采变化,不袭形貌,自创一体,皆与时代精神相吻合,共同塑造了汉代造物艺术的宏远意象和深微神理,真正体现了“神余象外”的艺术特点。一件造物艺术品,可以窥见创作者个体之心绪,而一个时代的造物艺术,可以想见一时代之精神也。今日中国躬逢盛世,如何构建正在崛起的中国形象和中国气派,或许,发掘、继承和弘扬刚健闳放、气魄雄大的汉代造物艺术思想,从中汲取有益的精神资源,以期重塑民族自信力——民族精神的表现和发扬,有赖于艺术的熏陶和浸润。
(李轶南,艺术学博士,副教授,东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
[1]龚鹏程著.汉代思潮[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徐复观著.两汉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4]韩兆琦译注.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0.
[5]周振甫著.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陈宏天等主编.昭明文选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1.
[7](明)王世贞著,陆洁栋、周明初批注.艺苑卮言(卷一)[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9.
[8]许结著.汉代文学思想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邓以蛰著.邓以蛰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
[10](东汉)班固著.《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11]钟基等译注.古文观止(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2]信立祥著.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0.
[13]陈广忠译.淮南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4]萧涤非,程千帆等著.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15](清)刘熙载著.刘熙载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16][德]雷德侯著,张总等译.万物[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7][美]巫鸿著,柳扬等译.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8]李泽厚,刘纲纪著.中国美学史(先秦两汉编)[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19]李松著.中国美术·先秦至两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0]宗白华著.宗白华全集[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1]唐明邦主编.周易评注(修订版)[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2]张道一著.吉祥文化论[M].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23]金春峰著.汉代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4]顾颉刚著.汉代学术史略[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5]钟肇鹏著.谶纬论略[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26]郭郛注.山海经注证[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7]张道一著.张道一文集(下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28](汉)班固著.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9](南朝)范晔著.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30]吕思勉著.秦汉史(下册)[M].沈阳:沈阳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