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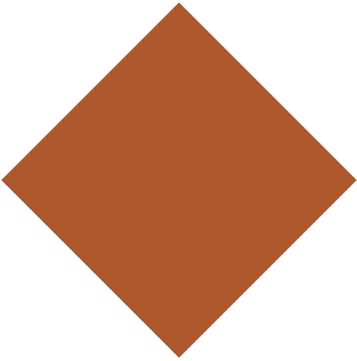 洗礼堂门饰之争
洗礼堂门饰之争
15世纪时,英、法、西班牙已成为强大的王国,意大利却仍旧小城林立,彼此在商业、战争和艺术中互争高低。佛罗伦萨也不例外,但在1400年前后它有一段相对安定的时期,七大行会的人轮流执掌市政公社大权,在有势力的商业望族保护下处理城市公务。公社政府保留着佛罗伦萨人十分珍爱的共和自由制度,当意大利大部分城市都被集权主义贵族统治者控制时,佛罗伦萨公民最喜爱的活动却仍然是针砭时政,讨论社会和艺术问题。外邦统治者似乎被佛罗伦萨人的分歧所鼓舞,因此在1400年,米兰公爵吉安加列佐·维斯孔蒂率军兵临城下,企图征服佛罗伦萨。佛罗伦萨人于是暂时团结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后来米兰公爵突然去世,解除了危险,佛罗伦萨人就把这看成是上帝在行使正义,标志着他们作为城邦权利和地区自由的保护者,在意大利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受这种乐观主义和城市自豪感的支配,各行会重整旗鼓,大兴土木,以适应自己作为“共和政治”的保卫者或意大利半岛上的雅典那样的新角色。羊毛呢绒商行会卡利马拉(Calimala)在新世纪开始时就宣布为建造圣约翰洗礼堂的两扇青铜大门征集图案,该洗礼堂是一座八角形建筑,位于佛罗伦萨中心。
“当人们回到高贵的古典雕塑形式和自然法则时,文艺复兴就在佛罗伦萨发生了。”吉贝尔蒂:《评论集》。
原来的一对门扇是安德烈·皮萨诺在1336年铸造的,上面有四瓣叶形花边组成的框格,格内以浮雕表现《新约》和圣母玛利亚生平故事。这就为构图规定了条件,参加选拔的人要在一年中把《旧约》中关于以撒作牺牲的故事铸在相同框格的青铜上,呈交给行业公会指定的评选委员会。瓦萨里开列了七个竞争人的名单(吉贝尔蒂说有六个),其中包括吉贝尔蒂自己,勃鲁奈勒斯契,雅可波·德拉·奎尔查和多那太罗。参加竞选的艺术家两种风格的都有,既有出自阿尔卑斯山另一面、被瓦萨里称作法国风格的哥特式,也有自乔托和皮萨诺以来一直影响意大利艺术的从罗马派生出来的本地风格。
评委会一定是把以撒作牺牲的故事描述得很详细,因为至今仍保存在佛罗伦萨巴杰罗博物馆的两块参加竞争的铸板,其场面完全一致。亚伯拉罕站在山顶上,正要把他的儿子以撒杀了敬神,这时突然从天上飞来一位天使阻止了他,指着一只羊让它代以撒受刀。两个仆人在一条溪边侍候,一头驴正在溪中喝水。在这么小的画面上表现出这么多内容,就使艺术家们面临着既要叙述清楚又要布局奇巧的大问题,他们不仅要详细表现故事的地点,而且要表现事件发生的那一瞬间。
不久,参加竞争的人就只剩下两个了——洛伦佐·吉贝尔蒂和菲力波·勃鲁奈勒斯契。吉贝尔蒂对他父亲传下来的哥特式传统深为精通,他父亲巴托卢齐奥是个金匠,铸造技术精湛至极。当时人们已认为吉贝尔蒂是佛罗伦萨最好的雕塑家之一,瓦萨里提到他年轻时曾受业于一个法国雕塑家,但此事人们知道的仅此而已。他还爱好并能鉴赏古代铜器和雕塑品,自己也拥有相当一批藏品。
勃鲁奈勒斯契年轻时曾由父亲安排去当公证人,但最后获准去从事他真正感兴趣的事业——艺术和设计,当时,这意味着各种技术发明和机械创造。他最初在一个金匠铺工作,不久就能够雕金镂银,铸造金属像,勾花刻线,制造钟表并进行建筑设计。


两位艺术家呈交的雕板初看之下十分相似,但实际上却极不相同,它们立刻成为评判人甚至是佛罗伦萨一般市民谈论的话题。两幅作品各有重点,对各部分的处理也不同,这就为故事表述定下了不同的调子。假如我们问哪幅作品更写实、描绘更佳、更优秀,我们一定会毫无疑义地说是吉贝尔蒂的。他把画面分成两半,相互间达到令人吃惊的协调和平衡;他对亚伯拉罕身体的处理极富“韵律”,由渐渐远去的风景带出一道优美的弧形,亚伯拉罕沐浴在一道流畅的光线中,形象十分突出,几乎像一尊立体的小雕像。以撒的形体以一具古典的阿波罗神像为楷模,第一个仆人的背影轻裹在一幅宽大的斗篷中,以撒衣物上的皱褶暗示着下面的流水。尤其突出的是吉贝尔蒂极巧妙地把整个作品一次铸成,而勃鲁奈勒斯契的作品则分成七块铸,然后焊接在一起。
但谈到空间和时间的问题,谈到背景和事件结局的急迫性,优势在哪一方呢?在勃鲁奈勒斯契那里。尽管他倾向于用象征性的手段去表现自然的东西——比如岩石、树木、流水等就是用某种速写手法表现的——它们却表现得很有力量。背景以低调来表现,创造出一个适合展开故事情节的空间。以撒的身体弯曲扭折,在他父亲绝望但坚定的手中拼命后缩。亚伯拉罕的手突然被天使抓住,没有把小刀刺进他自己儿子的喉咙。作品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圣经》中这一段故事所含有的强暴气息,一切都在倏忽间发生,就连伸出头去浅溪中找水喝的驴,也因为足下不知虚实需努力保持平衡,而使拉长了的肌肉和骨头凸显出来。这使它看上去更呈兽性,而较少优雅的风度,但由于动作的必然性却又显得真实可信。在勃鲁奈勒斯契的作品中,事件的时间和空间第一次具有更合乎历史的意义,而不再是超自然的了。


吉贝尔蒂的构思是卓越的,但它由两个独立部分组成,每一部分都应分开来理解。勃鲁奈勒斯契把故事画在一个锥形构图中,它从亚伯拉罕的头及举起的手开始,在右边顺着老人的背往下直到蜷着腰的仆人;左边由天使弯曲的身影直到山羊再到仆从。
两位艺术家都从古代作品中汲取灵感,吉贝尔蒂的浮雕中以撒的身体已在前面提到了,而两幅作品中孩子跪在其上的骨灵盒都是仿效古典形制。勃鲁奈勒斯契的浮雕中左面那个仆人是仿一尊著名的罗马青铜像《拔刺的男孩》(表现一个孩子正在把脚上的刺拔出来)。不过吉贝尔蒂参考古代作品就如同一个人在珠宝古董中寻觅搜索,想从中寻求启发或借一块宝石嵌进其他背景;而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勃鲁奈勒斯契则是有条不紊地在考察古代世界的艺术,他把它当作一部复杂而迷人的机器来考察,想看出它运行的奥妙。他们仍然在努力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他左盼右顾,想多方寻求启示。这种情况就解释了他作品中粗糙的细节、未经提炼的画面和过分拥挤的布局。吉贝尔蒂处于一种成熟传统的终端,他的笔触是磨炼过的,他甚至能使自己跟得上人文主义新文化的步伐,他无疑是竞争的获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