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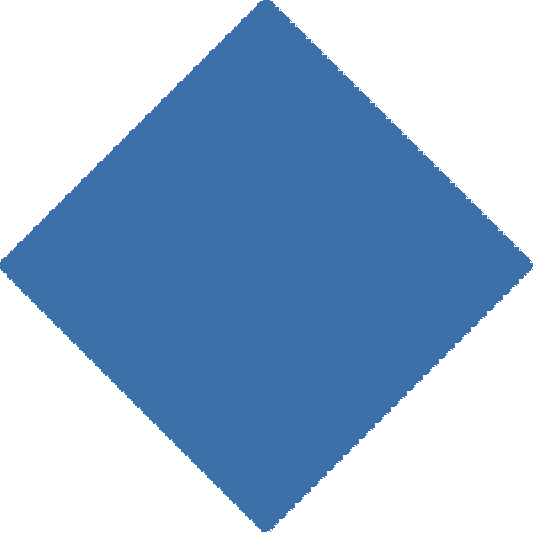 浪漫主义:激烈而热情奔放
浪漫主义:激烈而热情奔放
如果说威斯特的《沃尔夫将军之死》扩大了历史题材画的范围,从而为这种体裁开辟了新的途径,那么他的《青马上的死神》就再次表明他是个有创新精神的设计家。这幅画受《启示录》和爱德蒙·伯克的《关于崇高与美的思想起源之哲学思考》(1757年)一书的启发,表现“恐怖的”崇高,这种崇高的特征导致痛苦,引起恐惧,恰与美相对立,因为美使人平静,使人愉悦。他画中的一家人正在与仓皇逃遁的死神化身作斗争,表达了伯克的主题,即人的自卫本能和由此而引起的冲突。
伯克的思想也启发了其他许多画家如威廉·布莱克、亨利·富塞利和詹姆斯·巴里(James Barry)等。但威斯特的绘画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由于环境有利,使得这幅画在欧洲浪漫派绘画发展中确立了其地位。1802年威斯特带着他的画来到法国,当时正好是英法亚眠条约签订后,法国同意撤出那不勒斯,英国则答应放弃在法国革命战争中征服的某些地区。就在这时,一批英国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到法国去看拿破仑的艺术藏品。和当时正流行的大卫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威斯特自己也是这种风格的先驱)不同,《青马上的死神》主要是根据彼得·保罗·鲁本斯的巴罗克构图画成的,这是一个重要的新动向,至少在当时,似乎在风格上向后退了一步。威斯特的画没有被忘记,它预示了法国的浪漫主义大师如泰奥多尔·席里柯和欧仁·德拉克洛瓦等人的作品。
人类与自然斗争以求生存的主题,在英国还由另一位艺术家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发掘出来,虽说没有那么雄伟壮观。科普利和本杰明·威斯特一样来自美洲殖民地,他在威斯特和乔舒亚·雷诺兹爵士的鼓励下离开美洲,成为皇家美术学院院士,这时正值美国革命爆发前夕,以后他一直留在英国度过一生。
1778年,科普利随威斯特之后将一个当代事件提升为历史绘画,这就是《沃森与鲨鱼》,但他比威斯特走得还要远,他选择的事件既没有历史意义,也没有政治意义(虽说受害者布鲁克·沃森后来当上了伦敦市长)。沃森当时在哈瓦那港游泳,一条鲨鱼游过来咬掉了他的半条腿。科普利以历史画的雄伟格调来画这件事,中心画面安排成金字塔形,画中人物就要把鲨鱼打死,那人物取一种天使长的姿势,或圣乔治屠龙的姿势,使人觉得似曾相识,而沃森的裸体则又让人想起古典艺术。科普利引入了人向自然开战以求生存的主题,这个主题在四十年之后将由19世纪法国第一个重要的浪漫派画家泰奥多尔·席里柯重新拾起,表现在他的《梅杜莎之筏》中。
泰奥多尔·席里柯 “梅杜莎”号是一艘法国政府船,载满殖民者,在非洲沿海遇暴风雨沉没,据说是由于船长的不称职造成的。船上救生艇很少,很多人丧了生。公众认为这次悲剧表明政府对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漠不关心。席里柯(1791—1824年)被这次灾难深深地震动了,他选择了一个特别沉重而又痛苦的时刻:一群残存者向一艘过路的船拼命挥手求援,但没有被看见;有些人在继续坚持,其他人退缩到死者中去,在绝望中等死。
大约有一百五十个残存者挤在木筏上,漂浮了十二天,这期间除十五人之外其他人全死了。通过采访一些幸存的人和阅读报纸上对落水者的报道,席里柯凑出一幅同类相食、哗变闹事和持久心身痛苦的凄惨景象。他从陈尸所弄到尸体,研究尸体腐烂的不同程度;他在一所医院里草描下发疯癫狂者的脸。他在画室中造了一架木筏模型,还在勒阿弗尔研究过波浪的起伏。他的抱负是把真实事件中的迅即感和历史题材画的不朽性结合起来。死者以及挣扎的活人躯体摞成一座巴罗克式的金字塔,最顶端是一个黑人幸存者的形象(让人想起科普利画中的黑人),他正拼命地打信号请求救援,强烈的明暗对比强调了绝望与希望这两个极端。席里柯1816年在意大利曾见过米开朗基罗的《受诅咒者的堕落》(西斯廷壁画的一部分),这幅画的影响明显地表现在痛苦的人物形象的人体构造和姿态以及他们的组合上。席里柯用德拉克洛瓦(一个金字塔的顶点)和另一个画家朋友路易—亚历克西·雅玛尔(Louis- Alexis Jamar,在前排)作模特儿,从而加强了生活的真实成分。
虽然他这幅画在1819年巴黎美展上获奖(巴黎举办每年一次的公开展览),但他却从不认为他已对题材做出了充分的表现。展览会后,他把画送到英格兰和苏格兰去巡回展出(1820—1822年),因此这幅画也在那些地方广为人知。他在英格兰遇到一批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对约翰·康斯特布尔的风景画印象特别深。他在英格兰画了许多当代生活的速写,这些都是见闻报道的杰出之作,他运用平版画(石版画)新技术把这些作品印制了许多复本——席里柯是法国艺术家中第一批制作平版画的人,这项技术1798年由阿洛瓦·塞内费尔德(Alois Senefelder)发明。
席里柯终生爱马,这在画英国跑马比赛中表现出来。他酷爱骑马,后来他还很年轻时就因为从马背上摔下来受伤且产生并发症而死。他特别喜欢巴罗克式的骑马画(他的同学曾给他起诨名叫“鲁本斯的厨娘”,意指他对这位大师百依百顺)。他也喜欢乔治·斯塔布斯的画,这既是因为斯塔布斯狂热地研究动物,从而为浪漫派绘画引入了一个新主题,也是因为他独特而精湛的解剖学研究(《马解剖学》)。
席里柯出生于卢昂一个富裕家庭,曾随卡尔勒·韦尔内(Carle Vernet)学画,后又随大卫的学生皮埃尔—纳西斯·盖兰(Pierre- Narcisse Guérin)男爵学习,大卫的另一个学生与挚友安托万·让·格罗(Antoine Jean Gros)男爵对席里柯强调色彩与构图的做法也有很大影响。但席里柯的风格更倾向于向不用线条的方向发展,换句话说,新古典主义画家们用线条来确定形象,席里柯的人物则靠厚重的色彩来塑造。他不肯用学院派的方法在画前作轮廓草描。
席里柯还是位肖像画家,他在为友人艾蒂安·乔治(Etienne Georget)所作的组画中,表现出非凡的心理洞察力。乔治医生是法国治疗精神病的先驱之一,为揭示一个人的思想与其面部表情之间的关系,他想把病人的脸相永久记录在案,作为他临床研究的一个方面。席里柯受乔治之托而作的绘画,是西方艺术史上心理肖像画中最动人的样品,同时又是浪漫主义激情的极出色的珍品;对于这种激情,席里柯的绘画贡献甚巨。
为使肖像简单明晰,席里柯把多种因素化减为最少数量的精华,集中发掘对象表情中最微妙的部分(如《疯女》和《疯人》所示)。由于眼和嘴角周围部分最容易表现心理状态的变化,这些部位的特征因此是人类面部最有表现力的。席里柯把握了这一事实,因此能把姿态、头部位置和色彩光线的运用完美地融为一体,最大程度地表现面部表情的广度与深度。




画中面部呈正面稍偏,可见两眼及整个嘴部。头部处画面上方,后面是深色的单色背景。服饰是深色的,因此似乎是在阴影中往后缩,而且是大而化之地画出来的。头后面有柔和的光线,有白色的衣领或光环般的头巾,这些进一步勾画出脸部轮廓。明暗对比的效应显示出光线从略偏斜的方向照到脸上,但在阴影中的那半边脸又不完全阴暗,因此整个脸容仍清晰可见。脸部不用线条勾画,这种方法用面部的写实表达出内心的真实,它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它尊崇人的个性。画中的凝视(《疯女》)或散落的注视(《疯人》)漂亮地聚焦于一处,这是因为艺术家抓住了眼神的一瞥,并表现出眼虹与瞳孔的相互关系。头部的倾斜记录下了一个动作,脸颊上的一道纹表现了嘴的弯曲。
欧仁·德拉克洛瓦 1824年席里柯不幸去世,年仅三十二岁,此后浪漫主义风格的主要画家就是欧仁·德拉克洛瓦(1798—1863年),德拉克洛瓦很敬佩席里柯,而且和席里柯一样就学于盖兰,很崇拜格罗。早两年,评论家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已经对德拉克洛瓦在巴黎美展上的第一幅展品《但丁和维吉尔的小舟》大声叫好了,说它宣告了一代新秀的崛起,说它有诗一般的想象力,有高超的绘画技巧,有米开朗基罗—鲁本斯式的画面构思。但当德拉克洛瓦于1824年在美展上展出《希俄斯屠杀》时,作家兼评论家司汤达则一方面称赞德拉克洛瓦对观众的感染力(有些人甚至哭了)以及他对色彩的感受力(称他为丁托列托的继承人),一方面却声称这幅画描绘的不是“屠杀”而是“瘟疫”。画中没有刽子手也没有被害人,而任何像样的“屠杀”都应该有这些人。画中人物不像希腊人,而且服饰也不对。


德拉克洛瓦的许多画受启发于但丁和莎士比亚,以及像拜伦勋爵这样一些浪漫主义作家。在这方面他也突破了传统,因为过去总是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提取素材,他却既以历史也以当代事件作绘画来源。他和拜伦一样也关心当代事件,这些事件中包含了人类的痛苦,既有生理的,也有心理的。其中的一件——希腊独立战争,使德拉克洛瓦着手表现1822年土耳其屠杀希俄斯基督教徒的事件,传统上希俄斯岛被看作是荷马的出生地。因此在这场斗争中,该岛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1824年巴黎美展上另一幅画现在比德拉克洛瓦的这幅画更出名,那就是英国画家约翰·康斯特布尔的《干草车》。当德拉克洛瓦看见康斯特布尔画中卓越的自然气息时,他重画了《希俄斯屠杀》中的背景。第二年,他到英国去更仔细地研究英国绘画,他在那里遇见许多皇家美术学院院士,大量研究了马,正像席里柯以前曾做过的那样。英国绘画可能对他不受约束的作品《萨达那帕勒斯之死》有影响,这幅画在1829年的美展上大受贬责,说它色泽太鲜艳,笔触太自由,雕凿又不够。
拜伦勋爵讲过淫荡的皇帝萨达那帕勒斯的故事,他的诗《萨达那帕勒斯》给德拉克洛瓦的画以灵感。萨达那帕勒斯是亚述一个腐败王朝的最后一任统治者,他遭围困,没有丝毫逃脱的希望。德拉克洛瓦选择了这样的一刹那:萨达那帕勒斯下令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搬到一起——包括姬妾、马匹、卫士,他们将被杀死,然后和他自己一起付之一炬。
德拉克洛瓦把这奇怪的场面组织在一个异国聚宝盆似的对角线构图中,其中洋溢着各种耀眼的宝藏。斜线从左上方皇帝的形象开始,沿着衬托在血红色御榻上的不同程度裸露和有不同程度意识的人体向下,到右下角扩张开来,把一群形象包裹在内。这里有一个拱形,由一个生气勃勃地把手伸向皇帝的男子开始,继之以那个正被人刺杀的半月形女子,这个拱形把人们的注意力指向萨达那帕勒斯和躺在他脚边的切尔卡斯女奴,这里是全画的中心所在。在画这个其种族因身段与肤色之美而著称的女子时,德拉克洛瓦抓住了切尔卡斯人层次精细的肤色和栗色的头发与眼睛等这些特征。中心斜线左右两边的阴影中,德拉克洛瓦通过着重强调的细节片断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异国风采,加上了更多的滚动形象:左下角,一个奴隶正与萨达那帕勒斯的一匹宠马扭斗,这匹马与皇帝的其他所有物一起将被杀死。右上角,则有更多的人正在被杀死。
德拉克洛瓦是一个高超的人物画家,这雄辩地表现在《米索朗吉废墟上的希腊女神》中,这幅画他于1828年在伦敦展出,1826年则在巴黎一次为捐助希腊的独立斗争而举办的展览会上参展。
米索朗吉是战争中希腊起义者反抗土耳其的一个重要据点,1822—1825年间,土耳其人曾多次包围它,德拉克洛瓦当时深受感动,乃提笔作画。此外,拜伦勋爵在1824年的包围中就死在那儿,死于热病,他曾把自己的作品与精力献给希腊的事业,被尊奉为希腊事业的英雄。
德拉克洛瓦把象征希腊的女神画成真人大小,占据了几乎整个画面的纵中轴线(中轴线有两米多长)。她背对右面背景上胜利的摩尔人,像一个现代的圣母摊开双手,在被围困的废墟上寻找她死去的孩子。滋养生命的胸裸露着,温暖柔软的轮廓包裹在蓝白色披衣的轻垂褶皱中。德拉克洛瓦和约翰·康斯特布尔一样能够用冷色来表达温暖,光线从观众的左面进入画面,希腊女神正视着它,其形象衬托在早晨阴冷黑暗的旷野中。哭丧的天空呈寒冷厚重的蓝色,渐渐地远离,正好匹配女神飘动着的外衣。她倚天而立,似乎是座巨大的、温柔的灯塔。起先,德拉克洛瓦把希腊女神想象成一个意气消沉的形象,然而在作品完成时,她成了希望的象征(这是他自己的话)。她满怀悲痛,但体现着生的意志。德拉克洛瓦让希腊战士那只被压碎的无生命的手作为牺牲的象征,如果说席里柯出于写实而为他的《梅杜莎之筏》研究了许多残缺肢体,那么德拉克洛瓦现在却用它表达超越经验的含义了。


虽然德拉克洛瓦受青年画家们的百般崇敬,有些评论家也承认他作为画家的重要地位,但官方对他的承认却很缓慢,因为古典主义一直占统治地位。然而到1830年前后,偏爱的方向有所转变了,德拉克洛瓦开始得到官方的喜好,也拿到一些政府的项目。这时,他到中东去周游,去亲眼看一看那些长期以来使他神魂颠倒的地方与文化。泰奥菲尔·戈蒂埃在评述1841年巴黎美展时,把德拉克洛瓦称作是“本世纪真正的宠儿”,并预言“绘画的未来要在他的画布上出现”。德拉克洛瓦还是位天才作家,他在《日记》(1822—1824年,1847—1863年)中不只是谈艺术的事,而且对那个时代的社会作出了有益的观察。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1780—1867年)是学院派支持古典主义传统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德拉克洛瓦的主要对手。他生于图卢兹附近的蒙托邦,最早在图卢兹美术学院学习,1797年他到巴黎从大卫学画。安格尔和德拉克洛瓦的竞争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它集中体现了学院中长期存在的两极,一极是以尼古拉·普桑的绘画为代表的强调保持线条、素描与古典传统之纯洁性的普桑派,另一极则是鲁本斯派,他们忠实于表现在彼得·保罗·鲁本斯作品中的色彩和不用线条的画法。
1824年,当德拉克洛瓦展出《希俄斯屠杀》时,安格尔展出了《路易十三之誓》,这幅画是1820年受委托为蒙托邦大教堂而作的(在意大利作成,因为他从1806年起就一直在那里)。画中表现路易十三将法兰西置于升天圣母的保护之下,感谢她在1636年打败萨克森公爵的过程中给予的保佑。
这两幅画极好地体现了学院中对立的两种意见。当德拉克洛瓦的画受批评时,安格尔的画则大受赞赏,特别是因为它忠实于古典艺术的高标准及其出色的线描,而这正是安格尔的天才力量所在。这幅画把安格尔置于反对浪漫主义运动的前沿位置。


但也有人批评安格尔借用了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画,批评这幅画过分强调感官美。圣母妩媚娇艳,圣子毫无神性,他们认为安格尔已经把这个主题中的宗教色彩剥夺了。此外,圣母立于其上的云朵更像是大理石而不是云彩,对国王的处理也似乎太弱,不像王者的尊严。但安格尔笔下的天国与人间的区别,却是线条与色彩的上乘之作。圣母、圣子的天沉浸在温暖之中,似乎有无穷的深度,加上柔软圆润的轮廓,恰与路易十三地上王国的暗淡空间、阴冷色调、鲜明的反光和有棱有角的衣褶成截然对比。
安格尔画了许多文学与古典题材画,创造了许多沐浴与闺房场面,表现了他对女性裸体形象的兴趣与精通。他重复创作典雅的形象,有时只具有细微的差别,从而创造出一套丰富的“语汇”。
安格尔的主要成就之一,是完善由大卫发展起来的肖像画风格,这甚至在20世纪都对艺术家有广泛影响。他的肖像是一种精细的组合体,反映平面与立体形状的关系。身、脸、手、胸等更倾向于用平面形式表达,如《奥松威伯爵夫人像》那样。在这幅画中,他非常注意真实地表现物体的精细纹理,如衣裾、抽斗、镜子、丝带和一大堆其他东西,由此,安格尔消除了运笔的一切痕迹。他把素描的准确性和线条的优雅风格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观感,似乎在对象与观众之间无任何东西阻挡。


分析安格尔这种以假乱真的手法中的形式成分,对理解他关于写实与想象的看法很有用,这个问题在整个19世纪一直被艺术界所关心。伯爵夫人的脸、颈和手臂加工得如同象牙,没有自然线条,使其表面初看起来似乎毫无立体感。但细看之下,尤其是细看脸部,就会发现安格尔运用了一套虽有限度却十分精细的色彩变化,十分令人吃惊,使人想起拉斐尔的圣母,而他对拉斐尔是终身十分敬佩的。脸部轮廓干净而准确,包在头发和弯曲的左手食指间,手托在下巴下。安格尔从古典作品中借用了这个姿势,而在20世纪又影响到毕加索为他的一个情妇所作的肖像。左颊上暖色的阴影连接着左食指的线条,使画平面陷下去,从而塑造了她青春脸庞的柔软轮廓。她的身影柔和地映照在方形大镜中,那镜子的上方和右面被画切断,突出地表现了伯爵夫人和观众靠得很近,而且她就在观众自身的空间里。墙角的画法把两面墙接到一起,创造出一种包抄的印象,这其实起源于早期荷兰画家如佩特吕斯·克里斯特斯(Petrus Christus)和迪里克·鲍茨(Dieric Bouts)的作品。这个来源就安格尔而言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因为评论家早就注意到他受“布鲁日的扬”(扬·凡·爱克)所作的根特祭坛画中间那一幅的影响颇大,比如说,他在1806年巴黎美展上展出的拿破仑画像就是这样。
在他的肖像画中,安格尔把绘画与抽象结合在同一种线条风格里,创造出一种写实与想象的独特融合。如果把安格尔的《奥松威伯爵夫人》和席里柯的《疯女》放在一起,就可看出新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肖像创作都有很强的感染力,当然也可看出它们之间深刻的不同。对席里柯来说,重要的是如何用疯女的脸来表达其内心的状态,因此这张脸占了画布一大半。席里柯随心所欲的笔触和破碎的色彩加强了人物表情的感情深度。另一方面,安格尔则把注意力集中于画中每一样东西的形状与纹理上,伯爵夫人和画中其他每一样东西平分秋色。安格尔明快的线条、不留痕迹的运笔、色与光的细微差别等等使画面特别干净利落,而这正是他肖像画的特点。
弗朗西斯科·戈雅 另一个能代表时代的浪漫主义情感的重要画家是弗朗西斯科·戈雅(1746—1828年)。他出生在富恩德托多斯,学习和工作则在萨拉戈萨和马德里,曾短时期在意大利。那时,西班牙有一点脱离欧洲生活之主流,因此他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创作,他最有力的作品是在他死后才为西班牙之外的人所知晓,虽然从时间上说,他在题材和技巧方面比席里柯、德拉克洛瓦和马奈的某些创新还要早几年。
他活着的时候,西班牙人知道他画肖像画、历史画和教堂画。他的青年时期显然很动荡,此后他适应了宫廷的体制,逐步升迁到西班牙国王查理四世的首席画师的地位上。1792年他得了一场大病,几乎送命(可能是由性病引起的),后来留下了耳聋症。此后他仍受宫廷垂青,并在那里待到1824年,这时他受政局动荡的骚扰而移居波尔多。
对戈雅影响最大的是1762—1767年间乔凡尼·巴蒂斯塔·提埃坡罗在马德里王宫天顶装饰画中所作的不朽的人物形象,提埃坡罗是威尼斯的最后一位绘画大师;此外还有委拉斯开兹肖像画中永恒的现实主义和伦勃朗在其肖像画中所表现的对人物心理的洞察力。
在戈雅为王室所作的肖像中,他率直地描绘画中人物在生理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弱点,这在许多年里使艺术史专家感到迷惑不解。但正是他在绘画与版画中所表现出的深刻的洞察力及他对世界的高度个人见解,使他置身在时代的浪漫主义激情之中。
在耳聩日甚之时,戈雅的画作也越来越倾向于表现他自己那个充满奇思异想、内在冲突以及人类苦难的内心世界。他对事物理解的广度与深度表现在他的版画中,在《奇想集》里,戈雅创作了一组版画,尖锐地鞭挞政治的阴险、教士的腐败以及西班牙社会的浮夸与伪善。他是最早把版画用于教化的重要艺术家之一,其感化力深刻之至。他的第二组版画叫《战争灾难》,其中记载了各种可怕的凶残暴行,从各种形式的拷打到绑在光秃的树干上的无头尸体都有,其详尽程度前所未有,这些暴行都是1808年拿破仑入侵西班牙以及后来约瑟夫·波拿巴统治时犯下的。


《战争灾难》是用凹版镂蚀的,这种方法在戈雅那里尤有特色。凹版镂蚀大概在一个世纪之前就由扬·凡·德·威尔德(Jan van de Velde)加以运用了,1760年则由让—巴蒂斯特·勒·普兰斯(Jean- Baptiste Le Prince)恢复使用。这种蚀刻方法可以取得精细的色彩变化与多变的物体纹路,造成各种黑色的戏剧性变化效果,而用传统的蚀刻方法是不可能取得的。自戈雅以来,还没有人能在凹版镂蚀的表现力、线条多变以及色彩精细方面超过他。
这样,就不奇怪,当第一个西班牙平版印刷厂1819年在马德里(不久后第二个又在巴塞罗那)建立时,戈雅也抓住机会学习平版画(或称石版画)的新技巧,他很快用这个方法制作了一套出色的版画。搬到波尔多之后,他又制作了另一套版画《波尔多的牛》,在艺术和技巧方面,这套画都标志着版画史上的新高度。
戈雅在绘画方面也显现出他对当时发生的事很敏感,时刻准备把这些事反映在他的作品中。比席里柯的《梅杜莎之筏》早四年,比德拉克洛瓦的《希俄斯屠杀》早七年,戈雅就画出了他对1808年斐迪南七世退位后法国入侵西班牙时屠杀五千名西班牙人的反响(《1808年5月3日》,作于1814年斐迪南七世返回西班牙之时)。
对这场悲剧,戈雅用直截了当的“报道体”(一种对事件进行准确而如实地处理的艺术形式)非常率直地表达出来。看不见脸面的士兵们像机器人似的执行杀人命令,把平民随便抓了来枪杀,以向任何想反抗波拿巴政权的人示戒(确有人在枪杀事件后试图反抗)。在一道斜坡前,一个通体照亮的人如同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正等候排枪发射。有一些人缩着身,遮起双眼不敢看,另一些人则倒毙在自己的血泊中。一切都用以表达那有计划的野蛮屠杀。
在戈雅有生之年,其天才并未为世界所充分认识。原因之一是他作为宫廷画家,生活与工作时都需十分小心,不能做出任何可能危及其地位的事。因此,他的许多以绘画形式发表的最有力的宣言,如《战争灾难》,只是在他死后才得以面世。另一个原因是西班牙孤立于欧洲其他部分的艺术影响之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法国占领西班牙的暴行而在他那里产生的人物形象,却在19世纪中叶的法国先锋派画家和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画家那里激起了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