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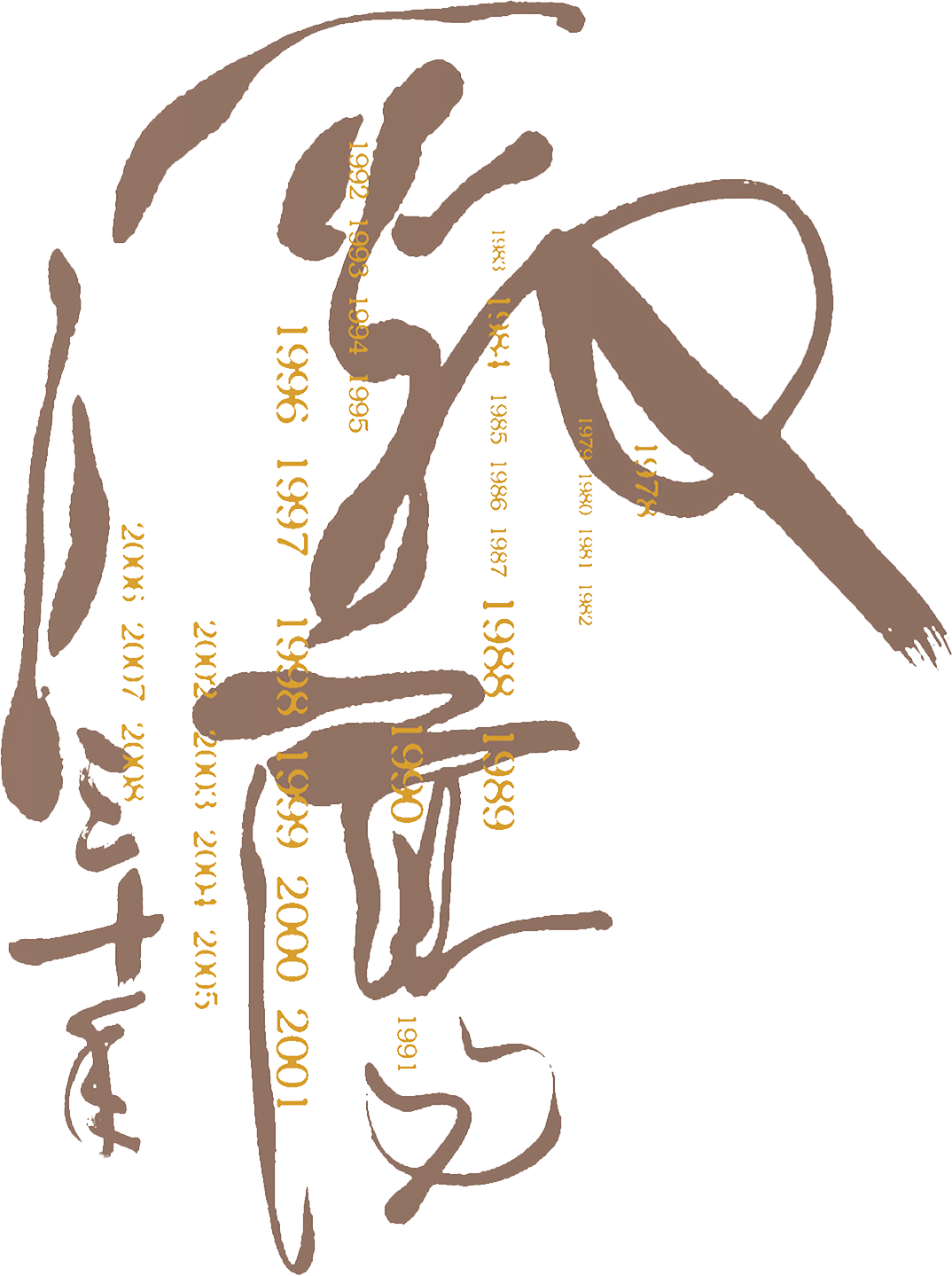
总序
1958年秋,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到河南检查工作。一日,他到南阳卧龙岗武侯祠游览,见殿门两旁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胡耀邦念罢此联后,对陪同人员说:“让我来改一改!”说完,他高声吟诵:“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
历史在此刻穿越。两代治国者对朝廷与忠臣、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进行了不同境界的解读。
中国是世界上文字记录最为完备的国家,也是人口最多、疆域最广、中央集权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如何长治久安,如何保持各个利益集团的均势,是历代治国者日日苦思之事。两千余年来,几乎所有的政治和经济变革均因此而生,而最终形成的制度模型也独步天下。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我将生命中最好的时间都投注于中国企业历史的梳理与创作。在2004年到2008年,我创作并出版《激荡三十年》上、下卷,随后在2009年出版《跌荡一百年》上、下卷,在2011年年底出版《浩荡两千年》,在2013年8月出版《历代经济变革得失》,由此,完成了从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到本轮经济改革的整体叙述。
2017年年底,我完成《激荡十年,水大鱼大》,又对刚刚过去的十年企业史进行了记录和不无偏见的解读,在这期间,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强大引起了普遍的惊叹和恐惧。
就在我进行着这一个漫长的写作过程之际,我们的国家一直处在重要的变革时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让它重新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同时,种种的社会矛盾又让每个阶层的人们都有莫名的焦虑感和“受伤感”。物质充足与精神空虚、经济繁华与贫富悬殊、社会重建与利益博弈,这是一个充满了无限希望和矛盾重重的国家,你无法“离开”,你必须直面。
如果把当代放入两千余年的历史之中进行考察,你会惊讶地发现,正在发生的一切,竟似曾相遇,每一次经济变法,每一个繁华盛世,每一回改朝换代,都可以进行前后的印证和逻辑推导。我们正穿行在一条“历史的三峡”中,它漫长而曲折,沿途风景壮美,险滩时时出现,过往的经验及教训都投影在我们的行动和抉择之中。
我试图从经济变革和企业变迁的角度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给予一种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一再地追问这些命题——中国的工商文明为什么早慧而晚熟?商人阶层在社会进步中到底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中国的政商关系为何如此僵硬而对立?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将以怎样的方式全面建成?
我的所有写作都是为了一一回答这些事关当代的问题。现在看来,它们有的已部分地找到了答案,有的则还在大雾中徘徊。费正清曾告诫他的学生说,“在中国的黄河上逆流行舟,你往往看到的是曲弯前行的船,而没有注意到那些在岸边拉纤的人们”。我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因此在我的著作中,有血肉、有悲喜的商业人物成了叙事的主角,在传统的中国史书上,他们从来都是被忽视和妖魔化的一群人。
即便走得再远,我对历史的所有好奇,也全部来自现今中国的困顿。因为我发现,中国的经济制度变革,若因循守旧,当然不行,而如果全盘照搬欧美,恐怕也难以成全,中国改革的全部难处和迷人之处,即在于此。所以,与历史修好,在过往的经验中寻找脉络,或许是解读和展望今日及未来中国的一条路径。能否在传统国情与普世规律之中探寻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实在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
我不能保证所有的叙述都是历史“唯一的真相”。所谓的“历史”,其实都是基于事实的“二次建构”,书写者在价值观的支配之下,对事实进行逻辑性的铺陈和编织。我所能保证的是创作的诚意。20世纪60年代的“受难者”顾准在自己的晚年笔记中写道:“我相信,人可以自己解决真善美的全部问题,哪一个问题的解决,也不需乞灵于上帝。”他因此进而说:“历史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就必须拒绝任何形式的先验论,必须承认一切社会或经济模式的演进,都是多种因素——包括必然和偶然——综合作用的产物。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任何一段历史,都是那个时期的国民的共同抉择。
是为总序。
吴晓波
2017年12月,杭州,大运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