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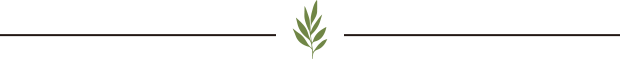
艾尔弗雷德·埃蒙德·布雷姆
1883—18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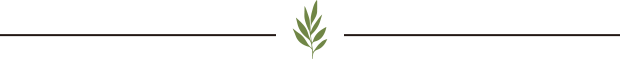
生物圈,是在任何给定时间地球上所有有机体的总和,是你在阅读这段文字时,地球上所有活生生的植物、动物、藻类、真菌和微生物的加和。
生物圈的上层界限由被风暴席卷到万米高空的细菌构成,其实际高度可能还要更高。在这一高度上的细菌物种占据了所有微观粒子的20%,其余都是没有生命的尘埃颗粒。有研究人员认为,其中一些细菌物种能通过光合作用和对死亡的有机物质进行分解,来实现物质的循环和个体繁殖。有关这种“高高在上”的生物层级能否被视为一个生态系统,目前尚没有定论。
生命的最底层界限,存在于科学家所称的深层生物圈的下部边界,即位于陆地和海洋之下至少3公里深的地方,细菌和线虫能在地球岩浆释放出来的强大热量中维持生存。目前,科学家在这炼狱般的地底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几类物种,可以依靠从身边岩石中提取的物质与能量来维持生存。
与庞大的地球整体相比,生物圈简直薄得像纸一样,重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生物圈像一层薄膜一样覆盖在地球表面,即使是在地球大气层外延轨道运行的飞行器上,如果不通过工具进行观测,都无法察觉到它们的存在。
人类自认为是生物圈的主宰,是生物进化的终极杰作,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力,可以为所欲为地对其他生命做任何事情。在地球上,“权力”就是人类的代名词。上帝对约伯设下的挑战,都不会令我们感到怯懦。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吗?
死亡的门曾向你显露吗?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
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若全知道,只管说吧!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谁为雨水分道?谁为雷电开路?
《圣经·约伯记》,钦定版

(38:16-19:25)
我们或多或少已经做到一些了。探险家下潜到海洋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之中,看到了鱼群和大量微生物。人们还完成了太空旅行,虽然这样做并没能让人们更接近不言不语的上帝。科学家和工程师向太空发射出太空舱和机器人,对太阳系中的其他行星和路过的小行星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将有能力探索其他星系,以及那些星系之中的星球。
然而,人类自身、人类的躯体依然像百万年前进化之初那样不堪一击。我们依然是有机体,完全依赖于其他有机体维持生存。借助生物圈中的其他有机体,人类便能生存于没有人工制品的环境中,但生物圈中可供我们利用的部分极其有限。
我们极端依赖于躯体,脆弱不堪,而且无人能幸免。我们都必须遵从军队在生存训练中提出的 “万事皆三”原则:没有空气能生存三分钟,冰点气温环境下没有住所和衣物能生存三小时,不喝水能生存三天,没有粮食能生存三周。
为什么人类会如此脆弱,如此强烈地依赖于外部条件呢?原因与生物圈中其他所有物种的脆弱性和依赖性如出一辙。就连老虎和鲸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都需要保护。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软肋,都受到“万事皆三”原则的限制。举个例子,如果你把一个湖泊的水质变酸,其中的某些物种就将消失,但也有一些物种会活下来。那些依靠灭绝物种维持生存的幸存者,大多都以灭绝物种为食或依靠灭绝物种而免遭捕猎者的攻击。这些幸存者将在不久之后消失殆尽。因物种间互动而引发的群体规模效应,被科学家称为“密度调节”(density-dependent)
 ,适用于所有生命。
,适用于所有生命。
密度调节的经典案例,是狼群在树木生长过程中发挥的促进作用。在黄石国家公园,只要某个区域内有一小群狼,就会极大地降低同一地区的驼鹿数量。一匹狼可以在一周之内吃完一只驼鹿(狼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将一顿饱餐消化掉),而一只驼鹿能在同一时间段吃掉大量的白杨幼苗。狼群作为顶级捕猎者,能将驼鹿从该区域吓跑。只要有狼在,被驼鹿吃掉的杨树苗就会减少,杨树林的密度就会增加。而当狼群离开后,驼鹿就会回来,杨树的生长速度也会大幅下降。
孟加拉孙德尔本斯国家公园中有一片红树林,在那里,老虎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那里的老虎以梅花鹿、野猪、猕猴以及人类作为捕猎对象,导致这些物种的种群数量不断减少,也由此促生了更加丰沛、更具生物多样性的动植物种群。
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整体,对生存于其间的每一个物种都具有保护作用,也包括人类。除了那些因人类行为导致灭绝的物种之外,倘若再有10%的物种、50%的物种,甚至90%的物种消失会发生什么事情? 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种消失或濒临灭绝,幸存者的灭绝速度也越来越快。 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效应会立即显现出来。一个世纪之前,曾经在北美洲东部随处可见的美洲栗树,因遭受来自亚洲的真菌疫情几近灭绝。7个飞蛾物种因其幼虫以美洲栗树的枝叶为食而消失,而最后一批旅鸽也随之灭绝。随着当地生物灭绝情况的加剧,生物多样性到达了一个临界点,至此,生态系统彻底瓦解。目前,关于这样的全球性大灾难何时以及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最有可能发生,科学家才刚刚开始展开研究。
真实的灾难性场景中,某个栖息地可能由于外来物种的侵入而被完全掠夺,这并非好莱坞剧本。每个进行生物多样性调查的国家都发现,殖民物种的数量在以指数级速度增长。其中一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有害,或对环境有害,抑或对两者皆有害。美国应颁布总统的行政命令,以明确政府政策,将这些物种界定为“入侵”物种。一小部分入侵物种就能造成巨大的破坏,还有可能诱发灾难性事件。其中一些物种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家喻户晓。在一张迅速拉长的“入侵”物种名单中,包括了外来火蚁(红火蚁)、亚洲白蚁(“吃掉新奥尔良的白蚁”)、吉普赛蛾(舞毒蛾)、翡翠榆树甲虫、斑马贻贝、亚洲鲤、蛇头鱼,以及两种蟒蛇和西尼罗河病毒。
在其原先居住的地区,入侵物种是作为生活了成千上万年的本土物种存在的。在自己的家园中,它们在自然条件下适应了其他本土物种,同时扮演着捕食者、猎物和竞争对手的角色,因此种群数量受到了控制。研究人员发现,入侵物种最能适应那些人类喜欢的环境,比如草地、河岸等。遍布美国南部、蜇伤疼痛难忍的外来火蚁作为入侵物种,在草地、住宅院落和道路旁最为活跃。而其南美洲的原驻物种则十分驯良,只在草原和冲积平原一带活动。
外来火蚁一直是我在野外考察和实验室中非常关注的研究对象。一次,为了拍摄一段影片,我将手伸进了火蚁巢穴。刚伸进去没几秒钟时间就被暴怒的工蚁蜇了54下。在接下来的24小时之内,每一个受到火蚁攻击的伤口都变成了又疼又痒的脓包。所以我建议:千万别将手伸到火蚁巢穴里,更不要坐在它们的巢穴上。
不被人类聚居地的规则所容纳的入侵物种,对自然环境而言,危害性尤其大。不起眼的火蚁比普通火蚁(我的另一个研究对象)的个头还要小,也是南美雨林的原生物种,但它能成群结队深入热带丛林,单枪匹马地灭掉几乎所有生活在落叶层和土壤中的无脊椎动物。
另一种可怕的栖息地破坏者是棕树蛇。这种蛇是在20世纪40年代被人们从新几内亚或所罗门群岛不小心带到关岛上的。棕树蛇尤其擅长捕食在树上筑巢的鸟类,因此,关岛上的7种鸣禽几乎被扫荡一空,幸存者屈指可数。
一些学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入侵物种最终会在当地安定下来,融入稳定的“新型生态体系”,但实际证据并不支持这样的说法。 应对生物界的混乱现象,唯一经实践证实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对大规模的保护区以及其中的本土生物多样性进行保护。
人类也受到物种相互依存的铁律的制约。我们并不是空降在伊甸园之中的成品入侵物种,也不是靠神明指引去主宰这个世界的统治者。生物圈并不属于我们,而我们属于生物圈。
围绕在我们身边的种类繁多、五彩斑斓的有机体,是自然选择通过38亿年的进化形成的产物。人类作为旧世界灵长类动物中的一个幸运物种,是自然选择演进至今的产物之一。而这一切从地质角度来看,不过是转瞬之间的事。我们的生理和思想都适应了存在于生物圈之内的生活。而关于生物圈,我们才刚刚开始了解。人类虽有能力保护其他生命,事实上却依然毫无顾忌地倾向于毁灭其中的很大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