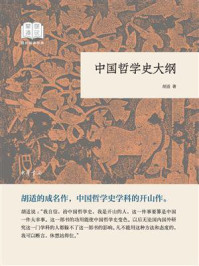庄子所关心的问题,乃是如何展现一己的真我。
然而,世俗人群,随波逐流,浑浑噩噩地混日子,其迷失真我固不用说;一般文化分子也在认知活动的过程中,溺于“成心”,卷入主观是非的争执漩涡里,而迷失了自我。于是庄子把笔尖转入认识的问题上,他的目的,在于指出百家认知活动之无意义、无效准。
首先,庄子指出物论起于“成心”,“成心”便是成见、偏见。他认为认识活动必然渗入主观成见,有了主观成见,就不可能得到客观的判准。“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这就是说,以自己的成见作标准,谁没有标准呢!显然,“成心”不足以作为判断真伪的标准。
“夫言非吹也”。前面说过,虽然“万窍怒号”犹如影射“百家争鸣”,但“地籁”无心而自鸣,人言则有意而争执。言论和风吹之所以不同,就在于言论发自于“成心”。发言的人须透过语言文字表达他的意见,而语言文字是否能和它所描述的对象产生一一对应的关系(one to one correspondence)呢?事实上,语言文字常带有人所赋与的目的性,因而人们一经使用语言文字,便渗入自己的意愿。这样一来,语言文字的功能又受了限制。许多的争论,并不是事实的争论(factual dispute),而仅仅是字面的争论(verbal dispute)或语言的争论(semantic dispute);文字的含混和歧义,常使它的意义失去了明确性,而引起许多无谓的争执,再加上发言的人各执己见,生是生非,所以大家议论纷纷,却得不出定论来。“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也就是说,由于每个人主观偏见的影响,因而无法对事实的真相作有效的判断。既然言论没有客观的实在性,那么众言喋喋,只不过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符号而已,这和小鸟叽叽喳喳的叫声有什么不同呢!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这里说到事物本然的情形是如何地被隐蔽,语言功能是如何地被误用,以至于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主观是非真伪的争论(《齐物论》中所说的“是非”,都是指主观性的争论,如“惹是生非”的“是非”);庄子指出事实全面的真相是被“小成”所隐蔽了,“小成”是局部性的成就,“小成”之人认识活动常被限制于片面的成就上,安于所见所得,对于系统外的东西不是茫然无知,便是采取排斥的态度。久而久之,心灵活动就被锁闭在局部的范围内,而永远无法了解事物最终的实在与全盘的真相。再说到语言符号,它的作用在于指涉对象的真况,即所谓“制名以指实”,然而使用者却常用来文饰,用来自圆其说。语言文字原本是中立性的符号,原来是超出主观是非的,却被有心人当成了巧辩的工具。以儒、墨的礼乐之辩为例,儒家视礼乐为“政治人情之大本”,礼以节欲饰情,乐以化性陶情,所以认为礼乐的效用足以维持人伦关系的和谐与发抒内心的柔美情感。墨家则站在社会功利的观点大加批评,特别针对儒家重丧礼一节,着力攻击,指责儒家“重为棺槨,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儒家重乐,墨家则以为“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这样的辩论可以发现几个问题:1. 双方并没有建立一个共同的标准,更没有在一个共同的前提下进行讨论。2. 即使在同一个论题下,各人也站在不同的角度而坚执己意。正如同瞎子摸象,仅仅依据自己所把握的一面去下判断,而不能作通盘观察,以求了解别方面的实况。3. 局部的认识,信以为真。于是认定同于己者为是,异于己者为非,由是产生排斥异己的思想:凡是对方所肯定的,尽加否定;凡是对方所否定的,尽加肯定。在态度上,成为牢不可破的武断。如何才能破除这种死结般的成见?如何才能解决这项认知活动的障蔽?庄子认为“莫若以明”。
各家囿于所见,以自己为价值核心,形成封闭的心灵,把精神困缚在狭窄的圈子里。“以明”是透过虚静的工夫,去除“成心”,扩展开放的心灵,使心灵达到空明的境地,一如明镜,可以如实地呈现外物的实况。因而,“以明”是指空灵明觉之心无所偏地去观照。
上面举儒、墨为例,说明“‘道’隐于小成”所产生的武断与排斥的态度,并提出破除主观是非争论的方法——“莫若以明”。下面再从事物的对待与转换,说明价值判断的相对性以及是非争论之无意义,并提出破除主观价值判断的方法——“照之于天”。
庄子的论点“物无非彼,物无非此”、“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是说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不因对待而形成的,有“彼”就有“此”,有“此”就有“彼”。“彼是方生”,就是“彼”、“此”并生(“彼”、“此”只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事实上举凡经验事物都是对待产生的)。一切事物都在对待的关系中,而一切事物又不断地流转,因而对待关系也不断地变换。“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正说明事物在倏忽起伏地变化发展着;“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说明了价值判断的流变无定。“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和“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对等语句,前者形容事象或存在物的变化不息,后者意指对事象或存在物所作的价值判断之无定性(“可”和“不可”是价值判断的字词)。在这种相因而旋转的情形下,是非判断,永无定准,“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各人由于角度、标准的不同以及所持的角度、标准本身的变动,因而产生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所以,庄子认为圣人不走是是非非的路子,“照之于天”。“天”是自然,“照之于天”,即是不投入是非争论的圈子里,撤除主观的成见,超拔于无穷相对的境地,而直接以明觉之心照见事物本真的情状。这也就是因任自然的道理(“亦因是也”)。
刚才说过“彼”、“此”是对待产生的,而对待关系又非恒定的,例如“我”和“他”是个对称,站在“我”的立场,我是“此”,他是“彼”;但是掉换过来,站在“他”的立场,他便成为他自己的“此”,我便成为他的“彼”了。所以可以说:“此”也就是“彼”,“彼”也就是“此”(“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对立的关系并不是永存的,而对立关系中所产生的无穷是非,乃是主观成心的设定,而非客观真实的存在。既然如此,我们的心灵应该超拔对立的关系(“莫得其偶”)。在这里,庄子再度提出“莫若以明”——打开封闭性的局限,从无穷的系统中深透到各个据点,了解其独特的内容;不以主观的成见去厘定是非,而以开放的心灵去照见事物的真相。
归结地说,庄子主张: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
其意为:以A譬喻A之不是非A,不如以非A譬喻A之不是非A,即是说,以“此”喻“此”之不同于“彼”,不如以“彼”去喻“此”之不同于“彼”。这话的意思是:以我来衡量他,不如以他来衡量我。由于争执的发生,常是从“我”的一方去断言,常是出于自我中心的观点。若能从他方看过来,许多争论也许不至于发生,因而在观点上不至于自我执着,在态度上不至于失之武断。但这不是庄子最后的主张,他最终的观点是:“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
庄子认为天地之大,无异一指;万物之多,无异一马。“一指”、“一马”,意指同一的概念,是针对杂多的概念而发的。杂多的概念都是人为设定的,天地万物本来无所谓“此”,亦无所谓“彼”;无所谓“美”,亦无所谓“丑”……这些纷杂的概念,都是人附加给事物的,附加上去以后,事物反而有被离裂的感觉。庄子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他说这话的目的,只在于弃差别而归同一,弃对立而求调和,弃分歧而归整体。
一切存在事物,它的本身事实上无所谓“可”,无所谓“不可”;无所谓“然”,无所谓“不然”。“可”或“不可”,“然”或“不然”,都是我们附加给事物的。事物的命名只是为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便,一切事物的名称和价值名词都是人为设定的,犹如道路是人走出来的(“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语言系统的设定和运用自然有一定的规律,也有充分的理由。然而由于人的主观成见渗入时,“名以指实”的作用就变质了,变成许多对立的判断,产生无穷的价值纠结。而人们就在种种的价值纠结中,沉溺于好恶爱憎的情绪漩涡里。事实上,一切纷纭杂乱的差别对立,都不是事物的本样,只是人为的结果。所以庄子说:“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恑憰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
“‘道’通为一”,这和“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意义是相对应的。其义为:
1. “‘道’通为一”,即是从“道”的观点看来并无分别。庄子认为事物的差别是人为设定的,同一件事物,由于不同的人作主观意识的投射,因而产生不同的性质差别。例如一棵树,它块然地存在着。同样的一棵树,有人说它高,有人说它矮;有人说它好看,有人说它不好看……其实,树本身无所谓“高”,也无所谓“矮”;无所谓“美”,也无所谓“丑”。所谓大小、高矮、长短、美丑的判断,都是人添加给事物的,它原本就是这个样子。所谓“一”,就是指事物的本然状态。但当它蒙上了人的主观认识活动,于是一如的、无分别的事物上,产生了分歧、多样相。
2. 主观的差别性渗入事物之后,人的心灵就被拘执、被“封”住了。被“封”住的心灵,只知拘泥于琐细,斤斤计较差别。我们须了解事物性质的差别,原来是主观意识的投射,原本是成心所致。这一反省觉悟,可使心灵活动致力于免除主观的偏执,照见事物本然的情形。“一”即是指破除封域而达到圆融和谐(comprehensive harmony)的境界。
3. “一”亦意指整体。任何事物都在不息的变化过程中,一件事物的分离消解,变迁为另一件新生事物的组成因素;新生事物的组成,就包含了原有事物的分离消解之因素。所以说:“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任何事物有分必有所成,有成必有所毁。好比砍树木做桌椅,对于树木来说则有所分,对于桌椅来说则有所成;桌椅虽成,对于树木则有所毁。若就树木与所成的器物来说,固然有分有成,固然在起生灭变化,但从通体看来,任何事物的生灭变化,不过是自然界全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部分,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所以说:“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复通为一”,即是说无论事物的分与成、成与毁,都复归于一个整体。
自然现象并没有所谓是非的问题,原本是同一的(质的同一),人类偏执成见,一味去区别,去争论。这里再度指责物论(人物之论)的弊端:本是同一的事物,却因“成心”作祟,“喜怒为用”,妄生许多是非。这里隐喻百家如同一群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的猴子一样,受了主观成见与情绪的左右,无谓争论,徒劳神明。庄子指出各家沉溺于是非争执的漩涡中,以至于劳形累心,疲困精神,迷失了真我。这样,还不如大家消除偏见,停止争辩,而保持事物自然均衡的状态,听任万物自然的演化。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这一段再度申论上面的意旨。庄子先将世界分成四个层次的演变:最初是一个整全无分的绝对境界,其次成为“有物”的境况,再次产生对立存在的世界,最后由于人的意识之投入,而成为纷杂的价值纠结的世界。其重点即落在这四个层次上的批评。他说:“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是非的造作,反而把存有的真相隐蔽了;存有真相的隐蔽,乃是由于主观情绪与成见所致。接着,庄子举昭文的鼓琴为例,他说:“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郭象注说:“夫声不可胜举也。故吹管操弦,虽有繁手,遗声多矣。而执籥鸣弦者,欲以彰声也,彰声而声遗,不彰声而声全。故欲成而亏之者,昭文之鼓琴也;不成而无亏者,昭文之不鼓琴也。”这是说,无论多大的管弦乐团,总不能同时把所有的音符全部奏出来,一定有许多音符被遗漏的。就奏出来的音符来说,固然是有所成;但就遗漏的音符来说,则有所亏了。所以一鼓琴就有成有亏,不鼓琴反而无成无亏。庄子的意思是指出昭文精于鼓琴,在广大的音乐世界中,只算是“小成”。昭文、师旷、惠子三人的技艺固然专精,但都是小成之人(即《天下》篇所说的“一曲之士”)。小成之人沉湎于他所成就的一面,而昧于世界人生其他广阔的天地,就像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书上所说的水蛭专家一样——“水蛭的脑子,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得清楚一件事,其他的一切都不知道。”在这里,庄子一再指出小成者领域的狭窄,心里被拘限于偏颇的范围,而得不到精神的大解放、大自由。
庄子的目的,在于破除小成与小成之间的封闭性,培养广大的开放精神;并图消解小成与小成之间的冲突(相非),培养广大的受容精神。本段最后又归结到“以明”的方法——使相对者互明;并以无所碍的空灵明觉之心,遍照存有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