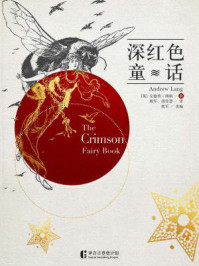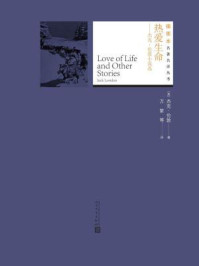我搂紧婴儿,坐进摇椅里,轻声哼着永远永远不会再撇下她。她真的开始哭了,愤怒而且狂躁,她抓住我的一缕头发使劲地扯,不停地闹,哭得自己气喘吁吁。我抱着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转悠,我好像听见格雷汉姆家妮娜·西蒙妮低吟浅唱的声音:“我对你施了魔咒。”他开得声音比以往都大。
难道是我的幻觉?
他是想压过我宝宝愤愤不平的哭声呢,还是在向我表明心意?我似乎看见格雷汉姆此时赤裸着身体琢磨着我刚到就离开的原因。
他在自己的家里,脱掉了背心,解开了裤子的拉链,接下来会做什么呢?他会打电话叫一个女朋友来填补空白吗?我强迫自己不去想,不去想漂亮的金发碧眼的女郎代替我躺在没有收拾过的床上。格雷汉姆无视这个改变,只在乎抚摸他的一双女人的手。我要把这个遐想从脑子里赶出去:如果不是为了婴儿,我会做什么,我会走多远?
不会的,我提醒自己。婴儿睡着了。是她吗?我突然惊愕地发现自己是那么无可救药地在意她的哭声,绝望的、无助的、彻底被遗弃的哭声,就像我在格雷汉姆家听到的一样。那个哭声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声音伴着画面:格雷汉姆脱掉背心,露出三角肌和腹肌,柔密的金发,以及牛仔裤上的铜扣。
婴儿真的哭了,我对自己说。她没睡。
我来回地摇晃她,像跷跷板似的上下慢慢地颠她,尝试各种方法安抚她。她嫌我丢下她不管。我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妈妈再也不会扔下你了,再也不会了。”我深深地吻她,徒劳地表达着我的歉意。
我告诉自己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妈妈不会把她一个人留下,自己出门。我想应该是一时的疏忽。蓦然间,克里斯遗忘在口袋里的避孕套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子里,一想起这事,那个闪亮的蓝色包装瞬间让我坠入深渊,心慌,手软。
露比的鼻子在黑裙子上的褶皱里蹭来蹭去,她总是这样,只要饿了就这样。我走进厨房,把配方奶倒进奶瓶,加上水,摇匀,假冒妈妈应该给她的食物。我使劲地回忆当时为什么用奶粉喂我的孩子,为什么不坚持母乳了。我喂过她母乳吗?我发现,站在厨房里,我回忆不起来。癌症,我对自己说。然而我又想,癌症?
或者癌症只是我的臆想,可是我想起腹部的那道线,格雷汉姆用指尖滑过的那道痕迹。他刚要问出口的时候,我把手指放在唇边,嘘——它是怎么来的?疤痕,它到底是不是刀疤?
这时一个词从脑袋里冒出来,丑陋,邪恶,我快速地摇头要把它甩出去。
流产。不可能。我搂紧婴儿,我知道那不是真的。
那个秃头的医生说,她,我的朱丽叶,已经被当作医学废物丢弃了。他说医学废物被带出医院焚化了。我终年无眠的夜晚总靠想象陪伴,或者睡着时的梦境总被恐怖填满:宝贝朱丽叶在2000度的炉子里,像搅拌机里的水泥一样翻滚着,她的每一个部分都暴露在烈焰之中,她幼小的灵魂化作气体融入空气里。
我疯狂地摇头,大声地喊叫:“不。”
我低头看了一眼怀里的婴儿,想:朱丽叶在这儿,她平安无事。
我接着想,也许是胎记,我肚子上的痕迹和我宝贝腿上的痕迹一样。这种东西遗传吗?我回忆起昨天,在去卢普区和克里斯吃午饭的路上,在L线列车上,路人称赞我可爱的孩子,他们说我们长得太像了。世界上每个妈妈都渴望听到这些话。一个说她的眼睛和你一模一样;另一个说,她笑起来和你一样。他们说他们的,我用手指滑过她弯弯的上唇,中间V形的凸起就是人们说的丘比特之弓。
就像佐伊那样,就像我这样。
“家族遗传。”我说,我的宝贝恰到好处地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像她一直知道自己就是大家谈论的对象,是大家注意的对象,所有人都在向她眉目传情。
她是我的,我这样想着,把她搂紧了,不去想杨柳,把露比的名字从脑子里赶出去。全是我的。
门铃响了,打断了我的思绪;声音很大,非常无礼。我把假母乳喂进我孩子的嘴里,不知道是奶的问题还是门铃的吵闹,我真不知道,总之婴儿用舌头把瓶子推出来,继续哭闹。
我走到窗边往外看,是詹妮弗,我最好的朋友詹妮弗,她手拿一杯星巴克咖啡站在玻璃门前。穿着医院的工作服和牛仔夹克,头发在芝加哥永不停息的风中乱舞。我嗖地一下蹲下去,不能让她看见我站在飘窗前,我希望她能离开。我现在不能见她。她肯定盯着我的裙子看,肯定会发现我系错位的扣子和深色的眼妆,现在它们毅然决然地流到了我的脸上。粉色的内裤和丝袜被揉成球,黑皮鞋又徒劳无功地回到了鞋盒子里。
她一定想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她会问起格雷汉姆,她会问起我的宝贝。我怎么说?我怎么解释?
门铃又嗡嗡地响起来,我跪着抱起嗷嗷叫的婴儿,从窗口偷偷地往外看。詹妮弗用手背遮挡着阳光抬头望着我家的窗户,我再一次趴下,不知道她到底看见我没有,然后我又往下瞄了一眼。我们躲在六十多厘米宽的窗下的时候,我险些把婴儿掉到地上。“嘘,”我用和她差不多的绝望求她,“嘘,别哭了。”我的膝盖开始疼。
我的电话响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是詹妮弗,她要知道我在哪儿?如果她打到办公室找我,肯定有人告诉她我病了。达纳,优秀的前台,告诉她我得了顽固的流感,我最好的朋友带着咖啡,也许是格雷伯爵茶,过来探望。而我却对她避而远之,跪在木地板上乞求孩子安静,不要出声。
电话不响了,门禁不响了,除了婴儿都安静了。我谨慎地站起来,看不见詹妮弗了,一分钟,两分钟。我在整个小区里搜寻淡色薄斜纹布的夹克,只看到邻居老太太拉着空购物车从楼门里走出来,奔向杂货店。
我长出一口气,确定脱身。我继续恳求我的宝贝喝奶,小心翼翼地把瓶子放在她的舌头上,盼着她喝。“喝吧,宝贝。”我说。我还没说出口就听见敲门声,我顿时魂飞魄散。詹妮弗,肯定是,格林老夫人出门去杂货店的时候,她端着星巴克的杯子顺势溜进来了。
“海蒂。”她说,然后又敲门——该死的,当、当、当——这声音比任何言语都更响亮。她知道我在。
“海蒂!”她又喊一声,我抱着婴儿迅速跑进屋里,跑到离门最远的地方。我猜我们是被一氧化碳拖累了,必须找个能呼吸的地方。我缩在卧室的墙角里。詹妮弗的声音从远处传来,小了一些。我把百叶窗调到冲上开,这样下面街道上的行人就不会看见了,不过,我确实听见她站在走廊里嘟囔着“我看见你了”和“我知道你在”,不停地拍打木门以引起我的注意。
他们会带走我的宝贝。他们会把宝贝从我身边带走。我乞求着:“求你了,朱丽叶,求你安静一下。”她不喝奶还不停地哭,让我惊慌失措。那个名字——朱丽叶——我脱口而出,是个十足的错误同时又是绝对的正确。哭声没有终止。婴儿佐伊又回来了,她得疝气的时候,大喊大叫,疼得打滚。但是带着佐伊的时候,我不需要躲闪,不需要蹲在卧室的地板上藏起来。
我不知道我们等了多久。一分钟,还是一小时,我说不清,我就是无声地贴着她,求她别哭了。詹妮弗敲门的声音越来越小,终于彻底消失了。电话铃声响了,停了,又响,又停,座机响了,手机也响了。
我从卧室的窗户隔着斜向上方的百叶窗看见詹妮弗的身影,她魂不守舍地在马路上转圈。她抬头看,对着我家客厅的窗户出神。她走了,把一个星巴克的杯子扔进了最近的垃圾桶。我从卧室出来,找到手机,它在门口,詹妮弗肯定听见了。手机上三个未接电话,一个语言邮件,一条短信。
“你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