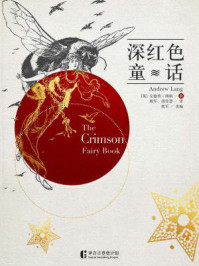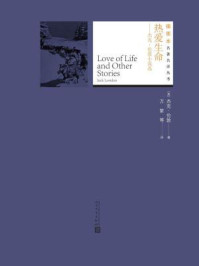我终于找到机会和海蒂谈谈了,婴儿还在没完没了地抽泣。我问海蒂怎么回事,她只是说:“是药效上来了。”她一直抱着孩子摇来摇去,想要安抚她,让她安静下来,连说话的时候都有些气喘吁吁。
“发烧?”我问,然后继续在我的电脑上打字:此处所指的证券投资是高风险……我没继续听,她接着说发烧不是什么坏事——她脱口而出的数字对我没有意义,即使我的命在那些数字里,我也不会多想的——然后喋喋不休地讲她们去湖景区诊所看病的事。
“找佐伊看病的医生。”我提醒她。
打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地解决这些麻烦了。
但是她说:“现在不行,克里斯。”她突然闭嘴,她不想听我唠叨。她知道我会说那个女孩,我会觉得她疯了才留女孩在家里住,我们三个人已经够挤的了,更别说五个了,还有如果事情败露,我们都会进监狱的。
股权分割没有……
她告诉我带婴儿去湖景区诊所看的是家庭医生。为了避免多余的询问,她们说孩子是海蒂的。我于是想象着海蒂在这个岁数有个婴儿的情景。海蒂真的没老到不可以有孩子,但是我们已经对尿片、奶瓶什么的太陌生了。
显然,孩子是谁的并不重要。当她们站在诊室里,心急如焚地想要一剂神药治愈孩子的时候,医生关注的只有孩子的高热。
我从她的声音里听出疲惫。我满脑子都是她:乱糟糟的头发,可能一整天都没洗澡了,头发一缕一缕的,像意大利面,她不好好洗头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棕色的眼睛透着疲惫和烦躁,眼袋浮肿。我看出来她有点儿手忙脚乱,我们说话的时候,她把一听汽水放在灶台的边缘,不巧汽水却掉了下去。
黏糊糊的棕色液体砰的一声喷出来,涌到实木地板上。
“混蛋!”她骂道。她从来不说粗口的。我看见她趴下,用纸巾擦地。头发糊在她的脸上,她吐口气吹开。她实在是太狼狈了,绝对需要洗澡睡个好觉。她的眼神游离不定,脑子里有千万个想法在横冲直撞。
这种现况已经伤害到我的妻子了。
海蒂说前几天她坚持给婴儿的屁股涂抹润肤乳很有成效,医生几乎没提湿疹的问题。在排除了所有发烧的病因之后,医生用导管抽取尿样进行化验才知道原来是尿道感染。
“她怎么得的这个病?”我问。想起她每次小便时的灼烧感和导管穿进她稚嫩的膀胱时的感觉,我不禁愁眉苦脸。
“不讲卫生。”她简单地回答。我想起来婴儿沾满污物的尿片,老天知道她用了多久。排泄物里的细菌侵入了膀胱和肾脏,导致了感染。
医生给婴儿开了抗生素,要求妈妈从前往后地给她擦屁股。这是佐伊戴尿片的时候海蒂对我反复强调的命令。我的脑子里出现杨柳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画面,她习惯对着电视发呆。她不到十八岁,我提醒自己,她是个需要提醒才记得洗手的小孩子。要提醒她吃蔬菜、叠床。提醒她从前往后地给她的孩子擦屁股。
我一直在等马丁·米勒,那个私人侦探的回信。虽然我在网上已经无计可施,但还是绞尽脑汁地想推进一下,希望能给他提供一些线索。我想要一张杨柳·格里尔的照片,但是我既不期望杨柳同意让我给她照相,也不期望海蒂说声“可以”。我在琢磨那只棕色的破皮箱,她离开房间的时候把它塞到沙发床下面,以为这样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了。我想打开它一探究竟,也许能发现点什么,随便什么信息,比如驾照、身份证,或者有通话记录的手机。
马丁建议我收集指纹,从玻璃杯、遥控器或者其他她动过的东西上提取,这样可以证明她真实的身份。他指导我如何保存杨柳·格里尔的指纹,然后寄到他的实验室。
但是这些都要等我出差回来才行。
我收到了W.格里尔的回复,确认她已经死了。是自杀,她说到做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不过,也许她蛰伏在芝加哥的某个公寓里,希望全世界相信她死了。我怎么知道?只能是每天看一下,以防万一。
“她对她的胎记很感兴趣,”海蒂的话打断了我的思路。
“谁?”
“医生。”
“婴儿的胎记?”我问。我想起海蒂给她垫着蓝浴巾擦身体的时候,我在她的腿后面看见过一块。
“是,”她说,“据说那个叫葡萄酒色痣。”我想象着一杯葡萄酒洒在她腿后的样子。她说起血管胎记和毛细血管扩张,还说婴儿皮下血管扩张。按照医生的建议,她对我说我们应该考虑激光切除。她这样说好像这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我们,她和我,好像我们在谈论的是自己的孩子。
我仿佛看见我的妻子,散着意大利面似的头发,睁着疲惫的双眼,面无表情地对着电话说:“医生说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会为此而自卑。趁婴儿的血管还比较细小,治疗更容易些。”
我没说话。我无言以对。我张开嘴,又闭上。因为实在没什么好说的,我问:“佐伊怎么样?”海蒂回答:“挺好的。”
对于胎记,我只字未提。
我们的对话从胎记转到天气,海蒂的声音听上去有气无力,已经到了极限,就像弹簧玩具一样,拉开太大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了。我差一点儿就心生愧疚了,差一点儿。
当时我的记忆飘回到我和海蒂没有孩子之前的日子里——在佐伊之前,在她不愿意承认的严重地毁了她生活的流产之前——每周六晚上,在我们以前住的公寓里,我们会一步两级地从楼梯爬上楼顶的平台,观看海军码头的烟花。我怀念我们坐在一起的时候,坐在一条长凳上,喝同一瓶啤酒,注视着城市的风景。那时我们有那么多的愿望:环球旅行,到处观光,一起参加三项全能竞赛。当我们有了一个孩子的时候所有的计划都泡汤了。我从来不想过这样的夫妻生活,不想两个人被各自的理想和共同的孩子折磨得精疲力尽,这种生活应该被看似更有意义的生活所摒弃、所掩盖、所代替。
我渴望婚姻让海蒂和我成为队友。但是最近我感觉我们好像是对手,打比赛的对手。在女孩和婴儿的乱麻里我开始烦她。
然而,再想想她疲惫的眼神和意大利面似的头发,我对自己说这是她的一贯作风。
无论如何,我总忘不掉那张字条,那张装在我的公文包里只写着一个“是”字的字条。我在机场把它掏出来,拿到飞机上。到了纽约,在市中心的豪华酒店办入住的时候我把它掏出来。在前台和卡西迪、汤姆、亨利分手各奔房间的时候,我又把它掏出来。我的房间富丽堂皇,我坐在整洁的白床单上掏出字条,拿在手里。我不知不觉地开始研究这张字条的细节。她哪来的紫色便签纸?她的字迹潦草,是因为紧张吗?还是因为婴儿的吵闹时间仓促?还是她的书写本来就比我的还糟?
我在琢磨她写字条的时间:是她听见关门的声音,在佐伊的呼吸变得沉稳,我们刚睡觉的时候?还是半夜,被人虐待的记忆像瘟疫般缠着她,让她整夜辗转反侧无法入睡的时候?再或者是凌晨,她听见我的闹钟响,趁我洗澡的时候蹑手蹑脚地到门口打开了我的公文包,然后返回屋里。
谁知道呢?
现在,过了一天,会议结束后我约汤姆、亨利和卡西迪二十分钟后在酒店的酒吧见。我在犹豫要不要告诉海蒂字条的事。但是告诉她有什么好处呢?只会让她更跟着感觉走。有证据表明女孩受虐——只是她承认了——足以让海蒂提出收留她,永远的,就像那两只可恶的猫一样。
有人敲门。我掩盖不了这个声音,所以对着电话大声喊道:“谁?”然后我撒谎说是“服务生”。我不能承认是卡西迪过来校对募股说明书——我们要卖的公司概况和资产分析——晚些时候,我们一起去酒吧。
我从床边往门口走,举着电话告诉海蒂我叫了客房服务。然后说我今晚要熬夜完成上周末就该完成的募股说明书。我点了鸡肉三明治和乳酪蛋糕。如果能按时完工,我可能会看小熊队的决赛。
我打开门,果然不出所料,卡西迪站在门口。她涂着鲜红的口红,让我除了她的嘴唇什么也想不起来了。
我竖起一根手指放到嘴边,轻轻地嘘了一下。
接着,为了让海蒂听见,我提高嗓门说:“你带番茄酱了吗?”然后看着卡西迪忍俊不禁的样子。
我感谢虚构的客房服务员,砰地关上门。海蒂让我挂上电话趁热去吃饭,我觉得自己真该下地狱。
“爱你。”我说。海蒂说:“我也爱你。”
我把手机扔到床上。
我看见卡西迪气鼓鼓地走进来,就跟这是她的房间似的。没等我邀请就毫不犹豫地跟进来,一点儿都不像往常的她。
她换了衣服。只有卡西迪会为了一杯睡前酒特意换套衣服。她用无袖修身的铁红色希腊裙装换掉了黑色正装。她坐到黄色的矮沙发上,跷起二郎腿,先问了募股说明书的情况,接着问起海蒂。
“她很好,”我说着打开电脑上的募股说明书,我把电脑递给卡西迪的时候小心地避免碰到她的手。“是的,她很好。”
在我准备说第三次的时候,我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我强迫自己盯着她的眼睛,而不是她的大腿、嘴唇或者铁红色裙子里的胸脯。不大,但是也不小,在她柔和的曲线上恰到好处。太大会影响整体的美丽。我站在浴室门口,看着黑色水盆上摆着的酒店用品——洗发水、护发素、浴液、肥皂——想她会显得不成比例。我拆开肥皂洗脸,冰冷的水扑在脸上抑制住我对她胸部的遐想。
还有她的长腿。
她的嘴唇,红唇,辣椒的颜色。
不一会儿她在隔壁叫我,我用毛巾擦干脸,从浴室出来。坐到她旁边的另一个黄色矮沙发上,然后把沙发拉到圆桌旁边。
我们过了一遍募股说明书。我把精力集中在“股份”“股票”和“每股资产净值”等字眼上,而不去关注划过屏幕的芊芊玉手和在我的腿边蹭来晃去的铁红色裙边。
看完之后,我们坐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们并排站在一起,卡西迪斜着身子向我靠过来,嘲笑一个和我们一起下楼的带着劣质假发的男人。她仰着脖子大笑的时候,用手指甲掐着我的前臂。
我想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们:我戴着结婚戒指,她没有。
他们会把我们当成来纽约出差的同事,还是其他的关系——奸夫淫妇?
在酒店的酒吧里,我拽过一把钢制的吧椅,这样卡西迪只能和汤姆还有亨利一起坐在矮沙发上。我们喝酒,喝了太多。我们聊天,讲八卦新闻;拿同事和客户开心,太轻松了;讽刺伴侣,然后谁的妻子成为笑柄,谁就要被取笑。
卡西迪呡了一口曼哈顿,在鸡尾酒的杯口印下宝石红的唇印,她说:“看见了吗,先生们,这就是我不结婚的原因。”我不知道她说的“看见”指什么,是她不愿意被取笑,还是不愿意取笑她发誓深爱的伴侣?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疾病还是健康,永远永远……
或许是一夫一妻制让她却步。
后来,在厕所里,喝得酩酊大醉的亨利递给我一个避孕套。“以备不时之需。”他说,然后放荡地大笑起来。这是亨利·汤姆林特有的黄色幽默。
“我觉得我和海蒂不用避孕。”我说。但我还是接过来,并且装进裤兜,因为我不想表现得很无礼,也不想把它扔在马桶里。
亨利靠近我,喷着浓烈的老田纳西杰克丹尼威士忌的酒味,露出粗鄙的本来面目,嘟囔着:“我不是说海蒂。”然后冲我眨眨眼。
我们忘了时间。汤姆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给我和他自己点了比尔森啤酒,给亨利点的还是杰克丹尼,给卡西迪的是阿拉巴马监狱。卡西迪把鸡尾酒里的水果拣出来——橘子和马拉斯金樱桃——先吃掉。酒保宣布:“打烊了。”
这时,我也把手机忘得一干二净,它还在床上,被压在白床单的褶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