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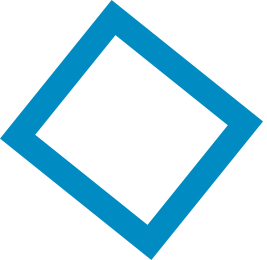
皮埃尔·阿多:我母亲是洛林人的女儿,1871年,当阿尔萨斯与洛林合并时,她父亲选择拒绝归入德国。他在兰斯找到一份工作,在一个乡下人家里做酒窖管理工。在我的孩提时代,1930年前后,我们每年都去洛林度假,洛林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重新归属法国。我的表亲们住在临近德国边境的法国小村庄或者小市镇里,离萨尔格米讷和萨拉尔布不远。当地许多人不讲法文,而是讲一种德国的方言。比如说,在那边的火车站,给旅客看的所有指南都是用德文写的。此外,当地的神甫们也都用上流的德文布道,他们并不掩饰对世俗化的法国的敌意,而孩子们在教堂里也用德文做祈祷。在那里严守天主教的教规。我在孩提时代穿短裤都有伤风化。和我同龄的男孩子们都穿着长过膝盖的短裤来遮掩他们的“肉棒儿”,布利斯布吕克的神甫常常这样说道。神甫们幸亏有梵蒂冈协议的资助,在一战后的法国,又由阿尔萨斯-洛林省供养,因而在他们的教区里做绝对的主人。比如,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泽汀的神甫曾拒绝给我堂妹做领圣体的仪式,根据一战后的风尚,他们给她剪了短发,在其他的信徒面前用这种方式羞辱她。
因此,我很早就遇到法国与德国之间的复杂关系的问题,当我童年时代在洛林度假时,也通过祖父和父母讲故事的途径了解。1914年,我父母不得不逃离兰斯市,最终到巴黎避难,我1922年出生在巴黎。在我出生的一个月后,他们便返回兰斯,回到那座被轰炸得几乎面目全非的城市。城中的大教堂要花二十年修复,等到1939年才重新启用……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从1922年到1945年间,我生活在兰斯,我一直爱着那座令人愉快的小城,它因大教堂与香槟而闻名。
说起洛林,我总是被内陆省份的法国人对当时一半属于法国但又讲德语的地区(所谓洛林人)的某种无知而惹恼。在二战初期,1939年,洛林的居民全部被疏散。我的一个表兄曾特别偷偷地回到他的村庄,发现他的家里被洗劫一空:有人甚至愚蠢地把一些猪关在大衣柜里。法国人看到德语的碑文,还以为到了德国境内呢。
总的来说,许多法国人对德国现实的无知让我愤慨。比如说,我想到相当戏剧化的一桩事件,发生在七十年代左右。一位年轻的德国教授曾被邀请到巴黎做讲座。值此之际,他遇见一位法国教授,史学家、犹太裔,其父母双亲在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中丧生。这位法国学者拒绝与他的德国同行握手。但那位德国教授告诉我,他也经历过可怕的痛苦,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位共产党员,也死在集中营里。为什么这位法国教授会用刻板而盲目的态度对待别人,却不知道或者说不想知道,在对立的阵营里,也可能有人会和他经历过同样的痛苦呢?但我想,关于这个话题,阿尔弗雷德·格罗塞(Alfred Grosset)在那本令人钦佩的著作《罪行与回忆》( Le Crime et la Mémoire )里已经都谈过,他讲到了一些知识分子“公开表示的不想知道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