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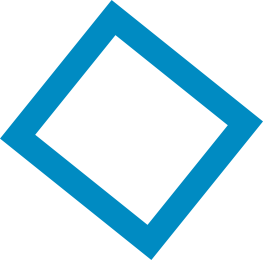
皮埃尔·阿多:我想,这里有一个历史问题。在我看来,在十六、十七世纪,在胡安·德·拉·克鲁斯的时代,或者随后在费纳隆(Fénelon)的时代,人们非常注重神秘主义现象以及从新柏拉图主义继承而来的古典路径:炼狱之道,启示之道,冥契之道。后来,人们心态发生了转变,但我并不了解个中理由。无论如何,人们完全不鼓励抵达神秘主义的体验,因为,归根结底,人们认为这关涉的是完全例外的一些现象。关键在于履行义务。不管怎样,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体验是一种神圣的恩赐,不能仅仅通过人类的力量抵及,人们认为,依据上帝的旨意,上帝本人负责赐予这种神恩。
无论如何,我从来没有体会到基督教意义上的神秘主义的体验,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的地方,但我有一种大动感情的恻隐之心。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所谓圣周,我用一种强烈的方式参与基督受难的痛苦,乃至于到了圣周的礼拜六或者复活节的礼拜日,我仿佛有一种真正的释放。在圣周从礼拜四到礼拜五的夜间,人们轮流守夜祈祷,我尝试着参与基督临终末日的仪式。我恰恰是在帕斯卡尔的作品里读到基督直到世界末日都处在缓慢垂危的过程中,而在这个时段里,世人不应当沉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