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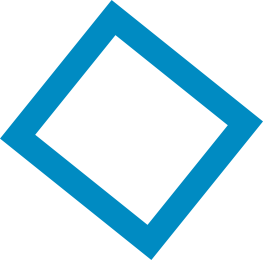
 那样最枯燥的哲学家的作品中,均反复出现。说到底,这难道不是与古代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断裂吗?
那样最枯燥的哲学家的作品中,均反复出现。说到底,这难道不是与古代之间的一种强烈的断裂吗?
皮埃尔·阿多:我要捍卫罗曼·罗兰所使用的“海洋般的情感”这一表述,由此出发,我甚至要把这种体验与我提到的在自然面前的心醉神迷的体验加以区分。在讲到“海洋般的情感”时,罗曼·罗兰希望表达一种非常特殊的细微差别,即犹如在无垠的海洋中的一朵浪花的感觉,作为神秘、无限的现实的一部分的感觉。米歇尔·于兰在他令人敬佩的著作《野性的神秘主义》(对他而言,野性的神秘主义只不过是海洋般的情感)中,用“在此时此地、以强烈的方式存在着的在世界之中在场的情感”来标志这种体验,他也讲到“在我自身与周遭世界之间的本质性的共属关系(co-appartenance)” [1] 。
面对自然的情愫,在《福音书》里也有。耶稣讲到开满百合花的田野的华美光彩。但我要说,如我前面提起的海洋般的情感与对自然的情愫不同,这与基督教完全陌异,因为在其中没有上帝或者基督的介入。这属于存在的纯粹情感的层面。我不确定古希腊人是否了解这种体验。如果您说,他们有过对自然的情愫,并且这种情感达到顶点,那么,您是有道理的,但他们只是很少讲到沉浸在作为整体的宇宙中的情感。在塞内加 [2] 的作品里,有一句话这样结尾,“toti se inserens mundo”(“沉浸在世界的整体之中”),讲的是完美的灵魂。此外,也不能断定这与我们在这里讲到的体验相吻合。吕克拉斯讲到(Ⅲ,29),当他想到无限的空间时,会有颤栗与神圣的快感攫住他的身心,他也许联想到这种体验。在文学中缺少相关的例证,但并不意味着这种体验缺席,我们只是限于对这方面的无知。
无论如何,这种体验并没有什么特殊。各种类型的作家都有过影射,比如,于连·格林(Julien Green)的《日记》(
Journal
),阿瑟·库斯勒(Althur Koestler)的《零度与无限》(
Le Zéro et l'Infini
),米歇尔·波拉克(Michel Polac)的《日记》(
Journal
),雅克琳娜·德·罗米莉(Jacqueline de Romilly)的《通向圣维克多的路上》(
Sur les Chemins de Sainte-Victoire
),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Les Frères Karamazov
),也许还有卢梭的《孤独散步者的遐想》(
Les Rêveries du Promeneur Solitaire
)(第五章)。可以有一长串的名单,在此仅列举几个书名。在其他的文化中,我们也可以找到类似的体验,比如在印度文化[《罗摩克里希纳福音书》(
Ramakrishna
)
 ]或者中国文化里:我们在中国思想或绘画里可以推测出来。
]或者中国文化里:我们在中国思想或绘画里可以推测出来。
[1] 米歇尔·于兰,《野性的神秘主义》( La Mystique sauvage ),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批评视野”丛书,1993年,第56—57页。
[2] 《道德书简》( Lettres à Lucilius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