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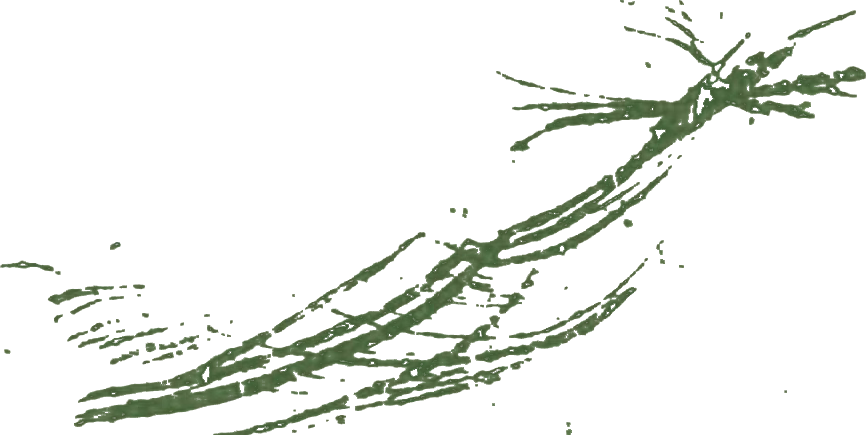
罗曼·罗兰创作《约翰·克里斯托夫》的时候,以音乐家贝多芬为蓝本,贝多芬通过痛苦争取欢乐的一生,对后人具有鼓舞斗志的作用。
傅雷在《译者弁言》中说:“这部书既不是小说,也不是诗,据作者的自白,说它有如一条河。莱茵这条横贯欧洲的巨流是全书的象征。”所以傅雷译文的第一句是:“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有一个读者说:“罗曼·罗兰的四大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二十多年前我曾阅读过,许多情节都淡忘了,但书中开头的‘江声浩荡’四个字仍镌刻在心中。这四个字有一种气势,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正好和书中的气势相吻合。”由此可见,傅雷的译本既得作者之心,又得到读者的共鸣,可以说是一本名著名译。这就是说,译者和读者都可以在书中读到自己,发现自己,检验自己。
这部名译是不是可以重译呢?傅雷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说道:“我们在翻译的时候,通常是胆子太小,迁就原文字面、原文句法的时候太多。”这句话一语中的,所以傅雷在译这部书的时候,尽量不受原文字面拘束。如第一句的原文和英译是:
1. Le grondement du fleuve monte derrière la maison.
2. From behind the house rises the murmuring of the river.
原文grondement(沉闷的隆隆声)译成英文可以用roaring(咆哮)或murmuring(潺潺声,低语声)。这里英译本采用了低沉的潺潺声,傅译本却用了高于沉闷的隆隆声而低于咆哮的“浩荡”二字。从这个词在句中的意义来说,既可以译成咆哮,也可以译成潺潺声。但从整段看来,下面接着写蒙蒙的雾气,涓涓流下的雨水,昏黄的天色,闷热的天气,可能“潺潺声”比“咆哮声”更加协调,因此英译本选用了“潺潺”。但从全书来看,“江声浩荡”具有一种排山倒海的力量,象征了横贯欧洲的巨流,有的读者甚至认为成了“一句话的经典”,那简直可以算是胜过原作的译文了。所以我提出过文学翻译是两种语文、两种文化的竞赛。一般说来,译文是比不过原文的。但两种文化各有所长,如能发挥译语的优势,译文也未始不能超过原文。
傅译已经成为经典,如果重译,如何能比得上原作和傅译呢?傅译虽有所长,可能也有所短。“浩荡”以气势论甚至胜过原文,但以意似和音似而论,却可能有所不足。于是我从音似入手,译成“江流滚滚”,自己觉得气势不在傅译之下,“滚滚”却和原文音似,可以说是在“浩荡”之上。后半句我译成:“震动了房屋的后墙”,觉得江声自屋后上升,可以象征克里斯托夫像一颗新星一样升起,那么江流震动屋后,也可以象征音乐家的成就震动欧洲。至于房屋的后墙,因为原文接着描写了房屋的窗户、室内的闷热,我就加了一个墙字,但总觉得拖泥带水,削弱了句子的力量。书出版后,我重新考虑,又在《罗曼·罗兰选集》中改为:“江流滚滚,声震屋后。”觉得这八个字更加精炼,才能和傅译先后比美,但傅雷这句译文已成经典,那就无法超越了。
至于其他译文,原作第7页有一段描写老祖父的话,现将原文和傅译抄录如下:
(1)Les Krafft étaient sans fortune, mais considérés dans la petite ville rhénane, où le vieux s’était établi, il y avait presque un demi-siècle. Ils étaient musiciens de père en fils et connus des musiciens de tout le pays, entre Cologne et Mannheim. Melchior était violon au Hof-Theater ; et Jean-Michel avait dirigé naguère les concerts du grand-duc. Le viellard fut profondément humilié du mariage de Melchior; il batissait de grands espoirs sur son fils; il eût voulu en faire l'hommeéminent qu'il n'avait pu être lui-même. Ce coup de tête ruinait ses ambitions. Aussi avait-il tempêté d'abord et couvert de malédictions Melchior et Louisa.
(2)克拉夫脱家虽没有什么财产,但在老人住了五十多年的莱茵流域的小城中是很受尊敬的。他们是父子相传的音乐家,从科隆到曼海姆一带,所有的音乐家都知道他们。曼希沃在宫廷剧场当提琴师;约翰·米希尔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老人为曼希沃的婚事大受打击;他原来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想要他成为一个他自己没有能做到的名人。不料儿子一时糊涂,把他的雄心给毁了。他先是大发雷霆,把曼希沃与鲁意莎咒骂了一顿。
我曾借用孔子的话,提出文学翻译的“三之论”:“知之、好之、乐之”。这就是说,文学翻译首先要使读者理解(知之),其次要使读者喜欢(好之),最好能使读者愉快(乐之)。那么,傅译是否使中国读者理解了克拉夫脱一家在法国当时的社会地位呢?我觉得称他们为“很受尊敬的”“音乐家”有点名高于实,从书中上下文看来,他们只能算是乐师。“很受尊敬”不如“很看得起”更加恰如其分,第二个“音乐家”不如说是音乐界人士,这样才能使读者知之。至于好之,“父子相传”、“一时糊涂”就用得很好,甚至可以使人乐之。其他译文都可使人知之,是否能使人好之,那就要看是否发挥了译语的优势。在我看来,“没有财产”更像法律词语,不如说“不是有钱人家”更加口语化,“莱茵流域”也像地理名词,并且范围太大,结合实际情况,不如说是“莱茵河畔”。“五十多年”时间不必要地说长了一点,原文只是说“差不多半个世纪”。说老祖父“从前是大公爵的乐队指挥”,那就是长期的职务,而原文只说是在音乐会上当过指挥。说老人为儿子的婚事“大受打击”未免太重,原文只是“深感屈辱”。对儿子“抱着极大的希望”自然译得不错,但用“寄托”二字可能更好地发挥了译语的优势。说儿子“把他的雄心毁了”,“雄心”不如“奢望”,“毁了”不如“落空”,因为“雄心”一般用于自己,“奢望”才可以对别人,“落空”又是发挥译语优势,因此。我把这一段重新翻译如下:
克拉夫特父子虽然不是有钱人家,但在莱茵河畔的小镇还是大家看得起的人物,老爷爷在镇上成家立业,差不多有半个世纪了。父子两人是世代相传的乐师,是科隆到曼海姆这一带音乐界的知名人士。梅希奥是宫廷剧院的提琴手;约翰·米歇尔从前还在大公爵的宫廷音乐会上当过指挥。老爷爷觉得梅希奥的婚事有辱门庭,辜负了他对儿子的莫大期望,原来他自己没有成名,所以把成名的厚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了。不料儿子一时冲动,却使他的奢望全落了空。因此,他先是大发雷霆,把铺天盖地的咒骂都泼在梅希奥和路易莎身上。
南京有一位女作家说:“傅雷的文字优雅,简练;许渊冲的译文生动,贴切,具有小说文字的张力。”比较一下这两段译文,可以看出这位作家言之有理。傅译“父子相传”说比许译简练,许译在“大发雷霆”之后,继续把咒骂比作暴雨,铺天盖地泼在儿子和媳妇身上,显得生动。是否贴切,可以有不同的意见,有人可能认为是画蛇添足,我却认为加的是原文内容所有、原文形式所无的文字,是发挥了译语的优势,就像傅雷译的“江声浩荡”一样,是1+1>2的译文。这是目前翻译界争论最大的问题。
据电子计算机统计,英法德俄等西方文字约有90%可以对等,所以西方提出了对等的翻译理论;而中文和西方文字只有约45%可以对等,所以对等的译论不能应用于中西互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例如上面举的《约翰·克里斯托夫》的第一句,英法文只有grondement一个词不完全对等,其余90%都是对等的;而从中文看来,傅译和许译只有“江”、“声”、“屋后”四个字相同,其他五个字都不同,差不多是40%对等。因此我提出了文学翻译的新“三似论”。(1)形似(不意似):说美而不美,公式是1+1>2;(2)意似:说美而美,公式是1+1=2;(3)神似:不说美而美,公式是1+1>2。例如《约翰·克里斯托夫》原书第1227页有一句:C'est une mort vivante。傅雷译成:“这简直是死生活”。从字面看,译文和原文是形似的,但是内容不通,这就是傅雷自己说的“迁就原文字面”太过分了,结果不能使人知之。如把这句译成“这简直是个活死人”或“行尸走肉”,我觉得前者既形似又意似,后者意似而不形似,两者都能使人知之,甚至好之。还可以把这句译为“这简直是虽生犹死”或“生不如死”,我认为这可以算是神似,虽然没有说到具体的死人活人,却能使人知之、好之,甚至乐之。这就是我文学翻译的“三似论”和“三之论”。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前面已经举例说明,需要发挥译语优势,或者说优化译文。因此,我的翻译理论可以概括为“优化论”。
(原载《一本书和一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