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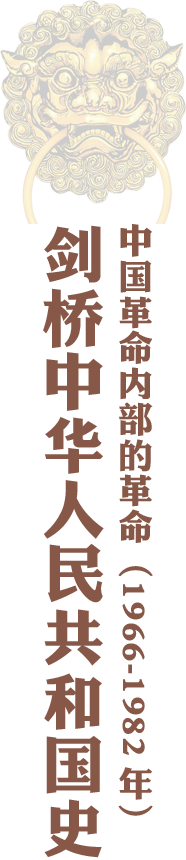
随着1967年8月底清洗“五·一六”兵团和翌年春天遣散红卫兵,“文化大革命”的重心从对旧秩序的破坏转变为创立新秩序——从中国人所谓的“斗批”时期转变为“批改”时期。重建政治体制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完善革命委员会组织和重新恢复党自身的地位。
这一时期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形式上,中国“新”政治秩序的结构与“文化大革命”前夕存在的那种结构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文化大革命”以沿着巴黎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辞藻开始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远不是那么富有远见卓识。干部们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群众代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然而,重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组织。
“文化大革命”以沿着巴黎公社的路线,“推翻”官僚机构并建立直接民主的乌托邦式的夸张辞藻开始的。但是,当政治重建的工作实际上已开始以后,重建的蓝图远不是那么富有远见卓识。干部们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他们在那里参加体力劳动和政治学习,认为这样就能培养他们更为无私和更为有效的工作方式。人们认为革命委员会及其监督下的官僚机构比之以前的机构更加精悍能干,而且更加忠实于毛主义的价值。而且由于其中包括了少数群众代表,这些组织被认为更能代表大众利益。然而,重建时期的组织路线在这两个方面仍然十分明确:政府机构仍按官僚政治路线来建设;中国共产党仍是一个指导革命委员会工作的列宁主义的组织。
新的政治体制区别于以前的政治体制的地方是它的成员而不是它的机构。军队官员比50年代初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级别较高的组织中。老一辈的政府官员靠边站,让位于那些缺乏经验、文化程度较低、视野狭窄而且更不称职的男男女女,尽管这些人并不比前者年轻多少。接纳新党员的工作重新开始。而且强调要大量吸收从红卫兵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积极分子。此外,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牺牲者、积极分子和旁观者之中所造成的冲突尚未解决,结果,党政机构受到了宗派主义的严重浸染。
毛的“战略部署”
1967年9月,毛泽东为结束“文化大革命”制订了所谓的“伟大战略部署”。在为前20个月的混乱辩护的同时(“不要怕制造麻烦,我们制造的麻烦越大,越好。”),毛承认,乱子已达到了它的目的,现在应迅速结束。毛告诫说:“车子开得太快就要翻,因此,谨慎是必须的。”

毛认为,当务之急是在中国29个省成立革命委员会。直到此时,成立革委会的进程十分缓慢,令人烦恼:1967年1月至7月底,在省一级仅有6个革命委员会成立。毛指示:现在我们必须“发展和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毛期望这些任务到1968年1月能完成。
毛认为两条指导方针有利于其余的革命委员会的成立。首先,毛现在准备让人民解放军主宰这个进程,(即使没有主宰的名分)因而毛愿意向人证明军队是有权威的,是忠诚的,他并愿意宽恕军队偶尔犯的过失。就像他在夏末所说的那样:“军队的威望必须坚决维护,无论如何都不能有任何迟疑。”有一次,毛以相当宽宏大量的口气提及“武汉事件”,他接着指出:“军队在首次执行大规模的支‘左’、支工和支农以及执行军管和军训的战斗任务时犯错误,这是难免的。当时的主要危险是一些人要打倒人民解放军。”
 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这反映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毛认识到军队的重要性,这反映在他不愿看到翌年春天杨成武解职后,人民解放军成为大批判的靶子。

第二条指导方针是,毛认识到,如果革委会中的群众代表来自于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不是仅仅从那些得到地方军队司令员们支持的群众组织中产生,那么,就能加速革命委员会的成立。这一强调包容性的观念在一份通知中得到具体体现。这份通知说,解放军应该“支‘左’不支派”。毛的一个指示指出:“工人阶级……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1967年底,新闻界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全国团结的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1967年底,新闻界对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断发起猛烈攻击,配合宣传毛关于全国团结的理想。现在,宗派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
1967年夏天毛巡视全国后,革命委员会分两个阶段建立起来了。1967年8月至1968年7月,18个省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最后五个省,如福建和广西这样分裂很深的省,以及像新疆和西藏这些敏感的边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是在7月对红卫兵运动最终压制下去后产生的。总之,革命委员会是在一系列协商之中诞生的。在这些协议中,地方军队指挥员和北京的领导人力求硬把互相竞争的群众组织拢到一起。
由于毛规定革命委员会应当广泛地代表各种观点,因此,革命委员会通常是庞大臃肿的机构。每个委员会都由100—250人组成。
 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相当数量的位置(在182个主任和副主任中占61个),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个主任中,有13个是部队司令员,5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军队司令员,5人是政委。其余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
不过,革命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是比较有效的机构,通常比“文化大革命”前存在的类似的党和政府领导组织还要小。常务委员会的构成随时代趋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较为激进的时期任命的群众代表多一些,在较为温和的阶段任命的群众代表就较少一些。尽管在这一时期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群众代表占据了相当数量的位置(在182个主任和副主任中占61个),但实权仍掌握在军队手里。23个主任中,有13个是部队司令员,5个是专职政委。第一副主席中,有14人是军队司令员,5人是政委。其余的都是党的干部,群众代表一个都没有。

过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后,毛也预见到,一旦在全国各省把革命委员会当作省一级的政府建立起来,就应进行党的重建。从一开始,毛主席就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个净化党的运动,而不是毁灭党的运动。就像在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十六条”中所说的那样,“文化大革命”委员会的目的就是用作联系党和群众的桥梁,而不是使其扮演一个党的替代物的角色。与此相似,红卫兵的目的就是推翻党内的“走资派”,而不是推翻整个党组织。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毛在1967年初反对把巴黎公社的模式应用于中国的主要原因是:党在这种结构中的地位不明确。这一点下面还会谈到。“如果一切都变成了公社,那么党怎么办?我们把党放在什么位置?……无论如何必须有一个党!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都必须有一个核心。可以称之为共产党,或社会民主党,或国民党或一贯道,但必须有一个党。”
 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如果党被红卫兵和革命委员会置于一边,那只是个暂时现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最终目的。
1967年9月,毛认为到了考虑重建党的时候了。毛说:“党组织必须恢复,而且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应该召开。”毛是乐观的,他认为能较快地完成这一任务:“我看,大约就在明年这个时候(即1968年9月)召开第九次党代会。”
 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谢负责政法工作,也出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基本原则。
毛把重建党的任务交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谢富治。“文化大革命”时期谢负责政法工作,也出尽了风头。10月10日,姚提交了一个初步报告,为党的重建设计了一个由上而下的基本原则。
 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具体体现三个“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姚的报告拟定出一个严密的程序,要求先召开一次全国党的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一个新的党章。参加党代会的代表将与各省“协商”后由中央指定。党代会结束后,就开始下级党组织的重建工作。根据姚的报告,各级新党委至少要具体体现三个“三结合”的原则,即每一个委员会都由老、中、青;工、农、兵及群众、部队官员和干部结合而成。
在姚的报告的基础上,11月27日,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关于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的通知”。12月2日,又发布了一个“关于整顿、恢复和重建党的机构的意见”的文件。这些文件遵循了姚报告的要点,作了两个重要补充。第一,“通知”增加了一个决定,它其实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隐隐约约存在着:现在林彪成了毛的接班人。“通知”宣布:“大批同志建议,党的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而且为了进一步加强林副主席的崇高威望,这一点要写进九大的报告和决议。”
第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通知各基层党组织重新开始过“组织生活”。为指导基层党组织的整顿,省革委会内部成立党支部,通常被称作党组,其任务是开始纯洁党员队伍,开除那些已蜕变为修正主义分子的党员,并从“文化大革命”的积极分子中吸收“新鲜血液”。
八届十二中全会
尽管预期在1967年秋天开始党的重建工作,但直到1968年9月最后一批省、市、自治区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这一进程才真正开始。不过,这个重要任务一旦完成,残存的中央领导人就迅速召开了第十二次中央全会,这次会议于10月13—31日在北京举行。
像1966年8月的十一中全会一样,十二中全会是党中央的一次残缺会议,中央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中,只有54人出席了会议,勉勉强强代表了这个机构现存委员的法定人数。
 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
此外,像前一次中央全会一样,非中央委员充塞了十二中全会。但是,1966年的特邀观察员是红卫兵运动中的“革命师生”,而1968年的特邀代表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各省革委会的代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负责同志”——即官员。换言之,这些人现在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幸存者和受惠者。

激进派怀着勃勃野心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要争取大会承认前两年发生的事件,并完成最高层党的机构的清洗。与第二个目标相比,他们在第一个目标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次全会最后的公报赞扬了“文化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歌颂了毛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坚信毛在这场运动中所作的很多“重要指示”和林的“许多讲话”是“完全正确”的,并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在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会议拥护毛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认为“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会议宣布:“这个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这次中央全会还放眼于未来,通过了一个新的党章草案,并宣布将在“适当的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全会宣布的最重要的决议大概是刘少奇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并被“永远”开除出党。在这一议题上,全会的决议——“文化大革命”期间,刘首次在正式公布的文件上受到点名批判——用煽动性的语言污蔑刘,把他定为“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然而,中央全会会后散发的证明材料(至少在西方能看到的材料)主要涉及刘在革命早期的1925年、1927年和1939年的活动,几乎没有提及他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表现。
 这表明,全会在如何叙述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这表明,全会在如何叙述刘在1949年以后的活动时,不能取得一致意见。
在中央全会的小组讨论会上,“文革”小组和林彪对1967年的“二月逆流”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奇怪的是,毛在中央全会的闭幕讲话中对那段插曲所持的观点比过去更为缓和。现在,毛主席把怀仁堂那次臭名昭著的会议看成是中央政治局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利,对一些重大的政治问题发表自己意见的一个机会。不过,全会公报还是把“二月逆流”斥责为对“以毛主席为统帅、林副主席为副统帅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一次攻击”。毛对此不置可否。
尽管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除了谭震林已在前一年遭清洗外,激进派仍没能把最积极地参与“二月逆流”的任何一个人排挤出中央委员会。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全都留在中央委员会。最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不但要把邓小平赶出中央委员会,还要把他与刘少奇一道,永远开除出党。这一建议在毛泽东本人干预后遭到否决。

除了这几点以外,十二中全会几乎没有作出什么重要决策。全会含含糊糊地提到将在工宣队领导下进行“教育革命”,但没有说要采取什么特别的方案。与此相似,全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正在促进并将继续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新的飞跃”,但没有宣布新的经济计划。“文化大革命”可能想要否定60年代初期毛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某些经济、社会政策,但全会表明尚未确立任何新的、可以取代它们的政策。
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969年4月召开的第九次党代会反映了许多相同的倾向。林彪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试图证明“文化大革命”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伟大的新贡献”。
 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里说成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林彪赞扬了军队和“文革”领导小组自1966年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不指名地提到了幸存的政府高级干部,又一次批判“二月逆流”(“这里说成是1966年冬季到1967年春季出现的那股逆流”)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猖狂反扑”,其目的是“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
关于国内政策,林的政治报告——与十二中全会的公报一样——实际上没有什么内容。报告只是指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农业生产连年获得丰收”、“工业生产……出现了一片蓬蓬勃勃的局面”、“市场繁荣”、“物价稳定”,并断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必将继续促使经济战线……出现新的跃进”。报告还宣称,“在文化、艺术、教育、新闻、卫生等部门”的夺权将结束“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这些部门的一统天下,但没有说明将有什么新政策出台。报告还用相当篇幅提及从党内开除一些老党员,吸收一批新党员。但是,对这个即将开始的过程,报告没有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九大对中国政治重建的贡献在于它对新党章和党中央领导人所作的决议。与上一次在1956年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相比,新的党章强调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和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这两种提法在以前的党章中都没有出现过。
 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所有“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人敞开大门。相反,1969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另外,入党的机会现在只给那些阶级出身好的人。1956年的党章向所有“参加劳动、不剥削他人劳动”及承担党员义务的人敞开大门。相反,1969年的党章原则上把党员的来源局限在工人、贫下中农和军人家庭出身的人。
新党章最重要的特点是简略而缺乏精确性。新党章只有12个条款,所占篇幅大约只有1956年党章的1/5。新党章没有一处提到党员的权利,也没打算要详细地阐明各级党委的结构和权力、处分党员的程序、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周期,及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都是以前的党章的重要特点。从党的结构中被撤销的组织有:领导中共党组织的书记处、主持党的日常工作的总书记和负责党内纪律的监察委员会的全部组织系统。因此,九大所产生的党的组织结构,比起“文化大革命”前的组织结构,必然更加灵活更加缺乏制度化,因而也更容易受到高层领导人物的操纵。
党的九大不仅为“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看来也为毛以后的时代选举了一个新的中央领导班子,林彪作为唯一的副主席和“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正式写入新党章,从而确定了他的地位。上一届中央委员会的167名委员,在九大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仅54人。一大批没有进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党的领导人,还有一些重要的经济专家,如以前一直在国务院工作的薄一波、姚依林,此时都被排除在党的精英集团之外。在经历了一场由激进派发起的旷日持久的运动之后,大部分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一辈文职官员和军官,尽管还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资格,但都丢掉了在中央政治局的职位。九大最主要的牺牲者是邓小平,他被贬出了中央委员会。不过,党代会的正式文件仍没有点名批判他。
很清楚,参加大会的代表和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影响。第一,他们表明了军队突出的地位。对大会纪录片的一份分析表明,在1500名代表中,大约有2/3的人身着军装。与1956年八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军队代表占19%的数字相比,这届中央委员会中,解放军代表占了45%。
 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极少。的确,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数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委员的1/3。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军队的崛起是靠牺牲文职官员和群众代表而实现的,前者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后者则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益者。在新的党中央机构里,群众代表极少。的确,有19%的中央委员“来自群众”,但是,他们往往都是老工人、老农民,而不是“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年轻的群众积极分子。军官代表数量大也意味着文职官员的代表数量下降了,尤其是国务院官员的代表数减少了,他们约占中央委员的1/3。众所周知,人民解放军和那些政府领导人所受的教育不同,他们的人生道路也不相同,中央委员会构成上的这种变化,关系到文化教育程度的下降和国外生活阅历的减少。
第二,与第一点同等重要的是,大会证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造成的权力分散。1956年,约有38%的中央委员是省里任职的干部,其余的都在中央党政军各部委任职。相反,在1969年,整整2/3的中央委员是地方代表。不过,这种倾向在中央政治局的反映还不太明显。“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只有3人可算是省、自治区的代表。相比之下,选进九大中央政治局的专职地方大员有2人(纪登奎和李雪峰),军区司令员3人(陈锡联、许世友和李德生)。
第三,从九届中央委员会可以看到,尽管权力还没有转移到年轻人手里,但却转移到了资历较浅的一代领导人手中。确实,人们讲到九大产生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特点是“年纪不轻经验不足”。170位正式中央委员中,有136人在“文化大革命”前没有担任过中央委员(在279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占225人)。但由于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平均年龄约为60岁,因而,这届中央委员会比它刚取代的中央委员会仅稍稍年轻一点,而实际上,它比1956年选出的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当时的年龄要大。此外,由于地方军队领导人、省里第二梯队的地方官员和群众代表充实进中央委员会,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人的级别明显比上一届要低。
从最后发展的结果看,这届中央委员会正式通过的政治局说明了北京最高层的权力继续分散。除毛和林之外,25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与林关系密切的中央军队官员5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系的6人;与林彪没有密切关系的大军区和省军区司令员3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冲击的高级文职官员2人;另有一位用来制约林彪的人民解放军元帅;由于“文化大革命”而登上权力宝座的党的中层干部3人;还有3位早过鼎盛期的老资格的党的领导人。因而,中央政治局的成分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幸存者和获益者之间,军队和运动期间上台的文职激进分子之间,林彪及其在中央军队领导层的对手之间,以及中央军事机构与大军区司令员之间的分裂。
总之,尽管有结束红卫兵运动暴乱的成功尝试,尽管开始了重建中国政治体制的初步努力,但是,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留给了这个国家一个捉摸不定的政治形势。“文化大革命”后的政策轮廓没有确定:权力在明显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间分割;党和国家的结构模糊不清,而且非制度化。尽管林彪在名义上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他的权力基础极为脆弱。在此后的两年里,林企图让军队永久性地支配政府事务,提出了一个他以为会受到广泛欢迎的政纲。他想以此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但是,这些努力最终导致了林在政治上的垮台,而且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