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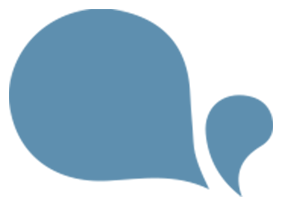
说来这事挺新鲜,活到如今这把年纪——上一次过生日,我已经满五十五岁——我居然拿起笔,要给自己写一部传记。唉,倘若我这一次历险能够坚持到底,而不是半途而废的话,那么,我真不知道会写出怎样惊心动魄的篇章!
我这一辈子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这或许是由于我很早就走上了社会,因而我的人生道路也就显得格外漫长:当别的孩子还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我已经前往旧殖民地
 ,以商人的身份给自己挣饭吃了。自从那以后,我做过商人,当过猎人,打过仗,还下过矿井。然而,只是到了八个月之前,我才开始发财。到如今,我发了一大笔财——这笔财富大得我自己都数不清——不过,假如为得到这笔财富,让我将这十五六个月的种种艰难困苦重新经历一遍,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即使我知道最终肯定会平安无事,那我也不干。给多少钱都不干!
,以商人的身份给自己挣饭吃了。自从那以后,我做过商人,当过猎人,打过仗,还下过矿井。然而,只是到了八个月之前,我才开始发财。到如今,我发了一大笔财——这笔财富大得我自己都数不清——不过,假如为得到这笔财富,让我将这十五六个月的种种艰难困苦重新经历一遍,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即使我知道最终肯定会平安无事,那我也不干。给多少钱都不干!
说到底,我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我不喜欢暴力,对冒险之类的事情烦透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这可不是我熟悉的行当。我不是耍笔杆子的,尽管我喜欢读《圣经·旧约》,还喜欢看《英戈尔兹比叙事诗集》
 。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写这本书的理由,假如我真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话。
。我想跟你们说说我写这本书的理由,假如我真有什么理由可说的话。
首先,亨利·柯蒂斯爵士和约翰·古德上校让我把这个故事写下来。
其次,眼下,我拖着一条伤残的左腿,终日躺在德班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自从碰上那头该死的狮子,我这条左腿十有八九就算废了,如今情况更糟糕,我一生里还从没像现在这么瘸过。狮子的牙齿上肯定有毒,要不,伤口愈合后——请注意,一般是在你受伤一年以后的同一时间——怎么还会裂开呢?一个人像我这样能在一生里打倒六十五头狮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第六十六头狮子就像啃嚼烟叶似的从我的左腿上扯去了一块肉。这下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不得不把其他所有的想法通通扔掉。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是个很有条理的人,这可不合我的脾气。
,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自从碰上那头该死的狮子,我这条左腿十有八九就算废了,如今情况更糟糕,我一生里还从没像现在这么瘸过。狮子的牙齿上肯定有毒,要不,伤口愈合后——请注意,一般是在你受伤一年以后的同一时间——怎么还会裂开呢?一个人像我这样能在一生里打倒六十五头狮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这不,第六十六头狮子就像啃嚼烟叶似的从我的左腿上扯去了一块肉。这下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我不得不把其他所有的想法通通扔掉。顺便说一句,我一直是个很有条理的人,这可不合我的脾气。
还有第三个理由,我的儿子哈里眼下在伦敦的一家医院学医,我想写出点儿有趣的东西,能让他在一两个星期之内不至由于烦闷而去搞什么恶作剧。有时候,医院里的工作很无聊,即使是解剖尸体也会有干烦的时候。不管怎么说,我的这本传记总不至于像解剖台上的尸体那样死气沉沉吧?哈里拿起这本书读一读,书中的这些故事总能给他的生活增添一点儿生气。
第四个理由嘛,也是最后一个理由,就是我想向世人讲述一个我所知道的最离奇的故事。这事说来有点儿不可思议,尤其整篇故事里你看不到一个女人——除了弗拉塔。噢,打住吧!还有一位加加乌拉呢,如果她也算作一位女人,而不是妖精的话。然而,她如今至少有一百岁了,不可能结婚了,因而,我也就把她刨除在外了。无论如何我可以向你担保,在这篇故事里你看不到一点儿脂粉气。
好吧,我最好还是把这份苦差事承担起来。如果拿拉车来做比喻的话,我觉得眼下两只车轮已深深陷进泥里去了,甚至已经陷到车轴了。然而,就像布尔人
 所说的:“苏特叶斯,苏特叶斯。”
所说的:“苏特叶斯,苏特叶斯。”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几个词是怎么拼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要柔和。只要是拉车的牛足够强健,就一定能冲破重重困难,坚持到底——如果这些牛还不至过于精疲力竭的话。谁也没法赶着已经累垮的牛再往前走了。好,我们开始吧。
(说实在的,我真不知道这几个词是怎么拼的。)说这句话的时候声调要柔和。只要是拉车的牛足够强健,就一定能冲破重重困难,坚持到底——如果这些牛还不至过于精疲力竭的话。谁也没法赶着已经累垮的牛再往前走了。好,我们开始吧。
我叫艾伦·夸特曼。我敢说,我算得上纳塔尔省德班的一名响当当的绅士——当我在地方法官面前陈述可怜的希瓦和文特沃格尔的死因时,我就是这么开场的。当然,这不大像是一本书的开场。另外,我能算一名绅士吗?什么是绅士?我实在说不清楚。我不得不跟那些“黑鬼”打交道——不,我得把“黑鬼”这个词划去,我不喜欢这个叫法。我认识一些当地土著人里的绅士。所以,哈里,我的孩子,在你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我要说,我认识许多卑鄙无耻的白人,他们手上有的是钱,有的还是刚从国内来到这里的,可他们不能算绅士。
嗯,不管怎么说,我天生就是一位绅士,尽管我这辈子除了做一名可怜的旅行商人和猎手之外一无所有。我如今是不是还算得上一名绅士,我就不知道了,你只好自己来判断。苍天在上,我一直在努力去做。我一生里杀过许多人,然而,我从不会轻易这么做,我的双手也从没沾上过任何一位无辜者的鲜血;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自卫。万能之主赐给了我们生命,我猜想,他肯定希望我们有勇气去捍卫它。至少,我一直是照这个信条去做的;在我的余生里,我希望人家不至在这些事情上跟我翻旧账。唉,说到底,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充满了残忍与罪恶,而我这么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却偏偏被卷进了这么多起凶杀事件里。我实在搞不清这些事情的对错,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从没做过贼,尽管有一次我曾经从一个卡菲尔人
 手上骗走了一群牛。不过,他后来确实狠狠地报复了我一下;另外,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就算倒霉了。
手上骗走了一群牛。不过,他后来确实狠狠地报复了我一下;另外,自从这件事之后我就算倒霉了。
嗯,大约在十八个月前,我第一次遇见亨利·柯蒂斯爵士和古德上校,也就是在这一次外出的旅途上。我原本是去巴芒瓦图一带去猎象的,可是我的运气真是糟透了。这一次狩猎可以说事事都不顺,结果,我最终患上了严重的热病。等病情稍稍有所好转,我立刻动身前往戴蒙德菲尔兹,将手里的象牙连同大车和拉车的牛一起卖掉,遣散猎人们,然后乘邮车来到了开普
 。在开普敦
。在开普敦
 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发现旅店的老板是在向我敲竹杠,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一看,包括这里的植物园,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益处;然而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国会,我什么都不能指望。
逗留了一个星期,我发现旅店的老板是在向我敲竹杠,而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值得一看,包括这里的植物园,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似乎可以从中获得不少益处;然而对于这个刚刚成立的国会,我什么都不能指望。
我决定去搭乘返回纳塔尔的邓凯尔德号,躺在船上等定期从英国开来的爱丁堡城堡号的到来。我拿到铺位号,就上了船。这天下午,爱丁堡城堡号到了,前往纳塔尔的旅客下了船,陆续登上邓凯尔德号,于是,我们的轮船离开码头,驶向广阔的海域。
在这些从英国来的乘客中,有两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一位是三十岁左右的男子,这是我见到过的手臂最长、胸部最宽的一个人。他的头发是黄色的,蓄着一部黄色的大胡子,五官轮廓分明,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得很深。我从没见过长得这么英俊的男人,他的相貌不禁让我想起古代丹麦人。这倒不是说我对古代丹麦人十分熟悉,尽管我确曾认识一个现代丹麦人,他从我手里骗走了十个英镑;不过,我曾经见到过一幅表现那些绅士们的绘画,我认为他们是白色的祖鲁人
 。画上的人物正在用大牛角杯喝着酒,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后背。我就想,如果站在升降梯旁的这位朋友的头发再长一些,给他一柄大战斧和一只牛角杯,再让他那宽宽的肩膀上穿上一件带链环的衬衣,他就满可以给那幅画的画家当模特了。顺便说一句,这事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血统居然能从长相上看出来,因为我后来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这是那位高大英俊的男子汉的名字——确实具有丹麦人的血统
。画上的人物正在用大牛角杯喝着酒,长长的头发一直披到后背。我就想,如果站在升降梯旁的这位朋友的头发再长一些,给他一柄大战斧和一只牛角杯,再让他那宽宽的肩膀上穿上一件带链环的衬衣,他就满可以给那幅画的画家当模特了。顺便说一句,这事的确有些蹊跷,一个人的血统居然能从长相上看出来,因为我后来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这是那位高大英俊的男子汉的名字——确实具有丹麦人的血统
 。他的相貌不禁强烈地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然而当时,我记不起这个人到底是谁。
。他的相貌不禁强烈地让我想到了另一个人,然而当时,我记不起这个人到底是谁。
另一个站着正在跟亨利先生说话的是个矮个子的健壮、黑黑的男子,相貌特征与前者迥然不同。我立刻猜想他是一名海军军官。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确实很难猜错。我一生里曾有几次陪着海军军官去打猎,尽管这些人喜欢说脏话,不过,他们的确全都是我遇见过的最优秀、最勇敢和最漂亮的男子汉。

在这些从英国来的乘客中,有两位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曾经专门请教过一两名旅店的招待,我问他们什么是绅士。现在我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一般来说,一名皇家海军军官就是绅士,尽管这些人里也不是没有一个半个败类。我想,这大约是由于长年航行在宽阔的海洋上,他们呼吸到的海风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拂去他们性格中的那些不洁的东西,逐渐将他们锻造成男子汉该有的样子。噢,话又扯远了,这一次又猜对了。我后来发现,他确实是一名海军军官,一位三十一岁的海军上校,已经在皇家海军服役了十七年,由于对一位上校失敬,晋升无望,如今已经从女王的麾下退役了。而晋升正是人们到女王的军中服役所期望的:他们在刚刚懂事的年纪就离开家门,在冷酷的社会上闯荡,为的就是要博得荣耀和名利。嗯,我猜想他们或许对这些并不在乎,可是,我作为一名猎手,我确实要给自己挣到面包才成。小钱也许让你瞧不上眼,然而,大钱并不是总能赚到手的。
他叫古德——我是通过旅客名录查到的——约翰·古德上校。他是个宽肩膀的中等身材的男人,皮肤黝黑,体格健壮,一眼看上去就禁不住会引起你的好奇心。他的穿着是那样整洁,胡须剃得那样干净,右眼上总戴着一只单片眼镜。这片眼镜仿佛是长在眼眶上的,因为你根本瞧不见金属丝一类的东西,除了擦拭,他也从来不摘下来。起初我还想,也许他睡觉都戴着眼镜,后来发现这是个误解。每天上床之前,他就把它摘下来,跟他的假牙一起放进裤袋里——他有两副做工精美的假牙,而我自己的却没这么好。我差点因此触犯了十诫
 ,好在我自己事先就有所警觉。
,好在我自己事先就有所警觉。
轮船驶到海面上不久,天就黑下来了。紧接着,天气也开始变得恶劣起来。一股强风从陆地的方向吹来,不久,渐渐浓重起来的雾气很快就将甲板上的旅客赶到船舱里去了。我们乘坐的邓凯尔德号是一艘方头平底的大船,吃水又浅,因而在航行中颠簸得厉害,甚至好像马上就要被风浪掀翻了,然而实际上并不会真的翻船。此时,在甲板上来回走动已经不可能了,因而,为了使身子感到暖和一些,我就站在靠近马达的地方,望着对面的一只指示摆给自己解闷:每当船体在风浪中左右摆动时,这只摆也会随之摆动,指出船体每一次倾斜的角度。
“这只摆所指的角度有误。摆锤的长度调得不对。”突然,有个声音从背后传过来,话语中还带着不耐烦的腔调。我转过身去,看到说话的就是旅客上船时我注意到的那位海军军官。
“确实有问题。然而,您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我问。
“怎么想到的?根本用不着想。喏,您瞧,”说话间,轮船刚刚侧倾了一下,“要是轮船确实倾斜到这玩意儿所指的角度的话,早就翻了。就是这么回事。就像商船的那些船长一样,他们干事全都粗心得要命。”
就在这时,开饭的铃声响了。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惜,聆听一位海军军官在这方面的高见,简直是受罪。当然,还有比这更受罪的事呢,那就是聆听一位商船的船长坦诚地谈出他们对海军军官的意见。
古德上校和我一同朝餐厅走去。到了餐厅里,我们发现亨利·柯蒂斯爵士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他们两个坐在一起,我坐在他们的对面。我和古德上校很快就聊起打猎以及打猎以外的话题;古德上校提了很多问题,我力所能及地一一给予了回答。不久,古德上校就把话题转到了猎象方面来。
“啊,先生,”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另一个人插话说,“说到猎象,您算找对人了,夸特曼是这一带有名的好猎手。您尽可以问他好了,他在这方面一点儿不比任何一个猎手差。”
听他这样说,一直坐在那里静静地听我和古德上校聊天的亨利爵士吃了一惊。
“请问,先生,”他把身子往前倾了倾,用一种深沉而又浑厚的声调开腔了,这种声调从他那宽阔的肺叶中吐出来,在我听来的确十分悦耳。“请问,先生,您的名字是叫艾伦·夸特曼吗?”
我说:“是的。”
大个子男人没再说什么,不过,我听见他的大胡子里吐出这么几个字:“真是幸运。”
晚餐很快结束了,离开餐厅时,亨利爵士走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到他的船舱里去吸一袋烟。我接受了邀请。于是,他将我领进邓凯尔德号的甲板客舱。这的确是一间相当漂亮的客舱。这原本是两间客舱,加尼特爵士
 或其他某个大人物曾乘坐邓凯尔德号在沿海一带巡视,卸去中间的隔板,以后就再也没有装上去。客舱里有一只沙发,沙发前还有一只小桌。亨利爵士叫船上的侍者送来一瓶威士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下来,点燃了烟斗。
或其他某个大人物曾乘坐邓凯尔德号在沿海一带巡视,卸去中间的隔板,以后就再也没有装上去。客舱里有一只沙发,沙发前还有一只小桌。亨利爵士叫船上的侍者送来一瓶威士忌,然后,我们三个人就坐下来,点燃了烟斗。
“夸特曼先生,”当侍者送来威士忌,点亮灯之后,亨利·柯蒂斯爵士开口说话了,“前年的这个时候,我想,您是在德兰士瓦省以北的一个叫作巴芒瓦图的地方吧。”
“是在那儿。”我回答说。就我所知,我的行踪在这一带并未引起如此普遍的关注,而这位绅士居然对此了如指掌,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愕。
“你是在那儿做生意,对吧?”古德上校插进来,用他那急促的语气说。
“是啊。我运了一车货物到巴芒瓦图,就在定居点外支起帐篷住了下来,直到出售完这批货物为止。”
亨利爵士坐在我对面的一张马德拉座椅上,两条胳膊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时,他抬起头,用他的一双灰色的大眼睛凝视着我。我暗暗想,他的目光里有着某种奇异的焦灼。
“您是否碰到了一个名叫内维尔的人?”
“噢,是的。他就在我旁边卸了大车,住下来。为了叫他的牛好好休息一段时间,他在这儿足足住了两个星期,然后就赶着车到内地去了。几个月以后,我收到了一位律师的来信,问我是否知道内维尔先生的下落。当时,我就自己所知道的情况给予了答复。”
“是的。”亨利爵士说,“律师把您的信交到了我手里。您在信中说,有个叫内维尔的绅士于五月初坐着大车离开巴芒瓦图,与他在一起的有一位马夫、一个赶牛的小伙子,还有一个是名叫吉姆的卡菲尔猎手。这位绅士声称,如果可能的话,他将一直走到伊尼亚蒂,即马塔贝莱地区最远的一个贸易点,他要在那儿把马车卖掉,继续徒步前行。您还说,他确实卖掉了他的马车,因为六个月之后,您看到这辆马车已经转到了一位葡萄牙商人手上。这位葡萄牙商人说,他是在伊尼亚蒂从一位白人手里买到这辆车的;至于那个人的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了。他还说,这个白人带着一名当地的仆人继续往内地走去,他猜想,他们是到内地打猎去了。”
“是的。”
然后,是一阵沉默。
“夸特曼先生,”突然,亨利爵士说,“我猜想,您是不是知道或者猜想到我的——我是说,您是否猜想到了内维尔先生去北方旅行的意图或此次旅行的目的地?”
“我听到了一些说法。”我回答说,然后就停住了。我不想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讨论下去。
亨利爵士和古德上校对视了一下。古德上校轻轻点了点头。
“夸特曼先生,”亨利爵士说,“我想谈一段有关我自己的经历,打算听听您的意见,也许还需要您的帮助。那位把您的信寄给我的代理人对我说,这封信完全靠得住,因为您在纳塔尔是那么受人尊重,尤其以您的审慎闻名遐迩。”
我向亨利爵士鞠了一躬。为了掩盖内心的慌乱,我喝了一点儿加水的威士忌,因为我是个十分谦虚的人。亨利爵士继续说:
“内维尔先生是我兄弟。”
“哦,”我不禁惊讶地说。此时我才恍然大悟,我知道我第一眼见到他时想起的是谁了。内维尔先生的个头比亨利爵士小多了,而且下巴上生着的是黑胡子。可是,他的一双眼睛也是这种灰色的,而且目光中也带有这样一种专注而犀利的神情;此外,兄弟俩在五官上也不无相似之处。
“他是我唯一的弟弟。”亨利爵士继续说,“直到五年以前,我一直都认为,我们兄弟俩决不会分离一个月以上的时间。然而这个时候,就像其他家庭里通常会有的情况一样,一场不幸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兄弟俩大吵了一场。当时正在气头上,我的表现对弟弟来说很不公平。”这时,古德上校使劲点了点头。恰好轮船猛地颠簸了一下,挂在对面(即右舷)舱壁上的一面镜子几乎晃到了我们的头顶上,当时我将两手插在裤兜里坐在那儿,抬头一瞧,刚好瞧见他那颇有些夸张的动作。
“我想你一定知道,”亨利爵士继续说,“如果一个人在没立遗嘱的情况下死去,而他除了土地——这在英国被称作‘不动产’——又没有其他遗产的话,所有的土地一律由长子继承。正在我们兄弟俩吵架的当儿,父亲就在没立遗嘱的情况下死去了。他迟迟不肯立遗嘱,可是,到了最后就再也来不及了。
“结果,弟弟从父亲手上连一个便士的财产也没继承到,而他又一直没学到一技之长。当然,我有义务向他提供一切生活所需;然而,当时我们俩吵得那么厉害,我拒绝这样做——这的确是我的羞耻。”说到这儿,他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当然,这倒不是说我舍不得给他,我是等着他自己提出来。然而,他并没这么做。很抱歉,夸特曼先生,我竟跟您说起这些家庭琐事;可是,我必须把这些事情讲清楚,哦,对吧,古德?”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上校连连点头说,“我敢肯定,夸特曼先生一定会替你保守秘密的。”
“当然啦。”我说。我很为自己的审慎感到骄傲。
“那就好。”亨利爵士继续说下去,“当时,我弟弟手上有几百英镑。他没跟我打招呼,就把这笔微不足道的积蓄取出来,起了内维尔这个名字,乘船来到南非,指望在这里发一笔横财。这是我后来才听说的。
“三年的时间过去了,我没有得到弟弟的任何消息,尽管我曾写过几封信。毫无疑问,这些信并没送到他手上。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担心起他来。我发现,夸特曼先生,血浓于水啊。这话一点儿不假。”
“的确是这样。”我说。我想到的是我的孩子哈里。
“我感到,夸特曼先生,为了打听到弟弟乔治的消息,我甚至愿意拿出一半的财产来。他是我唯一的亲人,我希望知道他如今是否过得平安、幸福;我真想再见到他一面啊!”
“可是,你再也没见到过他,柯蒂斯。”古德上校一边急促地说,一边朝这个大个子的脸上瞟了一眼。
“是啊,夸特曼先生,随着时间的一天天过去,我变得越来越焦急了:我想知道弟弟如今是不是还活着,我是不是还能把他活着找回来。我开始出发去寻找他,你的来信就是我找他的线索之一。你的来信的确让我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封信表明:直到您写这封信前不久,乔治还活着。然而,这以后的情况就说不清了。
“所以,夸特曼先生,我们长话短说,我下决心亲自来这里寻找他。古德上校出于善意,也陪我一同到了这里。”
“是的。”古德上校说,“你知道,我也没其他事情可做。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老天在上,靠着海军部的那一点儿薪水过日子,几乎饿得半死。现在,先生,或许您能告诉我们您知道或者听到过这位叫作内维尔的绅士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