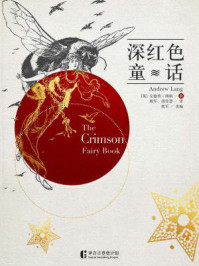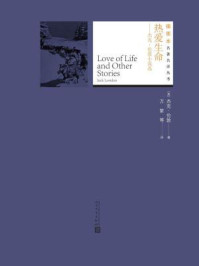11月的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在德莱佩修道院路,沿着聋哑学院的高墙前行。左边,矗立着圣雅克杜欧帕教堂的钟楼,我还记得圣雅克路的拐角有家咖啡馆,在乌尔苏拉影院看完电影后,我常去那里。
人行道上,落着一些枯叶,或者是几页烧焦的旧《加菲奥》词典
 。这是学校区和修道院区。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十八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当时,我在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一所中学读书。
。这是学校区和修道院区。几个过时的词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埃斯特拉帕德、壕沟外护墙、图尔纳福尔、波德费尔路……经过这些地方的时候,我感到有些害怕。十八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来过这里。当时,我在圣女日南斐法山的一所中学读书。
我觉得那些地方仍处于60年代初我离开时的状态。它们在那个时期就被抛弃了,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以上。盖鲁萨克路——人们曾撬掉那条僻静小路上的地砖用来筑起街垒——某家旅店的门已被砖封死,大部分窗户都已没有玻璃,但招牌仍然钉在墙上:“未来旅店”。什么未来?30年代的某个大学生,他的未来已经完蛋。他在这家旅店租了一个小房间,就在高等师范学院门口的地方,星期六晚上常邀请老同学去那里玩。人们绕过一片建筑群,去乌尔苏拉影院看电影。我经过铁栅栏和装有百叶窗的白屋,电影院在一楼。大厅里灯光明亮。我可以一直走到瓦尔德格拉斯,我和雅克琳娜曾躲在那个平静的地方,不让侯爵见到她。我们住在皮埃尔—尼古拉路尽头的一家旅店里,靠雅克琳娜卖掉她的毛皮大衣得来的钱生活。星期天下午,小街阳光灿烂。塞维涅学院对面,那座小砖屋门口有几棵女贞树。旅店的阳台上爬满了常春藤,通往大门的走廊上睡着一条狗。
我回到了乌尔姆路。那条小路很荒凉。用不着说,星期天的晚上,在这个学生区,没有任何特别的故事,看起来就像在外省一样,我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还在巴黎。我的面前就是先贤祠的圆顶。月光下,我害怕独自一人来到这个阴森森的圣殿脚下,于是便拐进罗蒙路,在爱尔兰中学门前停下脚步。有个钟敲响了八点,也许是圣灵修会的大钟,它巨大的外墙就在我右边。又走了几步,便到了埃斯特拉帕德广场
 。我寻找福塞—圣雅克路26号。在那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现代建筑,旧楼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掉了。
。我寻找福塞—圣雅克路26号。在那里,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栋现代建筑,旧楼可能二十多年前就已经被拆掉了。
1933年4月24日,一对年轻夫妇神秘自杀,原因不明。
这是一个十分奇特的故事,当晚发生在先贤祠附近,福塞—圣雅克路26号T先生和T夫人家中。
于尔班·T先生是个年轻的工程师,化学学校毕业,三年前娶了二十六岁的吉塞尔·S小姐,比他大一岁。T夫人是个漂亮的金发姑娘,身材高挑。而她的丈夫呢,也是个美男子,一头褐发。上一年7月,夫妻俩搬到福塞—圣雅克路26号一楼居住。他们把一个作坊改成了单身公寓。小两口很亲密,好像没有任何东西妨碍他们的幸福。
星期六晚上,于尔班·T先生决定跟太太出去吃饭。两人是晚上七点左右离家的,好像半夜两点才回家,还带回两对人。他们罕见地吵吵嚷嚷,门铃声吵醒了邻居。房客们通常都蹑手蹑脚,如今这般吵闹,让人很不习惯。也许在庆贺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凌晨四时许,客人们离开了。接下去的半个小时,寂静无声,只听到两记沉闷的响声。上午九点,一个女邻居走出家门,经过T的房门前,听到有呻吟,她马上就想起来,半夜里好像听见有枪声,她很担心,立即就去敲门。门开了,吉塞尔·T出现在门口,左胸有个很明显的伤口,血慢慢地从那儿流下来。她喃喃地道:“我丈夫!我丈夫!死了。”不一会儿,警长马尼昂先生赶到。吉塞尔·T躺在沙发上呻吟。人们在隔壁房间发现了她丈夫的尸体,痉挛的手中还拿着一把手枪。他朝自己的胸口开了一枪,自杀了。
在他旁边,有封被揉皱的信:“我太太自杀了。我们醉了。我也自杀。用不着……”

据调查,于尔班和吉塞尔夫妇晚餐后好像去了蒙帕纳斯
 的一家酒吧。另一个晚上,我从福塞—圣雅克路经过天文台黑乎乎的花园,一直走到圆顶饭店和圆亭饭店所在的十字路口。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蒙帕纳斯区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一样,总让我想起林中睡美人的城堡。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曾有同样的感觉: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正远离巴黎,慢慢地腐烂。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
的一家酒吧。另一个晚上,我从福塞—圣雅克路经过天文台黑乎乎的花园,一直走到圆顶饭店和圆亭饭店所在的十字路口。1933年的那个晚上,T夫妇跟我走的是同一条路。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自60年代以后我就避开的地方。蒙帕纳斯区就像乌尔苏拉修女会一样,总让我想起林中睡美人的城堡。二十岁的时候,我在德朗布尔路的一家旅店住过几个晚上,曾有同样的感觉:我那时就已经觉得蒙帕纳斯像一个死了的街区,正远离巴黎,慢慢地腐烂。下雨的时候,我觉得奥德萨路和德·帕路就像毛毛雨中的布列塔尼
 港口,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缺了两三个字母,被海风刮走了。
港口,布雷斯特人或洛林人一群群地从尚未拆毁的车站里拥出来。这里的寻欢作乐早就结束了。我记得老吉米家的招牌还挂在于根斯路的墙上,缺了两三个字母,被海风刮走了。
那对年轻夫妇是第一次——据1933年的报纸说——到蒙帕纳斯过夜生活。他们是不是晚餐时酒喝得太多了?或仅仅是想在那个晚上打破生活中的平静?有个证人信誓旦旦地说,半夜两点左右,在玛丽娜咖啡馆见到过他们,那是拉斯帕伊大街243号的一家舞厅;还有一个证人说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见到过他们,跟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女子。警方怕证据不可靠,还出示了他们的照片,因为有许多像于尔班那样的褐发小伙子和像吉塞尔·T那样的金发姑娘。几天来,警方试图查清T夫妇带到福塞—圣雅克路家里的那两对人是什么身份,后来调查就结束了。吉塞尔·T伤重身亡之前还能说话,但记忆已经模糊。是的,他们在蒙帕纳斯遇到了两个女人,完全不认识的两个陌生女人……这两个女人把这对夫妇带到了佩勒
 ,去了一家舞厅,两个男子在那里跟他们见面。然后,大家一起前往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
,去了一家舞厅,两个男子在那里跟他们见面。然后,大家一起前往一栋装有红色电梯的房子。
那天晚上,我沿着他们的足迹来到一个阴森森的街区,蒙帕纳斯大楼给它罩上一层悲伤的面纱。整个白天,它都挡住了阳光,把影子投掷在埃德加—吉内大道和周边的小路上。我走过正被水泥外墙压垮的圆顶饭店,很难相信蒙帕纳斯以前曾有过那么热闹的夜生活……
我究竟是在什么时期住过德朗布尔路的那家旅店?1965年前后吧,认识雅克琳娜的时候,是动身去奥地利的维也纳之前。
我隔壁的房间里住着一个三十五岁左右的金发男人,我在走廊里碰到过他,后来认识了他。他叫什么?好像是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之类的名字。
他总是衣冠楚楚,衣扣眼里戴着一枚勋章。他多次请我到旅店旁边一家叫“玫瑰花蕾”的酒吧去喝一杯,我不敢拒绝。他好像很喜欢那个地方。
“这里氛围不错……”
他说话带齿音,出身良好的小伙子的那种齿音。他告诉我,他在北非的阿拉伯山区待了三年多,他在那里获得了勋章。但阿尔及利亚战争让他感到恶心,他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正常。他经常去接替他父亲,在北部的一个大纺织厂当头。
很快,我就发现,他跟我说的并不是真话。关于那家“纺织厂”,他含糊其辞。有一天,他自相矛盾地向我保证说,他毕业于圣梅西安学校,离开学校后马上就去了阿尔及利亚。然而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他只在英国念过书。有时,他的齿音不见了,代而取之的是水手的那种油腔滑调。
那个星期天晚上,我必须去蒙帕纳斯走走,那样才能让这个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突然从虚无中复活过来。我想起来,有一天,我们在雷恩路相遇,他在阴暗的圣普拉西德十字路口的一家咖啡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在瓦凡路的伊勒人小酒吧,人们好像见过那对夫妻。这个小酒吧在“海盗”的地下一层。斯堪的纳维亚的气氛和“海盗”明亮的木装修与这个黑人酒吧兼舞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下楼梯就知道了:从一楼的鸡尾酒和挪威冷盘,很快就潜入到马提尼克
 的舞蹈当中。T夫妇是在那里遇到那两个女人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在拉斯帕伊大街,面向当费尔—罗瑟洛的玛丽娜咖啡馆。我记得杜韦尔兹带我和雅克琳娜去过那里,就在拉斯帕伊大街的路口。那次,我也同样不敢拒绝他的邀请。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天天逼我们俩星期六晚上去他的一个女友家,坚持要把她介绍给我们。
的舞蹈当中。T夫妇是在那里遇到那两个女人的吗?我觉得应该是在拉斯帕伊大街,面向当费尔—罗瑟洛的玛丽娜咖啡馆。我记得杜韦尔兹带我和雅克琳娜去过那里,就在拉斯帕伊大街的路口。那次,我也同样不敢拒绝他的邀请。在差不多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天天逼我们俩星期六晚上去他的一个女友家,坚持要把她介绍给我们。
她前来给我们开门,在半明半暗的前厅,我看不大清楚她的脸。我们走进客厅,里面的豪华陈设让我吃惊,与杜韦尔兹在德朗布尔路的小房间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他在那儿给我们作了介绍。我忘了她的名字:一个容貌一般的褐发女人,其中的一边脸,靠近颧骨的地方,横着一道很大的伤疤。
我和雅克琳娜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杜韦尔兹和那个女人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她应该跟杜韦尔兹的年龄差不多:三十五岁的样子。她好奇地打量着我们。
“你不觉得他们两个都很可爱吗?”杜韦尔兹带着齿音说。
她盯着我们,然后问:“想喝点什么?”
我们之间有点放不开。她给我们端来红酒。
杜韦尔兹喝了一大口。
“你们放松点,”他说,“她是我的一个老朋友……”
她羞涩地投来一个微笑。
“我们甚至差点结婚。不过,她后来不得不嫁给另一个人……”
她没有皱眉头,而是在椅子上坐得笔直,手里端着酒。
“她丈夫常常不在……我们四个可以乘机出去……你们说怎么样?”
“去哪?”雅克琳娜问。
“随你们的便……我们甚至没必要出去。”
他耸耸肩。
“我们在这里很好……不是吗?”
她一直在椅子上坐得很直。她点着一支烟,也许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安。杜韦尔兹又喝了一口红酒,然后把杯子放在矮桌上,站起来,向她走去。
“她很漂亮,是吗?”
他把食指放在她脸颊的伤疤上,然后解开她衬衣的扣子,抚摸着她的乳房。她并没有生气。
“我们曾经遭遇过非常严重的车祸。”他说。
她突然一下拨开他的手,重又朝我们笑了笑:
“你们一定饿了……”
她的声音很严肃,好像有一点点口音。
“你能帮我把晚餐端到这里来吗?”她有点不客气地对他说。
“当然。”
他们两人都站了起来。
“冷餐,”她说,“行吗?”
“很好。”雅克琳娜说。
杜韦尔兹搂着那女人的肩膀,把她拉出客厅,然后又从半开的门口伸头进来:
“你们喜欢香槟酒吗?”
他的齿音消失了。
“很喜欢。”雅克琳娜答道。
“马上就来。”
我们独自待在客厅里,几分钟。我搜肠刮肚,尽可能详细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由于炎热,朝着马路的落地窗是半开的。那是在拉斯帕伊大街19号。客厅的角落放着三角钢琴。长沙发和那两张椅子都铺着同样的黑色皮垫。镀银的金属矮桌。一个好像是叫德韦或者是杜韦尔兹的人。脸颊上的伤疤。解开的衬衣。射灯或者说是手电强烈的光芒,它只照亮了一小块地方,一小段时间,其他的一切仍处于黑暗之中,因为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事件的结果,准确地说,是不知道那两个人的情况。
我们悄悄地走出了客厅,甚至连门都没有关,就下了电梯。刚才,我们乘坐了电梯,但不是吉塞尔·T说的那种红色的电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