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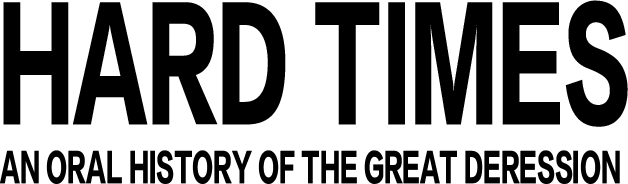
我们曾穿着卡其军装,
嗨,看上去真棒,
扬基歌歌声嘹亮。
五十万只靴子踏着沉重的步子,
我就是那年轻的鼓手。
喂,你还记得吗?他们叫我阿尔——
一直都叫我阿尔。
喂,你还记得吗?我是你的兄弟——
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
歌词和轻体诗作者。他曾为以下作品写过歌:《彩虹仙子》(Finian's Rainbow)、《大胆的女孩》(The Bloomer Girl)、《牙买加》(Jamaica)、《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和《卡罗尔伯爵的浮华世界》(Earl Carroll's Vanities)。
我可不喜欢窝在左岸的阁楼上嚼着大葱过日子。我喜欢创作的时候有个舒适的环境。于是,我下海经商,有个同学跟我一起。我想再干个一两年就该退休了。啪,结果股市大崩盘!血本无归。那是在1929年。我只剩下一支铅笔。
幸运的是,我有一个朋友——艾拉·格什温(Ira Gershwin) ,他对我说:“你还有支铅笔。拿上你的押韵词典,开工吧!”我按他说的做了——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我就到处写轻体诗,一次赚个十美元。当时的大学生都对轻体诗、民谣和十四行诗感兴趣。这是在三十年代早期的时候。
,他对我说:“你还有支铅笔。拿上你的押韵词典,开工吧!”我按他说的做了——反正也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我就到处写轻体诗,一次赚个十美元。当时的大学生都对轻体诗、民谣和十四行诗感兴趣。这是在三十年代早期的时候。
股灾的时候我反而很安心,觉得如释重负。我非常讨厌做生意。当我发现自己可以把歌或诗卖出去,我又变回我自己,重新活过来了。其他人不会这么看问题,他们的选择是从窗户跳出去。
有人没了钱就跟丢了命一样。当我失去财产,创造力却迸发出来。我感觉自己才刚刚来到这个世上。所以,在我看来,这个世界变得美好起来。
股灾让我意识到商业才是最大的白日梦。作诗是唯一现实的谋生方式。靠你的想象力生活。
我们以为美国的商业就像直布罗陀巨岩(Rock of Gibraltar)一样牢靠。我们是一个繁荣的国家,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脚步。一栋褐砂石房子会一直存在。你将它传给自己的孩子,他们给它加上大理石墙面。这就是延续传承。如果你办到了,它就一直在那儿。突然之间,梦想幻灭,带来的影响是难以置信的。
那时,我会一个人沿着街道散步,总会看到等着领救济品的队伍。在纽约,威廉·鲁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救济食物发放处排的队伍最长。他派了一辆大卡车,车上有好几个人,还有几大锅热汤和面包。那些鞋上套着麻袋布的人围着市中心的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排起长长的队伍——足有好几个街区那么长,就那么等着。
在我最初的作品当中有一个滑稽短剧——《美国轶事》(Americana)。那是在1930年。《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的奥格登·雷德夫人(Mrs. Ogden Reid)嫉妒在赫斯特那里领救济的队伍比她那里的漂亮,也比她那里的长。这是一个讽刺剧。我们需要给它配首歌。
在舞台上,我们让那些人穿上破烂不堪的军装,在那儿呆呆地等。这时响起这首歌。我们得给想个歌名。要怎么创作才能让这首歌显得不那么伤感?你不能说:我妻子病了,我有六个孩子,股灾让我失了业,给我一毛钱吧。我讨厌这样的歌。我讨厌如此直白的歌。我不喜欢用怜悯的笔调去描述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当时有一种打招呼的方式很流行。在你经过的某个街区,总有一个可怜的家伙走过来说:“能给我一毛钱吗?”或者是:“能给我点儿东西去换杯咖啡喝吗?”……最后,每个街区、每条街道都有人在说:“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歌名。如果我能把这首歌写出来,那它就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人在乞讨一毛钱。
这个人在说:“我修过铁路。我修建了那座高塔。我曾为你去战斗。我是那年轻的鼓手。为什么我现在站在这里等着领救济?我曾经创造的财富都去哪儿了?”
这首歌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当然,除了想法和意义,歌还得有诗意。歌词要能引发人们的回忆。写歌就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然而,《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揭露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人为什么会变得身无分文,就因为像大萧条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或是疾病或其他让人失去安全感的事情?
这首歌里,这个人真正想说的是:我向这个国家投了点儿资,可该死的红利去哪了?难道是红利在说:“兄弟,能给我一毛钱吗?”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让我们认真聆听一下。它不仅仅只是悲惋同情。它没把他贬低为乞丐,反而是让他成为了一个有尊严的人,提出自己的问题——带着一丝愤怒。他应该愤怒的。
1931和1932年,每个人都会唱这首歌。乐队会演奏它,也录制了唱片。在罗斯福竞选总统的时候,它让共和党很是苦恼。有人让电台的工作人员不要大肆宣扬这首歌。有时候,他们试图直接禁止电台播它。不过为时已晚。这首歌已经深入人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