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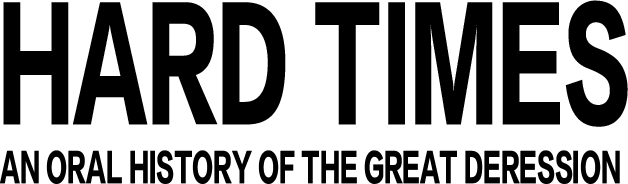
写下这几个字,史蒂芬·福斯特(Stephen Foster)的那首歌就开始在脑子里肆无忌惮地回旋。
这是1986年初,我却想起了“肮脏的三十年代(Dirty Thirties)” 。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很多年前,有一位议员就是这样定义那阴沉黯淡的十年的,我们将在本书中读到他的回忆。
为什么这会引发我们的回忆?《六点钟新闻报道》和最知名杂志的财经板块都在讲,通过政府的新闻稿来看,形势从未好转。即便是“繁荣年(boom year)”这个词也只是偶尔出现在标题中,权作一种乐观的预言。
没错,还有一些不大正式的警告严肃登场,都和“赤字”有关。除了这些通常无人相信的预言,没什么会让人失眠的事情。这个词比较晦涩难懂,会计才用得到。它同“饥饿”和“无家可归”完全不一样。这些让人不舒服的字眼总是出现在讲述“人情冷暖”的专题报道中,边上就是八卦专栏和戏剧新闻。
最开始出现了一些重大的情况。先来看看股市。“股市再次上涨12点……将道琼斯工业指数推向新高,说明对未来经济增长和公司收益的乐观情绪依然高涨。” 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是去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再来看看道琼斯指数。看看公司的广告,“责任”充斥其中。看看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生容光焕发的脸庞,他们煞有介事地拿着公事包,乘车赶往忙乱的办公室或是去更加忙乱的议院上班。
此外,还会不可避免地看到电视摄像机拍到的农民。你就知道这么一位:那是一个绝望的爱荷华人,杀死了自己的邻居,然后自杀。我记得一位银行小官员也曾遭遇这种事。这也不是他的错,他和杀死他的人一样心神错乱。这样的命运是他们自己不能左右的。
犹尼昂县拥有南达科他州最富庶土地。上个月,这里农场主住宅管理局(Farmers Home Administration)的一位年轻官员在自己的妻子、儿女及宠物狗熟睡的时候杀死了他们。随后,他去了自己的办公室,开枪自杀。他留下一份遗嘱:“这份工作给我很大压力,让我左边头痛。……”因为他是外地人,农场主住宅管理局显然认为比起南达科他当地人,他会更愿意以强硬的态度对待那些还不上贷款的本地农场主,所以将他派遣到本州各处去工作。
“我朝谁开了枪?”穆勒·格雷夫斯(Muley Graves)惊呼道。他是斯坦贝克(Steinbeck)笔下一个几近癫狂的“奥客” ,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被“拖拉机”赶离了自己的土地。镇上的银行职员回答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他自己都快要疯掉了。
穆勒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那个爱荷华人是八十年代的一个小农户。他们之间虽然隔了半个世纪,但导致他们穷途末路的原因却是一样的:还不起钱。
自大萧条以来,还没有个体农场主经受过这样的艰难与绝望。数以万计的人越来越消沉,正品尝着愤怒的葡萄。如果政府不施以援手,他们就会从别人那里寻求帮助。因此,身边总是不乏骗子的存在。
科尔尼,内布拉斯加州——在一间寒冷黑暗的粮食仓库里,二百个来自中西部的男男女女蜷缩在毯子底下,认真地听一个高个子男人讲话。他身穿黑色西装,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拿起武器保卫一无所有的农户。三十二岁的拉里·汉弗莱(Larry Humphrey)长相英俊,还带着点儿稚气。他说道:“基督告诉我们,他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当银行体系垮掉,亮出武器是再理所当然不过的事情。……人所周知的是,世界上的大多数银行都是犹太人开的。……”
在三十年代,乡下也曾弥漫着愤怒情绪,也曾出现过武装斗争,但两者是有差别的。“地方民团(Posse Comitatus)”和“雅利安国(Aryan Nation)”被当成小丑并有转移视线之嫌,让人从麦地里轰走了。人们多多少少知道根本原因之所在,但这种认识在接下来的五十年里已经不剩下什么了。三十年代的农户将矛头对准了华盛顿。
南达科他州的埃米尔·罗瑞克斯(Emil Loriks)回忆道:“在十到十一个州里,冲突一触即发。你几乎可以闻到火药的味道。当爱荷华的州长赫林(Herring)要出动国民警卫队时,米洛·雷诺(Milo Reno) 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说:‘等等!我不会让自己的双手沾染上无辜民众的血。’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农民离开75号高速公路。那里可能聚集了上千人。雷诺在苏城召集了一次会议,来了大约三万农民。我们决定前往华盛顿,勉强接受它的一个农场计划。如果胡佛在1932年不发挥点儿作用,我们就遇上真正的麻烦了。”
当时和现在的区别:在三十年代,政府确认一项需求便施予援手;现在,政府看到一种表象,报之以微笑。拉里·汉弗莱看到一颗苦果,已经熟透,等待采摘。
芝加哥南郊区最近发布的一份公报显示,美国钢铁公司的南部工厂准备解雇六千人。这样一来,在岗工人只剩下一千名,也只是暂时在岗而已。这算不得意外。钢铁行业的人都知道这是迟早的事:重工业里又多了好几千个无事可干的人。
艾德·萨德洛夫斯基(Ed Sadlowski)是一名工会领导,他的祖父、父亲还有他自己都是钢铁工人。最近,他驾车载着我在工厂里转了转。我就像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在电影《伯克利广场》(Berkeley Square)里扮演的主人公一样,进入了另一个时空。这位英国人发现自己成了乔治四世的臣民。而我发现自己回到了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治下的日子。
烟囱不冒烟。空中也不再出现橘色的火光。停车场空荡荡的。不管你的视力有多好,连一辆雪佛兰或福特车都看不到。偶尔会发现一辆废弃的破旧老爷车,这样的画面也会让人想起三十年代。我们的座驾是方圆几里之内唯一在行驶的车辆。只看到一条流浪狗,不见人影。那天算不上很冷,事实上,天气暖和得有些反常,让周遭的一切显得愈发萧条。
那片街区的店铺也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三间木板条搭建的铺子。艾德指给我看一家成衣店,挂着“开门营业”的牌子。“老板下个月就要关门大吉了。”
南芝加哥加入了扬斯敦、约翰斯敦和加里的阵营。八十年代前后的钢铁城变得像三十年代的鬼城一样。最近,我在一家艺术电影馆观看了威拉德·范·戴克(Willard Van Dyke)1938年拍摄的纪录片《山谷之城》(Valley Town)。它向我们展现了大萧条时期的兰卡斯特(宾夕法尼亚州),冰冷死寂。一时间,时光仿佛倒流,我看到了萨德洛夫斯基的南芝加哥。
此去何往?下一站是何方?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在他著名的长诗里提出了这些问题。他呈现了一个群体的集体回忆,跨越了好几代人。他不相信一代人会完全失忆。现在,他会将他的诗重新命名为《人民,可能吧》吗?
起居室里的报纸越来越多,上周的、上上周的,捆得像流浪汉的铺盖卷那样。我能从中发现那些与牛市有关的标题。其中,一个与众不同的题目吸引了我的目光。发稿地,爱荷华州滑铁卢:“迪尔公司(Deere and Co.)将再解雇二百人,自10月以来,该厂已逾千人下岗。”文章引述了美国联合汽车工会(UAW)838分部丹·佩奇(Don Page)的一番话:“你总是在说情况不会变得更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丹·佩奇和总统先生似乎在不同的频道上,当然更不在同一个星球上。默多克新闻集团的标题积极正面:《辉煌重现》。子标题是:“美国正日益强盛——里根”。尽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不那么浮夸,但同样兴高采烈。
让我们回到那捆报纸。发稿地,纽约州斯克内克塔迪:“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的涡轮发动机部门将在今年裁掉至少一千五百个工作岗位……”1974年,该厂雇用了两万九千人。到了1980年,这个数字降到了一万七千以下。
翻到漫画版块,是著名的《布鲁姆县城》(Bloom County)。作品采用的是旧图新画的手法,几乎不着痕迹。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发布了一条很严肃的声明:一千七百名空乘人员将被裁减,留下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将下调20%。运输工人工会(Transport Workers Union)则表示实际工资的降幅达到了32%。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 T)也发布了一项声明。它并没有出现在公司的电视广告中。演员克利夫·罗伯逊(Cliff Robertson)再也没有必要出现了。公司位于奥罗拉的工厂将把员工人数从四千裁减到一千五。就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所说的那样,就是这么回事。
上周,就在我的办公楼附近,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绕着街区蜿蜒前行。起初,我以为他们是在等着买芝加哥熊队比赛的门票。一个街区之外,还排着一条这样的长队。这里大部分都是黑人,大约有两百号人。其中一个只有十九岁,告诉我他们都是来求职的。当天晚些时候,人事部的一位熟人告诉我一共只有五个空缺职位。
1931年,艾德·保尔森(Ed Paulsen)十九岁。他也是一名求职者,在旧金山找工作。“我早上五点起床,赶到码头区。在史倍克糖厂(Speckles Sugar Refinery)的外头,门外挤满了上千人。每一个人都很清楚这里只招三四个人。负责人带着两个保安出来说:‘我需要两个小工,另外两个下到坑里干活。’上千个人就像一群阿拉斯加犬一样去抢这几根肉骨头。最后只有四个人能得到工作。”
年轻的保尔森开始了他的流浪生涯,和他同样命运的还有好几百万人。他搭乘货车,一半的时间都待在货车车厢里,仅仅只有立足之地而已。也许在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或者鬼知道的什么地方,会有一份工作在等着他。
路易斯·班克斯(Louis Banks)是一位二战黑人老兵。他回忆道:“白人黑人都一样,因为大家都是一样穷。所有人都很友善,睡在流民露营地里。我们有时候会让一名流浪汉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哪个地方在招工。他会回来说:底特律,没工作。或者说:有人在纽约招人。有时候,一节货车车厢里会挤上十五到二十个人;有时会更多。还有女人,她们中的许多甚至会假扮成男人。唉,每个人都在搭车,满心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
十五年之后,《萨克拉门托蜂报》(Sacramento Bee)派出两名年轻的记者戴尔·马哈里奇(Dale Maharidge)和克尔·威廉姆森(Michael Williamson)启程上路。他们搭乘货车走了好几个月。长辈们曾向他们讲述过三十年代的事情。他们自己也研究了多罗西亚·兰格(Dorothea Lange)、沃克·埃文斯(Walker Evans)和其他人的摄影作品。他们看到了同样的面孔。威廉姆森说:“穷困潦倒的人看上去都差不多。”
他们也看到了挤得无法动弹的货车车厢。这些新的流浪者来自“铁锈带”、废弃的农场以及破产的小店铺。其中的许多人都曾投票给里根,因为“他让我们感觉不错”。现在,他们感觉不那么好,但很少有人怪到总统头上。他们讨厌被称作“失败者”,但现在别人就是这样叫他们的。在三十年代(至少回想起来是这样),他们被称作“受害者”。如果说当时和现在之间存在什么主要的差别,那就是在语言上。当时,在失意者面前,意气风发的人的言语透着不安,现在则是些微的蔑视。
一名流浪者说:“我不知道在美国贫穷也是违法的。”你知道在路易斯安那州在车里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波特兰在天桥下睡觉是违法的吗?你知道在劳德代尔堡从垃圾箱里找吃的是违法的吗?有人告诉马哈里奇和威廉姆森,那些垃圾箱里会投放老鼠药。
这并非像它看来那样令人吃惊。在三十年代,流浪是逮捕和拘留最常见的罪名。盗窃紧随其后。现在,根据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当工厂倒闭成为常态,盗窃和抢劫案件增加了一倍。
一位越战老兵带着他的妻子、两个小孩子和一顶帐篷四处奔波。他正在盘算一些自己难以接受的事情。“我他妈的努力去当一个好市民,之前从未干过违法的勾当,现在却想着去打劫那家7-11便利店。我不会为了给孩子弄口吃的,就去朝别人开枪。”
艾德·保尔森能理解他的想法。“在三十年代,每个人都是罪犯,真是该死!你总得活下去。从晾衣绳上偷衣服,从后门廊偷牛奶,偷面包。我还记得搭着一辆货车穿过新墨西哥州的图克姆卡里。我们短暂停留了一下。那里有一家杂货店,相当于现在的超市。我下了车,搞了些面包卷和饼干回来。那个男人贴着窗户冲我挥拳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激发了我们的狼性。你从别人那里抢东西,你不得不这么干。”
现在的报纸又在报道股市上又一个破纪录的日子。财经专栏欢欣鼓舞:“经济即将上交一份上佳的成绩单,让其他一切都只称得上‘平庸’。今年将比许多经济学家(其中一些在华尔街上班)愿意承认的要好上许多。”
唯有《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不那么乐观。它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赌场社会》(The Casino Society)。在这篇令人惊愕的文章中,作者以与其他知名期刊截然不同的笔调写道:“不,这不是拉斯维加斯或是大西洋城。这是美国的金融体系。交易额已经远远超出支撑经济所需的数额。借贷(好听一点儿的话,可称之为杠杆)正在失控。因为期货的存在,人们无须拥有股票便可投机倒把,操纵市场。结局便是:金融体系从投资转向投机。”
这篇文章给未来敲响了警钟。假如阿瑟·A. 罗伯逊(Arthur A. Robertson)还在,他一定能分辨出丧钟的声音,至少能听出警告的意味。他是一个实业家,“一个清道夫。曾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他二十四岁就成了百万富翁。他认识市场上所有的传奇人物,这些人“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转手给毫无戒备的普通民众”。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Ponzi) 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西德尼·J. 温伯格(Sidney J. Weinberg)回忆起1929年10月29日那天,他惊愕地吹了声口哨:“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我不忍心问他谁来宣布点什么,是埃米尔·库埃(Emile Coué)?是上帝?还是罗杰·巴布森(Roger Babson)?温伯格是高盛(Goldman-Sachs)的高级合伙人,同时还是总统顾问。
“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严重到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其真实价值。现在,拥有股票的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1929年深。”
现在有一种政府行为,但不是温伯格所想的那样。1929年股市崩溃后制定的条规已经放宽了许多。对我们的银行尤其如此。
潘妮·乐培霓(Penny Lernoux)在作品《我们信银行》(In Banks We Trust)描述了这令人心寒的一幕幕。1982年位于俄克拉荷马州的宾州广场银行(Penn Square Bank)倒闭,这可能就是个象征,当时马克斯兄弟(Marx Brothers)和W. C. 菲尔兹(W. C. Fields)正当流行。这条小鱼在疯狂追逐高利息债务人的过程中,吸引了一群群更大的鱼。我们永远不知道大通银行(Chase Manhattan)、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和花旗银行(Citibank)有多侥幸才逃过一劫。因为太侥幸反而让人感到不安。政府救了它们一命,但与1929年帮助那些被大萧条击垮的银行所采取的方式截然不同。
罗斯福新政(New Deal)的监管机构因为里根革命(Reagan Revolution)而瘫痪,激进的银行业务(这个词是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者所乐见的)成为常态。在营造出来的投机氛围中,银行成为了布鲁斯特(Brewster),慷慨地借出他们(我们)的资金,期望得到更丰厚的回报,结果是血本无归。
拉美国家是最大的债务国,欠着好几家美国银行的钱,数额高达3500亿美元。如果它们当中有一两个国家无法还上欠款(比如说巴西、阿根廷或墨西哥),就可能清空我们九大银行的资金。我们来谈谈恐慌,谈谈两三家或者全部九家银行的挤兑。
大卫·肯尼迪(David Kennedy)在多年之前被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任命为财政部长,三十年代初他曾就职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他表示:“1929和1930年,数千家银行倒闭。纽约有一家银行——美利坚银行(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在它倒闭之前有两百家小银行破产。因为它的存款来自于这些小银行。”
潘妮·乐培霓得出一个结论:“这样下去的结局会让1929年就像是一场生日派对。”
但是,我们也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告诉我们不管现在和当时有多像,未来根本没那么糟糕。詹姆斯·内桑森(James Nathenson)是芝加哥建筑商协会(Chicago Homebuilders Association)的前任主席,他和美国的现任总统一样看到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内桑森是芝加哥熊队的超级球迷,持有他们的季票。“如果熊队赢了比赛,我会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当作芝加哥楼市的一个积极信号。”他指的是即将开赛的超级碗(Superbowl)赛事。(熊队当然赢得了比赛。)
幸好,这座城市(这个社会)有着沃尔特·佩顿(Walter Payton) 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
的双腿、吉米·麦克马洪(Jim McMahan)的胳膊以及威廉姆·佩里(William Perry)的块头。别管南芝加哥那些不冒烟的烟囱和木板条搭建的店铺,别管那两百多个排着长队求职的年轻人,也别管什么历史。内桑森的乐观丝毫未减:“在芝加哥,一旦我们成为赢家,就会在生活中开始像赢家那样去思考问题。如果成了输家,我们的态度难免会染上失败者综合征。”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也说不出比这更精辟的话。
有很多人起先像“赢家”一样思考的人,直到突然有一天变成了输家,令人猝不及防。他们的说法会出现在下面的章节中。西德尼·温伯格回忆道:“就像是晴天霹雳。”风向标是被拆除了吗?暴风雨来得征兆全无?我们是否从之前的痛苦经历中吸取教训?对有些人来说,这经历仿佛就在昨天;对另一些人而言却像是过了好几个世纪。一位年轻姑娘的祖父母曾向她讲过大萧条时候的事情,她说:“对我来说就像童话故事一样,有点儿像睡前讲的那种故事。”
吸取了教训?就像那个站在法官面前的醉汉,当被问道是否承认有罪,他的答复就是:保持缄默。
我们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在回忆中可能是最穷的。也许过去一个时代的幸存者的记忆可以用来提醒他人或者他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