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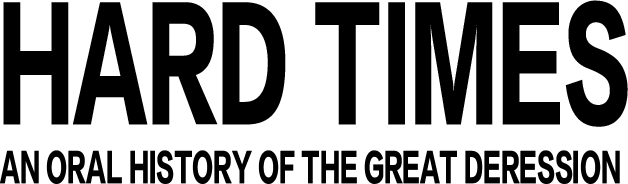
他在不同阶段曾经担任过: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助理国务卿、芝加哥大学副校长、大英百科全书出版人(经济发展委员会的发起人之一……“我们在三千个美国小镇做过调查研究,为转为和平时期的生产做计划,这都是源于大萧条时期的经历……”)。
他的理想是在三十五岁以百万富翁的身份退休。三十六岁时,他做到了。
1929年,他是洛德暨托马斯广告公司(Lord Thomas)的副总经理,公司老板是阿尔伯特·拉斯克尔(Albert Lasker)。在他眼里,阿尔伯特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广告人”。
1929年6月,我离开芝加哥,几个月之后股市就崩盘了。切斯特·鲍尔斯(Chester Bowles)和我组建了我们自己的公司 ,办公室有一千七百平方英尺。公司就我们俩,还有几个姑娘。1929年7月15日,股市指数在这一天飙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办公室有一千七百平方英尺。公司就我们俩,还有几个姑娘。1929年7月15日,股市指数在这一天飙升至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在我到处拉业务的时候,我的图上出现了一个十字叉。左边一根线从左上角一路下滑到右下角,这是股市指数;另一根线代表本顿暨鲍尔斯广告公司(Benton Bowles)的业绩,从左下角一路上扬到右上角。刚好形成一个十字叉。股市下挫崩盘的时候,我们的广告公司却一举成名。1935年,我卖掉公司。当时,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栋办公大楼,也是最赚钱的办公大楼。
我的朋友比尔兹利·拉姆尔(Beardsley Ruml)推崇这么一条理论:在灾难中进步。在所有的灾难中,都存在潜在的好处。我就获益于大萧条。其他人也一样。我想那些卖红墨水、红铅笔和红蜡笔的人也是大萧条的受益者。
那时候我只有二十九岁,鲍尔斯才二十八。经济好的时候,大客户都不愿意听年轻人的,不愿意接受新的创意。大多数的华尔街大鳄都将1929年称为一个“新纪元”,认为持久的繁荣将把我们推向新的高度,而现在不过只是个开始。
那一年,白速得牙膏(Pepsodent)的销量降了一半。牙医们都在说“白速得牙”,他们说这款牙膏太粗粝,会破坏牙釉质。老式广告都不起作用了。当时我还在芝加哥,为洛德暨托马斯广告公司工作,白速得是我们的客户。
1929年5月的一天,我离开了办公室。我们的办公室在新落成的棕榄大厦(The Palmolive Building) ,我们是它的第一批租客。我步行回自己的公寓。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我听到广播里黑人的声音
,我们是它的第一批租客。我步行回自己的公寓。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我听到广播里黑人的声音 从各家各户飘到大街上。我回转身,又回到街面上。当时有十九户人家在听收音机,十七家听的是《阿莫斯和安迪》(Amos and Andy)。这可能是广播历史上的第一次听众调查。
从各家各户飘到大街上。我回转身,又回到街面上。当时有十九户人家在听收音机,十七家听的是《阿莫斯和安迪》(Amos and Andy)。这可能是广播历史上的第一次听众调查。
第二天早上,我跑去见拉斯克尔先生,告诉他我们应该马上为白速得买下《阿莫斯和安迪》的广告时段。我们当时就买了。后来,我就去了本顿暨鲍尔斯广告公司。
白速得在广播节目中出现了,而这个节目在几周时间里就成了美国广播史上最轰动的节目。当时比《阿莫斯和安迪》更有名的只有林德伯格(Lindbergh)飞越大西洋的新闻。白速得的销量一路飙升。
华尔街股灾也没有影响到白速得。它的销量翻了两三倍。这个品牌后来以天价卖给了利华兄弟公司(Lever Brothers),拉斯克尔也从中大赚一笔。本顿暨鲍尔斯广告公司也为了我们的客户大张旗鼓地进军广播领域。
我们并不知道当时大萧条已经来临。只是客户们的产品销量都大幅下跌,他们开始愿意听听我们的新点子。经济好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让我们进门。因此,我们算是大萧条的获益者。我的收入每年翻一番。我离开本顿暨鲍尔斯广告公司的时候,赚了将近五十万美元。在当时,电影大腕都赚不到这么多。那是1935年。大萧条与我擦肩而过,所以要聊大萧条,我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阿莫斯和安迪》的诞生与我没有丝毫关系,我只是觉得应该买下它的广告时段。但是《麦斯威尔演艺船》(Maxwell House Show Boat)这个节目,我很是花费了一番心血。它后来成了排名第一的广播节目。听众都信以为真了,以至于在头几个星期,有十到十五万人跑到孟菲斯和纳什维尔的码头,因为我们说“演艺船”会在那里停靠。
《演艺船》是1933年开播的,当时是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可是,麦斯威尔咖啡的销量在六个月之内飙涨85%,而且还在增长。因此,麦斯威尔根本觉察不到什么大萧条。连锁店里卖的咖啡几乎一样好——尝不出差别,而且价格要低得多。可是广告让麦斯威尔咖啡平添魅力,让大家觉得它要好喝得多。它的销量翻了一番、两番。
在《演艺船》中,我们尝试了一种之前从未有过的做法——两人同饰一角。我们找来一位性感歌手,她可能不是一个好演员。然后又请来我们所能找到的最性感的女演员,台词由她来讲。她的声音让听众的心都沉静下来,变得温暖,马上就要融化的感觉。然后,女歌手开始唱歌。
戏剧工作者怎么都想不出这个点子。广播让它成为可能。这是广告界的新人想出的新创意。好莱坞反对这个,齐格飞(Ziegfeld)也不擅长这个 。广告人成就了广播。我们的想法无拘无束。我们可不知道不能让两个不同的人扮演同一个角色。
。广告人成就了广播。我们的想法无拘无束。我们可不知道不能让两个不同的人扮演同一个角色。
我们继续制作像这样的节目,都成了大热门。比如,《棕榄美丽魔盒》(The Palmolive Beauty Box)。我从大都会歌剧院挑了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歌手——格拉迪斯·斯沃索特(Gladys Swarthout),把她打造成了一个大明星。我们又找了一个出色的女演员,当时她的周薪是一百块,由她来说台词,而格拉迪斯用她极具魅惑力的嗓子来演唱。有人告诉我不能用她,因为她不是女高音,而这部分的音调太高了。我冷冷地说:“那就重写,把调子写低点儿!”搞戏剧的人不会想到这个……我们在广播领域大获全胜,就因为我们不熟悉它的游戏规则。
这是大萧条期间的新花样。产品销量上去之后,那些大客户才开始正眼瞧我们:想出这些新点子吸引年轻人的新人都是谁啊。我们看上去就像大学生,但他们还是付给我们大笔大笔的钱。这就是鲍尔斯和我逃过大萧条这一劫的缘故。
大萧条之前在广告界呼风唤雨的那帮人渐渐销声匿迹,他们做生意的方法就是陪客户打高尔夫球。大萧条加快了营销研究的应用。在为拉斯克尔工作的时候,我捣腾出新的方法,后来在自己的公司沿用。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 引入新的标准。他曾经称呼我为前辈,因为我是广告行业的开拓者,搞清楚了消费者的需求。
引入新的标准。他曾经称呼我为前辈,因为我是广告行业的开拓者,搞清楚了消费者的需求。
麦斯威尔咖啡的广播节目促使商业广告出现了变化,这是我永久的遗憾。当我们让安迪船长喝着咖啡,咂摸着嘴唇,你都能听到咖啡倒入杯中时咖啡杯清脆的叮当声以及咖啡汩汩流动的声音。它将表演和演员引入广告。这是一次变革,但我们当时并没有料想到它日后的全部影响。在它的影响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广告歌和现在肆无忌惮的广告。就像在芝加哥大学为我举办的宴会上,鲍勃·哈钦斯(Bob Hutchins)在介绍我时所说的那样——我发明了我现在要为之道歉的东西。
1937年,我在股票投资上大概损失了十五万,因为我对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言听计从。我的意思是——购买别家公司的股票,这是傻瓜才干的事情。我打算买下自己的公司。我不去运作它,只是有它在名下,由我制定策略。我四处打探,买下了缪扎克公司(Muzak)。要不是大萧条,我绝不可能买到这家公司。它当时已经破产,经营不下去了。那是在1938年前后。
在纽约,只在酒店和餐馆能听到缪扎克音乐 ,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现场音乐的替代品。吉米·彼得里洛(Jimmy Petrillo)恨它到骨子里,视其为音乐家的头号敌人。我对自己说:其他地方也应该播放这种音乐。
,人们只是把它当作现场音乐的替代品。吉米·彼得里洛(Jimmy Petrillo)恨它到骨子里,视其为音乐家的头号敌人。我对自己说:其他地方也应该播放这种音乐。
我去见我们的五个销售员,当时我们总共就五个销售员。他们对我说:“我们已经占领了纽约80%的市场。再不可能卖到别的地方去了。”我说:“你们怎么不试试理发店和医生办公室?”“不,你不可能在那样的地方播放缪扎克音乐!”我说:“你们五个都这么想吗?”他们当中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在公司才干了六个星期。他说:“不,我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说:“那么,你们另外四个最好另谋高就,我要让这位年轻的先生做公司的销售经理。我们一起把缪扎克推向新的领域。”
这个决定让缪扎克为我们大赚了一笔,现在它的利润是一年两百万。我们没有为它额外投资,是大萧条让我挖到了这个金矿。
除开那些常规的公共空间,第一个安装缪扎克的是纽约的一家银行。银行经理说:“上夜班的工作人员待在亮着电灯的办公室里觉得很压抑。他们想要一台收音机,我不同意。我说给他们装上缪扎克。现在整个银行都能听到音乐了。”有一个姑娘,在银行个人贷款部门做前台接待。人们在那里小额贷款,除非还得出分期付款,不然就一去不返。姑娘对我说:“缪扎克音乐让这个地方变得没那么可怕。”
我想出了这样的句子:“不需要聆听的音乐”。这是我推销缪扎克时用的广告语。这种不需要聆听的音乐,缪扎克当属首创。它是一种新型的背景音乐。我母亲是个出色的音乐家,就是因为这个她对缪扎克不屑一顾。任何稍懂点儿音乐的人都对缪扎克非常不齿。
我是个没有乐感的人,所以,我才对广播那么有一套。在美国,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没什么乐感。耳朵迟钝到完全没有乐感。我非常喜欢鲁迪·瓦利(Rudy Vallee)、平·克劳斯贝(Bing Crosby)和其他通过广播大红大紫的明星。
二十年来,我一直都是缪扎克公司的老板。后来,我花光了自己第一个一百万,手头缺钱,就把它卖了,赚了好几百万。
缪扎克会让人上瘾。买走缪扎克公司的那个人给了我四套系统装在家和办公室里。我总是把缪扎克开着。因为没开的时候我总能发现,可当它开着的时候我反而没有察觉。这就是所谓的不需要聆听的音乐。它就是这样让人上瘾的。
每个生意人都希望自己的产品能让人上瘾。这也是香烟、可口可乐和咖啡一直卖得这么好的缘故。就连肥皂都会让人上瘾。我在广告界从业期间,肥皂是我经手过的最主要的产品。
在本顿暨鲍尔斯广告公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再干六个月,再干三个月就行了。但我们的业务每年都翻一番。每年我都会讲:一旦拉到这个新客户,我就不这么卖命了。如果能预见未来六年的情况,没有哪个聪明人能忍受我所忍受的一切,即便可以赚到一百万。
1937年秋天,我成了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我的日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我开始阅读经济学教授的文章,并与他们结识;开始对教育广播感兴趣;开始举办和主持“芝加哥大学圆桌会议”。但是,勤奋工作的习惯已经根深蒂固。虽然受折磨的方式跟以前不一样了,但每周都工作很长时间,很辛苦。不过,我的傍晚跟以前过得大不一样。
大萧条对芝加哥大学的影响非常大,医学院和附属诊所格外耗钱,导致亏损越来越严重,捐款却越来越少。
沃尔格林先生(Walgreen) 让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他指责大学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一时间,芝加哥的所有报纸几乎都在批评、嘲弄我们学校。大萧条让人们对共产主义更加敏感。
让他的侄女从芝加哥大学退学,他指责大学向学生灌输共产主义思想。一时间,芝加哥的所有报纸几乎都在批评、嘲弄我们学校。大萧条让人们对共产主义更加敏感。
我打算去拜访沃尔格林先生,跟他谈谈这个事情。芝加哥大学从来没人干过这种事情。我找到以前的一个客户,他把我引见给沃尔格林先生。我说:“沃尔格林先生,这些伟大的学校都是靠像您这样的人的无私捐助才能维持下去。您为什么不伸出援手,让芝加哥大学按您预想的那样——教授与美国制度相关的课程呢?”是哈钦斯给我出的这个主意。我问他:“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说:“太简单啦。让他给学校捐笔钱。”在我们聊天之后的第二天,哈钦斯跑去沃尔格林先生那里,搞来五十万美元。我们与沃尔格林先生之间的麻烦就这么解决啦。
你觉得大萧条对人们的分期付款购买行为有什么负面影响吗?
《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主要靠分期付款购买,我们的整个商业模式就是这样。我们并不觉得信用是个问题,尤其是在大萧条这个时期。失业的人越多,我们就越容易找到出色的销售人员。失业的人越多,我们的求职者也就越多。随着销售人员的增多,这样也就抵消了消费者减少产生的影响。在灾难中进步。
他的办公室位于纽约一幢摩天大厦的顶楼,墙上挂着许多画作和照片。其中有一幅约翰逊总统的画像,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朋友——一位为国效力的爱国者。”还有一幅是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的画像,上面写着:“献给我的朋友阿瑟·罗伯逊,并致以美好的祝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照片上写着:“献给我的朋友阿瑟·罗伯逊。”此外,还有美国的达官显贵们送的纪念品。
他讲述了早年间的经历,那时他做过战地记者、广告人,还有工程师。“我们修建了纽约地铁的第六大道段。我的职业生涯很特别。我现在是个实业家,曾在德国收购了几家搪瓷工厂。我曾获得俄国政府的猪毛交易特许经营权。我把这些猪毛卖给户外广告公司做刷子。十九年前,我和几个合伙人花一百六十万美元买下一家公司。现在,我们已经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最近有人出价两亿要买这家公司,我们拒绝了。我是董事长、公司的掌控者,是我创建了这家公司。”
“我曾认真地考虑过在1928年三十岁的时候退休。二十四岁的时候,我的身家已经是七位数了。”
1929年,那确确实实是一个暗中搞鬼的赌场。为数不多的骗子从众多上当的人那里占尽便宜。交易就像是用昂贵的狗来换昂贵的猫。1921年的时候经济出现衰退,1924年开始好转。之后,股市一路攀升,就像没有上限一样。失去理智的金融市场让庞兹看上去就像个业余玩家。我看到擦鞋工用五百块定金购买价值五万块的股票。一切都是赊账买的。
现在,如果要购买价值一百块的股票,你得支付八十块,另外二十块由经纪人支付。当时,你可以只付八块或十块。股市崩盘的原因正在于此。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能酿成巨祸,因为人们没钱支付另外的九十块。那时不像现在有这些控制措施。你只能平仓:心不甘情不愿的卖家和勉强的买家。
那个时候,有一家香烟公司的股票卖到每股一百一十五块。股市崩溃了。公司老总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借他两亿。我回绝了,因为我当时也得保护自己以及密友们的资产。他的股票跌到两块钱一股,他也从自己位于华尔街的办公室纵身跳出窗外。
还有一个人,他的公司有一千七百万美元现金。他是自己所在行业的领军人物之一,手下的三四个品牌现在都家喻户晓。当他的股票开始下跌,他出手补救。第二波大跌之后,他彻底破产了,欠三家银行的钱,每家一百万。
银行的处境和他一样,只不过政府伸出了援手,把它们拉出火坑。突然之间,它们变得高你一等,接管了欠它们钱的公司业务。它们解雇原来的专家,换上自己人,而公司正是由这些专家一手打造的。我从银行手上买过一家这样的公司。它们把公司卖给我是为了止损。
最糟糕的公司经营者莫过于银行家。说到审查资产负债表,他们是专家。职业培训让他们保守谨慎,因为他们借你的钱是别人口袋里的。所以,他们连公司运营过程中必要的适当风险都不愿意承担。因为亏损太多,他们急于甩掉身上的包袱。我最近把那家公司卖了两百万,1933年买的时候才花了三万三千美元。
三十年代初,我可是有名的“清道夫”。我买下那些因为破产而被银行接手的企业,这是我最赚钱的几个时期之一。这个时期不乏传奇人物,一百万在他们眼里只是零花钱。三四个这样的人聚在一起,将一只股票的价格抬到高得离谱,然后再丢给毫无戒备的小股民接盘。当听说像杜兰特(Durant)或杰西·利弗莫尔(Jesse Livermore) 这样的人物在买某一只股票,所有的人都会跟风。他们知道股票价格会被抬起来。唯一的问题是在他们抛出股票之前逃出来。
这样的人物在买某一只股票,所有的人都会跟风。他们知道股票价格会被抬起来。唯一的问题是在他们抛出股票之前逃出来。
杜兰特,通用汽车的创始人,两度拥有了通用汽车,又两次失去了它……通用公司当时的股票价值已超过十亿,相当于现在的三四十亿。他开创了自己的汽车公司,之后公司破产。当股灾到来,他举手投降,就像其他人一样。我最近一次得知他的消息是他开了一家保龄球馆。一切不过只是股票账户上的数字而已。那个时候,每个人都希望阳光能永远灿烂下去。
没错,就是1929年10月29日,股市大乱。那天,我接到了十七八个朋友的电话,他们听上去都很绝望。借钱给他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转手把钱交给股票经纪人,而第二天情况会变得更糟。到处有人自杀,这种感觉太可怕了。都是我认识的人,真是让人伤心。你在某天看到股价还是一百美元,第二天就变成了二十块、十五块。
在华尔街,人们跟行尸走肉一样。有点儿像电影《死神假期》(Death Takes a Holiday),天昏地暗的感觉。你昨天还看见一个人开着凯迪拉克,如果够幸运的话,他现在还能有钱搭车。
一个朋友对我说:“如果情况继续恶化下去,我们只能去讨饭啦!”我问他:“向谁讨?”
许多股票经纪人并没有亏钱。他们的客户破产了,他们却因为拿了佣金大赚一笔。只有那些拿自己的钱去博弈或是没能及时卖空亏钱账户的经纪人才元气大伤。经纪业务也自然而然地一落千丈,股票经纪公司只好勒紧裤腰带,关门裁员。
银行活期贷款的利率是18%,借出去的钱被拿来买股票,而股息可能只有1%到2%。他们觉得股价能一直上涨。每个人都这么指望。曾经有股票经纪人从我这里借钱,利率是22%。22%啊!
至于那些在公共事业领域打下江山的人,他们会先买下一个小规模的公共事业公司,鼓吹它利润惊人,然后再把它卖给自己名下的上市公司。塞缪尔·英萨尔们就是这样累积巨额财富的。导致英萨尔帝国坍塌的原因和导致这些失去理智的投资者破产的原因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有多少钱,都会层层加码,以求赚得更多。
我的好友约翰·赫茨(John Hertz)一度拥有黄色出租车公司(Yellow Cab)90%的股票。此外,他还拥有洛杉矶柴克出租车公司(Checker Cab)以及芝加哥地面电车公司(Surface Lines)的公交车。他的资产足有四五亿。一天,他邀我一起坐游艇出游。在那里,我结识了两个声名显赫到让我敬畏的人物:杜兰特和杰西·利弗莫尔。
我们聊了他们手头的股票。利弗莫尔说:“我相信我手里的股票将来足以掌控IBM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 。”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可操心的?”他回答道:“可是我只懂股票,不会做生意。”于是,我又问:“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都存了一千万,任何人都不能动用。”他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年轻人,如果你赚不到大钱,有一千万又有什么用呢?”
。”我问他:“那你还有什么可操心的?”他回答道:“可是我只懂股票,不会做生意。”于是,我又问:“像你这样的人是不是都存了一千万,任何人都不能动用。”他看了我一眼回答说:“年轻人,如果你赚不到大钱,有一千万又有什么用呢?”
到1934年,他已经先后经历了两次破产。我的会计问我要不要帮利弗莫尔一把。他破产了,想在股市里重振雄风。他总能东山再起,连本带利地还掉借款。我同意了,借给他四十万。到1939年的时候,我们赚够了钱,每个人税后能分到一百三十万的利润。杰西这个时候已经快七十岁了,经历了两次破产。我问他:“是不是兑成现金好一些?”在那个时候,每年有五万块就能过上国王般的生活。他说,就这点儿钱他是过不下去的。
我卖光了股票,把现金装到口袋里,剩下杰西继续在股市打拼。他一直跟我讲他马上要在股市大赚一笔。人称“卖空本”的本·史密斯(Ben Smith)当时在欧洲,他告诉杰西不会有战争爆发。杰西信了史密斯的话,做空 粮食。他能让自己手里的每一块钱去赚更多的钱。
粮食。他能让自己手里的每一块钱去赚更多的钱。
我到阿根廷的时候,听说德国已经入侵波兰。可怜的杰西在电话里说:“阿瑟,你得救救我。”离得这么远,我什么也没有答应他。我知道给他钱就是打水漂。
几个月之后,我回到纽约,杰西在办公室等着我。这个可怜的人已经输得血本无归。他跟我借五千块,我当然给了。三天之后,杰西去荷兰雪莉酒店吃早餐,在盥洗室开枪自杀。他们找到了他为那五千块给我写的借据。就是这个人,他曾说过:“如果你赚不到大钱,有一千万又有什么用呢?”杰西是最出色的股票交易人。他知道每个粮食种植地区每一种作物的情况。他是个孜孜不倦的好学生,不过总是过于乐观。
你有预感股市会在1929年崩盘吗?
我在5月就感觉到了,为自己保住了一大笔钱。5月的时候,我抛售了大量股票。那是一种很可怕的感觉。不过,我没有卖光,最后也损失惨重。
1927年,当我得知林德伯格在筹划他飞越大西洋的壮举,就买进了莱特航空(Wright Aeronautical)的股票。我听说他驾驶的飞机就是莱特公司制造的。当时,我住在密尔沃基 。办公室距家只有一英里左右。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股票经纪人联系。等我到办公室,已经赚了六十五个点。所有一切发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这确实挺吓人的。无论你买什么股票,似乎都涨起来没个头。
。办公室距家只有一英里左右。每次离开家的时候,我就开始跟股票经纪人联系。等我到办公室,已经赚了六十五个点。所有一切发生的速度是如此之快,这确实挺吓人的。无论你买什么股票,似乎都涨起来没个头。
有人说我们在重演1929年的悲剧,我不这么认为。现在有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和银行保险,人们知道自己的存款是安全的。如果每个人都相信这一点,就像相信假钞可以用是一样的。除非事发,否则就一直管用。
1932年,我在纽约的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 新租了一间办公室。热衷健康养生的麦克费登(MacFadden)创办了廉价餐馆。我非常欣赏一个同我做生意的黑人小伙。他承诺为七十五个饿着肚子的人提供食物。我六点就离开办公室,越过这七十五个人排的长队进到麦克费登的店里,为他们每个人支付七分钱。我每天都这么干。等着领食物的队伍,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只有1922年的德国能与之相提并论。看上去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新租了一间办公室。热衷健康养生的麦克费登(MacFadden)创办了廉价餐馆。我非常欣赏一个同我做生意的黑人小伙。他承诺为七十五个饿着肚子的人提供食物。我六点就离开办公室,越过这七十五个人排的长队进到麦克费登的店里,为他们每个人支付七分钱。我每天都这么干。等着领食物的队伍,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我觉得只有1922年的德国能与之相提并论。看上去就像没有明天一样。
我还记得银行假日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有个非常聪明的小舅子,做律师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对银行有不好的预感。我觉得我们应该手头多拿点儿现金。”就在银行关闭潮的两个月之前,我们决定把存在银行的所有钱都取出来,近一百万美元。我在俄亥俄州的克莱德有家瓷釉厂,他们用我的签名抵钱。我每个周六、周日都会送现金过去。我在密尔沃基的百货商场转一圈,如果他们付不出现金,我就开一张为期三十天的欠条,每欠一块还1.05块。
。我算是比较幸运的。我有个非常聪明的小舅子,做律师的。有一天,他对我说:“我对银行有不好的预感。我觉得我们应该手头多拿点儿现金。”就在银行关闭潮的两个月之前,我们决定把存在银行的所有钱都取出来,近一百万美元。我在俄亥俄州的克莱德有家瓷釉厂,他们用我的签名抵钱。我每个周六、周日都会送现金过去。我在密尔沃基的百货商场转一圈,如果他们付不出现金,我就开一张为期三十天的欠条,每欠一块还1.05块。
1933年,杰克·法克特被绑架的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合伙人、他夫人,还有从怀俄明州来的一个侄女正在夜总会跳舞。我们每个人的袜子里都藏了两万五千块的现金。我们准备第二天早上到克莱德去,我原本打算带十万块过去支付账单和工人工资。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两万五千块在跳舞。绑架杰克·法克特的绑匪索要的赎金正好是十万。这帮蠢蛋,如果抓到我们,他们就能拿到这么多钱了。
爵士音乐人,小号手,被比克斯·贝德贝克(Bix Beiderbecke) 钦点为接班人。二十年代末,他离开芝加哥,和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巴德·弗里曼(Bud Freeman)吉恩·克鲁帕(Gene Krupa)以及艾迪·康顿(Eddie Condon)一起来到东部。
钦点为接班人。二十年代末,他离开芝加哥,和班尼·古德曼(Benny Goodman)、巴德·弗里曼(Bud Freeman)吉恩·克鲁帕(Gene Krupa)以及艾迪·康顿(Eddie Condon)一起来到东部。
因为亏了钱,太多人从窗口纵身跳下。天哪,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几个人曾经议论过:这些人是疯了吗?钱是什么?我们是音乐人,钱对我们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什么都不是。生命、生活和享受生活才更重要。这些人亏掉了所有的钱,那又怎样?我们曾说过:“你还活着,不是吗?”他们可以从头再来。这是我们之前的想法。
事实上,我们不怎么想到钱。反正我个人是不会,因为我总能赚到钱。对我来说,一切都来得太容易。我自己觉得很惭愧。但我从来不为钱烦恼。如果有人缺钱,我很乐于施以援手。
我还记得我们乐队失业的时候。那是在1928年、1929年,华尔街股灾之前。比克斯还在保罗·怀特曼(Paul Whiteman)的乐队。我们已经七八周没活儿干了,手里也没剩下什么钱。天,我都快要饿死了,没钱买吃的。
他们邀请我们去聚会上表演,社会名流、有钱人举办的聚会。那里供应最好的威士忌和类似的东西,不过没吃的。(笑)只有各种各样的酒。我们会问:“有三明治吗?”
我们曾受邀参加在派克大街举办的一次聚会,班尼·古德曼和乐队其他人都去了。除了我们,还有怀特曼的整个乐队,比克斯·贝德贝克和所有人。我们喝酒,玩乐,即兴演奏。主持人是个大块头。我把比克斯叫到一边,向他求助:“比克斯,我们现在没活儿接。你能借我五块钱吗?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他打开钱包,里面有两张一百、一张五十的钞票。他非要把那两张一百的塞给我。我说:“不用,不要这么多,五块十块就够了,够买吃的就行。”他说:“小朋友,你拿去吧,等你们接到活儿干了,再还给我。”
后来,比克斯生病了,离开了怀特曼的乐队,回家休息了一段时间,完全没了收入。我当时参加了《混球》(Sons of Guns)节目,每周能赚二百七十五块。光是这个节目就能让我赚到这么多。一周赚三四百块是件很轻松的事情。我又有钱了。我和比克斯过去曾在一家地下酒吧见面。一天,我去了那家酒吧,他也在,身无分文,恶疾缠身。他说:“小朋友,你有钱吗?”我说:“当然,你需要钱?”我口袋里有一百七十五块。旧事重演。我给了他一张五十的钞票。我说:“给!”如果我有更多,我什么都会给他。他说他有一份工作,会还我钱的。五六天之后,他就死了。只有三十二岁,因为肺炎死的。
在那家地下酒吧里,我们听说了有些人过得不太好。管他的,你会掏出五十块,或者十块、二十块的,塞到他们口袋里,对他们说:“拿去用吧!”他们重新开工后,会把钱还来。就算不还,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过去都是这样的。我知道蒂加登(Teagarden) 是这样,比克斯也是这样,好多人都是这样。
是这样,比克斯也是这样,好多人都是这样。
当时是在国家禁酒期间。我们会在表演间隙溜进地下酒吧喝上一杯。一天晚上,我们进不了酒吧了。老天,警察就在外面。黑帮杀了三个人,都是上流社会的人,所以这家地下酒吧就开不下去了。警察偶尔也会象征性地来酒吧检查。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我猜酒吧也有警察的份。
一天晚上,有人走进中央公园酒店说:“有人中枪了!”那是阿诺德·罗斯坦(Arnold Rothstein) 。我们听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曾经看见这些人在酒店进进出出,那个时代所有的黑帮大佬,他们一直很喜欢我们。当然啦,我们又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到酒店来,下楼去地下室,吃饭,跳舞。
。我们听说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因为我们曾经看见这些人在酒店进进出出,那个时代所有的黑帮大佬,他们一直很喜欢我们。当然啦,我们又不给他们惹麻烦。他们到酒店来,下楼去地下室,吃饭,跳舞。
三十年代中期,全国各地的俱乐部和舞厅都会约请各种大乐队和小爵士乐队表演。“我们在一些很不错的地方演出,包括最高级的酒店,很赚钱。虽然有人找不到工作,但还是有很多钱可赚的。乐队里的乐手都聊些什么?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说姑娘。”(笑)在这段时期,他是芝加哥一家爵士俱乐部“三颗骰子”的主持人。
我们的节目还请了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 。她曾经唱过《奇异果》(Strange Fruit)。哦,实在太动听了。我和比莉相处得很好。有时,我会在后台读书给亚瑟·泰特姆(Art Tatum)
。她曾经唱过《奇异果》(Strange Fruit)。哦,实在太动听了。我和比莉相处得很好。有时,我会在后台读书给亚瑟·泰特姆(Art Tatum) 听。他在节目间隙弹钢琴。你知道,他看不见。我有时候会带书过去。他总是提起这个:“吉米,还记得你那个时候读书给我听吗?”他坐在那儿喝着啤酒,我就读书给他听。
听。他在节目间隙弹钢琴。你知道,他看不见。我有时候会带书过去。他总是提起这个:“吉米,还记得你那个时候读书给我听吗?”他坐在那儿喝着啤酒,我就读书给他听。
我从来不纠结于一个人的肤色。如果你会唱歌或演奏,那就行了。我从来不知道情况已经变得那么严重,直到我在1934年去了新奥尔良。我们表演的地方有个赌场——森林俱乐部。附近有一些警察,因为这地方有可能被打劫。他们甚至在高处架了一挺机关枪。所有人都带着枪。
一天深夜,我们都在外面喝酒。还有三四个警察。其中一个说:“那边有个黑鬼,我去逮住他,打爆他的头。”他们朝那个人走过去。我感觉他是真的要开枪。我把他的手推到一边,对他说:“别开枪。我不想看见你杀人。”这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我只不过推开了这个警察的手,就救了那个黑人一命。那些警察看样子是想把我的头打爆。他们开始摸抢,一个家伙准备揍我。另一个人阻止了他们。然后,我意识到:老天,这些家伙太危险了。他们可以无缘无故地杀人。就因为……唉,老天。
那时,人们之间更加友爱。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一样。只要你是一个好的音乐人,这就够了。现在,黑人会说白人演奏不出真正的爵士乐,所谓的灵魂音乐。真见了鬼了,除了灵魂,我们还用什么去演奏?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不一样的。你懂我的意思吗?迈尔斯·戴维斯(Miles Davis) 觉得我很不错——他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但还是有很多人说:这个白人根本不行,他没有那种灵魂。开什么玩笑呢?!没有人的灵魂是上锁的。如果我忘乎所以,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演奏,那就是我的灵魂,难道不是吗?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演奏。
觉得我很不错——他很喜欢我,我也喜欢他。但还是有很多人说:这个白人根本不行,他没有那种灵魂。开什么玩笑呢?!没有人的灵魂是上锁的。如果我忘乎所以,按照我自己的感觉去演奏,那就是我的灵魂,难道不是吗?不管你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该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演奏。
三十年代的音乐很不错。我的意思是没有停滞不前。我没这样。只是,我必须按照自己的感觉去演奏。如果我的风格不错,它就会延续下去,在三十年代或直到六十年代,或者一直到七十年代。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有份工作,政府应该确保每个人都有工作可干。成立公共事业振兴署就是个相当不错的办法。我很幸运,不需要它的帮助,但我觉得就应该这么干。每个人都应该工作,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我并不是说共产主义什么的,可能算得上社会主义,我自己也不清楚。就像我是一个音乐人,那就出钱给我开音乐会,大家都来听。
政府应该想点儿办法,让人们有事可做。在这些城市,有太多事情等着人去做。工作比领取救济的感觉好太多了。你有了自尊,这是最重要的。戏剧、舞蹈学校、音乐人……可以让像我这样的人去做老师,教爵士乐。这样,我的平生所学就能传承下去。年轻人可以将它们发扬光大,做出自己的选择,不过他们最少也得有点儿背景知识。这就像学习历史,就像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著名投资公司高盛的高级合伙人。他曾在罗斯福的前两届政府出任顾问。
1929年10月29日,这个日子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在办公室待了一周,没有回家。股票交易显示牌一直在转。我已经不记得那晚有多长了。一直等到十点、十一点,我们才拿到最后的报告。那简直就是晴天霹雳。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华尔街的人也普遍觉得困惑。他们并不比其他人知道得多。他们觉得会宣布点儿什么。
知名人士都在发表声明。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 站在J.P.摩根公司前的台阶上宣布他和他的儿子们在买进普通股。很快,股市再度下挫。共同基金被用来救市,可惜只是徒劳。大众开始恐慌,拼命抛售。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们投资公司的股票上涨了两三百点,然后又跌成渣。所有的投资公司都是这样。
站在J.P.摩根公司前的台阶上宣布他和他的儿子们在买进普通股。很快,股市再度下挫。共同基金被用来救市,可惜只是徒劳。大众开始恐慌,拼命抛售。这段时间对我来说真是度日如年。我们投资公司的股票上涨了两三百点,然后又跌成渣。所有的投资公司都是这样。
过度投机是罪魁祸首,完全无视国家的经济状况。有那么一伙人肆意做空。你什么都可以卖,过度打压市场。越是打压,越是恐慌。现在,我们制定了防护措施。活期贷款的利率提高了,20%对吗?
没人那么有远见,可以预见股灾。你当然可以马后炮,许多人都说:“我就知道有股灾,所以把所有证券都卖掉了。”我觉得这不一定可信。不过总有些保守的人,他们真的卖掉了股票。但这样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
在我认识的人里,没人跳楼。不过有人扬言要跳。他们最后不是进了养老院就是进了疯人院。这些人在股市或是银行做交易,最后身体垮了,钱也没了。
罗斯福上任后力挽狂澜。说我们的金融体系会出问题,这都是陈词滥调了。但确实有许多制度需要改变。我们正处于崩溃的边缘,有可能发生叛乱,还有可能爆发内战。
华尔街是反对罗斯福的。1932年,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我和乔·肯尼迪(Joe Kennedy) 是支持罗斯福的。我当时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出任财务副主管。在他头两届任期过后,我就不再支持他了。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我认为没人可以连任超过两届,那套“新政”也让我有些心力交瘁了。1940年,有人请我到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工作,他迟迟不肯在我的聘用文书上签字。后来,我们又冰释前嫌了。
是支持罗斯福的。我当时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出任财务副主管。在他头两届任期过后,我就不再支持他了。我和他大吵了一架。我认为没人可以连任超过两届,那套“新政”也让我有些心力交瘁了。1940年,有人请我到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工作,他迟迟不肯在我的聘用文书上签字。后来,我们又冰释前嫌了。
1934年,信心终结了大萧条。1937年,我们又经历了一次经济衰退。经济回暖之后人们有些兴奋过头了,你得矫正一下。1939年二战爆发,给经济注射了一剂强心针。
不可能再出现经济萧条了,至少不会发展到1929年那种程度,除非通货膨胀失控,价格远超真实价值。没错,股市的深层反应会引发经济萧条。政府当然会立即回应,暂停交易。但在恐慌之中,人们会乱卖一气,不顾其真实价值。现在,拥有股票的人数超过了两千多万。当时,这个数字只有一百五十万。股市现在的跌幅要比1929年深。
现在,人们的资产净值都是以价格计算的,而不是手头的现金。恐慌之下,价格会无视价值一路下滑。一幢房子值三万块,一旦你陷入恐慌,它就一文不值。之前五十块买进的股票现在的卖出价是八十块,大家都很开心。于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可是这不过是票面价值而已。
当时,大家都在投机。造成现在的局面,除了自己他们还能怨谁?这是他们咎由自取。我的观点是什么?如果你在赌博时犯了错,为什么要怪别人?是你自己的错,难道不是吗?
就像那些排着长队领救济的人。我当然同情他们。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日子好过的时候并不会过日子,他们什么都没存下来。如果会过日子,许多人都不会沦落到这个地步。二十年代的时候,人们都穿二十块一件的丝绸衬衣,大手大脚。如果他们只买两块一件的衬衣,把另外十八块存到银行,大萧条到来的时候,他们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1929年,我有一个朋友在搞投机。他会问:“有什么赚钱的好门道?”我说:“我们在卖联邦爱迪生公司(Commonwealth Edison)的高等级第一抵押债券,收益不错。”他说:“不怎么样,才5%的收益,我在股市能赚10%。”他当时用保证金买股票。他觉得自己很有钱。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吗?一枪打爆了自己的头。这跟政府没有关系,都是咎由自取。
现在,大部分人都在寅吃卯粮。他们自己一点儿也不担心。反正政府日后不会坐视不理。现在,没人想工作。我们有个黑人女佣,人很好,在我们家已经干了十五年。她有个孙子。我们请他帮忙揭下卧室的壁纸,一小时给他两块钱。很简单的活儿,只是撕下墙纸。我们提供桶、海绵和梯子。你觉得他会干吗?不干。我们找不到愿意干这个活儿的人。最后,我只得自己动手,很容易就搞定了。
你觉得这是因为“新政”?
当然。他们启动了规模如此巨大的救济项目。不然为什么所有黑人都跑到芝加哥和纽约去了?
所以,当我说到富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我就激动了。“新政”开始之后,迅速着手整顿华尔街。就全国而言,华尔街是一切动荡的罪魁祸首。他们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对的。就我所知,也存在一些弊端。罗斯福任命一帮年轻人执掌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刚从哈佛毕业,只会空谈理论。年长的乔·肯尼迪是个例外,他是个强盗资本家。这些实施“新政”的人觉得自己使命在身。罗斯福抨击华尔街的人有他的理由,但不公平。并非所有华尔街人都恶贯满盈。
我和我的朋友们经常聊起这个,尤其是在他表演过火的炉边谈话之后。我们缴税,不要求任何回报。其他人却在申请救济,用我们的钱帮他们渡过难关……从某种层面上来说,这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他们花光了你的钱,还是没有什么作为,这就不公平了。
他们是不切实际的社会改良家,试图有所作为,我对此表示赞赏。但他们听不进别人建设性的意见。
胡佛时运不济。大萧条来的时候他在位。就算是耶稣在位,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怜的老胡佛真是够倒霉的,赶上了大萧条。这是世界范围内的大萧条,不是胡佛的错。1932年,就算是只猴子都能击败胡佛,赢得总统大选。这一点毫无疑问。
他是芝加哥一家大经纪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傍晚时分,我们从他位于拉塞尔街的办公室往下看,熙熙攘攘的人群正拥向公交车站和停车场,急着回家。
“从1924年到1968年,这个行业始终让我着迷。我从业很长时间了,也为此感到骄傲。现在和二十年代截然不同了。现在的道德准则异常严格。偶尔也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毕竟是少数。”
他身上散发着一股看破红尘的味道。
1924年圣诞节前后,我离开芝加哥大学,进入这个行当。我股市的资产有三千块,那是我的全部家当。黑色星期五那天——其实是星期四?我的保证金账户出现异动,可能只剩下了六十二块钱。
那时,我太太在一家莎士比亚剧团工作,每周的薪水一百二十五块,那真是一笔巨款啊。那天晚上,她回到我们的小公寓,对我说:“猜猜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怎么啦?”她回答说:“我辞职了。”我一个星期赚六十块,她赚一百二十五块。我们收入的三分之二和全部积蓄就这么没了。
我当时的工作是管理保证金。如果客户使用保证金购买股票,也就是说没有付钱就买进股票,那我就在他们的个人账户上记下数额。
当股市开始崩盘的时候,人们从大幅缩水的保证金账户里疯狂抛售。我们整晚都在记账。我们工作到夜里一点,然后跑到拉塞尔酒店休息,五点起床吃早饭,然后接着给保证金账户记账。因为每个人都陷入困境,无人幸免。
我的老板坐在电信交易室里看股价收录器。是要看的,因为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95%的资产都在股市交易记录单上,它们可以让股票大厅里显示的指数下降六十个点。交易大厅就是个疯人院。我问他:“我们还得出钱吗?”他说:“要到晚上十二点才知道。”他是半开玩笑半认真。现实就是那么残酷。
股市崩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之前出现过多次警告。整个国家都疯了。每个人都在买股票,不管自己是否支付得起。擦鞋匠、服务员,还有资本家……许多公司都是金字塔式的控股结构,但这些金字塔不过是虚拟的票面数值。英萨尔先生的公司就是个很好的例子。那真是快速致富的噩梦。
保证金账户不仅仅只牵涉到股票经纪人,还有银行。银行的很多贷款都收不回来。它们的工作方式和经纪人一样随意。当它们打开账户……
我在辛辛那提有个年轻朋友,很有魅力的一个人,已婚,还有几个孩子。他为自己购买了十万美元的保险。对他来说,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他选择了自杀,好让妻子和孩子们能靠那笔保金活下去。当时有很多人为了保金自杀。现在想来有些不可思议,至少现在你知道很多人出了门之后还能回家。
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的印象也很深刻。我一直听说有人的生意出了问题。但他们从不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他们过着国王般的生活,整个大萧条时期都是如此。我一直没搞明白是为什么。我认识的一些人保住了他们位于芝加哥河南岸湖滨大道(Lake Shore Drive)的公寓,还有汽车,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遇上了麻烦。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办到的,当然我也不关心。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破产了,我们从来不假装日子还好过。
政府对保证金没有管控,人们用很少的钱就可以买进股票。当政府不再支持保证金交易,大家的资产就大幅缩水。此外,你还可以做空,又没有规则约束。 当时,有许多保守、信誉良好的银行家都搞特殊交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证券卖给他们的朋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当时,有许多保守、信誉良好的银行家都搞特殊交易,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将证券卖给他们的朋友。结果,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但凡有点儿声誉的银行家,几乎没有反对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他们认为1933年的管控对我们的行业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1932年、1933年,根本没有证券业务。我们午后就在拉塞尔大街打桥牌。不用给人打电话,也不用去拜访谁。办公室安静极了,你都能听到单据飘落到地上的声音。(笑)没人去打工挣钱。许多人想方设法每周挣个四十、六十块的,但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打桥牌。(笑)
我发现国人对当时的状况反应很迟钝。即便股市崩盘之后还是一样。在实施“新政”之初,资本家理所当然地将罗斯福奉为金融系统的真正救星。《芝加哥论坛报》写了很多盛赞他的文章、社论。情况稍微好转之后,蜜月期也告一段落。你应该晓得那帮在森林湖站上车的家伙:他们每天早上都在找头条新闻,让罗斯福出糗的头条。这些人哪……
这个叼着长烟嘴的家伙做了一些基本规划,像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公共事业振兴署,甚至是糟糕的“蓝鹰运动”(Blue Eagle)。他给这个国家注入了一种新的精神。
1933年的“银行假日”催生了一种快乐、肆无忌惮的情绪。其实,人们的日子只是能过下去而已。但他们相信:哎呀,天哪!情况不可能更糟了吧。他们开始以物易物。
当时,“爱尔兰乐手”乐队在芝加哥演出,大家都拿着土豆进场。人们拿着蔬菜去买票。这个乐队的观众可不少。
我也无意让大家忽略这样的事实——大萧条时期普遍存在的苦难生活。你要知道还有人在密歇根大街桥(Michigan Avenue Bridge)下生活。还有些斯文人,穿着两百块一套的旧西装在卖苹果。苦难实在是太多了,我永远不想再看见……
我发现人们不再记起大萧条或是想到它,聊天也不会提及它。此外,我还发现许多人——甚至是教授,他们在大萧条期间每个月的薪水是三百块,他们其中的一些人现在可以拿到十万、甚至是十五万。过去,你从来也见不到这么多钱,怎么都见不到。工业的发展和交易中的公平公正也都是过去两三年里的事。
关于大萧条,还有一件事情值得关注——它没有导致革命。我记得在艾奥瓦的某个地方,有个叫米洛·雷诺的家伙,颇有一些追随者。他们推翻卡车,不让警察没收抵押品。但是,当你考虑到全国的情况,整个国家居然秩序井然:人们只是坐在那儿,接受命运的安排。现在回想起来,这有些不可思议,真的不可思议。无论他们是感到震惊,还是觉得情况会出现转机……我太太经常跟我讨论这个问题。在她看来,没有出现暴力抗议,尤其是在1932年、1933年,这真是令人惊讶。
我的父亲是位理发师。就在股灾之前,他买了一栋房子。我们的日子开始过得紧巴巴的。我们保住了房子。他是个很节俭的人,我还记得他省吃俭用,攒下钱来还抵押贷款。他经常找一家贷款公司借钱。每当爸爸到处找钱还贷款,家里的气氛就很紧张。我还记得这件不体面的事情。
那是一家非常有名的贷款公司。我记得那个地方很阴森。当然,我知道那里并不阴森,只是我的感觉而已:总觉得那个地方有问题。我并不觉得丢脸,但很憎恶我们无法掌控的状况。
现在,每个月里我最不想做的就是去还抵押贷款。我讨厌想起自己付的那些利息。如果我有钱,就一次付清。我就是非常讨厌这个。
心理医生。他曾师从弗洛伊德,病人都来自中上阶层。他从二十年代开始执业。
百万富翁因为焦虑到我这儿寻求治疗。1933年,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我来这儿是因为钱都亏光了,只剩下长岛的一栋房子,价值七十五万。我不知道如果卖掉它能换回什么。”他浑身上下透着一股贵族气派。“我常常因为自己赚的那些钱心怀愧疚。”
我问他:“为什么觉得愧疚?”他说他是股市的场内交易人,当他看到股市下挫,就开始做空,狠狠推它一把。每天交易结束的时候,他能赚五万到七万五千美元不等。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说:“我一直觉得自己好像在从那些孤儿寡母的手里抢钱。”
华尔街股灾之后,他感到很内疚。他开始尝到没钱的滋味。告诉你一件事,你就能掂量出他的分量:他在摩根大通参加了一个秘密会议,希望股市能止跌企稳。他本来和我预约的是五点,结果来电话说:“我今天来不了。不过下次见你的时候,会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如果我在1933年3月买进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的股票,一万块的投资足以让我赚上好几百万。不过,这不是他给我带来的消息。他说:“我们打算关闭美利坚银行,因为总统想维持极端膨胀的股价。”这不过是纽约一家规模极小的银行。他们决定让总统去碰壁。银行倒闭了。
这个人让我去银行把所有存款都取出来,换成黄金券。黄金券的背面写着:可在美国财政部兑换成金条。我换了一万块的黄金。我想:“我拿着这些东西怎么办呢?”沉得要命,全是金条。我把它们放在一个保险箱里。两天之后,我不得不把它们又拿出来,因为总统宣布持有黄金是违法的。我把黄金带回银行,他们给了我一万块。
我听说,早在1929年股灾之前我们的经济就千疮百孔了。我的一个病人是美国最大的厨具经销商。他的工厂规模极大。他说:没有任何事先通知,突然之间就没有订单了。那是1929年五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所有人都认为金融“新时代”已经来到。我在股市多长时间?从1926年到1929年。我的资产翻了倍。我还记得自己曾经买过的一些股票,像是电气债券及股份(Electric Bond and Share)公司的股票,买的时候一百块一股,卖出时四百六十五块一股。
那是你能赚到大钱的唯一方式。工资收入都不值一提。医生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明的业余投资客。医生开始对这个感兴趣是因为他们的部分病人来自金融界的高层,我的一些医生朋友就是这样。这些病人告诉医生买进哪些股票。好多医生就是这样走上了不归路。
我自己从1926年开始往股市投钱。那个时候,我在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工作,我觉得那里的医生多少都买了些股票。有的赚得多,有的赚得少。我胆子太小了。直到几年之后,我得到消息买了蒙哥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的股票,十天之内就赚了一千块。
1929年5月,我退出股市。我把钱从证券交易所拿出来,委托给了这么一个人,他为美国最富有的一些人理财。我想他总该万无一失吧。他开始买进股票。佳斯迈威(Johns-Manville)是其中一只,当时它的价格是一百一十二块,他买得比较便宜,一百零五块,买了一百股。我最后以五十块的价格卖掉了。
1929年春天,他盗用了价值三百万的股票。他陷入了大麻烦,最后死于冠心病。他为之管理资产的那个人身家大约一个亿。那个人在股灾中毫发无损,并通过交易欧洲的贬值货币赚取了巨额财富。他向自己的朋友提供内幕消息,其中很多人都赚了六百万到八百万。六百万是一大笔钱了。欧洲货币的贬值让他们大赚一笔。
人们经历了什么?
人们没有太多感觉。你都不知道正在经历大萧条,除了有人在抱怨自己没工作。你花一点点钱就能得到最棒的服务。人们的工作报酬几近于无。那时,人们都在兜售苹果,整座城市里都有人在排队领救济。但总的说来,最高的失业率还不到20%。
那你的病人也都受到影响了吗?
影响不大。他们支付不菲的诊费。我刚翻出了一本1931年到1934年间的银行存折。天哪,那个时候我每个月挣两千块,那可是一笔巨款啦。到了1934年、1935年和1936年,情况开始好转,大批病人拥来。人们四处求助。都是中产阶级,手头又松了。二战爆发的时候,纽约的心理医生都忙死了。我早上七点开始看第一个病人,一直工作到晚上。
他仔细回想了1937年的经济衰退、对西班牙内战的兴趣、对罗斯福针对西班牙禁运武器政策的失望、巴塞罗那的陷落……他的很多病人都是自由派,有的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或许能解决问题,其他人则是“大商人的中坚力量”。
你和下层人民打过交道吗?
下层社会?没有。我知道一个包工头,算中下层吧。我花了八千五百块请他帮我建一栋十个房间的石头房子。每平方英尺的节疤松木,我付他五分钱,现在你得花一块五。在那儿打工的人每天赚不到五块钱。我问包工头他能赚多少,他说:“够吃半年。”算是能拿多少拿多少。贱卖自己的劳动力,把活儿干好,指望着能得到另一份工。
在那时候,每个人都安于自己的角色,为自己的命运负责。大家或多或少地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要么是怠工,要么是无能,要么是坏运气。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的过错,是因为自己的懒惰和无能。你接受这种命运,缄默不语。
人们会因为自己的失败感到羞耻。我想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自己并没有受过什么苦。
大萧条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几乎没什么动乱。倒是有一些大规模的游行。有人在华盛顿游行,胡佛承诺所有问题都会解决。人们抱持希望,不知所措。
在1930年和1932年,大企业向罗斯福求助。他们从来都没有克服自己的羞耻心,也从来没有原谅罗斯福,因为他本有能力做点儿什么,采取措施刺激经济。
现在,人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整个精神面貌都变了。整个国家充满了更多的敌意和毫无收敛的攻击性。我们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每个人都在问:“为什么不是我?”这个富足的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让大家知道富有的那一半是如何生活的。就在电视上,你看得到。大家都在问:“这些家伙究竟是谁?我有什么问题?我是黑人,那又怎样?”大家不再愿意为自己的命运负责。这都是其他人的错。这很可怕,有可能把我们的国家弄乱。
如果再来一次大萧条,你觉得有可能爆发革命吗?
应该发展不到革命,它没有组织。
现在,没人能忍饥挨饿。他们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应当。事实上,正是三十年代的政府给人们灌输了这么一种观点。那时,人们不会要求政府什么,只会提出一些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为什么我是替罪的羔羊?为什么是我?他们希望天上掉下馅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