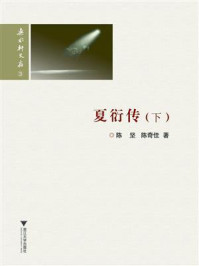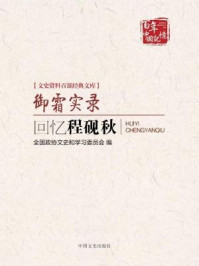卡尔舅舅坐在外祖母的绿色沙发上,对她的训诫洗耳恭听。他是个大胖子,额头很高,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额头的皱纹由于烦恼更为明显。他的秃头顶上有棕色的斑点,后颈上长着一小撮卷毛。多毛的耳朵红红的。整个肚子胖得圆鼓鼓的,扣在难以承受的大腿之上。他的镜片老是模糊不清,总是蒙着一层雾气,将温和的紫罗兰般的蓝眼睛挡住了。此刻,他正将柔软肥胖的双手并拢着夹在双膝中间。
相比之下,外祖母显得那么瘦小,她坐在客厅桌边的扶手椅上,尽力挺直身子,她的右手食指上戴着一个顶针箍。每当她要强调所说的话时,就不时地用它敲击光亮的桌面。她总是穿黑衣服,配有白领子,胸前还佩戴着镶有宝石的胸针。她每天系着蓝白相间条纹的围裙,浓密的白发在一缕阳光下闪闪发亮。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壁炉中的火呼呼咆哮着,玻璃窗上布满了白色的霜花,像繁星一样。圆玻璃罩里的时钟刺耳地敲响了十二下,牧羊姑娘为她的伴侣轻盈地跳着舞。一辆马拉雪橇从门厅前穿过,铃儿叮当作响,它的滑橇擦碰过鹅卵石路面,沉重的马蹄声回响着。
我坐在客厅旁边房间的地板上。卡尔舅舅和我刚刚为火车铺设了铁轨,那是富有的安娜姑母送给我的圣诞礼物。这时,外祖母突然出现在门廊上,用简短而冷淡的声音叫卡尔舅舅。他站起身,长吁短叹着,穿上夹克,把背心抻得平平的。他们在客厅里坐下。外祖母关上了门,但它又不知不觉地敞开了,我能看清楚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像在观看舞台演出一样。
外祖母在说着什么,卡尔舅舅噘着他紫红色的嘴唇,硕大的脑袋越缩越紧。其实,卡尔舅舅只能算半个舅舅,因为他是外祖母最大的继子,比她小不了几岁。
然而,外祖母是他的监护人。他是一个弱智的人,没有能力照顾自己,有时候住进收容所。但是,他大部分时间是和两位中年妇女生活在一起,她们是贝达姨妈和埃斯特姨妈,她俩百般关照他,而他就像一个付账的客人。他像一只大狗那样富于献身精神,忠厚老实,温和善良,只有一次表现太失常。一天清晨,他突然冲出房间,外裤内裤都没有穿,粗鲁地抱住贝达姨妈狂吻,并说一些猥亵的话。贝达姨妈并没慌张,而是很镇静地用手掐他某个相应的穴位,正如医生所叮嘱的那样。然后她给外祖母挂了电话。
卡尔舅舅事后很懊恼,沮丧地哭泣着。其实他是一个很平和安分的人。每个星期天,他都穿着整洁的黑套装,跟随两个姨妈去行道会教堂做礼拜。以他那温和的形象和悦耳的男中音,他完全可以成为一名传道士。他为一切适宜的团聚活动帮忙,像个不领薪水的教堂司事,而且在女人们的缝纫茶会和宴会等场合中,他都是受欢迎的人,当女士们忙着做她们的手艺活时,他便大声给她们朗诵诗文。
卡尔舅舅的确是一个发明家。他常常拿着他的设计图和说明书向皇家专利局申请专利,但很少成功。在一百多种这样的发明申请中,只有两种发明获批,其中一件是把马铃薯削成同样大小的机器,另一件是盥洗间的自动刷。
卡尔舅舅疑心很重,老是惧怕有人会偷走他的最新设计,所以他常常把设计图纸装进外裤和衬裤之间的油布包里,随身带着到处走。使用这个油布包对他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他患有小便失禁的毛病。有时,特别是在大的聚会中,他就会失控。他常常用右脚盘住凳子腿半站起来,让外裤和内裤被一股“自发的洪水”浸湿。
外祖母、埃斯特姨妈和贝达姨妈都知道他这个毛病。当她们知道他又要犯病时,只要用短促、刺耳的声音叫一声“卡尔”,他就能及时控制住。但阿格达小姐有一次曾大惊失色。她听到炽热的火炉里发出嘶嘶的声音,卡尔舅舅被抓到后大声欢呼:“啊哈,我正在这儿烘煎饼!”
但我尊重卡尔舅舅,相信西格纳姨妈所言,卡尔舅舅是三兄弟中天赋最高的一个,出于妒忌,弟弟阿尔伯特用一把铁锤在他头上狠狠地一击,因此导致了这可怜的孩子一辈子智力上的愚钝。
我小时候很钦佩他,因为他为我的魔灯和电影放映机发明了不少东西。他重新改装了幻灯片滑动夹和镜头,在镜头里面安装了一块凹面镜,然后又在三块玻璃上画上影像,同时把它们安装在幻灯片滑动夹里更方便地来回滑动。他用这种方式为人物创造了活动的背景。于是,人物的鼻子变长了,人们飘浮着,幽灵从月光下的坟墓中闪现出来,船沉入水底,一位被水淹没的母亲将孩子高高举过头顶,直到他们一同被巨浪吞没。
卡尔舅舅买了一些电影胶片,五欧尔一米,然后把胶片泡在热苏打水中,以便去掉感光乳剂。等胶片晾干了以后,他用墨汁直接在胶片上画活动影像。有时,他画一些能变形的、爆炸的、放大或缩小的、没有象征意义的中性画面,以便能组合成各种变换的影像。
在家具拥挤的房间里,卡尔舅舅吃力地伏在工作台上,把胶片放在一块下面透亮的毛玻璃上,将眼镜推上额头,右眼戴着一个放大镜,嘴里则叼着一只弯曲的短烟斗,又准备了几支类似的烟斗擦得干干净净,装满了烟叶,整齐地摆在他的桌面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毫不犹豫、迅速从画框中出现的小人。卡尔舅舅工作时吸着烟说东道西,嘴里边吐着烟边嘟嘟哝哝:
“这是泰迪,马戏团里的一只长卷毛狗,正在向前翻着筋斗。它翻得棒极了。主人知道如何操纵它。现在,凶残的马戏团老板正在命令这只可怜的狗向后翻筋斗,可泰迪翻不过去。它的头撞在场边,眼冒金星。我要把这里的星星涂上红色,现在,它的头上撞出的大包也是红的。我想埃斯特和贝达姨妈出去了,你现在去餐厅,打开放餐具的橱柜,左边的小抽屉里有一包巧克力糖,你拿四块来,但要小心一点,不要被抓住,因为妈妈禁止我吃甜食,所以她们才藏起来不让我偷吃。”
我按照他的吩咐,拿来了四块巧克力糖,我得到一块。他把其余三块一气全塞进胖嘟嘟的嘴里,亮晶晶的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然后,他往椅子背上一靠,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冬日黄昏出神。“我要给你看样东西,”他突然说,“但是,你千万不能告诉妈妈。”他站起身,朝中间大吊灯下的餐桌走去,把灯打开。黄色的灯光洒在东方风格图案的桌布上。他坐下,并要我坐在他的对面。然后,他在左手腕上缠一块布,开始慢慢地绕,后来就越绕越快。最后他的手自腕部以下从浆洗过的袖口处脱开,几滴浑浊的液体流在桌布上。至少看起来如此。
“我有两套西装。每个星期五,我被叫到你外祖母那里,换掉内衣和套装。我已经这么过了二十九年。但我不得不照办,好像我是个孩子。那是不公平的。上帝会惩罚她。上帝会惩罚强人。看那儿,房子对面有一堆火!”
冬日的太阳在铅灰色的云层中撕开了一条裂缝,阳光直射在对面老奥戈坦大街房子的窗棂上,光的反射透过壁纸,投下暗黄的方形阴影。卡尔舅舅的半边脸神采奕奕。那只“卸下来的”手平放在我们之间的桌面上。至少看起来如此。
外祖母死后,母亲成为卡尔舅舅的监护人。他搬到斯德哥尔摩。在那里,他向自由教会的一位老太婆租了两间斗室,在离哥特街很近的环城路住了下来。
按惯例,他每星期五来牧师住宅和我们全家共进晚餐,被换上整洁的内衣以及干干净净、压烫平整的套装。他的样子没有变,身体仍然是圆滚滚的,面颊照样是玫瑰色的,那双紫罗兰般温顺的眼睛也依然在厚厚的镜片后闪烁。他还是照样孜孜不倦地到皇家专利局申请他的发明专利。每个星期天,去行道会教堂唱赞美诗。母亲掌握他的财产,定期给他零用钱。他管母亲叫“卡琳妹妹”,偶尔也讥笑她模仿外祖母生前的习性。“你总想模仿继母,算了吧,你的脾气那么好,她的脾气那么坏,你模仿不了。”
一个星期五,卡尔舅舅的房东太太来了,她和母亲进行了一番长谈。并大声哭泣着,隔几堵墙都能听得清清楚楚。约一两个小时后,她起身告辞,脸哭得又红又肿。母亲走进厨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哈哈大笑起来。“卡尔舅舅已经和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女人订婚了。”她说。
几星期之后,这对刚订婚的未婚夫妇来拜访我们。他们来和母亲谈结婚典礼的事情,打算一切从简,但要在重礼仪的正统路德派高教会的教堂举行。卡尔舅舅随意穿着一套运动衫,未打领带,法兰绒的运动衣裤都熨烫得很整齐。他不戴角质架的新式眼镜了,换了一副老式眼镜,换上系扣的靴子,也不穿平底便鞋了。他那天显得沉默寡言,神态严肃,注意力集中,没有吐露一句紊乱或是想入非非的狂言。
他在索菲娅教堂找到了管理邮件的差事,不再搞发明创造了。“发明东西,那是幻想,是骗人的。”
他的未婚妻三十出头,又瘦又小,双腿颀长,肩膀瘦削。她牙齿大而洁白,栗色的秀发耸立着,鼻子长而挺立,嘴小小的,下颚则是圆圆的。她那双眼睛黑而明亮。她以充满占有欲的柔情体贴她的未婚夫,她强有力的手漫不经心似的放在他的膝盖上。她是一名体操老师。
母亲对卡尔舅舅的终身监护权将要告终了。卡尔舅舅说:“我的继母对我智力状况的观察仅仅是她的一种错觉。她是一个强人,喜欢支配别人。妹妹绝不像继母,无论她怎样学。那只不过是一种幻想。”
他的未婚妻睁着明亮的双眼注视着我们这个家庭,一言不发。
几个月以后,卡尔舅舅的婚事告吹了。他又搬回到他在环城路的房间,也不在索菲娅教堂管理邮件了。他私下告诉母亲,婚姻告吹的原因是未婚妻竭力阻止他的发明创造。一切都在尖叫和混战中结束了。卡尔舅舅抓抓自己的脸说:“当时我觉得自己能放弃发明,但那只是一种幻想而已。”
母亲再度成为他的监护人。每星期五,卡尔舅舅照样来牧师住宅更换内衣和套装,与家人共进晚餐。他小便失禁的毛病更厉害了。
他还有一个相当危险的习惯,去皇家图书馆或市立图书馆里消磨时间的时候,途中喜欢抄捷径穿过通向南斯德哥尔摩的隧道。毕竟他的父亲曾是一个铁路工程师,建造过通往克律尔布到英舍湖之间的铁路,因此,这位铁路工程师的儿子也喜欢火车。每当火车在隧道里从他身旁呼啸而过时,他会把身体紧贴隧道的岩壁,他喜欢这种隆隆声,震颤的古老岩石、灰尘和烟雾使他陶醉。
在一个春日里,人们发现他遍体鳞伤地躺在铁轨中间。在他外裤里的油布包里,装着一幅关于便捷更换街灯灯泡的设计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