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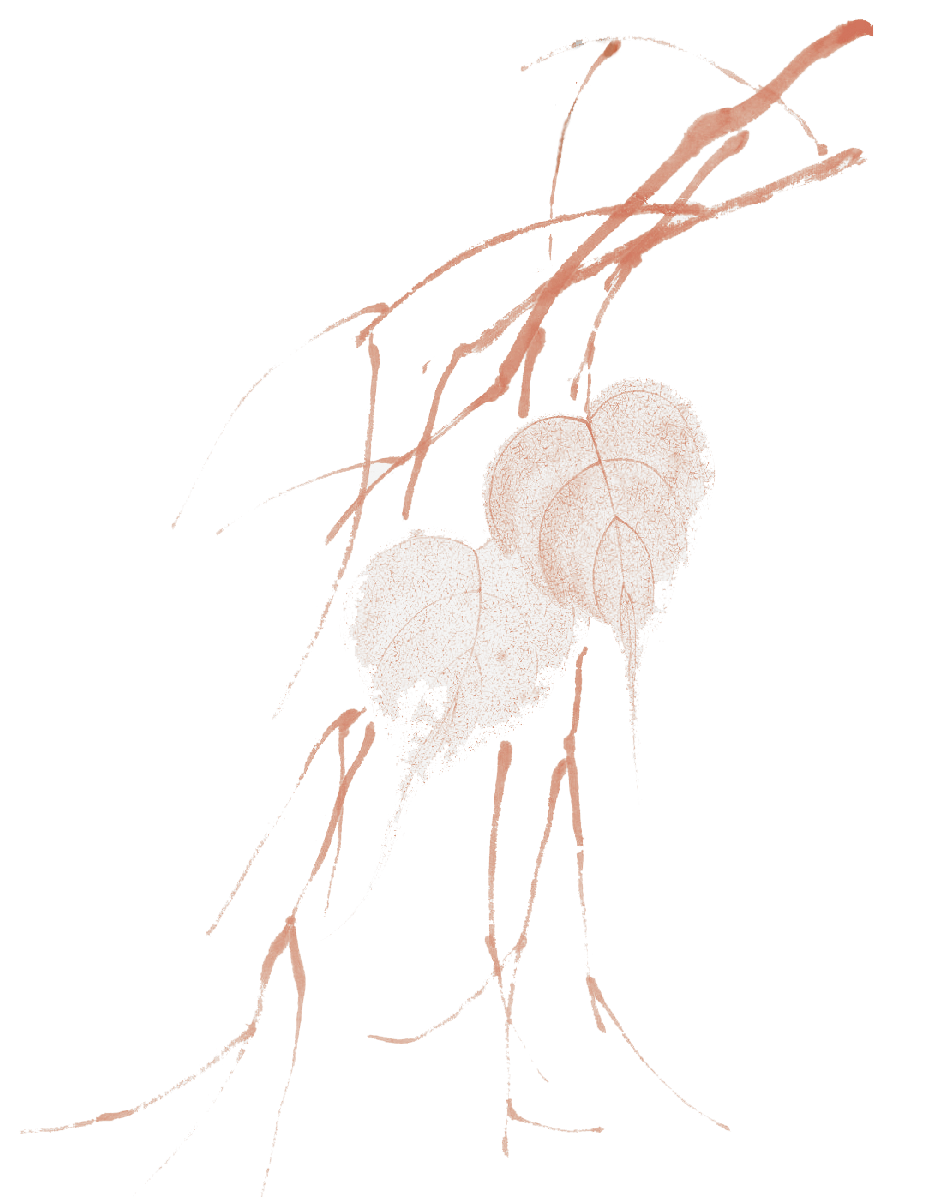
开场白
说老实话,贵校请我来讲武侠小说,我本来不敢应邀的,因为我在一九八三年就已“封刀”,武侠小说那是早已放下的了。一九八七年移民澳洲之后,更是连兴趣都已差不多转移到别的文学领域了。如何还敢“接招”?但邝教授和我说:“不必紧张,你只当做是讲故事好了,讲自己的故事。说不定从你的故事中,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给研究武侠小说的专家学者参考。”他这一说,倒真的打动我了。我如今快八十岁了,老人记远不记近,说说早期的新派武侠小说,我大概还可凑合。
释 题
“早期”的界定为一九五四年至一九五八年,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新派武侠小说”,这是当时公众的说法,八十年代之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中,亦大都沿用这个名称了。这段时期我认为是“探索期”,一方面形成了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一方面又在追求自我突破,打破“定型”,而以一九五八年作为一个比较明显的分界线。(在这一年,我完成了《白发魔女传》,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大约十分之八。)
白头宫女说玄宗
套用股票市场的术语,新派武侠小说真是其兴也速,一开始上市(见报),就有颇不寻常的走势。一九五八年更是它的第一个高峰。辛弃疾词句:“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句出他六十五岁那年所写的《永遇乐》。辛弃疾生长于北方的沦陷区,二十三岁始归南宋,成为他生命中重大的转折点(后来做了浙东安抚使这样的大官)。一九五八年至今(二〇〇一年)也正好是四十三年,那一年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在《香港商报》连载了大约两年光景(总共是连载约两年半),正在踏入突破早期模式的阶段,极受读者欢迎。我在那年完成《白发魔女传》,反映似亦不差。不过我可不敢比辛弃疾,要比也只能比作“闲坐说玄宗”的“白头宫女”。好,现在就让我这个有份参与的“白头宫女”来说“开元旧事”。
吴陈比武
一九五四年一月,香港发生吴(公仪)、陈(克夫)比武之事,两位拳师从报上骂战到擂台比武,不到五分钟,就以吴公仪一拳打伤陈克夫的鼻子告终。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香港是个“静态社会”,难得有这样充满刺激性的新闻,因此纵然比武告终,也还是个热门话题。罗孚遂“忽发奇想”,立刻把我找来,要我马上写一篇武侠小说。于是这一场不到五分钟的比武,竟“连累”我写了三十年的武侠小说。罗孚后来有一篇文章提及此事,说“这一拳也就打出了从五十年代开风气,直到八十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看目前武侠小说的“走势”,最少恐怕还有十年以上的“天下”吧。那么这一拳的影响所及,就不只五十年了。
但对罗孚的“点将”,最初我是颇有顾虑的。
一、由于所受教育(家庭、学校及因特殊机缘而得受业的老师)的影响,我认为写武侠小说即使成功,也不是“正途”出身。(想不到三十年后,我却成为了武侠小说的辩护士,并因此曾在海峡两岸成为新闻人物,命运真会开玩笑!)
二、出于在报馆地位的考虑。当时我是《大公报》社评委员兼《新晚报》副刊编辑,另外还写两个颇受欢迎的专栏。改写武侠小说,不无“委屈”之感,但最后我还是被罗孚说服了。
《龙虎斗京华》面世
吴、陈十七号比武,《新晚报》十九号登出预告,二十号我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就在报上连载了。由于匆匆上马,说真的,当时只是想好这个篇名,至于写什么,怎样写,都还茫无头绪。只好来个“楔子”,拖它几天。“开篇词”调寄《踏莎行》,其中有一句“卅年心事凭谁诉”,不料竟一语成词谶。
拖了五天,得出初步构思。我把十九世纪末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作为历史背景,这是历史上一次非常复杂的群众运动。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廷的腐败逼出来的,此一“运动”,固然是民族主义情绪的发泄,但其表现方式则为盲动(不分青红皂白地极端排外)与愚昧(乱七八糟的迷信)。义和团内部亦分成三派,内斗甚烈。较有理性者大都属于并不拉帮结派这一类“独行侠”,为数少之又少。小说女主角柳梦蝶的父亲和情郎就都是被以慈禧为靠山的“保清派”害死的。我要写的是历史的悲剧,在那种混乱的局势中,纵有真知灼见的英雄,亦只能是“枉抛心力”而已。
但这样“新”的题材,读者会接受吗?报馆有的同事都曾为我担心:“你写义和团,不怕吓走读者?你的‘新’,在别人心目中可能被当做洪水猛兽呢?”我则以一贯的书生气作答:“题材本身无‘左右’之分,问题只在于你怎样写?你觉得对,你就写,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话是这样说,读者能否接受,我亦殊无把握。能想到的只是从三十年代说到五十年代的一个“文艺理论”——旧瓶装新酒。在形式方面,我尽量采用旧式章回小说写法,用回目,讲对仗,求典雅,用诗词作开篇;至于我完全不懂的江湖术语、武功招式等,则只能从前辈作家的著作“偷师”了。我曾在这方面闹出笑话,这倒启发了我的灵感,若要藏拙,须创新招,因此其后我遂改“写实”为“写意”。
出乎意外地流行
没想到我这个毫无准备便即登场的处女作,竟然立即就成为流行小说,令人感到意外的消息频频传来。试举几例:
一、报纸的销量增加了(行话叫“起纸”),当年《新晚报》的竞争对手是《星岛晚报》,《星晚》领先(可能高达六四之比)。《龙虎斗京华》刊出后,差距逐渐缩短。以前是有“大新闻”才起纸的,如今则小说打到紧张的时候,也会起纸。这真可以说是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武侠小说逐渐成为城中的话题了。以前是只有“连续性的新闻”才可以有话题,如今则不但在公共场所(如茶楼、巴士)听得有人谈武侠小说,文化圈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也在谈了。我的老友舒巷城有一次就忍不住好奇,用话试探,想要“撞”出我的“秘密”,后来他告诉我,他的许多朋友都想知道《新晚报》的武侠小说作者是谁(见舒巷城《犹是书生此羽生》一文)。
三、在小说结集出版之前,粗制滥造的盗印本已充斥市面。
四、外地的中文报纸也出现了争相转载的现象。首先是泰国,然后是越南、柬埔寨、老挝、印尼、缅甸、菲律宾。至于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纸则大约是在一年之后,通过合法的途径,取得版权的。(最先那家《民报》,销量有限,但却是颇有影响力的“小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两家大报则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取得和港报同步刊载的版权才开始连载的。那时《龙虎斗京华》早已结束,连载的是我别的作品了。)
五、最先在香港吹起了“武侠风”。具体表现在:许多“大报”增加了武侠小说。而武侠小说作家更是人才辈出,最有贡献的当然是今日名满天下的金庸。我在上面说的那些现象,到了金庸登场,那更加愈演愈烈了。
金庸登场
金庸的处女作《书剑恩仇录》是根据一个关于乾隆皇帝的传说来写的,说乾隆皇帝其实是海宁陈家的后人,一出生就被换入宫中。后来陈氏夫人又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小说中作为乾隆皇帝对立面的红花会首领陈家洛了,戏剧性很强。金庸是浙江海宁人,对他家乡的传说自是耳熟能详,因此他是一开始就有缜密的构思的。这当然要比《龙虎斗京华》登场时,题材都还没想好强得多了。
《书剑恩仇录》也是采用旧式章回体的写法,用回目,正文之前有诗词。作为“开篇词”的好像是辛弃疾的那首以“绿树听鹈鴂”起头的《贺新郎》。这首词的后半阕“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慨当以慷,沉郁苍凉,王国维评为“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是辛弃疾的名篇。
《书剑恩仇录》是长篇小说,在报纸连载差不多两年,是《龙虎斗京华》加《草莽龙蛇传》的一倍。当然也取得了比《龙虎斗京华》更大的成功。
上下求索
我在《草莽龙蛇传》之后写的又是一部较短的小说,名为《塞外奇侠传》。我对《龙虎斗京华》不满意,想做多方面的尝试,小说取材自新疆一首歌颂他们女英雄飞红巾的民歌。飞红巾爱上一个流浪草原的歌者,不料这歌者后来变成叛族的罪人,她强抑悲伤,手刃情郎,祭奠亡父。我把这个情节作为“序曲”处理,大部分篇幅则用来描写后来成为天山剑客的汉族英雄杨云骢,把主要矛盾转变成飞红巾、纳兰明慧(满洲贵族)和杨云骢的三角恋情。并尝试用新文艺手法,不用回目诗为新式标题。这部小说前几年曾被新加坡编成电视,看来它的艺术生命似乎比《龙虎斗京华》更长。
一九五六年初,我开始写《七剑下天山》(我的《塞外奇侠传》尚未结束,金庸的《书剑恩仇录》大约也只写到一半多一点),又再做一个新的尝试,这本书是模拟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小说甚至运用弗洛伊德有关潜意识的心理学说,来为书中一个人物桂仲明解梦。运用得不够自然,但也说明了当时“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心情。
金庸的第二部小说《碧血剑》也接受了一些外来的影响,如西方电影的手法;有些地方则似乎还可以看做是早期意识流的手法(至《射雕英雄传》时更成熟)。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我认为在一九五七年这一年(其时金庸的《碧血剑》已经完成,《射雕英雄传》亦已写了三分之一,我写完了《七剑下天山》,开始写《白发魔女传》)已经奠基。
新派武侠小说的特点
一、从旧到新的演变。此处的“新”“旧”,专指武侠小说而言。从这一时期的梁、金小说,已可略窥其演变过程。更具体地说,即是既有继承,亦有拓展。例如上面说过的:
(一)招式从写实到写意。
(二)同门师兄妹的三角关系,从白羽到梁羽生,再到金庸都有不同的表现手法,个人觉得以金庸写得最好。
二、有比较清晰的历史背景,有较新(视野较为宏阔)的历史观。
三、重视中国传统,亦向西方取经。
四、有比较深广的中华文化内涵。
五、比较讲究章法及节奏。
六、“侠”的提升。
因何在香港勃兴
新派武侠小说热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那自是因为在其演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新的特点,因而也就产生了新的魅力。但何以它在香港兴起呢?依我看,这是由于历史的因素加上机遇了。
一九四九年之后,内地已经不再出版武侠小说。到了一九五四年春,新的武侠小说突然在《新晚报》出现,这可真的是像“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了。
从内地来的“新移民”,一九四九年后数量大增,很快就超过了“原居民”了(但这也并不排除新旧移民的意识形态都会随着内地形势的变化而变化)。香港本地的“广派武侠小说”质量不高,缺乏源头活水,更难免令人日久生厌;至于那些新移民呢,他们熟悉的是“北派武侠小说”,对“广派小说”是不屑一顾的。
这个对香港社会结构的分析,“基本上”是对的,但错误在于对历史的因素重视不足,对读者的思想情况也估计失准。而且我们当初谁也没有想到一点——武侠小说的本质是可以超越政治的。
后来据报馆的调查采访所得,有许多新移民就因为要看武侠小说才买《新晚报》,因为他们觉得小说的写法很像他们熟悉的“北派小说”。
这也难怪,我这部处女作的确是受到白羽的影响。
一九八八年初,我的作品获得台湾当局“解禁”之时,台北开了“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出版为例”,与会者提出一个“文学断层”的观点,意思是台湾和大陆有三四十年的文学断层,必须设法补救。他们认为过去国民党政府把梁羽生和大陆作家等同处理,因此如今对梁羽生的作品“解禁”,也等于是接上了一块文学断层(一九八八年一月二日台湾的《中央日报》首先刊出我的《还剑奇情录》,颇获好评)。我觉得一九五四年的香港,虽然并没和祖国分开,但在武侠文学方面,却的确是存有断层的。我写《龙虎斗京华》,就是想要接上那一小块断层。看到新派武侠小说如今在中国流行的情况,我想或许这也算得是一种“文化断层”的“互联”吧。不过对我而言,则还要加上“回馈”二字。
新派武侠小说(早期)的模式
特点与模式相连,特点是内容方面比较属于本质的东西,模式是某些近于固定的表现手法:
一、章回小说的脱胎换骨。
二、故事的“时”“地”“人”方面表现在:
(一)时间大都选择:
1. 外敌入侵。
2. 民族矛盾深化。
3. 政治腐败、官逼民反,用当时“新史学术语”,即“阶级矛盾激化”。
(二)地点经常选择:
1. 边疆地区。
2. 北京与江南。
(三)人物方面:侠士、美人的结合。侠士大都是有抱负的,甚至有使命感的,“艺高”之外还要“德高”;美人则是纯真兼痴情。
三、爱情的矛盾往往采用“双方分处敌对阵营或出身背景差异极大”。
新派武侠小说的自我突破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越来越深入地着重于人性的刻画(如郭靖、杨康、梅超风,尤其是后者的“邪中有正”),着重于表现历史人物的真实(如成吉思汗),这就突破了善恶分明、大侠的“道德形象”等模式。对于金庸不断的突破和创新,许多“金学家”已有鸿文发表,我只是第一个知道金庸有写武侠小说之才的人,但并非“金学专家”,在此就不多说了。
《白发魔女传》在卓一航与练霓裳之恋中,也是突破了上述的“侠士模式”与“爱情模式”的。
台湾作家陈晓林在“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中提到了“后现代主义”,虽然我在写武侠小说时,连什么是“后现代主义”都不懂,但他这段话说得的确很有见地。“后现代主义”中的一个特色是去“中心化”、去“主体化”,也就是不再以固定的概念形态来诠释现实。例如,以前我们中国人都有强烈的正统观念,每个人都是从《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以及正统的教科书中了解历史。但除了这些之外,生命还有无穷多的层面……另外,他在台北《中央日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说:“梁羽生的著作若是串联起来,即形成了一个与正统历史发展相平行的草野侠义系谱。从这个草野侠义系谱回看权欲纠结的正统王朝,甚至构成了对中国历史的一种诠释和反讽。”“白发魔女”是“女强盗头子”,可说亦属“草野侠义”一类。陈晓林对梁羽生的了解比我更深,我在对自己的作品作“分期”的界定时,可说部分是得到了陈晓林的启发。我只想“加多一点”说,如果以《白发魔女传》作为“反正统”的标志,则这个“反正统”不单是反《二十四史》之类的正统,也反“左派”“早期模式”的“正统”。
(演讲于二〇〇〇年十一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