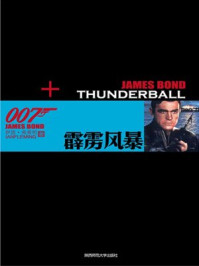天快亮才睡下,感觉刚睡着,咚咚的敲门声一下将陆二禄惊醒,慌忙起身穿衣,但心却提到了嗓子眼儿里。他真怕又是掺沙子的事,更怕公安或者工商找上门来。陆二禄努力镇定半天,才使自己的心跳平稳了一点,急忙穿戴整齐,然后让春枝出去开门。
却是老家来的亲戚,八九个人,还开了拖拉机。不知又发生了什么事,陆二禄惊得嘴和眼睛都圆了。还没等陆二禄问,二爹陆来旺便说,我们在电视上看到三寿了,我们一晚上没睡着,你姑夫半夜就开了拖拉机拉我们上路,一路快跑,现在才赶过来。
二爹虽然当过生产队队长,但毕竟是个没识几个字的庄稼人。陆二禄对二爹笑笑,然后轻松地说,就是电视里胡叫喊,电视又不是法律,说了屁用不顶,过几天,啥事都没了。
二爹一连叹气摇头,然后说,你们年轻人不懂,共产党历来都是说到做到,说啥就要做啥,有时做的比说的还厉害。"三反五反","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哪一个做的不比说的更凶?上面说一句,下面就要说十句,而且做过头。
陆二禄心里还是禁不住一阵阵紧缩。昨天电视台的一位副台长警告他不要再活动,活动也没有用。副台长告诉他,中央很可能在近期来一个经济大整顿运动。大整顿,就要有大动作;搞运动,就要有典型,抓要害。现在的要害是经济无序,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成风,如果不整顿,如何了得。掺沙子,正是一个难得的触目惊心的典型,这样的典型,作为新闻媒体确实难得,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如果掺沙子的事情再在省台甚至中央媒体报道,老三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反面典型,到那时,杀头判重刑也有可能,而且不仅是老三,如果深挖严查,他和老四以及全家都逃不脱追究。
还得使钱找门路把事情摆平。现在事出了,就不能怕花钱,钱花完了,还可以挣,如果被抓了典型,就什么都完了。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电视台那里。人言可畏,舆论确实可以杀人。陆二禄躲进卧室沉思一阵,觉得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找电视台的上级单位,让上级领导出面,才有可能让电视台不把录像送到省里,也再不要在市台播出,更不要搞后续报道。
病急乱投医。市委宣传部长也是五寨乡人,说起来也算老乡,虽没见过面,但拿一份重礼,找找也许能通融一下。
收拾好准备出门时,老四表情慌张地跑进来,对陆二禄小声说,三嫂的弟弟蹬了辆三轮车来,要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拉走。
这还了得,老三刚出点事,还没怎么样,就往娘家转移家产。陆二禄没顾多想,急忙往后院老三家走。
看到的又是满院子的封条。陆二禄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发紧。
但财产完全可以转移到别处,转移到她娘家,有些东西肯定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特别是她的弟弟二兵,那是个典型的二流子。二兵原本也在拖拉机修造厂上班,眼热姐夫做生意挣了钱,就也下海跑生意。因为既不努力又不谨慎又没脑子,结果是跑啥赔啥,倒啥亏啥,拖累老三也贴进去不少。二兵做生意不行,却学会了吹牛说假话大手大脚,更要命的是赌博,和那些大赌家赌都毫不害怕。二兵现在是做生意没本钱,干粗活儿没力气,整天坐在家里等天上掉钱下来。一旦钱财真的掉进他的嘴里,他绝不会轻易让这笔钱财溜走。看到电视机电冰箱已经搬到了三轮车上,陆二禄真担心这些东西会被二兵卖掉。他想提醒一下彩玉,但二兵毕竟是人家的弟弟,想想,陆二禄又没说什么。再站一阵,又觉得没什么可说:人家的家,人家怎么折腾那是人家的权利,说了又能怎么样。再说,现在这么大的灾祸压在身上,生死都成问题,这点钱财又算个什么。陆二禄什么也没说,然后心情沉重地默默离开。
陆二禄决定拿五万块钱去找宣传部长牛如刚。
一下送这么多钱,妻子春枝坚决反对。陆二禄恼怒凶恶地说,不拿钱,就拿一家人的命,用不了明天,我也得被抓进去,到时你就守着钱过日子去吧。
再掂掂包里的钱,陆二禄心里还是发疼。更让他心疼的是,这些年只顾挣钱,竟然没在官场上结交一个有实力的朋友。官场上没后台,就没人给你撑腰。相比之下,人家乔保中还是聪明有远见,不仅广交官场朋友,还傍上了市领导做靠山,还搞到了一顶政协常委的红帽子戴在了头上。这样的人别说一般部门不敢把他怎么样,就是犯了大罪,抓不抓那也得市委开个常委会讨论讨论。而自己不但没有一个后台,遇到事连个可求的人都找不到。
也许这次的事件是个契机。乘这个机会,一定要攀上一个有实力能管官的大领导,让大领导发一句话,各部门各部下就坚决照办,立即执行。这样,哪里还用得着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一尊门神又一尊门神地去拜。
可眼下还得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去求人。这送钱求人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今天电视台、明天公安局、后天还有工商局。想想这些,陆二禄的腿都有点软了。
宣传部在市委大院里。每次进这个大院,陆二禄心里就犯紧张。大院的大门看起来敞着,但你走到门口,冷不丁就传来一声断喝:"干什么的!"吓一跳后,才知道声音从旁边的门房里传来。然后就是出示证件登记姓名单位。陆二禄没有证件。那次他掏出名片递上,门卫老头以为是什么新证件,接过一看,一下将名片扔到陆二禄的脸上。今天又没带证件,当然也没证件可带。没带证件就得说出找谁,然后给要找的人打电话,要找的人出来把你接进去。想说去找牛部长,又怕人家不认识拒绝接见。好在陆二禄还认识市经委的一个副主任。给副主任打电话,陆二禄才算进了大门。
不顺连着不顺。来到宣传部,牛如刚不在部里。问到哪里去了,谁都说不知道。不知道怎么行,如果错过今天,录像就会送到省台播出。陆二禄再推开一个门,见里面只有一位中年男人,陆二禄便急忙掏出红塔山烟,抽一支递上,然后恭恭敬敬将整盒烟放到男人面前,然后求他问问牛部长到哪去了。中年男人出去一会儿就问清楚了,说牛部长去了郊区工地,说一建筑工地挖出了新石器时期的彩陶,牛部长到现场去了。
陆二禄打了车好不容易才问到工地,工地的人说都回去了,可能是到文化馆去了。
文物都放在文化馆,应该是随文物到文化馆了。陆二禄又急忙往文化馆赶。到了文化馆,又说牛部长已经回宣传部了。
再次来到市委宣传部,终于见到了牛部长。让陆二禄没想到的是,牛如刚竟然知道他,而且知道他是发了财的陆老板。
感觉牛如刚要比电视里的老一点,头发基本都成了白色。好在牛如刚很客气,不仅让座,还给他倒了水,然后开门见山问他有什么事。陆二禄急忙将整个事情细说了一遍。
牛如刚虽然在认真地听,但头却在不住地摇。听完后立即说不好办。牛如刚说这件事是电视台的正常业务,播出这样的节目既没政治错误,也没经济错误,而且还符合当前的宣传政策,宣传部没有权力也没有办法让人家不播。
牛如刚扫一眼钱,一下脸都变成了白色。那包钱犹如一盆炭火,烫得牛如刚一下将钱包掀翻在地上。见钱滚出几捆,又惊恐了将钱拾起装入包里,然后紧张地向门外看看,对陆二禄说,快拿起,快拿走。
不知哪里来的毅力,陆二禄上前抓住牛如刚的双手,说,咱们是老乡,你早就是我心目中的亲戚,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和办事没有关系,办成办不成那是另外的事,请你一定要收下我的一点心意,也给我这个老乡一点面子。
牛如刚后退两步,又快步上前拉开门向外看看,然后将门关死。紧张的在地上走几步,对陆二禄说,你先坐下,你让我想想,你让我问问,看有没有办法。
感觉牛如刚有点动摇。陆二禄打定主意今天一定要缠住牛如刚,不答应帮忙决不罢休。牛如刚又在地上转几圈,然后出了门。
半天不见牛如刚回来,陆二禄不禁慌张起来。会不会是乘机跑了?会不会再出什么差错?正当陆二禄焦急不安不停地探头向外张望时,牛如刚走了进来。
牛如刚仍然关死了门,然后悄声说,你先把包放在这里,然后你回去,你再让我想一想办法,过一会儿不管有没有办法,我打电话和你联系。
出了市委大院,陆二禄的心情轻松了许多。刚才牛如刚出去半天才回来,很可能是请示了某个领导或者和电视台的领导通了电话。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可能大有希望,要不然牛如刚也不敢收礼。但不管怎么样,只要他把钱收下,他就会想办法也会有办法把事情办成。
陆二禄抬头望望,太阳黄灿灿地悬在西天,大概是下午四五点了。秋老虎天气还真有点热。陆二禄感到口干舌燥。来来往往的汽车人流更让他心烦。前面有个卖凉粉的。陆二禄想在那里坐坐喘口气,也吃一碗凉粉,压压肚里的热火。
虽然卖凉粉的很热情,但感觉凉粉并没有平日的好吃,有点干硬,也有点苦涩。卖凉粉的是个中年瘦女人,她一口否定她的凉粉有问题。她说是不是你的嘴出了问题,比如上火,肝火上升舌头就苦。陆二禄一下将碗重重地撂在桌上,想骂几句什么,又不知该骂什么。见女人仍然望着他笑,他不知道自己哪里让她好笑。有可能是自己的脸色很不好看,或者是哪里不大合适。陆二禄用手抹把脸,然后一声不响地站起身,默默地交了钱,转身离去。
陆二禄还没回到家,牛如刚就打来了电话。可以明显地听出牛如刚有点兴奋,语气都变得快速有力。他要陆二禄快到饭店定一桌饭,然后请电视台的几位领导吃饭。
陆二禄问怎么请,牛如刚说,怎么请你不用管了,定好后你就在饭店等,到时你再向他们表示一下歉意,也表示一下感谢,也解释一下你的情况。
牛如刚虽然不说事情能不能办成,但从他兴奋的口气判断,事情肯定有了一个眉目。陆二禄也禁不住高兴起来。牛如刚说请电视台的人吃饭时让他表示一下感谢,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准备点谢礼,还是人家已经答应了,到时感谢一下人家。他觉得不管是什么意思,都应该准备一点谢礼。但电视台那几位领导他都领教过了,不仅不收礼,还气势汹汹,真有点刀枪不人油盐不进。陆二禄不由得有点烦恼。但细想,又觉得也未必。前面不收钱,是因为人家不能答应他的要求,现在能够答应要求,当然就要另当别论。再三考虑,陆二禄觉得面子是部长的,有部长的面子,他只表示一下意思就行了,没必要再送大礼。再说,如果来的人多,大礼也没法送。陆二禄只买了十简高档茶叶:如果来的人多,就每人送一简;如果人少,就每人送两筒。因牛部长要亲自来,不仅电视台的领导都来了,当事记者也都全部到场。按牛如刚的意思,酒宴开始,就由陆二禄先敬酒认错。敬过酒,牛如刚就巧妙地将话题转到了掺沙子上。牛如刚说,你们也知道,市里刚召开了经济工作会议,李书记对全市的经济工作很不满意。李书记把咱们的情况沿海一带的情况做了对比,说咱们的自然资源比人家优越,经济却和人家相差很远,为什么,关键是人,关键是人的思想不解放,关键是人的胆子不够大。人家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试,什么都敢干,什么人都敢富,而咱们,只知道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敢想不敢干,不敢出门闯世界,不敢摸着石头过大河。人家个个都是商人能人,咱们一千个里面也没一个商人能人,即使有,咱们的领导还是用老眼光老思想看待人家,不是看不起人家,就是吃拿卡要,更别说支持帮助了。最后李书记说咱们还是没有一个宽松的经济环境。你看,李书记的讲话多好,一语中的。咱们搞宣传的,也应该为经济工作推波助澜,引导人们彻底改变无商不奸的观念。这次掺沙子虽然是严重的错误,但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一方面是没有经商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情势所逼,不得不跟了人家学。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商人还不成熟正因为他们不成熟,正因为他们是索者,正因为他们是全市少有的几个能人,所以咱们才应该像爱护幼苗一样爱护扶持他们。如果一棍子将他们打死,伤害的是全市的商人,损失的是全市的经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咱们市这些年就出了几个倒卖皮毛倒卖瓜子的生意人,正是有了他们,才带动了全市的种植和养殖,才使全市的经济有了活力,才使全市的财政税收有了大幅的增长。如果掺沙子的事在全省甚至全国播出,那么大家就会说我们市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掺了假使了杂不能用的,这样一来,谁还敢要我们的东西,谁还敢和我们做生意。现在全国都叫喊了要打假,如果我们的事在中央台播出,肯定会被当做反面典型,如果是这样,咱们市就成了造假的反面典型,就成了一个假货市,那时全国人民反对我们,全国人民抵制我们,我们就成了全市的罪人,这样大的责任,我们谁能负得起。
电视台的人都低了头一片沉默。陆二禄心里一片温暖,一片感激,连眼睛都有点湿润。这么多年,有哪位领导如此关怀过商人,如此站在商人的立场上说过话。难怪人家能当宣传部长,肚子里确实有点水平。如果由这样的人来当市委书记,全市的经济早就腾飞了起来。陆二禄情不自禁想给牛如刚鞠个躬,刚起身牛如刚示意陆二禄坐下,然后对着台长温柔地说,我说了这么多,不知有没有道理,你也说两句吧。
台长觉得这是要他表态,便附和了说部长说得很对,很中肯,高屋建领,然后又很空洞地表态说今后电视台要好好为经济建设鼓劲服务等等。牛如刚还是很满意,表扬电视台几句,又问和送录像的人联系上了没有。台长说联系上了。台长说他亲自给送录像的小王打了传呼,小王也回了电话,但录像已经送给了省台,他让小干想法要回来小平已经去要了。
陆二禄这才推断出事情的大概过程。但他担心能不能要回录像带。牛如刚也同样担心。台长说,问题不大,我告诉小王说录像有问题,播出会有麻烦,作者也不同意播了,这样,省电视台肯定不会再播。
牛如刚还是要台长再呼一下小王,问问具体进展。台长用大哥大呼了小王的传呼机,时间不长,小王就回了电话,说录像带已经要回来了。
犹如卸下了千斤包袱,陆二禄重重地舒了口气。陆二禄轻松得有点松软。牛如刚也高兴,他高兴地对陆二禄说,我们台里的几位领导都是好同志,特别是王台长,办事认真,又有原则性,组织观念也强,是难得的好同志。这次,台里的领导为了你的事,也为了全市的经济,出了不少力,也费了很大的劲,怎么办,你表示感谢一下?
东西确实买的少了,档次也有点低了。早知人家如此痛快,就应该再买点别的。十筒茶叶,光电视台的人就来了六个,只能一人分一筒。陆二禄口头表示感谢后,急忙将放到桌底的茶叶拿出来,边道歉边发给大家。在座的谁都没有推辞,什么话也没说,都将茶叶收了起来。
轻松地回到家,夜已经深了。陆二禄给母亲和弟兄们通报了一下情况,然后就回屋睡了。
夜里竟然梦到了陈小玉。陈小玉仍然高雅地坐在那里,仍然除了偶尔笑一下,一言不发。他有点急,便说他马上要到俄罗斯去做生意,问她去不去。她仍然不说话。他觉得无论如何也要和她更亲近一点,但又不敢更进一步表达。他鼓了很大的勇气,提出一起出去走走。她仍然不说话,但却起来跟他一起出了门。不知怎么,却来到了小时生活的村子里,来到村东的那几棵大树下。两人都抬了头望树,树上落满了麻雀和乌鸦,枝上又到处都是鸟窝。他问陈小玉会不会掏鸟窝,陈小玉仍不说话。于是他蹲在了她的脚下,让她踩在他的肩膀上掏鸟窝里的鸟蛋。她轻轻地踩在了他的肩上,他感觉她是那样的轻,轻得让他飘飘然很是爽快。好像陈小玉穿着裙子,他抬头便看到了她的裤衩。裤衩好像是红颜色的,又不太清楚,但他的浑身都蓬勃了起来。他激动得几乎有点发抖。他就那么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看着。不知看了多久,他颤抖的手去悄悄揭她的裤衩。这回裤衩清晰起来,裤衩又成了白色,和肉体的颜色一模一样,而且轻轻一接触,立即有种柔软的肉体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浑身一阵麻木。但他努力了无数次,才揭开了她的裤衩,但里面的东西还是看不清,感觉什么也没有,又好像是眼睛有点模糊。他擦把眼睛,终于看清了一点,他的心一下急速地狂跳起来,血都一下涌到了头上,下面也止不住要喷涌而出。他一下被惊醒了。
他睁开眼四下看看,屋子里已经一片明亮,身边的半张床空空荡荡。妻子已经起床干家务去了。他的心仍然跳个不止。心跳停下来的时候,一股惆怅又浓浓地涌上心头。他真想闭上眼重新回到梦境,但一切又都是那么的不可能。
陆二禄突然心里很难受,难受得直想哭。
那天说过送陈小玉一件羊绒衫,应该尽快拿一件送去。他控制不住想尽快再见到她。他决定今天就去。尽管他觉得很荒唐,但他就是控制不住想见她的欲望。
屋子里很安静,不知春枝在干什么。陆二禄将弄湿的裤衩脱掉,但他还想再躺一躺。侧身躺了,又觉得贷款的事得加紧办。这次事件,花钱不说,被封存的羊毛肯定要被没收。这一来损失将是惨重的,如果再没有贷款,一家人就会彻底破产。如果贷一千万,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就什么事情都不怕了。
他决定马上和胡行长联系,把贷款的事定下来。然后再到乔保中的羊绒衫厂,给陈小玉挑两件最好的羊绒衫。
正要起床,母亲进来了。母亲进来便哭,然后要陆二禄去看老三,说已经过去两天了,不知老三是死是活。
陆二禄能够理解母亲。母亲毕竟快七十岁了,又不识字,在她看来,监狱是最可怕的。陆二禄答应晚上去,母亲一下哭得更伤心了。母亲哭着说,我原以为你们兄弟比别人家的兄弟亲热,看着你们弟兄亲亲热热我也高兴,可现在一个坐了牢,也不知给人家打死了没有,你们却一个个不管不问,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让我怎么能看得下去。
差点跑死,怎么说是不管不问。陆二禄想诉一肚子的苦,但又觉得没有意思:自己做的事情,母亲都已知道,但不论你做多少,老三不出看守所的门,母亲就不会认可你。看着哭泣的母亲,陆二禄还是心里软了。再说,老三坐牢了,自己还在想无关的女人,还要关心无关的女人,确实说不过去。大哥不识字也没在社会上闯荡过,老四还小很不成熟,家里也再没有人能指望了。母亲也说得对,也确实该看看老三,不知副所长真的给优待了没有。他想,去了即使见不到老三,了解一下情况,再活动落实一下,让老三少受点罪,还是能办得到的。他只好答应母亲洗漱完就去看守所。
这回到看守所,陆二禄径直来到副所长的办公室。他已经搞清楚了,副所长叫伍根定,城里长大,下过乡,父亲在市公安局当过科长,去年已经退休。伍根定办公室的门开着,陆二禄进去坐着等半天,也不见伍根定回来。陆二禄来到院子里,听到隔壁房子里有伍根定的声音,男男女女说笑成一片,很是热闹。陆二禄再回到屋里坐着等。又等了半个小时,伍根定才一脸喜悦走了进来。
递上烟问候几句,陆二禄说,你昨天说的事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我没问清楚你有多少毛,是细羊毛还是粗羊毛,价钱怎么样,弄清了,我就能尽快给你处理。
昨天朋友托朋友找了半天,朋友才找到一位在供销社工作的朋友,这位朋友经营过羊毛,但现在手里没货,他只问清土种粗羊毛的价格每吨大约九万到十一万,细毛大约十六万之间。究竟能从哪里弄到毛,他还没个大概方向。他决定明天请两三天病假出去跑跑,背上猪头肯定能找到庙门,只要是羊毛,管他粗细,反正要赚一笔才推给陆二禄。伍根定笑了说,这两天工作太忙了,昨晚你猜我干什么了?我把管监舍的几个朋友都请到饭馆,让大家吃喝了半夜,然后我一个个提住耳朵告诉他们,要把你家老三照顾好,不但不准虐待他,还要让他住单间,还不能让他掉一斤肉,少一块皮。少了掉了,我拿他们是问。
真是个痛快人。陆二禄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些。既然伍根定先说了,陆二禄便细问住宿伙食等情况。伍根定说,这些你放心,我答应你让他住单间,就肯定住单间。伙食的事,也包在我的身上,我负责给他从职工灶打饭,每天给他改善一次伙食。
能有这些待遇就够了。陆二禄提出能不能偷偷见见老三。伍根定说暂时还不能,暂时最好也别见,等过一阵子风声不紧再说。
陆二禄的心一下有点发凉。刚才他还对伍根定一肚子感激,此时,他觉得这笑面虎比赵得厚、牛如刚更凶狠,更险恶,胃口也更大。赵得厚、牛如刚偷偷摸摸,充其量只收个几千几万,而伍根定这大盗,却要名正言顺地大敲一杠。他清楚,如果想得一两万,伍根定也不会用这种形式:人在人家手里,张口要就是了。做生意,那当然是要赚大钱。真他妈的吃人不吐骨头,敲诈了你,还要说成是靠本事赚的。但他也清楚,这种凶残的饿狼,得罪了可就不得了,老三在人家手里捏着,要你扁要你圆,人家根本不用自己动手,更用不着打你一百杀威棒,只把你投到牢头狱霸那里,使个眼色,就能让你皮开肉绽生不如死。
但也不能太由他肆意敲诈,得一步一步退让,适度和他讨价还价。陆二禄叹一声,然后苦了脸说,最近毛价开始下跌,毛也不好出手,说好了把毛送过去,送去了,人家又嫌这嫌那,然后压价扣杂质。货到地头死,有时只好亏本出手。更倒霉的是这次毛被封死在家里,即使不被没收,时间长了交不了货,人家那边按违约罚款,弄不好我就不仅是亏本,而且得彻底破产。
伍根定似乎看透了陆二禄,他笑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俗话说无商不奸,谁有本事能让你们奸商亏本,不说别的,你有给羊毛掺沙子的本事,怎么会赔了老本。沙子一斤值几个钱,你怎么会亏本。我知道你是在向我哭穷,要压价从我手里弄点便宜毛。这就有点不够朋友。陆老板,我可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且冒了很大的风险,你可不能不够朋友。
真让他哭笑不得。肚子里的恼火直往上蹿,陆二禄还得努力压住,装出一副笑脸,说,你开天大的玩笑,现在毛纺企业的效益都不好,都在抓整顿,进原料关把得越来越严。羊本来就是土地上卧的动物,身上哪能没土没沙子,可人家就是要扣除杂质,土越大,扣除的就越多,再说,老三掺沙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我听到掺沙子就心惊肉跳,谁还再敢干那种事。
伍根定仍然笑着说,拉倒吧,你逗三岁小孩儿玩,毛纺企业效益好不好,都是国家的,和厂长经理有啥关系,只要你把老人头往他们眼前一亮,哪个不被刺得睁一眼闭一眼。还有掺沙子,你们老三也真笨,还用大张旗鼓吗,拉一车毛到沙滩里,让车翻了打几个滚,就能沾它几万斤沙,用得着人去掺吗。
世上的事竟然让他说得如此简单。陆二禄明白,他打定主意要吃你,和他说什么都是废话。要暗算就暗算吧,只能听天由命了。他不想再说这些。陆二禄问老三关进来被审问了没有,怎么审问的。伍根定说,关进来就再没人问,也没人来提审。
陆二禄吃惊了问为什么。伍根定起身将门关死,然后神秘地小声说,咱们是朋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想了一夜,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给你出一个绝妙的主意,你按我说的做了,你就能躲过致命的打击。
听是听明白了,可怎么办?怎么才能让案值变小。陆二禄只得再次请教。伍根定说,说你们商人聪明,关键时候也犯糊涂。封条再多,它也没封在每根毛上,门窗封了,咱从墙上挖窟窿;毛堆封了,想办法把封条剪接拼凑一下,留下痕迹也不用怕,你可以说是风吹雨打的,也可以说成是其他。你不是钱多吗,打听到谁去勘察现场,你就向他们使钱。如果他们不睁眼闭眼,怎么办?那你也得冒险干,因为这太重要了,这关系到老三的性命,也关系到你们的前途,冒多大的险,也值得。另外,干了,你死不认账,贼把毛偷走的可能性也有,反正他们没留人看守现场,你们也没有看守现场的义务,丢了的东西,谁能说清。反正现场没那么多的赃物,谁也不能凭空给你定那么多的案值,凭空给你定那么重的罪行。
确实是个好主意。这样的朋友看来不能不交。这样的朋友,打了灯笼也难找哇。陆二禄起身,握住伍根定的双手,从内心表示了感谢,然后说,你弟弟的事你也放心,我也会想办法,至少不会让他亏本。
从伍根定那里出来,陆二禄不想回家,他决定直接去胡行长那里,谈一谈贷款的事。
陆二禄觉得应该先给胡行长打个电话,联系好了再去更合适一些。陆二禄拿出大哥大,很气派地将大哥大举到耳朵上。他喜欢在大街上打电话。他知道,也不仅是他一个人喜欢在大街上打电话,有大哥大的人都喜欢在大街上打电话,而且有许多是将大哥大捂在耳朵上一路哼哼哈哈,实际并没和任何人通话。陆二禄有时也这样做,因为平时并没有那么多的电话,再说话费也贵得可以,偶尔真有电话,却巴不得快点结束。拨号时,他突然觉得这样不好,一是街上太吵听不清,二是有些话也不好大喊大叫去说。陆二禄左右看看,来到一个没人的地方,才拨通了胡行长的手机。
让陆二禄意想不到的是,胡行长说不用面谈了,你的情况我都清楚,我的情况你不清楚。现在银根紧缩,批贷款比上天还难,我也得跑许多门路才行,我最多只能给你贷一千万,回百分之五就行。
百分之五的回扣,虽然不小,但也在他的预料之中,他估计也得这个数。好吧,没有这笔贷款,日子就没法过,更别说做生意。但陆二禄还想讨价还价,生意就是讨价还价的艺术。胡行长立即不耐烦地说,这我已经是给你不小的面子了,我也是看在杜丙雄的面子上才给你跑的,如果你不想要,那就算了,我也省点心。
陆二禄只好一口答应。
回到家,一家人都在等他回来。陆二禄把今天一天的事说完,然后把老大和老四叫到卧室,关死门,严肃而神秘地说了拆封条转移掺沙毛的事。见大哥老四一脸害怕,陆二禄只好又把伍根定说的那番话细说一遍,然后要大哥马上到外面雇两辆汽车或者拖拉机,而且要私人的;要老四想办法到哪里找几个民工,先让他们吃饱饭,半夜后,再领来装卸搬运羊毛。
具体操作时,却遇到了许多困难。门窗上的封条贴得又牢又密,根本不可能揭下来或者再剪接,只能在墙上打洞。好在库房的后墙是大哥家的院子。五个民工得知让他们在墙上打洞时,一下吓得脸都白了,以为落在了土匪大盗手里。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一下跪倒,磕头作揖求陆二禄饶了他,说他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祖祖辈辈都是老老实实的庄户人,提到偷盗做贼,浑身就发软,没一点力气,打死他也不敢干偷人抢人的事。陆二再三解释是工商封了门,然后领他们看了封条。民工们还是不干。陆二禄只得许诺每人再加一百,然后说,干几个小时挣二百块,你们一年能挣多少,这比当土匪抢劫都来得便当,你们还想干啥民工们互相看看,觉得确实是一笔大钱了,才点头答应。把库房里的毛基本装到车上后,陆二决定将堆放在院子里的毛和沙子也拉走,不然光院子里的那些,也够定个什么罪了。堆放在院子里的羊毛和沙子上都横七竖八拉了纸带。纸带是拼接起来的,上面工商局的公章也稀稀落落。陆二禄细细查看一番,觉得这倒好办,把纸带取掉一截,留一小堆毛,然后把纸带再接起来,事情就妥了。
一不做二不休,陆二禄心一横,决定就这么干。
让老大老四押车把毛拉到乡下二爹家,陆二禄又指挥民工把墙上的洞补好忙完这一切,陆二禄长舒一口气,才感到衣服都湿透了。可见是紧张。抬头看天,东边已露出了鱼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