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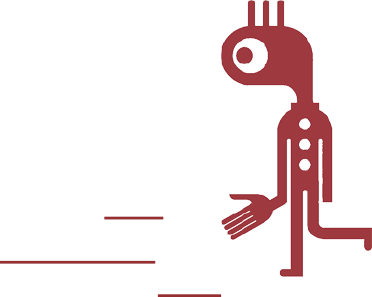
请想象一下,你遭到天谴,必须把一颗大石球推上山。你别无选择,只好往手心里吐口水,开始认真工作。你用全身的力量顶住那颗浑圆的石头,慢慢往山上推去,汗水从你的额头滴了下来,你双手流血,用整个身体撑着石球,你的脸颊紧紧地压在那坚硬的石头上,满脸因疼痛而扭曲。但是你继续推着,一步又一步,石球滚了一圈,又是一圈。
渐渐地,你忘记了一切周遭发生的事,不再想昨天或明天,天地间只剩下你跟石头,你仿佛跟石头合为一体。你忘记了时间,直到你突然发现,你已经到了山顶。终于到了!但是当你一意识到这件事,石头就从你手中滑走,滚往山下去了。一切辛苦都白费了。这个工作毫无意义。
此时你听到诸神的笑声。他们对你呼唤:“这就是你的命运!你必须一再地推这颗石头上山。而且每次它都将再度滚下山去。”
你挫败地往山下走,朝着山下的石头走去。你深深吸一口气,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处境。“这块石头是我的命运,我的使命。”你这么想。到了山下,你再度投入这项任务,开始顶那颗石头——不是因为诸神要求你,完全只因为你愿意这么做,你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并突然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
这些思考来自20世纪的法国哲学家加缪(Albert Camus,1913年—1960年),他是除了萨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与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986年)之外,最为人所知的存在主义者。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是,人类是孤立无援的存在——处在没有上帝、没有命运也没有计划的世界里。存在主义者思索着人类的存在,也关注人生黑暗的一面——死亡、恐惧、绝望与荒谬。然而超越这些现象的是,人类有绝对的自由,如同黑暗世界里的一道光芒。萨特认为,人类是由自己造就而成的,其本质就是没有本质,也就是变化多端的存在,能由自己变成一切。我们每个人随时都可以辞去工作,结束一段关系,移居国外,把一切抛在脑后——我们的人生完全握在自己手中。
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加缪撰述了讨论荒谬性的哲学,他认为,上帝既不存在,世界也没有意义,我们生活在没有边际的宇宙里,住在行星的表壳上,位于银河系边缘的某处。日复一日我们出门上班,完成我们的工作,晚上喝点啤酒,然后躺下来睡觉,我们如此生活,仿佛不知道有一天我们都要死去。可是死亡是确定的,我们死亡之后,一切就结束了,然而世界会继续运转,好像我们从不曾存在。人类有一天也将完全灭绝,而且不会有人在乎。我们的一生,就像朝生暮死的蜉蝣。
生命没有意义,这种想法常常为我们所排斥或遗忘,我们如此做事,好像我们所做的事情皆有意义可言,我们把自己跟我们的计划看得很重要。我们追求各种目标,也为我们的未来做各种准备。也许我们别无选择,但事实就是如此,我们确实只能这么做。尽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相信,究竟说来,这一切毫无意义。加缪认为,荒谬性就是建立在这一组对照上:人类会寻求意义,会追求目标,会为自己打算,实际上却处在漫无边际、没有意义的宇宙里。这种荒谬性,就如同西绪弗斯的处境,他也被迫从每日的劳动里找出意义来。然而终归而言,他很清楚一点:石头会再度滚下山。根据加缪所想,我们的人生就像“西绪弗斯的任务”,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行动,没有用处,也不会成功。
但是,最精彩的地方就在这里:加缪认为,“我们必须把西绪弗斯想象为幸福的人”。人生的毫无意义,对加缪而言,既不该让人绝望,也不该让人逃避到幻觉里,更不是自我了断的理由。正好相反:我们应该充分享受我们存在的一切面貌,尽可能积极地把此时此刻过得更好;意识到人生的荒谬性,就等于发现我们的自由。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失去,规范、义务、计划、忧虑等都变得无关紧要,它们随意地运作着,就像其他一切事物一样。唯一能决定我们该怎么办的,唯有我们自己,我们终于把自己的命运握在手里,这种感觉真是棒得不得了。
西绪弗斯体认到,那块石头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他的命运只属于他自己”,加缪写道。这是他觉得幸福之处。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全人类,在没有上帝的宇宙中,不存在任何计划,除非我们自己打造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如加缪所写,就是“他自己人生的主宰”,自己命运的舵手,他过着自主、完全清醒、充满热情、富好奇心且充实的生活,而且他一再地反抗其荒谬的命运,“没有任何命运是不能用鄙视加以超越的”,加缪又写道。人类唯一的尊严,就在于其有这种反叛的姿态,这种反叛同时是加缪人性伦理学的基础(以情感为核心的伦理学)——因为对非人处境与苦难感到愤怒,人们从孤独中走出,与身边的人团结起来,在反叛之中,人从“孤立”(solitaire)变得“团结”(solidaire),也就是从独行者变成团体中的一员。他开始捍卫某个将他与其他人联结在一起的事物,并为之奋斗,那就是人类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