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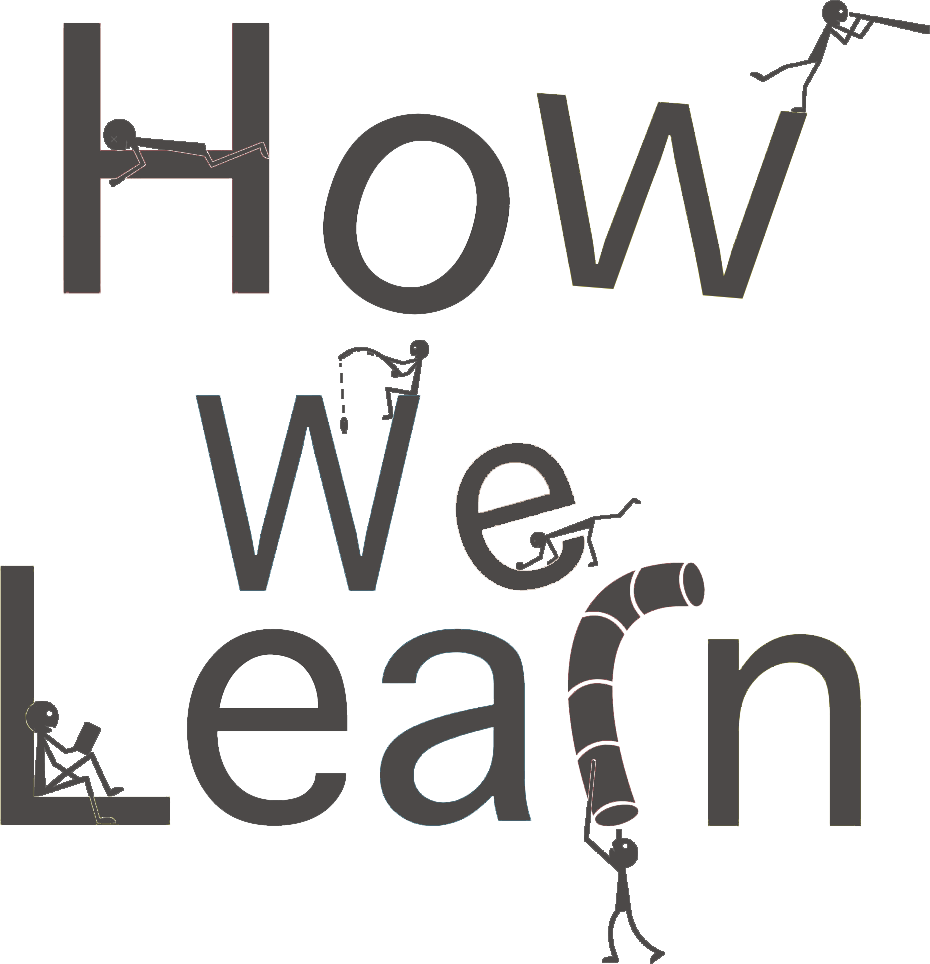
学习科学,从本质上来说研究的是“意念肌肉”如何工作,即大脑是如何运作的。而大脑的运作,指的是它如何处理我们日常生活中输入大脑的视觉、听觉、嗅觉等信息洪流。这本身就堪称奇迹,何况大脑还日夜不息地运作着,其超凡卓绝就更加无可比拟。
想象一下,在你醒着的每一刻,各种信息如潮水般不停地涌进大脑:水开的哨音、大厅里穿梭的人群、后背忽地一痛、一股烟味传来……然后,在此想象之中再加上一组一心多用的画面:一边准备晚餐,一边照看旁边的宝宝,还要时不时回一封邮件,甚至还要拿起电话来跟朋友聊上几句。
够忙乱了吧?
能够同时处理这么多信息、完成这么多任务的机器,远不是“复杂”二字所能描述的。那像是翻滚着的魔法锅,像是一脚踢翻了的大蜂窝,蜂群轰然而出……
请你想象以下几个数据:人类大脑里的神经元,也就是形成脑灰质的大脑细胞,平均在1 000亿个左右。这些脑细胞大多都与千千万万个其他脑细胞互相连接,组成一张张密网,交织成一个小宇宙。如果用电子技术来形容,那么这个小宇宙中不但储存着,而且不停歇地传导着上千TB的无声信息风暴,足以支撑300万套电视节目同时播放。这架可观的生物机器即便在“休息”的时候也一样不停地忙活着。比如说,你正盯着鸟笼发呆、做着白日梦,或是无聊地玩着拼字游戏,此时,你的大脑仍在继续运作,消耗着90%的能量。哪怕你夜间入睡,大脑的某些部位也照样十分活跃。
大脑就好像是一个黑黢黢的、大部分地区都没什么特色的星球。如果能有一幅地图的话,将会容易表达得多。那就先从一幅最简单的图示开始吧。图1—1中显示的几块区域是人们用以学习的核心部位:内嗅皮层,它类似于某种过滤器,专门过滤涌入大脑的信息;海马,是构筑新记忆的地方;还有新皮层,某种信息一旦被打上“储存”的标记,就会被存放到这里,这是储存我们显意识记忆的地方。

图1—1 大脑中的学习区域
这幅图的意义远大于一幅简单的大脑图绘,因为它彰显了大脑运作的基本模式。大脑中有不同的运作模块、不同功能的元件,它们各自担当着不同的功用。内嗅皮层负责这一摊子事儿,海马做另一些事情;右脑所承担的功能不同于左脑;还有负责感官功能的区域,负责处理所见、所闻、所感等。不同区域各司其职,同时紧密结合形成整体运作,源源不断地更新着过去、现在以及可能的将来的信息。
我们不妨把大脑的不同区域看作电影摄制组的工作人员。摄影师负责取景、构图,他们把镜头拉近、推远,然后用胶片录下影像;录音师负责录音,他们会调整音量大小,并过滤掉背景噪音。还有剪辑师和编剧、绘图师、道具设计师、作曲家,他们负责展现角色的语气、感受,也就是情绪的表达,还有专人保管书籍、整理财务单据、记录人物与事件。再就是导演,他会决定将哪段剪辑放到哪里合适,恰到好处地把前因后果都编织到一起,从而演绎出一个完整的故事来。这故事并不是随意编就的,而是针对灌输到你各个感官中的“原材料”所做出的最恰当诠释。
任何一件事物,一旦进入大脑,大脑便会当即对其作出回应,并在最快时间内添加上它所作出的判断、赋予事物的意义以及说明。之后,大脑还会对这一切进行“重整”,并思索:“老板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大脑会对原始胶片再度仔细推敲,以确定该从何处做出怎样的剪辑,从而使这段“胶片”最恰当地嵌入“整部电影”。
这是我们生活中的故事,是讲述我们自己的“纪录片”。在本书中,我会继续借用“电影摄制”的比喻,以求形象地讲解大脑究竟是怎么工作的:记忆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被提取的;为什么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更模糊或者更清晰,甚至连记忆内容都会发生变化;还有,我们是否有可能把握这每一步的运作,从而让记忆的细节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明了。
请记住,这部“个人纪录片”的导演可不是从某电影学院毕业的高才生,也不是来自好莱坞、有一大帮随从的大牌导演。这导演,就是你自己。
在我们开始涉足“脑生物学”之前,我想先针对“比喻”讲几句。比喻,从其定义来说,就不可能是准确的。比喻所表达的意思既明明白白又含含糊糊,而且往往带有“自私自利”的意味,以突出比喻者最主要的意图。
我们这个“电影摄制组”的比喻,不消说,也是一个不太准确的比喻。不过,科学家们针对记忆的大脑机理,即脑生物学的研究,不客气地说,也同样算不上准确。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最好程度,就是用戏剧化的比喻来讲解我们是怎样学得新东西的。这个“电影摄制组”的讲法,其实还是挺合适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且用我们大脑中的某个具体记忆来详细阐述一下。
举一个比较有趣的例子吧,不要用什么俄亥俄州的首府是哪里、你的某位朋友电话是多少、《指环王》里扮演佛罗多的演员叫什么名字等,那些例子都算不上有趣。这样好了,请大家回想一下自己上高中的第一天,跨进主楼大厅时你那怯生生的脚步,高年级同学那不怀好意的目光,储物柜那把青铜锁猛地扣上时砰然作响……每个超过14岁的人都会多少记得那一天的情形,而且往往会是一段完整的录像片段。
那段记忆,储存在以网状连接着的脑细胞里。这些脑细胞一旦同时活跃起来,也就是“点亮起来”,便恰似圣诞节时大型商场里的圣诞彩灯,比如说,蓝灯一起闪烁,显现出一架雪橇的图案;红灯亮了起来,构成一朵雪花的图案。大脑里差不多也是这样,神经元的网络也会连成“彩灯图案”,形成大脑中的一幅幅图像、一个个想法、一种种感受……
将这一幅幅“彩灯图案”连接起来的一个个脑细胞,叫“神经元”。一个脑神经元的核心作用是充当一个开关,它从通道的这一头接收信号,然后“点亮”或者“翻转”这一信号,随即从另一头传送出去,送到这个神经元连接着的另一个神经元。
由一张张神经元网络形成的一段段特别记忆并非一连串的随机连接。当我们听到那把青铜锁“砰”地扣上时,大脑里便有一串细胞被同时“点亮”,这就形成了对一个特别信息的第一次“记忆”。而这同一串细胞组,也就变成了这一特别记忆的集体见证人。把这一串细胞串联起来的,叫作神经元突触,每当记忆被提取一次,这些突触就被加厚一次,该信号的传递速度也就变得更快一点。如图1—2所示。

图1—2 脑神经元
直觉上,我们都认为这挺有道理,对回忆的体验也的确很像情景再现。但是,直到2008年,才终于有一群科学家从人的大脑中直接捕捉到了记忆的组成以及提取的时刻。在一项治疗实验中,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群医生分别往13位病人的大脑深处植入了一组纤维电极丝,这些病人都是癫痫患者,他们正等待着脑部手术。
这本是一项常规作业。癫痫是怎么一回事?人们尚未了解透彻,大脑里导致人们忽然发病的那股活动剧烈的“小型风暴”似乎总是凭空而起。这一“台风中心”在不同人的大脑里常常起自于一个大致相同的区域,只不过准确的位置因人而异。主刀医生可以摘取这一“核心地带”的小块脑组织,可是,医生须得等待“台风”生成时,看到并记录下“台风中心”的位置才行。这就是植入那些纤维电极丝的目的——准确定位。这当然需要时间。病人们因此有可能在医院里躺上好几天,才能等到大脑的一次失控发作。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这群医生则利用这一等待时机,回答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医生先让每位病人都观看一段5~10秒钟的录像片段,内容来自当时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电视节目如《宋飞正传》《辛普森一家》,或像“猫王”这样的名人剪辑,或是一些著名胜地。看过之后,稍等片刻,医生便请这些人回忆他们刚才看过的内容,说得越详尽越好,以求刚才看过的内容能再现。在刚开始播放这些录像片段的时候,一部电脑记录下了观看者脑中的影像,大约有上百个脑神经元亮了起来。放映不同的录像,脑部亮点所构成的图案也不一样:有些脑神经元会格外亮,有些则没什么反应。当观看者稍后回忆所看录像时,比如在讲霍默·辛普森时,脑部亮点所构成的图案则跟他刚才观看相同片段时的大脑图案完全相同,就好像在重播一样。
主持这次研究的资深学者伊扎克·弗里德(Itzhak Fried)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以及特拉维夫大学(Tel Aviv University)的神经外科教授,他告诉我说:“在这样一次独特的尝试中能看到这样的结果,实在太让我感到惊讶了。观察对象太清晰了,看来我们这次的确找对了门道。”
这项实验便到此结束。病人的这些记忆片段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成什么样,人们并不知晓。假如某个人已经看过数百集的《辛普森一家》,那么这5秒钟关于霍默的记忆也许不会太长久。可是,也不一定。假如这次体验中的某个特别因素让你感到格外震撼,比如说,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在你敞开的脑颅里拨弄着一丛电线,这场景与剧集中的霍默捧腹大笑的样子相联结,那么你的这段记忆很有可能会根植于你的心灵深处,终生难忘。
我上高中的第一天,是在1974年的9月,至今我还能“看见”第一堂课上课铃响之后,我在主楼大厅里遇到的那位老师的容貌。大厅里人群蜂拥,我却不知该往哪儿走,脑子里急切地转着这么一个念头:我会迟到的,我会漏掉老师讲了些什么。至今我还能“看见”照射在大厅里的那束飘浮着灰尘的晨光,那难看的蓝绿色墙壁;我还“看见”一个比我大一些的男孩往他的储物柜里塞进去一摞关于温斯顿·丘吉尔的书刊。我走向那位老师,说了一声:“对不起,请问……”声音大得出乎自己的意料。那位老师停下脚步,眼睛看向我手里的课程表。他神情友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顶着一头红色而稀疏的头发。
他淡淡一笑,对我说:“你可以跟着我走,你是我班上的学生。”
我得救了。
我已经有35年没再想起这段往事了,可是这一幕仍然历历在目。那情景不但“回来”了,而且一个个细节竟是那样详尽。我越是长久地驻足在这段回忆中,就越能“看见”更多的细节填充进来:我把课程表递过去时,书包从肩膀上滑下来的感觉;我犹犹豫豫慢下了脚步,心里不太愿意跟老师并肩而行;我落在了他身后几步……
这种“时光隧道旅行”,科学家们称之为“往事片段”,也叫“自传体记忆”(autobiographical memory)。在这类回忆中,往往有一些与当初的体验相同的细微感受,以及相同的叙事脉络结构。
自传体记忆跟俄亥俄州的首府是哪里、某个朋友的电话是多少那类记忆不一样。我们并不会清楚地记得,当初是在哪里、在什么时候记下那些东西的。这一类记忆,科学家们称之为“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它们并非根植于某种叙事式的情景当中,而是根植于某些相关数据与资料的记忆网络中。比如,俄亥俄州的首府、哥伦比亚市,这些词汇可能会“连带”出一幅你某次去那里的景象、某个搬家到俄亥俄州的朋友的面容,甚至是小学时的一个谜语:“两头圆、中间高的是什么?”
 这类记忆的网络结构是以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的,而并非以故事场景为基础。不过,每当大脑调出“哥伦比亚市”这条记忆时,与之相关的“资料网”一样会被“连带”出来。
这类记忆的网络结构是以相关数据资料为基础的,而并非以故事场景为基础。不过,每当大脑调出“哥伦比亚市”这条记忆时,与之相关的“资料网”一样会被“连带”出来。
在充满奥妙的宇宙世界里,这一定算得上最为奇妙的事情之一:某种分子式的“书签”被“夹”在了神经网络中,方便我们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翻”回去“查阅”,让我们得以看到自己曾经的历史,以及曾经的认知。
科学家们尚未弄明白这个“书签”怎么就能被“翻”出来。这跟你点击电脑屏幕所得到的电子数据链接完全不一样,因为脑神经网络系统是不断变动的,1974年形成的记忆跟我今天回忆出来的相比,有很大的差别。我忘掉了一些细节、一些色彩,而且我毫不怀疑,就在我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我已经对某些细节做了小小的“改编”,甚至是很大程度的“改编”。
这就好比是八年级的时候,你在夏令营里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探险,第二天早上,你写了一篇历险记;6年以后,已经上大学的你根据这次往事又写了一篇历险记,这两篇作文毫无疑问一定会大相径庭。6年时间过去了,你已经完全变了样,你的大脑也是如此。而这生理上与记忆上的改变不但被染上了谜一样的色彩,更被染上了你自己人生阅历的色彩。可是,那场景本身、那最核心的部分从根本上来说却分毫未损。不过,对于记忆到底储存在哪里、为何储存在那里,科学家们倒是已经有了解释。
20世纪,科学家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曾深信:记忆弥漫性地渗透在控制思维的那部分大脑区域里,就好像橙子汁充盈在橙子瓣里一样;任何两个神经元都是大致相同的,要么亮起来,要么不亮;而且,没有哪一个特定的脑部区域会是构成记忆的核心部分。
早在19世纪,科学家们就知道,某些技能,比如语言,会集中在大脑的某个特定部位。可人们一直认为这应该只是例外。20世纪40年代,脑神经科学家卡尔·拉什利(Karl Lashley)还曾展示过他的研究成果:会跑迷宫的大鼠在被摘除大脑中的不同部位之后,照样知道怎么跑迷宫。如果说大脑中有个部位是记忆中心的话,那么这些切除手术中总应该会有一个能导致大鼠丧失跑迷宫的技能。拉什利因此认为,任何控制思维的大脑区域都有记忆功能,如果其中某部分受到损害,周围其他部分就会自动接替那一部分的任务。
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一理论开始出现坍塌。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们接二连三地发现新的现象,首先就是神经细胞的发育,准确地说,是婴儿脑神经的发育。他们发现,担任不同职责的细胞仿佛必须按规定去往各自不同的领地:“你是视觉神经细胞,去,到大脑的后边去。”“你,去那边,你是负责运动的神经元,到运动控制区去。”这一发现瓦解了过去的“内在各部分可相互置换”的假说。
而最后的“致命一击”则来自这么一个事件:英裔心理学家布伦达·米尔纳(Brenda Milner)遇到了来自哈特福德市的亨利·莫莱森(Henry Molaison)。
莫莱森是一个修理机器的工匠,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这种病让他无法继续工作。他每天都要犯病两三次,而且往往没有什么预兆,发病时,他会忽然倒地、人事不省。天天发生这类突发事件让他没法维持正常生活。因此,1953年,27岁的莫莱森来到哈特福德医院,走进了神经外科医生威廉·斯科维尔(William Beecher Scoville)的办公室,期待能被医生解救。
莫莱森的病可能是癫痫的一种,抗癫痫药是那个年代针对癫痫的唯一规范疗法,可是服药对他已经没什么作用。斯科维尔是一名技术高超、享有盛誉的神经外科医生,他怀疑造成这类病症突然发作的根源埋藏于大脑的内侧颞叶中。颞叶在左右脑各有一叶,彼此呈镜像对称,就像切开苹果看到的果核那样,每一侧的颞叶里面都有一个脑组织,叫海马,很多癫痫患者的病发都与这一部位有关。
斯科维尔判定,最好的治疗方案是通过手术,从莫莱森的大脑里切除两块手指大小的脑叶,其中包括海马。疗效怎样,就只能靠运气了。而且,在那个年代,很多医生都认为,脑部切除手术是针对很多种精神失常病症的有效治疗手段,包括精神分裂症和严重的抑郁症。果然,手术后,莫莱森的癫痫发作大大减少。
可是,他同时也失去了构建新记忆的能力。
他每吃一顿饭、每见一个朋友,或者带他的狗去公园散步,都好像是生平第一次做这件事。他仍然保有手术之前的一部分记忆,比如他的双亲、童年的家园、小时候爬过的山。他也同样有很好的短时记忆,能把某个电话号码或人名记住大约30秒,并能背诵在30秒内所记的事物。他照样能跟人闲聊,也和其他青年人一样,可以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管随后会忘记。可是,他没法继续工作,也比任何一个神秘主义者都更加彻底地活在当下。

也是在1953年,斯科维尔把他这位病人的苦恼讲述给了另外两名医生——蒙特利尔的怀尔德·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和他年轻的助理研究员布伦达·米尔纳。不久,米尔纳女士就开始每隔几个月搭乘一次晚间火车前往哈特福德去见莫莱森,和他在一起,并研究他的记忆。从此,他俩开始了一个长达10年、最为不同寻常的“合作伙伴”式交往:由米尔纳引导着莫莱森做各种各样的稀奇事情,而莫莱森总是十分配合,怎么要求他都会点头同意,而且他很清楚两个人合作的目的,只要在他短时记忆的时间范围内。米尔纳后来说,在那一个个飞逝而过的短暂瞬间里,他们俩真的是合作伙伴。而且,那一次次的合作迅速而永恒地改变了人们对学习与记忆的理解。
米尔纳对莫莱森的第一次记忆实验是在斯科维尔的办公室里进行的。她先是让莫莱森记住三个数字:5、8、4,然后她离开办公室去喝了一杯咖啡,20分钟之后再回来问他:“那几个数字是什么?”莫莱森在她离开之后一直都在反复默诵着那几个数字,所以,他说对了。
米尔纳道:“哦,这好极了。”然后她接着问道:“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吧?”
“对不起,我不记得了,”莫莱森道,“我的问题就是记忆时间较短。”
“我是米尔纳博士,我来自蒙特利尔。”
“哦,蒙特利尔,在加拿大。我去过一次加拿大,我去过多伦多。”
“唔,好。你还记得刚才那几个数字吗?”“数字?”莫莱森道,“什么数字?”
“他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非常有耐心,每次都很愿意完成我交代给他的任何事情。”米尔纳告诉我说。如今,她已经是认知神经科学专家,在蒙特利尔神经科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以及麦吉尔大学担任教授。她说:“可是,每当我走进那间工作室,他都像是从来没有见过我似的。”
1962年,米尔纳发表了她里程碑式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她与莫莱森的研究项目。为了保护莫莱森的隐私,她在报告中将他化名为H.M.。该报告表明,莫莱森的一部分记忆能力完全没有受到损伤。在一系列的实验中,她让他对着镜子,看着镜子中的手,在一张纸上画出五角星来。这么做当然很别扭,而米尔纳还偏要加大别扭程度:她让他拿笔沿着五角星的边框画线,就像是在让他走迷宫,一个五角星形状的迷宫。每次莫莱森做这个练习,都像是第一次做,感觉很是意外。他完全没有曾经做过这件事的记忆。可是通过反复练习,他终归熟练了起来。米尔纳说:“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之后,有一次莫莱森告诉我说:‘哈,这东西做起来比我想象得要容易好多嘛。’”
米尔纳这次研究报告的深远影响,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逐渐显露出来。莫莱森没有能力记住新的名字、面容、数据、体验等。他的大脑虽然仍有能力吸纳新的信息,可是因为没有了海马,他没有办法记住任何新东西。海马这一块脑组织及其周边的部分,也就是莫莱森在手术中被切除的部分,很显然正是构建记忆不可或缺的部位。
不过,他却仍然能够构建新的身体技能记忆,比如对着镜子画五角星,他在上了年纪之后,还学会了借助步行器走路。这种学习,叫动作技能学习,并不依赖于海马进行记忆。
米尔纳的报告表明,人的大脑中至少有两套系统负责记忆的构筑,一套负责显意识的记忆,一套负责潜意识的记忆。我们可以复习、写下今天在历史课或几何课上学到的东西,可是却不能用同样的方式复习足球场上、体操房里的训练,或是其他任何类似的动作学习。
那种身体技能上的学习会自然而然地熟能生巧,不需要我们去记忆和背诵。我们也许能说得出自己6岁时,在练习了几天后就能骑着自行车跑了,可是我们却说不清具体哪个动作技巧是在哪天学会的:掌握平衡、把握方向、踩脚踏板……这些能力在不知不觉中就提高了,而且突然就自动整合了起来,让我们能骑着自行车跑了,完全不需要去“复习”。
因此,认为记忆是均衡地分布在大脑中的理论就不成立了。大脑中应该有特定的、不同的部位,担当着构筑不同记忆的职责。
亨利·莫莱森的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米尔纳的一名学生苏珊·科金(Suzanne Corkin)后来在麻省理工学院把这一研究项目继续了下去。通过整合横跨40多年的数百次会晤与研究,她证明莫莱森的确保有手术前的记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童年家园的具体格局,等等。科金博士告诉我:“我们把这种记忆称为‘要点记忆’,也就是说,他有这些记忆,可是他没有办法把这些记忆按时间顺序串联起来,给人一个完整的叙述。”
除了莫莱森,还有其他人也接受过类似位置的脑组织切除手术,针对这些患者的研究同样显示,他们手术前后的记忆能力有着相似的变化模式。没有了能正常运作的海马,人就没有办法构筑新的、有意识的记忆。他们在手术之前已经记得的名字、面容、数据、体验,术后几乎仍然全部记得。那些记忆一旦形成,就一定是被放在了什么别的地方,而不可能是在海马里。
根据科学家们的研究,唯一可能存放这些记忆的地方,应该是大脑最外面那层薄薄的外皮层,也叫“新皮层”。新皮层是存放意识的地方,这里就像一个构图复杂的“百衲被”,每一块布片都担负着特殊的任务。视觉“衲布片”在后脑勺附近;控制运动功能的“衲布片”在大脑的两侧,也就是耳朵附近;还有一块“衲布片”在左侧,负责语言的翻译与诠释;其近旁还有另一块负责语言的说与写。如图1—3所示。

图1—3 大脑新皮层的分工
新皮层中的脑组织,也就是大脑最“表层”的部位,是唯一能够借助自身所具备的多种“工具”再现记忆的部位。正是它,使得大脑能够重现“自传体记忆”带来的那种生动而丰富的五官感觉,比如,能够重现“ohio”这个词,以及“12”这个数字所串联起来的相关资讯。而形成“高中第一天”的记忆网络,或者说网络群,一定就在这层脑组织里,即使不是全部在此,至少也是大部分在此。在我的“第一天”记忆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像红色头发、金丝眼镜、蓝绿色的墙面等视觉印象,以及嘈杂的大厅、砰然扣上的锁头、老师说话的声音等听觉印象,因此,这张网络中一定连带着很多位于视觉皮层以及听觉皮层的神经元。而你的“第一天”记忆中,有可能包括了学校食堂的气味、背上那重得要命的书包,因而也就连接到了那些负责感官的“衲布片”皮层。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衲布片”的位置来准确定位各种记忆在大脑中的具体储存位置。也就是说,记忆并不存在于某个单独的地方,而是沿着大脑新皮层各个不同功能的区域分布其间。
大脑不但能找到这些记忆,而且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将其再现,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眨眼间的事情,而且,那些记忆不但带有完整的情绪,还带着一层又一层的细节……这是无法轻易解释清楚的事情,没有人能说得明白大脑是怎么做到的。大脑这种最了不起的即时再现本领,倒是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图景: 记忆就好像是已经“存档”的一个个视屏,脑神经一个点击,就能启动播放,再一个点击,则又放回去了。
其中的真相,不但比这更为奇特,而且更是非常有用。
如果你的视线只顾着往大脑里面越钻越深,那么很可能会忘掉外在的主体——人。而且,这里说的不是泛泛而指的人,而是具体的人:一个直接拿着一盒牛奶往嘴里灌的人,一个总是记不住朋友生日的人,一个老是到处找钥匙的人,一个懒得计算角锥体表面积是多少的人。
我们稍微花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对大脑的近距离特写让我们大致了解了脑细胞是怎么构建出一个新记忆的:首先,当我们体验到一些事物的时候,脑细胞们就“唰”地亮了起来;然后,它们通过海马将亮起来的神经元连接成网络;再之后,还要沿着大脑新皮层中不同功能的不同据点,以一定的排列组合把这一记忆网络固定下来。
好,现在如果我们想看一眼人的记忆是怎么被“抓出来”的,即我们是怎么“记起来”某件事的,则需要退后几步,用广角镜头来看。也就是说,刚才我们把镜头拉得很近很近,以至于能清楚地看到电子地图上的一条条小街,而现在,我们却要把镜头拉远,来看看整个地区的总貌:看看人,看看以其认知方式揭示了记忆提取秘密的人。
这里我们所提及的人,还是癫痫患者,不得不说,我们的脑科学家们欠这些癫痫患者的债,可真是怎么也还不清了。
有些癫痫患者在发作时,大脑的神经元就像是化工产品的燃烧所造成的燎原之火,蔓延得又快又广,以至于整个人都瞬间遭了灾,像年轻的莫莱森那样,一下子就失去了知觉。这样的发作让人没法正常生活,而且药物治疗常常毫无作用,因此,人们不得不考虑大脑的手术治疗。当然,莫莱森经历过的做法是不会再被考虑了,因为毕竟还有其他办法。
办法之一,叫作“裂脑术”,也就是通过手术,切断大脑左右两个半球之间的连接,以求把癫痫发作的狂暴蔓延限制在半个大脑之内。
这样做能有效抑制癫痫发作,但代价是什么呢?是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之间没办法“对话”了!在我们的想象中,被分割开来的大脑一定会严重受损,甚至严重扭曲人的性格,至少也会严重损伤人的知觉能力……可事实并非如此。接受裂脑术之后,人的变化非常细微,以至于20世纪50年代针对裂脑患者的首次研究并没有发现任何在思考与感知能力方面的变化,智商也没有任何下滑,分析能力也没有任何损伤。
可是,一定会有什么不同,因为大脑切切实实被割裂成了两个半球!只不过,若想发现这种分割所带来的变化,必须要动脑筋想出足够巧妙的办法来才行。
20世纪60年代初期,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终于做到了这一点。他们设计了一种特殊的方式,能让患者一次只用半个大脑来扫视图片。这就成了!当接受过裂脑术的患者只用右脑看过一张餐叉的图片后,他们说不出那是什么,就是叫不出它的名字来。由于左右脑的连接已经被切断,所以,他们负责语言功能的左脑没有收到任何来自右脑的信息,而“看到”了餐叉的右脑又没有语言能力来描述所看到的东西。
这里,关键来了:右脑可以指挥它控制着的手,画出那把餐叉!
加州理工学院的三位科学家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后来由这些患者配合的一系列实验中他们发现,右脑还可以通过触觉来辨识东西,比如说,看一眼水杯或者剪刀的图片,这些患者就能凭触觉准确地把东西挑出来。
这一发现的意义显然很明了:左脑是智者,是语言专家,与右脑割裂开来后,人的智商完全不受影响;右脑是艺术大师,是处理空间与视觉的行家。左右脑必须密切合作,恰如正副两名飞行员。
关于左右脑分工的研究成果后来迅速渗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中,用来概括地描述某种本领或某种人的特征:“那家伙是一个右脑人”“她好像左脑更发达”……这还真令人颇以为然:我们所具备的敏锐而感性的审美能力,肯定不会来自善做冷静推理的那部分大脑区域。
不过,这些跟“记忆”有什么关系呢?
要弄明白这一点,须再等25年。而且,如果不是有人提出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那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这个问题是:既然我们有正副两名飞行员,为什么我们不觉得大脑是分两边工作的呢?
“最终,这个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迈克尔·加扎尼加(Michael Gazzaniga)
 写道。加扎尼加是20世纪6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那份研究报告的主笔者之一,另外两名科学家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左右脑是各自独立的体系,那是否意味着大脑具有统筹意识?”
写道。加扎尼加是20世纪60年代加州理工学院那份研究报告的主笔者之一,另外两名科学家是罗杰·斯佩里(Roger Sperry)和约瑟夫·博根(Joseph Bogen)。“这是为什么呢?如果说左右脑是各自独立的体系,那是否意味着大脑具有统筹意识?”
这一问题悬置了数十年,没人能找到答案。科学家们越是往深处探究,谜团似乎越难破解。探索者们的研究不但昭示了左右脑各自清晰而奇妙的不同功用,而且还源源不断地发掘出更多、更复杂的独立体系:大脑有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个独立模块,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比如,这个负责计算光线的变化,那个负责声音的辨识,再一个负责分析面部表情的变化……科学家们所做的尝试越多,他们发现的大脑独特功能就越多。他们还发现,所有这些“小型程序”全部都能同时运作,并且常常同时跨越左右两个脑半球运作。
也就是说,大脑不但在统筹左右这两名“正副飞行员”时带着整体意识,而且,在应对来自各个角落互不相让且鼓噪程度不亚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的神经元时,也以整体意识统筹着一切。
大脑是怎么做到的呢?
答案,竟然还是在裂脑术之中。
20世纪80年代初期,加扎尼加博士在他的“招牌研究”,也就是裂脑研究中又添加了一个变式。举其中一项实验为例,他拿了两张图片给一名患者看,不过,其中一张只有患者的左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只鸡脚;另一张只有右脑能看到,上面是一幅雪景。请记住,左脑是语言控制中心;右脑则是全能大拿,感知敏锐,只是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它感受到的一切。
然后,加扎尼加博士拿出另一组图片,包括一把餐叉、一把铁锹、一只鸡、一把牙刷等,这回,他不但让患者左右脑同时都能看到,而且还要让他从中挑选出跟刚才看过的那两张图片有关联的图片。这位患者挑选了一只用脚走路的鸡,还有一把可以铲雪的铁锹。看起来都蛮有道理的样子。
再然后,加扎尼加博士请患者解释为何要挑选这两幅图片。答案却很让人惊讶。针对第一个选择,患者解释得很有条理:鸡要用脚走路。他的左脑看到了那只鸡脚,而左脑不但为他提供了语言来描述那只脚,更给出了脚与鸡相关联的合理解释。
可是,他的左脑并没有看到那张雪景图片,只看到了铁锹。因而,他只是凭直觉选择铁锹,却做不出条理清晰的解释来。博士要求他解释为何认为铁锹是有关联的东西,他搜寻了自己的左脑,却找不到有关雪的象征符号。怎么办呢?他又看了看铁锹图片,说:“铁锹是用来清理鸡屎的。”
左脑根据它能够看到的铁锹,抛出了它能够给出的解释。“这种做法,正是我们胡说八道的老套数。”加扎尼加博士对我说。回想起实验中的这段往事,他忍不住哈哈大笑: “编出一个故事来。”
在随后的一系列实验中,他和他的伙伴们发现,这一“编造模式”与我们的日常表现相当一致。左脑能根据它所看到的东西编造出一套有条理的说法来。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脑每天都做着这样的事情,你我都有过相似的体验,比如,听到别人在悄悄话中提及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就会假想出一些东西来,把那段我们没听清的“八卦”给补上。
大脑里的这些鼓噪之所以能让我们觉得尚有一致的逻辑性,是因为大脑中的某个模块或者网络在不断地抛出一串串符合逻辑的故事。加扎尼加博士说:“我足足花了25年时间,才终于想到问题的真正核心:为什么你要选那把铁锹?”
人们目前只知道这一模块藏在大脑左半球的某个地方,可没人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以及它怎么就能那么迅速地把那么多信息一下子串联到一起。这一模块有了一个名字,加扎尼加博士把我们左脑的这一叙事系统模块命名为 “解释器”。
借用前面“电影摄制组”的比喻,这就是我们的“导演”。这位导演要让每一段情节都合情合理,要根据其现有的材料找出答案、做出判断,要把松散的资讯拼合成一个能让人理解的整体。借用加扎尼加博士的话说,这位导演不但能让人觉得情节的结果合情合理,而且还能编出一整套让人觉得合情合理的故事来:它会创造出一套意义、一套说法、一套因果关系。
这可不仅是一台解释器,更是一位编故事的专家。
而这套模块,恰是构筑一段记忆的关键所在。它每时每刻都忙于解答“发生了什么”,而它作出的判断,则通过海马汇编成码。这还只是它的一部分工作而已,因为,它还需要不断解答“昨天发生了什么?”“昨天晚餐时我都做了些什么?”这类问题。它还需要回答全球宗教课堂上的问题:“请再回答一遍,佛家最根本的四大真相是什么?”
这时,它同样要收集现有一切可收集的素材来解答,只不过,它需要向内搜寻感官上以及数据资料上的提示,而不是向外部搜寻。这就叫“思考”。要回想佛陀所说的真相,不妨从其中一个开始,或者是从其中之一的某个局部开始。对了,痛苦。佛陀谈到痛苦,他说痛苦是……是要先弄明白痛苦是怎么一回事。这就是第一真相。第二真相好像跟冥想有关,不需要做什么,只须放下。放下痛苦?是的,或者说很接近了。还有一个真相是……脑海中浮现出一条山道,一个穿着长袍的和尚在道上踽踽独行……对了,道路。走这条道?跟随这条道?
思绪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串。每当我们“回放胶片”的时候,似乎总会有新的细节冒出来:厨房里传出的香味、一个营销电话的打扰……还有,当你读到“放下痛苦”时,心里感受到的平静。哦,不对,要放下的是让人感到痛苦的“根源”。还有,不是要“走过”那条道,而是要“滋养”那条道。这些局部的细节之所以像是“新”的,是因为大脑在那一瞬间所吸纳到的信息远比我们能意识到的多,而这些我们当时没有意识到的感知,会在我们回想时浮出表面。
换句话说,大脑并不会像电脑那样,把数据、想法、体验等先储存起来,等我们点击文件名时,每次都显示出完全一样的画面来。大脑的做法固然是把它的感知、想法、得到的资讯等都放进记忆网中,可是,每当这些记忆往外冒时,“泡泡”的组合总会略有不同。还有,这段刚刚被提取出来的记忆并不会从此替代掉上一次的存储内容,而是与之相互交织在一起,相互重叠在一起。
没有任何细节会彻底丢失,只不过,记忆提取的“踪迹”每一次都略有不同,而且永远如此。用科学家的话来说,这是用我们的记忆来改变我们的记忆。
到此,我们已经讨论了脑神经元以及细胞网络,讨论了拉什利的大鼠还有莫莱森先生,讨论了海马以及接受了裂脑术的患者,还有编故事的专家,这一切,似乎都是很初级的东西,甚至可以说是再普通不过的东西。
其实不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