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APT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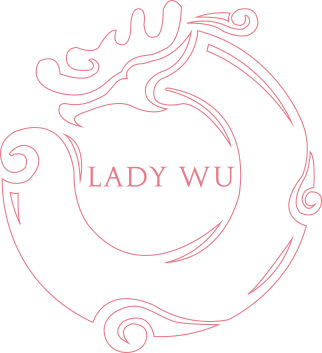
在过去数十年间,残杀纷乱,诡诈争夺,大唐皇室势将中道沦亡,真使人肝肠痛断。现在我(邠王守礼)决心把那些年间的回忆写出来。过了二十四年之后,现在在当今玄宗皇上御临之下,天下太平,万民安乐,我辈唐室王公才得重沐皇恩,再享荣华。我们这一些老一辈的人,亲历过那些年月,真觉得往事如噩梦一场,几乎无法信以为真。许王素节之子堂兄郢国公璆也蒙上天嘉佑,得以幸全。在当年一次大屠杀当中,他父亲与先父同时遇难。璆为人仁厚,曾经帮助过很多王公的子孙。他也是早丧双亲,伶仃孤苦,饱受恐怖饥饿之苦,在中国南海之中,海南孤岛之上,在亚热带灌莽丛林内,徘徊踯躅,寂寞凄凉,心里时时觉得如罪人之子,姓名之上,也蒙羞带垢。他母亲和九个弟兄同日遇害,他自己和三个幼弟被放逐海外。近来他和我常把杯共坐,谈论惊世骇俗的祖母则天武皇后。他对他父亲的所作所为极其仰慕,颇以为荣,正如我对先父一样。他父亲和先父贤王同时摄政在朝,都是当代通儒。学问地位有什么用呢?他父亲身受绞刑,先父被迫自缢身死。今日我俩追谈往事,正如舟子自海上惊涛骇浪中得幸归来,畅谈当时情况一样心情。
一个人怎样写自己的祖母呢?如果祖母是个娼妓怎么办?在皇室里,连当今皇上玄宗皇帝在内,虽然对祖母的子侄等我们不讳言他们的背逆,对祖母却不可出言不敬。说话的时候,有人偶尔提到祖母的名字,大家立刻肃静下来,因为她是我们的祖母。不过,我个人对这件事并不太拘谨,因为她是不是我的祖母,颇可怀疑。我颇为相信先父是武后之姐韩国夫人所生,不是武后生的,此点以后在书中交代。
现在,我必须说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人们都以为我有一种洞察先兆的能力。有一次在今年四月,天气晴朗干燥。玄宗皇帝的皇兄岐王来访,我微微觉得不舒适,心绪不畅快。我说:“我敢说天要下雨了。”果然不错,才过了半天的工夫,天就变了,大雨倾盆,一下十几天。在另一次吃饭的时候,我向岐王说,“不久天要放晴了。”当时天空没有一点儿放晴的样子。岐王不信我的话。我说,“你相信吧,没错儿。”第二天,果然雨止天晴。岐王告诉皇帝陛下,说我有未卜先知的能力,皇上问我是不是。
我说:“我并没有道法仙术。只是年轻时在东宫幽禁的时候,一年之中总受武氏兄弟鞭打三四次。当时陛下年纪太小,还不记事。伤疤后来是好了,可是留下了病根儿。天气一变,就浑身彻骨疼痛。天要放晴了,我才觉得轻捷。不过如此而已。”我又补上一句说,“谢谢祖母老人家。”
空气立刻紧张起来。好像我有什么失礼之处似的。
我并不相信我们应当这么拘谨。皇上对我很恳挚,就跟对其他诸弟兄一样。当年就是玄宗皇上他本人带兵进宫,在突然袭击之下,结束了武氏乱政的残局,扑灭了余党。他内心何尝不深恨武懿宗、武三思?有一次,他十几岁的时候,被放出宫去祭谒太庙,他本人和随从都被武懿宗横加阻挡。那时武氏正权倾一时,气焰万丈。他当即怒斥武懿宗说:“你好大胆!这是我们的祖庙,李家的祖庙!与你有什么相干?”但是现在他不愿我们提到祖母的事情。传统看法都认为祖先所作所为不会有过错——这又何必?不论如何吧,我若不把祖母武后她个人生活的或政治上的非常奇特的行为措施和她那惊世骇俗的勋功伟业,坦白忠实地写出来,这种回忆录就根本不值一写了。
时代已经变了。武氏宗族已然过去,虽然仍为人所记忆,但已埋葬入土,长此已矣。当年一提到祖母,我们就心惊胆战。如今追忆当年,她只像一个势穷力蹙的魔鬼,已经消失不在了。有时候,她的暴乱奢侈,她的刚愎自用,看来甚至滑稽好笑。她爱生活,生活对她一如游戏,是争权夺势的游戏,她玩得津津有味,至死不厌。但是,到了终极,她所选择的游戏,并不很像一个顽强任性固执己见的妇人统治之下的一段正常的历史,倒特别像一出异想天开的荒唐戏。她当然是决心要做一个有史以来最有威权最伟大的女人。她之终于失败,绝不是她的过错,她的武家全族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她一半的智慧、一半的个性、一半的才能。
现有我清闲无事,写下那些往事的回忆,正好使得我有事情做,这项工作既是值得做的事,我又觉得胜任愉快。我相信对我一定很有益处。我当然不敢希望写出一部像先父编的那部详赡渊博的《后汉书注》,要藏之名山,传诸后人,我只盼望据实写出来我当年知晓的那些人的秘史和那些值得记忆的故事,尤其是我们皇家的情形。关于我自己的话,就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