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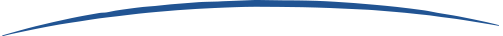
3.25 通过观想将我们化身于大象的力量和勇气之中,久之我们即会充满如大象般的力量和勇气。同理,通过观想将自己化身于某个事物,久之我们即会拥有此事物的品质和特征。
唐末五代道家有一部书,是谭峭先生著的《化书》。《化书》分为“六化”:道化、术化、德化、仁化、食化和俭化。《化书》本齐物以言“道化”;本虚无以言“术化”;本无为以言“德化”;本道德以言“仁化”;本税多民饥以言“食化”;三宝之一为俭,本之以言“俭化”。谭峭所著《化书》之基本思想与圣哲此节经文旨趣一脉相承。在其他经文处,圣哲多言道化、德化、仁化,唯于此节经文,圣哲所论重心在术化。用中国哲学的观点看,“术化”就是“气化”。“气”是能量和势力,这是一个形而下的概念。庄子曰:“气聚成形,气散为风。”这与现代物理学,特别是量子物理学有相通之处。气是一个形势到另一个形势的中介。以此中介,一个形势就可以转化为另一个形势。这就是中国传统医学和哲学所谓的“气化”学说。
“一个形势转化为另一个形势”有两种转化方式:一种为显形,一种为隐形。显形就是不仅内在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就是此事物的外在形象同样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隐形就是只是内部结构和功能等发生巨大变化,而外形看上去很少或没有发生变化。此节经文所论,主要指的是第二种转化——隐形的转化——“久之我们即会拥有此事物的品质和特征”,但我们的外形(即身形)并没有因“拥有此事物的品质和特征”而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我还是我,但又不再是我。我还是我,那是因为我的外形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又不再是我,那是因为我的内在获得了新的品质和特征——“如拥有大象般的力量和勇气”。
时常观想自己的身体转化为大象(也即观想大象的身体成为我们的身体),逐步地大象越来越精神化,沉入到我们的精神深处而成为我们固有的品质。如此,我们(主要是指精神方面)就拥有“大象般的力量和勇气”。同理,也可以观想自己化身为狮子、老虎等等,久之,我们的精神深处即拥有狮子或老虎的品质。也可以观想白云、花朵(莲花等)、太阳、月亮等,“通过观想将自己化身于某个事物,久之我们即会拥有此事物的品质和特征”。
认同于什么(即我们化身于什么),我们即是什么。如某画师生而五官丑陋,因久画佛像,面相遂转端庄俊美。但此例仅是外表之转变,瑜伽修行可实现诸多更内在更深刻之转变。
3.26 深度沉潜于光明之中,我们就越来越能洞悉(一切事物深处的)精妙、隐蔽和深远。
光明分为两种:一种是可见光,一种是不可见光。可见光就是物理学的光,不可见光就是意识里的光。意识里的光就是般若,就是智慧。这种光看不见,物理学测不到。过去称之为“心光”“神光”“佛光”“性光”等等。耶稣说“我是生命,我是光”的“光”,就是这个不可见光。
“深度沉潜于光明之中”,即时刻观想自己的整个身心、整个存在不断深入地化为光明。把自己光化就是精神化,就是智慧化,就是清净化,就是无我化,就是无形化,就是自性化。后来的瑜伽称此观想出来的光明为“子光明”,把本性本有之光明(即觉照)称为“母光明”。通过观想“深度沉潜于光明之中”,就是通过“子光明”进入到“母光明”之中,最后子母光明融合为一:开始是强制性地观想自己化身为光明;一段时间过后,逐渐发现,我们本来沉潜于光明之中;再后来就发现,我们不只是沉潜于光明之中,我们就是光明本身;最后蓦然发现,岂止是我们这个个体就是光明呀,整个天地宇宙,一切的一切,都是光明之化现,都是光明本身,这个世界除了光明之外,别无他物。——这个光明就是本性,就是般若,就是觉照。这就是从“子光明”过渡到或进入到“母光明”的过程。这个过程之长短因人而异。有些人可以在一次禅修中完成全过程,有些人则需要数年或数十年。
在公元5到7世纪,是印度的佛教在密宗化的过程中,大量吸收各流派瑜伽、印度教等思想、习俗、学说、修行方法等最为集中的时段。7世纪前后,密宗又经历了一次深度消化所有的吸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的时段。由于对各种修行方法的吸收和创新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乱,令修学者难以适从。史称此时期为印度佛教密宗的“杂密时期”。“杂密时期”持续了三四百年。直到公元10世纪及以后,经过无数密宗大师们的努力,将佛教内已有的修行方法,还有从各流派瑜伽和印度教等流派大量吸收来的修行方法和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二次创新等,进行深度的融合和提炼,最后诞生了一位叫那若巴(1016-1100)的大师,将其提炼出核心的六类方法。因这六类方法皆可让凡夫直达圆觉,故名“六根本成就法”,简称“那若六法”——拙火成就法、光明成就法、幻观成就法、梦境成就法、中阴成就法和迁识成就法。其中“拙火成就法”与“光明成就法”因修行方式类似,存在相互关联,为一对;“幻观成就法”与“梦境成就法”为一对;“中阴成就法”与“迁识成就法”为一对。
佛教密宗六根本成就法之光明成就法即来自《瑜伽经》中圣哲于此节经文处的教授。拙火成就法在另一节经文中也有明确教授。至于其他成就法——幻观成就法、梦境成就法、中阴成就法和迁识成就法等根本成就法之教授,《瑜伽经》中或虽无明文教授之,但并不是没有教授之,圣哲将其隐于相关经文的字里行间,以殊途而同归、一体而异名的方式教授之。
般若有两种功能,一为认知(觉照),一为创生。因光明就是般若,“我们就越来越能洞悉(一切事物深处的)精妙、隐蔽和深远”,此处是就般若两种功能之一的(存在性)认知而言。
3.27 通过观想将自己化为普照天地的太阳,可达到洞悉宇宙万物。
3.28 通过观想将自己化为月亮,可达到洞悉各星宿的位置。
3.29 通过观想将自己化为北极星,可达到洞悉各星宿(包括北极星在内)的运行。
此三节经文教授的是关于印度传统星相学的奥秘。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一样,也是视人体为小宇宙,有“天人相应”“天人感应”之说。此三节经文就是在“天人相应”“天人感应”学说基础上进行禅修和观想,旨在进入深度的禅定中体会和洞悉出日月星辰的方位、运动轨迹、对身心的作用和对人生(即命运)的影响等相关知识和学问。在过去的印度,瑜伽士担负的文化使命和社会职责非常多,一名合格的瑜伽士,不仅是一名杰出的修行家、理论家、哲学家、慈善家、医学家,调解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外交家,甚至还要成为演讲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等等。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成为一名预言家——需要成为一名精通手相、面相、星相、梦相(即解梦)等知识和学问的预言家。因为在印度瑜伽史上,瑜伽师和预言家是不分的——多数瑜伽师是预言家,多数预言家是瑜伽师。根据这一历史事实,圣哲于此处给出与预言学中的星相学相关的教授。但这里也有需要提示之处。
1.此三节经文中所言日、月、星宿是星相学中的日、月、星宿。星相学中的日、月、星宿与现代天文学中的日、月、星宿,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其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星相学中的日、月、星宿主要是从它们对人类的身心和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角度来看待和理解日、月、星宿的。因为动机不同,如此理解和研究出来的知识和学问,属于星相学,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2.“各星宿的位置”是指它们在星相学中各种星宿图上的位置,不是它们在现代天文学上的精确位置;“各星宿的运行”是指这些星宿对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规律性作用,同样不是指它们在现代天文学上的精确运行规律。
3.尽管古印度星相学的发展,对原始天文学和历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但古印度星相学毕竟不是以成就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为目的。古代星相学的动机和目的是不变的,即渴望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天体对个体的身心活动和社会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从这些影响和作用中发现规律以实现预言之目的。故印度传统的星相学与肇始自西方的现代天文学终究不可同日而语,它们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学科。星相学隶属于生命学范畴,而天文学则是现代物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天体物理学。
4.研究和探索方法的差异。星相学十分注重禅定体悟和般若直觉——通过身心的内在体证和感受来发现和探索日月星宿等对人体内在身心的影响和作用,以及这些影响和作用的规律等。这种知识和学问更多地偏向于存在之知、生命的学问。天文学的研究和探索方法是常规的物理学方法——实验法、观测法等,所获知识和学问则属于结构之知、物理的学问。
5.尽管在古印度有着瑜伽师就是预测师的,或反过来,预测师就是瑜伽师的传统,但并不是所有的瑜伽师都必须得精通预测学。在古印度,对包括星相学在内的各种预测学的精通者,毕竟是少数人。在历代著名的瑜伽大师那里,事实上多数瑜伽师是反对弟子们花大精力和时间来研习预测学的,因为些大师们认为,预测学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太强,更重要的是它与瑜伽所追求的开悟和解脱没有关系。花大精力来研究它,这有违瑜伽修行的终极目的。故不予提倡。
圣哲在此处涉及到星相学,其意并非希望人们都去研究星相学,只是因为瑜伽中有此一项,有此一分支,不可完全地无视之。故于此作一原则性的提示和方向性的指导。若深入星相学等印度传统预测学,那是一个书山学海,风格各异,流派纷呈,非数十年之功不能得其门而入,岂是仅此短短三节经文而能详尽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