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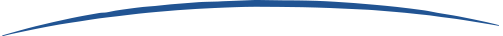
1.6 它们是:正见、邪见、概念化、昏沉和记忆。
1.7 正见来自直接的觉察、推理或他人(圣贤)的教导。
“正见”是“正确见解”的简称。那“正见”从哪里来呢?从“直接的觉察”“推理”和“圣贤的教导”这几个方面来。“直接的觉察”就是感官的直接觉察。这是我们作为一个常人获得知识的最主要的方式。用五官来认知这个世界,久了,将形成一些经验和常识。这些经验和常识将是我们生活的保障。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个一个这样的个人经验和常识集聚延伸出来的。没有经验和常识,则无人类的历史。从个人的五官的觉察开始,到经验的形成,再将经验提炼为普遍化的常识,最后将这些常识集聚延伸为民族的或人类的历史。这些历史将成为人们判断对错好坏的重要标准,是保障人们不迷失方向的重要参照。这就叫“以史为镜”。
比如说,老人们常讲:“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一个常识吧。近几年来,在我身边三十多岁仍然没有成婚的大龄男女们,他们的精神痛苦程度远比其他人多很多。他们中人格扭曲、性格变异者,远比其他人多很多。为什么呢?就是这些人违背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一人类常识。引用西方宗教的观点来看,男婚女嫁是上帝规定的,是上帝的意志。你男大不婚,女大不嫁,就是违反上帝的意志。一旦违反了上帝的意志,那必受上帝的惩戒。
人类数千年来发现的一些普世价值体系,以及一些用无数人鲜血换来的常识,自有它们如此这般之道理,自有其存在之必然。对于这些常识和经验,是我们正见的重要来源。
其次,正见的另一来源,是合乎逻辑的“推理”。推理能力是人类异于动物之处。只有人类才有这种能力,它能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事物,更抽象地认识事物,也更精确地认识事物。
正见的第三个来源是“圣贤的教导”。无论是文化的传承,还是瑜伽的传承,师者所扮演的作用,是无论如何高估也不为过的。在中国,在印度,在所有传统文化深厚的文明古国,无不极力提倡尊师重道。像佛陀和帕坦伽利这样的大彻大悟者,他们了彻生命的所有内涵,他们知晓修行所有可能的方法,他们明白所有的道路通向哪里,所以,他们是人间的导师,乃至三界六道一切众生的导师。故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和生命。”尤其是我们瑜伽修行和生命觉醒,没有不在明师的教导和启迪下就可以达到开悟的。师者之传道,师者之授业,师者之解惑,是我们在这个迷乱颠倒的世界里拥有正见的又一保障。
1.8 邪见是错误的知识,这些知识与事实不符。
“邪见”又名“恶见”“非正见”。不同的学术流派对正见与邪见的定义是很不相同的。婆罗门教(即印度教前身)有三大基本宗旨:《韦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佛教和耆那教同时崛起于公元前6-5世纪,作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坚定批判者。在佛教眼里,《韦陀》类经典,固然有其开一代文明先河之功,但这些经典的不足之处,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思想原始,学说粗糙,观念混乱,谬论满篇。至于其他两项——“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就更是荒诞不经,可笑之至。
但印度毕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文化源远流长,其思想精致入微。有一些基本哲学观念为印度各思想流派所共识:中道为正道,无偏之见为正见。非中道皆为邪见。如“增益见”——人为地附加一些东西于事物。“减损见”——人为地消减一些东西。“断见”——万物皆灭,死不复生。“常见”——万物永不消灭,恒常不变。“见取见”——不虚心学习,一惯地认为只有己对,他人皆错。“虚无见”——认为人类不可能认识生命和宇宙的真相,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明智之举就是得过且过,甘心做一名犬儒即可。“障道见”——修行和觉性成长的根本障碍,印度修行者总结了五大类:贪——占有之念太重,永不知足;嗔——仇恨一切,甚至包括自己;痴——以无知为伍,以堕落为荣;慢——自大骄矜,仗势欺人;疑——对任何人与思想学说等一律作邪恶想,皆有害于己。
这些统统是恶见、邪见、障道见。
1.9 概念化来自语言上的知识,但与事物的真相并无关联。
人类有一种非常流行的疾病:爱说话。人类是一个如此爱说话的动物。对于很多人来说,不让他说话,就意味着宣判他死亡。打开电视和广播,看看马路上的人群——在任何一处有人的地方,就会听到无休无止的说话声。甚至当这些人在独处时,没有人和他说话,他就会自言自语——和他自己说话。天呀,我们竟然没有疯掉,这真是一个奇迹。
人们创造了很多很多个概念,这些概念只有一个用处,就是提供人们说话之用。这些概念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为了让人们能保持着无休止地说话而创造出来的。每个人都像是一个醉汉,在嘴上,在心里,在办公室,在家里,在可能的所有地方,对着自己、别人和一切可能之物,不停止地说呀说,大有说到海枯石烂之势。整个人类之所以如此虚弱、混乱、肤浅、堕落,如此热衷于制造问题与麻烦,其中有95%以上,是因为我们说话太多之故。如果我们减去时常讲话的一半,每个人都是智者;如果我们减去一半在心里对着自己的喋喋不休,我们必定是一名瑜伽大成就者,至少也是一名身心高度健康而长寿的人。
语言是一个可怕的囚笼,它能编造出很多很多枷锁——意底结牢,然后将我们装进去并抛弃到荒漠里。我们中语言之毒是如此深重,以至于我们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它了。每天我们在大量地使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名词和术语,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它们的含义的——我们仅仅是在一次又一次地使用着它们,至于它们究竟是什么意思,似乎从来没有思考过或留意过。对概念和术语的误用和滥用,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在当代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峰,但它们“与事物的真相并无关联”。
印度的瑜伽修行里有个很好的方法就是禁语——让自己从语言中摆脱出来,从各样的概念中摆脱出来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当年圣雄甘地就有一个时常禁语的习惯。不只他有这个习惯,印度多数人都有此习惯,禁语一天,数天,一年乃至一生等。即使没有修行禁语的瑜伽士,也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话很少,每天只说一些非说不可的话,能一句说完的,不说三句,能用一个字表达清楚的,不使用一句话,也就是尽可能地减少对语言和概念的运用。干扰我们身心和谐最主要的敌人就是言语,障碍我们深入静定的,最主要的就是言语。
瑜伽传统里的禁语法,后来成为了佛教、印度教等各修行流派的一个共法。大家都在采用这种有效的方法。再后来,禁语随着佛教一起传到了中国并成为中国佛教徒的一个重要的修行方式。
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有位禅师向路边的小和尚问路。只见小和尚指指自己的嘴巴,摆了摆手。禅师明白了,这个小和尚正在禁语期间,不能说话。于是禅师对小和尚说:“小师父,你在禁语呀?”小和尚点点头。禅师接着说:“很好呀,如果把内心中的自言自语,也一并禁了,那就更好了。”小和尚一听,颇有省悟。禅师说完后就走了。小和尚在后面大声喊:“大德,大德。”禅师回头问小和尚:“你是在喊我吗?”小和尚说:“不是我喊的,我在禁语。”禅师含笑着点点头,走了。
1.10 昏沉是没有任何觉知的存在状态。
其实不受控制的喋喋不休就是一种动态的“昏沉”。昏沉未必一定是躺在那里陷入昏迷中。失去觉知的状态就叫昏沉。哪里没有觉知,哪里就是昏沉。瑜伽修行的目的就是获得生命(意识)的终极觉醒。要想获得这种生命的终极觉醒,必须不断地深化和拓展我们的觉知,让我们的觉知不断地成长、清晰,并尽可能地在生活和禅坐时,保持着持续的“在场感”。“在场感”简称为“在”,时时在我们的生活中,时时在我们的精神中,时时在我们的感受中,时时在我们的体验中,时时在我们的瑜伽中……这种时时不离的“在”就是觉知。这种不断深化的觉知是我们获得终极觉醒的唯一途径。
昏沉是瑜伽修行的天敌。尽管导致昏沉的因素很多,但不受控制喋喋不休地说话——对自己说和对他人说,是引发我们昼夜皆处于昏沉的主要途径之一,因为说话和语言对我们构成了极深的催眠——一种动态下的催眠,这种动态催眠就是昏沉。昏沉与睡眠不同。昏沉是一种失念状态,是一种闷厥状态,是一种不在场的缺席状态,是一种魂不守舍、行尸走肉、空虚麻木的状态。这是一个人所能有的最糟糕的状态之一,也是最为可悲的状态之一,它有时候甚至比邪恶更可怕——当进行邪恶之事时,至少他是清醒的,是处于自控状态的,是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的状态。放下屠刀的人,有可能立地成佛(“佛”者,觉醒义);但处于“深度的动态催眠之中”的昏沉之人,是断不可成佛开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