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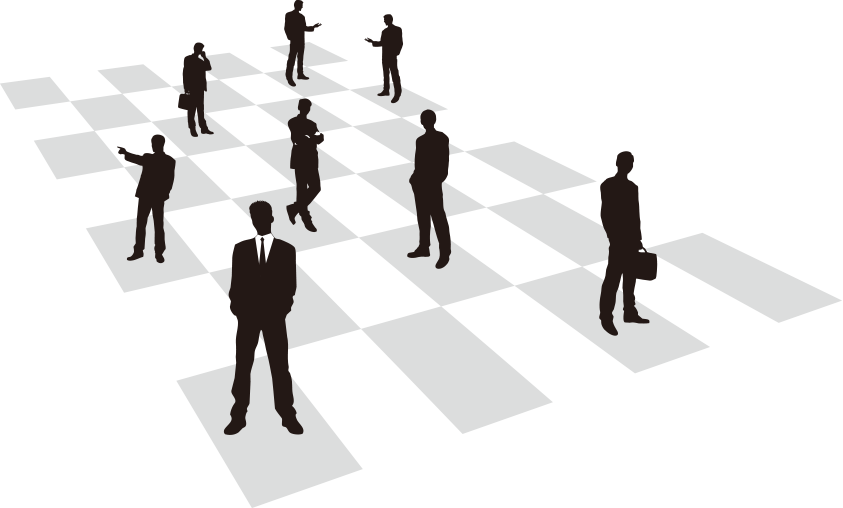
“拿起这把刀,我现在轻而易举地就可以扎他个透心凉。”大多数人都有过这样的念头,这称作侵入性想法。但大多数人都对自己的侵入性想法避而不谈。
事实是,大家自己不去谈论这些想法,直到有一天,精神病医生不得不问起它们。而等大家开始讨论侵入性想法的时候,一个又一个调查结果却显示,十分之九的人都承认他们有过侵入性想法,这让他们感到痛苦、迷惑、震惊、茫然不知所措。大多数人也都有过把车开到马路外面去的想法。有三分之一的人承认自己生出过抢钱的念头。有四成的人有过从高处跳下去的冲动,这种冲动极为常见,因此有了自己的学名:高处综合征。五成女性和八成男性幻想过陌生人赤身裸体,而有一半人则会不由自主地想象自认为“恶心”的性行为。
侵入性想法无处不在,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有人注意到它的存在。当时出生于南非的心理学家斯坦利·拉赫曼和他的斯里兰卡同事帕德马尔·德·席尔瓦有了震惊世人的发现。他们试图了解强迫思维的性质,但是在此过程中,两人却意识到很多正常人似乎跟强迫症患者有着一样的奇怪想法和冲动。
他们研究的强迫症患者有辱骂和攻击别人的冲动,但是他们发现,其实自己的朋友也有同样的冲动。患者说自己有时想把别人推到火车或汽车下面,或是从高处跳下,或是有意撞车。而他们的同事也曾有过同样的想法。患者和正常人都在做爱时幻想过暴力行为,都觉得自己可能犯过新闻里听到的罪行,也都非理性地担忧自己正遭受某种毒害,如辐射或石棉污染等,还把这样的忧惧隐藏起来。
这些心理学家把从强迫症患者和自己“正常”的同事那里收集到的奇怪想法写在检索卡片上。当他们把卡片放在一起打乱以后,即便是诊所里最有经验的同事也无法区分,到底哪些想法来自于那些所谓精神病患者受到损害的头脑,哪些来自于和他们共事与来往的备受尊敬的同事。
我自己的强迫症始于一个侵入性想法,一片从夏日的天空飘落的雪花。“我们上楼去好吗?”女孩问我道。她很漂亮,一头黑发长长的,在我们亲吻的时候她不得不把头发从眼前拨开。她手臂的皮肤很光滑,而她的手在我记忆中好像很小巧。她比我大一些,尽管她不晓得。她问我:“你不会是一年级的新生吧?”这就没给我多少回旋的余地。除此之外,我对自己在大学上的课程也没说实话。其实我对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状况一窍不通,但对她来说这比化学工程要有意思。说实在的我对化学工程也知之甚少,那时候我才刚开始学一两个月而已。
那时候我18岁,是个快乐的大学生。真正的生活遥遥在望,时间对我来说就是白天上流体力学跟数学课,晚上享受美好的夜生活。我不了解化学工程师干的是什么工作,但是我才不管呢。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只用考虑第二天就可以了,这种感觉真爽。
时间是1990年11月,地点是英格兰北部。她穿着松松垮垮的T恤,紫色的裙子套在黑色紧身裤和马丁靴外面。我们一开始的对话干巴巴的。当时我对自己新留的连鬓胡有些洋洋自得,因此满心以为她会赞叹两句。后来我们出了大学校园,向外面那一排排迷宫般的带露台的房子走去。这时我才终于意识到她对此完全不以为意。于是我们就边走边谈,聊音乐,聊各自的朋友。我们到了她家,她邀请我进屋,关上了前门。一个新世界在向我招手。
这是个利兹常见的冰冷的夜晚,约克郡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她家厨房里的煤气嗤嗤地燃着火,却没有生出多少热,只能当照明用。寒意赶得我们在房间里四处乱转,就像林间野火吹出的飞烟。上楼这个主意听起来不错。
“你和那个女孩做爱了吧?”我的朋友诺尔第二天问道。
“不错。”我撒了谎。
“你戴避孕套了?”
“没有。”
“那可是容易染上艾滋病啊。”
“别说傻话。”
我和那个女孩做爱了吗?没有。我们戴避孕套了吗?没有。我会染上艾滋病吗?别傻了。但是可别说,尽管时时有人提醒,我当时还真的想都没想过有发生这种危险的可能。晚上我请诺尔喝了一杯,心想下回我可得谨慎一点儿了。我之前的确应该谨慎一点儿的。这样一个在谈话间生出的想法——你会染上艾滋病的——又时不时地飘入我的脑海,在里面回响,一直持续了几个月,但是每次我都能聚起足够的精神把它掐灭。别傻了。但是到了1991年8月的一个炎热的夜晚,我却再没能把它灭掉。
那是大学的暑假,我回到了父母家中。这个想法毫无征兆地再度出现。你会染上艾滋病的。但是这次我没办法再无视这个想法,也不能摆脱它引起的恐慌。危险实在过于强烈,后果实在过于严重,“别傻了”这个回答突然显得有些轻飘飘的。要是当时事情真的发生的话,我就有可能染上艾滋病。而如果染上了艾滋病,我就死定了。生活还没有真正开始就结束了。更糟糕的是,不管之后我怎么做,不管之后别人怎么说,都于事无补了。得了这种病,任谁都是无力回天的。我的命运将不再受自己的控制。我努力要把这个想法、这片雪花扫出自己的意识,然而它却挣脱了我的精神掌控,牢牢扎下根来。很快,又一片雪花和它搅在了一起,再一片,又来一片。接踵而来的暴风雪将雪花吹遍了我头脑的每个角落,铺下了厚厚一层雪毯,把所有地方都裹得严严实实。
卧室里闷得像是要窒息一样,我推开窗子,猛吸着外面的空气。关灯以后,我还能听到夏天的虫子在天花板上蠕蠕而动。音响的红色指示灯还亮着,从下午开始就一直开着了,我就在这同一张床上躺着,现在想起来已恍如隔世。我一把扯下墙上贴着的已经卷了角的海报,心中惊疑不定。为什么是我?我心惊胆战,指尖阵阵刺痛。我记得当时告诉自己,睡一觉,到了明天早上一切都会恢复正常的。生活就是这样——大家在晚上杞人忧天,但是到了第二天这些担心却都烟消云散了。
太阳升起来了,窗子和窗帘依旧敞开着。那个想法也依旧压在我的心头。你会染上艾滋病的。我下楼进了厨房,在新世界里用了早餐。从这天起我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我的余生都将在此度过,而这只是第一天罢了。我默默地看着父母有一搭没一搭地隔着木头餐桌拌嘴,心里想,要是我得了艾滋病,他们可不知道要有多伤心。我决定还是不告诉他们。回到楼上的卧室,我把脸埋进枕头里痛哭起来。我可能会得艾滋病的。
强迫症的强迫思维与那些可以排挤其他精神痛苦的执念不同。反复出现令人痛苦的想法并非就一定是强迫思维,至少从临床上来讲不是。有时我们头脑中只想着一个念头,要么是夸张而痛苦的忧虑,担心自己的孩子如何才能在世上安身立命,要么是学校测验或驾考前不堪忍受的神经质。但这类想法的出现都和我们真实生活中的规则与节奏相符,因为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幸福,我们也希望能通过考试。我们可以一刻不停地思虑和忧心,怕自己会丢掉工作,但这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需要这份工作带来的收入以养家糊口,凭感觉和本能我们都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
这样的想法是“自我协调的”。它们和我们的动机及意愿相一致。自我协调的想法使我们变得阴沉,但这是其内容所致,这种想法本身并非问题所在。我们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别人自我协调的想法没我们自己严重,那就还要遭到嫉恨。“真是难以置信,你居然火烧眉毛了才开始操心!”“这才过去一个月,我还挂念着他难道不是很正常吗?”
这种自我协调的想法强烈到极点就会导致精神疾病,经常是焦虑症。但是在其核心,焦虑的主要方向都是理性的。同样,抑郁症的阴郁念头也大多是理性的——对外界事务的反复咀嚼,对错误决定的遗憾,对生活不如意的悔恨等都是如此。就算是强烈的悲痛,甚至是歇斯底里,也都是出自理性的失落感。
而那些不请自来的侵入性想法,也就是强迫思维的原材料,却有所不同。它们是非理性的,与我们的心理并不协调。它们是“自我排斥的”,与我们秉持的观点相互冲突,也不符合我们在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只要转一下强迫思维的念头就足以让我们怀疑自己的人格。我们并非恶人,然而却在心里念叨着“从那个开着的钱箱里抢一把钱出来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我们不希望自己有这样恶劣而又荒唐的想法,不希望成为这样可怕的人,但大多数人却都转过这样的念头。
温斯顿·丘吉尔曾一度担任海军大臣,但他却讨厌乘船,因为他有种自我排斥的冲动,想要跳进水里去。丘吉尔是个著名的抑郁症患者。但尽管有这样的想法和类似的想去撞火车的念头(因此在站台上他常常站在柱子后面),他却并非是真的想要自杀。有一次,他告诉自己的医生查尔斯·莫兰,说自己特别讨厌睡在和阳台相连的卧室里,因为他会因此产生跳楼的冲动:
这种时候我其实一点儿也不想告别这个世界。我没有任何离世的意愿。但是这样的想法——让人绝望的想法,还是会进入我的脑中。
就像丘吉尔所说,生出侵入性的想法并不意味着人们希望把它们付诸实施。如果你产生了令人头疼的想法,想和儿童发生性关系,这并不能说明你就是恋童癖;就像一个人产生了不应有的冲动,想用榔头砸人,却并不能说明他就是暴徒或杀人犯一样。实际上正相反。一个人认为这样的念头或冲动是不应有的、恼人的、讨厌的——因此是侵入性的——恰恰足以说明它是自我排斥的,因此与这个人正常的性格和行为是对立的。
那么这些离奇的想法到底从何而来呢?答案很简单,却无法令人满意:“我们还没有搞清楚。”研究强迫症的心理学家给出的理论是我们大脑里有某种认知性的,他们称作“想法发生器”的东西。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发生器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为了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头脑需要产生新奇的主意,而不会立刻就对它们进行审查和排除。我们在公司里会进行头脑风暴,思考如何才能增加销售或是吸引顾客。这时候使用的是类似的原则——不管主意有多蠢,都会被写到记录本上。而经理则是斗志昂扬,点头称许。同样,想法发生器产生的反应不一定符合现实。侵入性想法可以天马行空,毫无事实根据。它产生的时候,我们的头脑一般说的是“好吧,那么……”,而不是“好吧,但是……”
不请自来的想法并不都是让人讨厌、惹人不快的,实际情况绝非如此。莫扎特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思绪,常常陶醉在音乐的遐想中无法自拔。贝多芬则说过类似的话:
你们问我从哪里来的灵感,但我却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灵感不请自来,有时候是直接的,有时候是间接的。我可以用手抓住它们;在大自然中,在林间,在散步的路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晨曦微明之刻,因境而生的情感可以被诗人转化成字句,而对我而言就是乐声,那种声音澎湃汹涌,回肠荡气,最终在我眼前化为一个个音符。
音乐天才偶尔生出的灵感固然是难能可贵,但前提是你要足够幸运才能拥有它们。而那些动不动就让我们这些凡人悚然惊起的想法却是奇怪而又惹人不快的。偏偏这些想法又阴魂不散地纠缠着你。没有人的强迫思维是对别人过于友善,也没有人会因为自己产生了冲动,要把所有财产都交给流浪汉而感到纠结。人们也不会向精神病医生抱怨,说自己的侵入性想法是要把一个身材堪比重量级拳击手的人推到地铁的车轮下。侵入性想法之所以恼人,是因为我们想象中的受害人都是些弱小者,是那些孱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人,是没长大的小孩子和弱不禁风的小老太太。心理学家称之为施瓦辛格效应。
这似乎有些道理,前提是想法发生器的理论能够成立,要确定的确是它在我们的头脑中运作,帮我们在生活里找到方向。有的想法让人感觉比较野蛮,但是在某些情形下见到陌生人时我们确实会自然而然地冒出一个反应,就是在陌生人的头上狠狠来那么一下。陌生人跟你相比越弱小,伤害你的几率越低,这个想法的诱惑性就越大。
根据这个理论,有时候外部的提示——火车的隆隆声或是肮脏的地板——就可以启动想法发生器,从而吐出好多侵入性想法来。而有时候触发想法发生器的是内部原因——重重压力或情绪低落的结果,抑或是来自潜意识情绪的转移或是不完整记忆的残留。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迫性想法的侵入看上去几乎是随机发生的了。
这种观点无从用实验来证明,因此我们没有实验证据进行支持。我们能确定的是侵入性想法在某些情形下冒出来的几率比较高,比如说在有压力的情形下。而它们一旦出现,我们如何应对就成了关键。自然的应对方式,特别是在这些想法不会自动消失的时候,就是力图赶走它们,把它们压个粉碎,把这些令人不快的念头推到我们精神空间里的家具背后,或是塞到地毯下面。这样的应对很糟糕,问题就是因此产生的。
列夫·托尔斯泰就很明白,头脑是无法驱除这些不应有的想法的。在孩提时代,这个俄国作家同家里的兄弟们玩过一个游戏。他们创建了一个叫作“蚂蚁兄弟”的俱乐部,其成员据说会发现奇妙的事情。而要加入这个俱乐部,只要能站在屋子的角落里克制自己不去想北极熊就可以了。但无论如何费力,托尔斯泰他们都做不到。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托尔斯泰同时代的人。他也知道这个有关熊的谜题。在1863年《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一书中,他写道:“给自己布置一个任务,尽量不去想一只白熊,但是这个可恶的东西却无时无刻地闯进脑海里来。”一个世纪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这段话又出现在美国杂志《花花公子》的一篇文章中,凑巧被一个学习心理学的大学生丹尼尔·韦格纳读到。
2013年7月,本书正在收尾的时候,韦格纳由于运动神经元疾病逝世了。他曾一度主管哈佛大学的心理控制实验室,但却总是被大家记作是和白熊有关的家伙。他的白熊实验解释了为什么即便看到路上有个洞,我们还是会骑车摔进去,为什么禁忌之爱给人带来的刺激最大,为什么足球运动员一心想让点球避开守门员,却偏偏走上前去把球踢进了他怀里。2009年的时候他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如何在任何情形下想、说或者做最糟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韦格纳的研究告诉我们不应有的侵入性想法为何会挥之不去,为什么有些人怎么都无法摆脱它们。他的研究也揭示了我们是如何把这些想法转化为强迫思维的。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离阿拉莫
 不远的三一大学,世界上和北极熊最不搭边的地方,韦格纳让学生在科学条件下重复了托尔斯泰的实验。他要求他们不去想白熊。
不远的三一大学,世界上和北极熊最不搭边的地方,韦格纳让学生在科学条件下重复了托尔斯泰的实验。他要求他们不去想白熊。
被要求不想白熊的学生发现很难做到。同时还有另外一组学生被要求做相反的事情,他们被鼓励去想白熊,当然,也就更多地想到白熊了。(韦格纳让他们通过按铃来做记录。)最让人吃惊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韦格纳把交代的任务反了过来,之前被要求去想白熊的现在被要求不去想,而被要求不去想的现在被鼓励去想。结果之前被要求不去想白熊的现在发现脑海里全是白熊——比之前被指示去想白熊的学生想得还要多。
这个实验被重复了多次,每次结果都类似。这证明要压抑不应有的想法即便不是全无可能,也是相当困难的。而如果竭力不去想一个念头,结果只会导致这种念头在停止压抑之后剧烈反弹。这种效应被心理学教科书称作“后抑制反弹效应”。大多数心理学家则称之为白熊效应——力图赶走一个不应有的想法,结果却导致反弹,而且这个想法再出现的时候比以前更强大,更难以克制。
借奥斯卡·王尔德的话来说,有些人什么都不怕,就是怕诱惑,因为他们明白,要压抑自己的思想简直难比登天。正在戒烟或节食的人都能明白这一点。那种感觉,那种冲动和渴望,就是那头白熊在外面挠门发出的声音。
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效应——压抑一个念头,结果反而导致它的反弹——可以作为人类的一系列反常行为的注解。比如说它可以解释为什么最希望戒烟的人反而是最难戒的。我们的大脑会将有关某种事物的侵入性想法认作是对它的渴求。吸烟者越有排斥香烟的想法,对烟的渴求就被放得越大。研究表明戒烟失败的确实是那些更倾向于压抑自己想法的人。类似的效应也在暴饮暴食的胖子身上有所反映:他们更倾向于压抑关于巧克力和薯条的念头,但却因此强化了自己对这些食物的渴求。在睡前抑制一个念头甚至会导致它在梦中再次出现。
到底怎么回事呢?根据头脑工作的原理,白熊效应可以分为两个心理过程。在第一个过程中,尽力不去想白熊的人必须选择去想另外一样东西,就这样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说去想他们早餐吃的是什么。但是要转移注意力,我们就必须事先知道要把注意力从什么目标身上转移开来。于是,在抑制自己的念头之前,我们必须仔细察看自己的显意识,找一下是否存在这种念头。而要这么做,我们就必须想到自己需要找什么,这样一来就必须想到白熊——这个我们不希望想到的目标。
第二个心理过程是一个独立过程,它被启动来确保我们头脑中不存在目标——也就是我们不希望出现的白熊。这第二个用来监控的过程自动实施自己的任务,它是种无意识的例行程序,不用费太大气力。但是转移注意力的过程,也就是抑制想法的过程却截然不同。这个过程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也因此无法长久维持。而如果在注意力转移完成之后监控依旧继续的话(心理学家认为监控过程其实还在继续进行),那么我们的头脑就会继续寻找目标。而这就意味着我们会更频繁地发现自己不希望出现的念头,比不压抑它的时候出现得要频繁。
这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法消除侵入性的想法,至少在短期内是可以的。转移注意力——让我们的头脑忙于别的事务——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但是注意力的转移很难维持长久。马库斯·瓦斯迈尔只能维持三分钟而已——但就是这三分钟也已经足以让这个德国选手在滑雪界名垂史册了。
20世纪90年代初,在一座山顶上,瓦斯迈尔的队友汉斯雄格·陶舍听取了职业生涯中最与众不同的建议。他的速度很快,这一点毋庸置疑——1989年,在科罗拉多的比弗克里克,他征服了让人望而生畏的速降滑道,获得了世界冠军,整个冬季运动界为之叹服——然而教练却发现他可能存在一个缺陷。“你想得太多了。”陶舍在弯道滑得很快,但是在连接弯道的速滑区却绷得有些紧。阿尔卑斯山修整过的滑道布满冰雪,滑雪选手以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飞驰,似乎是一泻而下,但细细看来却是在不断颠簸和碰撞,让人精疲力竭。
滑行过程中,选手会俯下身子让重力驱使自己顺势而下,这时他们会开始想一些东西。大多数人不会让自己的思绪走得太远。他们开始思考怎么样才能滑得更快,但他们一旦这么想,就会下意识地用力控制脚部和腿部的动作。结果是他们会因此绷得过紧,着地的时候碰撞得更剧烈,从而落后关键的几分之一秒,在积分榜上惜败于对手。
教练约尔根·贝克曼认为自己找到了解决方法。他自己本身就是高山速降选手,后来在一次高速碰撞中几乎折断了脖子才退出了。贝克曼对滑行中出现的问题了如指掌。在观察过陶舍训练以后,他决定使用一种非正统的控制手法。这种方法是他从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有关短期记忆的研究中找到的。贝克曼那天提出,为了不让自己想东想西,陶舍应该倒着数数。在他开始滑行以后,从999起,每次倒数三个数。这样他的头脑和思维就会被数字占据,如果成功的话,他的双腿会更加灵活,也就会滑得更快了。陶舍对此将信将疑,但却愿意试试看。他从山上一跃而下,嘴里小声数着:“999,996,993……”
时至今日,贝克曼已经是慕尼黑工业大学的运动心理学专家。他帮助运动员在竞技中克服压力的研究已经名扬天下。但他最大的成功无疑是在1991年到1994年为德国阿尔卑斯山滑雪队工作时取得的。自陶舍开始倒数之后,他的滑行节奏大有改观。很快,前世界冠军感到这种方法十分好用,而贝克曼则受此鼓舞,开始把秘诀传授给队中其他选手。
此后贝克曼开始和瓦斯迈尔展开了密切的合作。瓦斯迈尔也是位前世界冠军,他的头衔则是早在1985年于一个大回转赛事中斩获的。大家都认为他的巅峰状态已经过去了,就连贝克曼的母亲都说自己儿子的工作是浪费时间。但是到了1994年挪威冬季奥运会的时候,马库斯·瓦斯迈尔为德国赢得了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两个项目的金牌,出乎所有人意料获得了德国有史以来最伟大滑雪选手的称号,并被选为德国年度最佳运动员。他就此退役,之后应该就有足够的时间尽情思考了吧。
贝克曼的倒数策略是种仪式性程序,是将不应有的想法驱逐出脑外的方法之一。仪式性程序很常见,使用者并不仅限于滑雪选手。大多数人都有侵入性想法,而在心理学家对普通人的调查中,有一半人承认他们会进行奇怪而又毫无意义的仪式。有些人总是会去检查煤气灶有没有关掉,尽管他们知道其实已经关了。也有人会不由自主地叩击墙壁或是默默地数数。要么是在碰触了别人左肩之后感到有必要在他右肩上也碰一下。这些不是迷信的仪式。典型的迷信仪式一般是对外部提示做出的反应,比如看到喜鹊后认为出现了好兆头,因此要跟它打招呼等等。这些仪式则是强迫行为,是种发自内心的、无法抗拒的冲动,想要进行某种非理性的行为。人们一般也会对自己的强迫行为避而不谈
 。
。
多数人看起来都可以应付自己的日常仪式和强迫行为——最起码他们没有求助于医生。但就像强迫思维一样,有些人的强迫行为会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无法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他们之后的求助,往往是在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合力作用后开始的。这样的组合就可以导致临床性强迫症。简单来说,大多数强迫症患者出现强迫行为就是为了驱赶自己的侵入性想法。
有些人使用强迫行为赶走侵入性想法的目的很明显,即用它来为某个问题提供答案。如果一个想法反复出现在脑海中,比如问自己锁没锁后门,那么强迫性而又安慰性的解决方法就是检查一下门锁。有些人则更间接,他们用强迫行为来防止侵入性想法出现。比如说,有个14岁的女孩子,她的侵入性强迫思维是有虫子会进入体内,于是她就整整10个月拒绝开口说话以杜绝这种危险。
而有时强迫行为则似乎是纯粹发自臆想,与强迫思维的对象并无实际关联。比如说,强迫症患者会强迫自己叩击物体表面或数数或是对自己讲一些秘语以“消除”侵入性想法臆想出的后果,例如最好的朋友会死去,等等。这听起来好像是在做无用功,但难道从999开始倒数就真的能使滑雪选手的技术更上一层楼吗?
强迫行为确实可以赶走强迫思维,但这维持不了多久。强迫症有众多残忍的反讽,其中之一就是患者用来驱赶强迫思维的武器——强迫行为,只是雪上加霜罢了。强迫行为的作用就是压抑想法,因此强迫行为所压制的侵入性想法还会故态复萌,而且变本加厉。
心理健康专家认为强迫症是种隐疾,一种无声的流行病。研究表明,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在世上猖狂肆虐,然而向医生提起症状的人却寥寥无几。许多强迫症患者选择默默地忍受折磨。他们奇怪的想法成了自己龌龊的小秘密。他们相信自己是变态,而正是沉默给了强迫行为火上浇油的机会。强迫行为,这种强迫自己不断洗手、来回检查后门是否锁住或者反复开关电灯的行为是处在明处的动作,这与强迫思维——那种阴暗的、见不得人的侵入性想法——有所不同。如同强迫症(OCD)中的字母“C”的半开口形状一样,强迫行为(compulsion)对世界是开放的,它们为处理病情提供了一个把手,而同强迫症(OCD)中的字母“O”的形状一样,强迫思维(obsession)对世界是封闭的。
侵入性想法是赤裸裸的野蛮念头,令人无法接受、让人反感,多数人产生以后会予以回避,但并非所有人都如此选择。这种让人不快的念头带给一些人的体验迥然不同,这些人并不觉得伤害他人的想法是自我排斥的,这种想法与他们的本能和意愿并不冲突。不幸的是其中有些人实施了自己的想法。我们对此有所了解,因为有的人因此成为了性犯罪者。
性变态的侵入性想法让大多数人感到惊诧莫名,然而这些人却似乎无动于衷。尽管听上去不可思议,但这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们相信自己的罪恶是无害的。有些男性对儿童施以性虐待,但他们认为小孩子会喜欢与成人发生性关系;有些强奸犯以为女性会享受强奸;有些露阴癖则觉得自己的行为非但无害,而且甚至会给别人带来快乐,因为他们并不直接触及受害者。但即便是这类道德罗盘已严重失灵的人也会为自己的想法感到苦恼。即便是这类人也会出现自己抗拒的侵入性想法,并会因此感到极大的痛苦。
艾迪就是这么个人。艾迪32岁,已婚,有一个孩子。他也是个顽固的露阴癖。他会开车到陌生的镇子上,等在一个公园里,直到一个女性出现,然后他就会走出来露出自己的下身。他相信自己的惯例——包括把车停在远离犯罪现场的地方——会让别人抓不到自己。他干了好几十回。但是不管他如何绞尽脑汁地避免被查出来,之后他的头脑里都会充斥着侵入性的、反复出现的以及非理性的想法——觉得自己会被找出来。在艾迪第一次露阴之后,他就生出了反复出现的念头,认为自己会在妻子和孩子面前被捕,然后被当地报纸指名道姓地称作性犯罪者。这样的想法占据了他几乎所有的时间,持续了差不多一个月。
艾迪的情况并非偶然。心理学家对其他性犯罪者出现的侵入性想法做了调查,包括儿童猥亵犯和强奸犯。这些人经常性地出现顽固而强烈的念头,担心自己被抓的后果,尤其是刚刚开始犯罪的时候。但其实他们最害怕的并不是进监狱,而是随之而来的无尽羞辱和地位丧失。他们非常清楚,尽管在自己看来这些行为是正常的,但社会上的其他人会把性犯罪者看成是怪物。这质疑了他们的世界观。可能被抓的念头冲击着他们自认为是好人的感觉,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我排斥的体验,因此他们也会觉得这是不应有的侵入性想法。
不应有的想法有时候针对的是最平常的情境。比如,不少人说自己出现过关于伴侣——男朋友、女朋友、妻子或丈夫——缺点的侵入性想法。当然,没有人十全十美,不管什么样的感情都会时不时产生点摩擦,但是近年来心理学家吃惊地发现这方面的强迫症状正在不断增多。
比如说迈克,28岁的已婚男性:
我总是为妻子的情绪失调忧心如焚。她在工作上一遇到点小矛盾或者小困难就会大惊小怪一番。每次我看到都会对自己说:“就这样她怎么能当个好妈妈呀……”这着实让我痛苦。我了解她所有的优点,也知道她爱着我。我晓得自己是小题大做,但就是无法泰然处之。
另外还有珍尼弗,25岁的女商人:
我一直在想他真是个没用的废物,怎么也停不下来。然后我就开始担心将来谁来照顾我跟孩子们……我爱他,也觉得他会是个了不起的父亲,理性的时候我就不觉得这是个问题。
2012年,在以色列,科学家发明了一种调查此类症状的方法。这被称作是伴侣相关强迫症状目录。被调查的有伴侣者要回答是否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如“我感到有种让自己不自在的冲动,要把伴侣的缺点和其他男性/女性做比较”,“我老是为伴侣的社交技巧忧心忡忡”,或者是“我很难不去想自己的伴侣有情绪失调的毛病”。这样的问题大家可能会付之一笑。但如果这类想法总是纠缠着你,那么它就可能像那些有关暴力和疾病的强迫思维一样给你带来极大的痛苦。
杰克40岁,和伴侣一起生活已经4年了,但是有关两人感情的侵入性想法却让他备受折磨。
我总是问自己是否还感觉到爱,自己的感情是否和电影里讲的如出一辙?我会想象如果接下来20年都和她在一起的话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还会想象如果换个人会如何。我害怕自己会永远纠结于这些问题,或者有一天再也无法接受现有的生活。
这是强迫症吗?当然。杰克抱怨自己不应有的想法,这些想法反复出现,给他带来痛苦,迫使他不断寻求安慰。但是真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有多少人——特别是女人——会抱以同情。已婚的人有谁不会在某个时候产生这样的疑问呢?这不就是男人害怕付出的典型案例吗?如果这是强迫症的话,是否需要治疗?能治得了吗?
精神病学家对此态度明确:强迫症不仅仅是日常忧虑的简单放大。如果觉得侵入性想法或强迫思维的对象无足轻重就意味着它们不会导致严重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贝拉只是想着一堵土墙而已,结果这个想法主宰了她的生活。迈克、珍尼弗和杰克都曾向外界求助,因为有关感情的强迫思维和这些想法给他们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堪忍受。这些想法让他们每天都要连续痛苦几个钟头。这是显而易见的强迫症。
我知道,有些人在读本书时,肯定是每翻一页都要摇头。伤害儿童的念头?把车开出马路的冲动?我可没有这么离谱的想法。
这当然没什么可奇怪的。就算是执行得最认真的调查,使用有经验的调查员进行面谈,还是有5%左右的人坚决否认自己现在有或者曾经有过不应有的侵入性想法。有些人应该是在撒谎,尽管心理学家不会这么讲。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使你绝对肯定自己没有侵入性想法,也不用急着得意。其实有些人的确有这样的想法,有谋杀别人或虐待动物的冲动,但他们却并不觉得这些想法是不应有的,也不会告诉别人。对这些人来说,出现这样的想法就像是要考虑给自己的孩子买什么生日礼物一样天经地义。对这些个体我们有个称谓:精神变态者。
2008年,加拿大的心理学家发表了自己实验的结果。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测试精神变态者是否会较少出现自己抗拒的侵入性想法。精神变态者一般被定义为行为违反社会期望及规范,但却不会因此感到悔恨或羞耻的人。他们满口谎话、偷鸡摸狗、坑蒙拐骗、凶狠残暴,别人认为这不对,他们却不以为然。
为了找到精神变态者,加拿大心理学家对纳奈莫改造中心的犯人进行了测试。这是个中等戒备的监狱,位于温哥华岛上的布莱农湖。这里是个景区,有很多游客来此度假。有个囚犯说自己曾想过把一个婴儿从桥上扔下去,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看看大家会作何反应,而另外一个囚犯则说自己曾经有过无缘无故的冲动,想在别人身上表演功夫。但是接受询问的犯人有四分之三说自己从来没有侵入性想法。
这些否认有侵入性想法的罪犯是精神变态者吗?科学家让他们回答了60个问题。设计这些问题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在人们身上找到精神变态者的特征。这也就是那个所谓的精神变态测试的自我报告版。显然,在这个测试中得分最高的囚犯也是那些最不可能报告有侵入性想法的人。即便体验到侵入性想法和冲动,他们似乎也不以为意。他们并不反感这些念头,这也许是因为他们对这样的想法已经习以为常。
或许这些囚犯并非精神变态者,只不过是骗子罢了。兴许在匿名研究的可控条件下,他们还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最奇怪、最抗拒的想法。也许他们担心自己最阴暗的想法会被记录在案,成为控诉他们的证据。而我们很快就会了解,他们确实常常如此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