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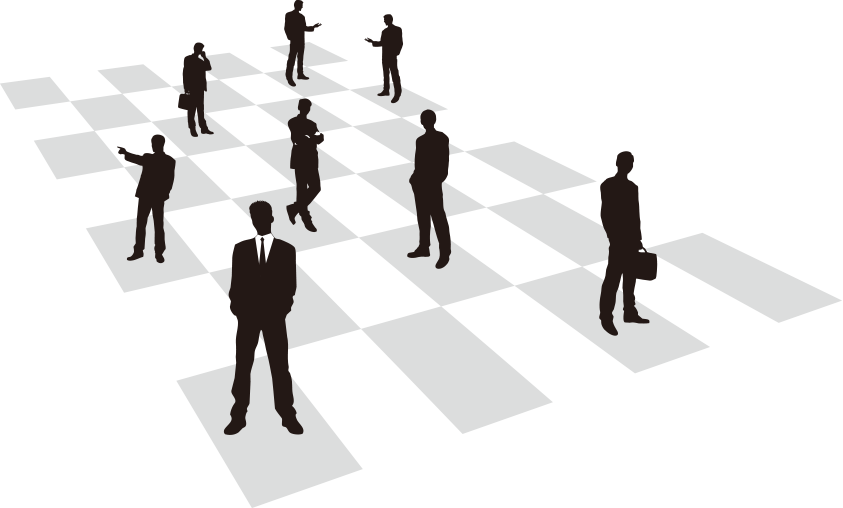
在埃塞俄比亚,有个叫贝拉的女学生啃掉了家里的一堵墙。她自己也知道不该这么做,但是她无时无刻不想着这堵墙,要停下来就只能去吃它。她自己也知道不该想着这堵墙,但是眼前挥之不去的尽是墙的模样,心里转的全是墙的念头,要赶走这些想法,平息这些想法引起的焦虑,就只有顺着自己古怪而又难以克制的强烈冲动,把墙给吃掉。所以她就开始慢慢啃那堵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17岁的时候她已经把墙给啃掉了8平方米,吃下的土砖超过半吨。
贝拉家住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父亲在她年幼时就去世了,陪她长大的只有母亲。自记事起贝拉每天都吃土,十来岁的时候转为只吃家里墙上的土砖,情形愈发不可收拾。她就这么吃啊吃,脑海里土墙的模样越来越形象,念头也出现得越来越频繁,想要消除它们只能靠吃墙才行。因为吃土,贝拉便秘、腹痛如绞。埃塞俄比亚的巫医试图用祷告和圣水来治好她,还告诫她不要再吃土。但是她做不到,她始终断不了对那堵墙的念想,也就只好时时去吃它。
终于有一天,贝拉挺不住了。她胃部肿胀,疼痛难忍,腹部时时抽搐,喉咙被土砖里的草梗刮得伤痕累累,体内长满了土里的寄生虫。她一边哭,一边走进了当地的医院。那时候,埃塞俄比亚这个七千万人口的国家一共才有八个精神病医生,但贝拉运气不错,找到了其中的一个给她看病。她求医生救救自己,她知道自己不该成天有那些念头,但是她也明白,靠自己一个人是没办法终结掉这些想法的。
普通人每天可以生出四千种想法,其中很多既没有用,也不理性。这些精神垃圾通过许多不同的形式存在。在我们工作枯燥的时候,脑海里常常会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一些毫无关联的字词、短语、名字和形象。还有耳虫现象——挤进我们脑袋里萦绕不散的曲子,通俗的叫法是“卡歌综合征”。有时候还有负面的念头——“我不行的”“我不干了”,这是全世界运动心理学家的死敌。
还有些很奇怪的念头,不知道从哪里偶然地、随机地、不受控制地冒出来,让人不知所措,因为这些想法是可耻的、邪恶的,令人反感,让人作呕,而又确实不可思议。还有“要是怎样怎样的话会如何?”这个让人浮想联翩的问题:要是我蹦到公共汽车前面的话会怎么样?要是我给那个女人来一拳会怎么样?
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其实这些想法很常见。大家可以问问周围。我有个朋友每次坐上马桶之前都要检查里面有没有老鼠;还有个朋友每次用完熨斗、拔下插头以后都会把它放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以便之后问自己“你真的关熨斗了吗,你确定?”的时候能放心地给出肯定的答案;另外一个人则是一晚上受尽煎熬,苦苦思索之前申请梦寐以求的工作时发出去的表格上有没有在无意间写下“笨蛋”二字。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奇怪念头,大多数人都能把它们抛之脑后。但也有人不能。
如果我们不能让奇怪的想法销声匿迹,它们就有可能导致痛苦和精神疾病。我在上文提到的朋友并未让自己的想法产生如此恶果,我却有。
我的想法转化成了强迫症。
这天,巴西赛车手埃尔顿·塞纳在意大利的大奖赛中撞车丧生。而我则被困在曼彻斯特的一个游泳池的厕所里。门其实开着,是我自己的念头挡住了出去的路。
那是1994年5月,我22岁,肚子正饿得咕咕叫。在游泳池里游了几个来回以后,我从水里爬出来,往更衣室走去,走下台阶,一级、两级、三级——哦!下最后一级的时候我的脚后跟底部在尖锐的台阶角上刮了一下,擦出了一个小口子,里面淌出一滴血来,挂在擦破的皮肤上。我把血擦到手指上,很快又有一滴从伤口里挤了出来,取代了原先那滴的位置。我从洗手池上方抽了张纸巾,裹在湿漉漉的脚后跟上。手指上的血滴和水一起顺着手臂流走了。当然,我的目光一直跟着血滴走。焦虑也理所当然地涌上心头,甚至比记忆重现来得更快。我的肩膀垮了下来,胃紧绷着。公共汽车站台上发生的一幕已经过去了四个星期,尽管我告诉自己对此已经无所谓了,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之前,我的手指被公共汽车站台波纹状挡板上冒出来的螺丝钉刺了一下。那是个忙碌的星期六下午,来来往往的人很多。我觉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很可能像我一样被刺伤。要是其中有人是艾滋病患者怎么办?那就有可能把感染了艾滋病的血液留在螺丝钉上,然后螺丝钉又刺破了我的皮肤,这就会使病毒进入我的血中。啊,我知道按官方的说法这种传染途径是不可能的。艾滋病毒不可能在体外存活。但我也知道,如果刨根问底的话,那些了解内情的人就会改口说是“几乎”不可能。他们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确信。实际上有几个专家承认理论上来说的确是有风险的。
于是我静静地站在更衣室的厕所里,一手拿着护目镜,一手拿着沾了血的纸巾,身上的水珠还在往下滴着,就这样我把汽车站台上发生的事的前因后果又过了一遍。我告慰自己,当时检查螺丝钉没有发现任何血迹,至少我没觉得有别人的血液残留下来。嗨,我当时怎么就没弄个清楚,好确保万无一失呢。
这时有人嘭地推门进了更衣室,嘴里还吹着口哨。我盯着自己的手指。等一下。我刚才真是傻了!我用纸巾擦了新伤口上的血。天哪。纸巾上可能什么都有。你这个蠢蛋。我仔细地审视着纸巾,现在它已经是湿乎乎的了。上面有血。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血。你真的确定吗?可能之前有艾滋病人手上出了血,然后又碰过它。天哪。我把它扔进垃圾篓,从取纸器中又抽了张纸巾出来,细细打量。上面没有血,这让我松了口气,微微松了口气。下一张也没有血迹。但这不能保证第一张纸巾是干净的。我又把最初那张纸巾从垃圾篓中取了出来。上面有血。如果上面有别人的血,那你把它拿出来不是要作死吗?我赶紧洗手。要是那艾滋病人的血也滴进了水池呢?千万别摸见鬼的脚后跟。千万别摸见鬼的脚后跟。这是不可能的。要是刚才拿起来的纸巾根本就不是我扔进去的那张呢?那可能是别人扔进去的纸巾,别人的血。我往垃圾篓中看去,没有看到别的纸上有血迹。那张有血的真的是我扔的吗?
吹口哨的人准备去游泳了。他走到水池边,抓出一张纸巾,擤了下鼻涕,把纸巾扔进篓里。我有模有样地照做了一遍。他看了我一眼,我冲他笑了笑。他没理我,走开去了。我待在原地没动。他游完泳后就离开了,我却还不能。
后来,我骑车回了家。一路上我对找到的解决方案颇有些沾沾自喜。终于还是找到办法了!一时间柳暗花明,鸟儿在欢唱,和煦的春风拂在我的脸上。当然,我不可能因为在公共汽车站刮伤就染上艾滋病,这是无稽之谈,我对此深信不疑,因此对这个问题我无须再担惊受怕。到家以后,我从包里拿出泳裤,放在卧室的暖气片上,然后从衣柜里翻出了冬天的手套戴上,把游泳时带的毛巾一层层打开,把里面包着的那片湿漉漉、沾着血迹的纸巾小心翼翼地取出来。我把纸巾也放在暖气片上,就在泳裤的旁边。大概要十分钟,我觉得,纸巾就会干透,好让我彻彻底底地检查一番了。接下来我又从包里把其他皱皱巴巴的纸巾一一掏出来。这些是当时垃圾篓里的所有纸巾,我都装了回来,现在放在桌子上,我也要一一检查,仔仔细细、彻彻底底地检查一遍(在更衣室里可办不到),之后嘛,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完全把这件事抛在脑后了。总算是松了一口长气,我脱了手套,打开电视,汽车大奖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些就是我的古怪想法,这也就是我的强迫症。我对自己可能染上艾滋病的渠道充满执念,总是强迫自己通过检查来确认不会染上艾滋病,而且我平时的一举一动也都会小心翼翼以确保自己不会染上此病。在我眼里,到处都充斥着艾滋病毒。牙刷上,毛巾上,水龙头上,电话上都潜伏着这种病毒。所以我时时擦拭杯子、瓶子,讨厌跟人分饮料喝,每次有点擦伤刮伤我都会用好几条创可贴把伤口裹得严严实实。强迫心理要求我每次被生锈的钉子或是玻璃片刮伤以后都要把那个钉子或是玻璃片用纸包起来,以便之后检查上面是否存在感染了艾滋病毒的血液。要是脚趾之间的皮肤干裂了,那我就不得不在人满为患的更衣室里用脚跟走路,生怕地板上有饱含病毒的血渗到里面去。在火车上落座之前我会检查座位上有没有注射器,上厕所则要细细查看马桶座位,一切小心为上。
作为一个记者,我会和很多人见面,跟他们握手。如果我手指上破了个口子,或是注意到跟我交谈的人在自己的伤口上缠了绷带或是创可贴,我的脑袋里就不由自主地开始考虑握手的问题,绞尽脑汁地思索怎么才能避免握手,别的一切都被挤出了我的思绪。我理性的一面明白这样的恐惧是杞人忧天,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感染上艾滋病。但是这样的念头和焦虑还是照来不误。
贝拉在亚的斯亚贝巴看的医生告诉她,她患上的也是强迫性思维及行为障碍(即强迫症,缩写为OCD)。她产生了不正常的顽固想法;因为无法无视或压抑这些想法,她产生了焦虑;为了减少、防止焦虑,她开始形成了强迫行为,而强迫行为又加深了她的强迫思维。就这样,强迫思维和强迫行为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了巨大的痛苦,毁了她的生活。
大多数人都听说过强迫症,但是对其情况的认知却多有混淆。一般人认为强迫症是一种行为怪癖。实际上,强迫症是种严重的疾病,可以使患者深受其害,其症状为反复出现、不断给患者施以精神折磨的古怪念头和身体行为如重复洗手等。贝拉被诊断为中度强迫症。是的,尽管把家里一堵墙都啃得干干净净,这个女孩子得的还只是中度强迫症。因为比这严重的大有人在。贝拉每天花两个小时想墙吃土,而强迫症病人平均每天差不多要花六个小时在自己的强迫思维上,还要花四个小时进行强迫行为。巴西有个强迫症患者叫马库斯,他主要的强迫思维就是担心自己眼眶的形状,因为他一天到晚都在想这件事,所以老是要强迫自己不断用手指触碰眼眶,结果到最后把自己的眼睛给戳瞎了。
要说清楚强迫思维——严重的、具有临床症状的强迫思维,那种独占一切的念头——到底是什么,可不容易。要人类大脑去感知地质年代的久远,电子运动的速度,或者甚至是蜂鸟翅膀每秒振动的次数是很困难的。同样,要说一个简单的想法或独特的观点真的能霸占一个人的思想几天几夜、几星期、几个月甚或几年时间,这对大家来说也是不可思议之事。下面是我个人能给出的最好的解释。
让我们拿个人电脑和它能同时运行的不同窗口及任务做类比。我在这台电脑上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还有一个窗口正在后台运行,不断更新我的电子邮件,而同时还有一个网络浏览器正在记录足球赛的比分。我可以选择在这些不同的窗口间自由切换,放大或缩小它们,按我的意愿选择打开或关闭其他窗口。这就是我们的头脑处理各种想法的一般方式,它将我们显意识的注意力分散到不同任务上,而我们的潜意识则改变着不同窗口的内容,或者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某些特定窗口上。
而强迫思维就是一个无法缩小、移动或关闭的大窗口。即便其他任务在头脑中排在了前面,强迫思维的窗口依然在后台运行,闷声不响地起着作用,随时准备攫取我们的注意。这个窗口不断消耗着我们这台电脑的电力,同时也让其他任务无法正常运行。到了一定时候你会对此感到十分无力,因为你无法强制退出,也不能通过重启解决问题。只要你醒着,窗口就存在。有时你可以把注意力投向别处,但是你会意识到自己是有意费力才做到的,很快,原先的强迫思维就会把你的注意力拉回来。有时候,一般是你睡着的时候,它会消失一会儿,这时屏幕空白了。但只要你按一个键,动一下鼠标,开动下脑子,它就会嗖的一下回复原位。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精神病学家还认为临床性强迫思维和行为是极端罕见的。而现在他们相信大约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的人在生活中有过强迫症。也就是说在英国有超过一百万人直接受到强迫症的影响,而在美国这个数字还要加上五百多万。强迫症在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中排名第四,前三大精神障碍分别是抑郁症、致瘾物质滥用和焦虑症。强迫症的常见程度是自闭症和精神分裂症的两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强迫症列为第十大致残疾病。它对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被认为已经超过了糖尿病。但是强迫症患者一般都要在患病10年甚至更长时间以后才开始寻求帮助。
男性和女性患上强迫症的几率差不多,这种症状一般在患者十岁出头,或者是青春期后期、成年早期的时候形成,却能影响患者一辈子。无论是何种文化、民族、人种或地域的人,都有可能发病。强迫症是一种社交障碍,也给社会造成负担。患有强迫症的儿童更希望有朋友,却很难交到朋友。患有强迫症的成人很容易被解雇和离婚。他们会把自己的家庭拖下水。他们倾向于和父母同住,也倾向于独身。如果结了婚的话也不大会要孩子。他们离婚的可能性很大。即便如此,很多第一线的医生却依旧无法识别强迫症的症状和表现,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症状和表现的意义。强迫症患者很少能够自愈,但是他们中却有三分之二的人从来没去看过心理医生。
强迫思维即“着魔”(obsess),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英文中是在16世纪。它源自于拉丁文词语 obsidere ,字面上的意思是“坐下之前”,但更常见的意思是“围困”,常见于与军事相关的文字中。围困(obsess)一个城市的意思就是包围了城市,但是还没有掌控城市。相关的拉丁文词语,就是后来形成英文中“入魔”(posses和possessed)的来源词 possidere ,描述了接下来的状态——取胜的军队控制了城市,征服了市民。
这些用来形容精神上受到困扰的词语一开始和宗教相关,后来被用在临床医学中,其分界也是同样明显的。人们在最初使用“着魔”这个词的时候相信种种奇怪的想法——那时候被认为是邪魔所致——来自受害者体外。因此着魔是由于外力作用于患者产生的,并非是患者抓住执念不放,而是执念抓住患者不放。这就和入魔有所区别,入魔是邪魔自内而外地侵占并控制受害者所致。
要确诊一个人是“着魔”还是“入魔”,就经常得判断受害者是否能感知到邪魔,是否认为心中的执念来自外界,是否力图抗拒这些执念。着魔的人被认为是能够如此做的,而入魔的人则不能,因为他们已经把心灵交给恶魔掌管,他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一无所感。这种区分一直到今天还在被使用。要诊断出强迫症,常常需要精神病学家所说的某种程度的了悟——强迫症患者必须认为驱动强迫思维的奇怪想法是外来的、让自己痛苦的,必须努力抗拒它们。
时至今日,“着魔”这个词已经越来越常用了。因为我们经常有各种各样的想法,来了又消失了,头脑里时时充斥着各种不请自来的情绪和感觉,只要在一个反复出现的想法周围萦绕的宛若星尘般的各种思绪间稍稍纠结一下,就能形成一个暂时的疙瘩、一个解不开的结,也就是人们所说的着魔。就这样,要是无法把某个魅力四射的人赶出自己的脑海,或者不由自主地老是馋一样好吃的东西,人们就说自己是着魔了。我们的头脑就是一个柔软的流体,不论多和缓的波动都会受到注意。我们说自己为体育着魔,为性爱着魔,为鞋子着魔,为奶油面包着魔,为车子着魔,为数以千计的各种享受着魔,有时候还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到了一定时候,经常用不了多少时间,这些所谓的着魔就都烟消云散,被我们流淌的思绪冲走,消失得一干二净。这可不是我们要讲的强迫思维,这也不会驱使一个人去啃土墙。
强迫症的强迫性思维有所不同,一般会围绕几个有限的主题展开。有关受污和疾病的强迫思维是最常见的,占所有案例的三分之一左右。非理性的担忧——我锁上后门了吗?烤箱关掉了吗?这样的情况占四分之一左右。还有一成左右的患者则成天在和一定要满足某种模式或对称性的强迫需求抗争。更少见但却更重要的强迫思维关注的则是有关身体或生理症状的想法,有关宗教或渎神的想法,还有让人讨厌的性幻想以及实施暴力行为的臆想。正是由于强迫思维经常和这些禁忌以及让人尴尬的问题相关,很多强迫症患者都对它们秘而不宣。
强迫思维不接受理性解释。任何病态的思维都无法通过更多的思维来解决。20世纪杰出的数学家库尔特·哥德尔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朋友和同事,他终生的追求就是理性,他所证明的不完全性定理使用逻辑来探讨和揭示逻辑的局限。然而哥德尔却受到极不理性的强迫思维的困扰,认为自己会意外中毒,毒源可能是腐坏的食物,也可能是冰箱里逸出的有害气体。如果食物妻子没有先试尝过,他就一口都不肯吃。后来他的妻子生病了,无法为他试吃食物,结果哥德尔被心中的执念所困,活活把自己给饿死了。
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何在?强迫思维使人过度关注自我而无法与他人专心交往。强迫症使一个人的全部存在都固结在自己的想法和行为上。它还使人无法全神贯注,总有其他事情更值得或者不值得我们思考。我不想再继续藏私,因为我现在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他们需要我,我不希望他们重走我的老路,我不希望他们形成强迫思维,被自己奇怪的想法拘为人质,在自己的头脑中产生出怪兽来。如果他们不幸患上了这样的病症,我也希望能对他们施以援手。
要这么做,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研究这些奇怪的强迫思维,了解它们从何而来、如何作用,而我们又可以从中学习到什么。我们要问问自己,人类的大脑——我们最亲近的盟友,人类百万年进化而来的最大财富为何会如此背弃我们。我们要了解在每个化身博士道貌岸然的外衣之下——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里——所潜藏的恶魔在平时到底会有些什么表现,要了解究竟如何才能终结这个恶魔对我们的背叛。而这终将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故事。
奇怪的想法,这些强迫思维的种子,在世界上比比皆是,人群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它们的痕迹。但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它们才会生根发芽。因此我们理解强迫思维的旅程第一站就是要看一看它是如何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