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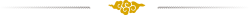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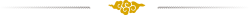
幼虫一旦跨过出口的大门,地洞就被废弃了,它张着大口,就像是一个用粗大的钻子钻出的孔。幼虫会在四周游荡一会儿,寻找一个空中支点:一棵小荆棘、一丛百里香、一根禾本植物或者一棵灌木。它找到了。于是它立刻爬上去,两只前爪的钩子合上,牢牢抓住,头朝上,再也不松手。如果枝杈的形状允许,其他爪子也会悬在上面;反之,它用两只前爪钩住也足够了。接下来,它要休息一会儿,让悬着的爪臂伸直,变成固定的支点。
幼虫的中胸首先沿背部的中线开裂。裂缝的边缘慢慢撕开,露出浅绿色的昆虫身体。几乎与此同时,前胸也开裂了。纵向的裂纹向上延伸到头后,向下则抵达后胸,但不再向更远处扩张。接着,头罩横着在眼睛前面开裂,露出红色的眼睛。开裂后露出的那部分绿色身体膨胀起来,尤其在中胸的部位形成一个突出物。它缓缓抖动着,随着血液的涌入和回流而一胀一缩。一开始,我们还看不出这个突出物的作用;可现在,它就像一个楔子,使幼虫的胸甲沿着阻力最小的两条十字形直线裂开。
蜕壳的速度很快。现在,头已经解放出来了,喙和前爪也正在慢慢地从套子里脱出。蝉的身体水平悬挂着,腹部朝上。然后,在敞开的旧壳下面,又伸出了后爪,那是最后获得自由的部位。蝉翼湿漉漉、皱巴巴的,蜷成弓状,像是发育不全的残肢。这是蝉蜕变的第一阶段,只要十分钟就够了。
接下来是第二阶段,时间要长一些。这时候,蝉除了尾部还留在壳内,其余部分已经全部自由了。那层蜕下的旧壳继续牢牢地挂在树枝上,在干燥的环境中迅速变硬,却仍然保持着原先的姿势,一点都没有变化。这是下面一个蜕变阶段的支撑点。
由于尾部还未完全抽出,蝉依旧穿着那件旧衣服,它垂直翻了个身,让头部朝下。它的身体呈淡绿色,略带些黄。原先紧贴在一起、像厚厚的残肢的蝉翼,此刻已经伸直、舒展,并随着体内血液的注入而张开。这个缓慢而细致的过程结束之后,蝉用一个不易察觉的动作,依靠腰的力量重新翻了个身,恢复了头朝上的正常姿势。它用前爪抓住空壳,终于把尾部抽出了套子。蜕壳结束了。这个过程总共用了半小时。
现在,蝉完全摘下了面罩,可它和不久之后将要拥有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它的翅膀沉重、湿润,像玻璃一样透明,上面有着嫩绿色的脉络。前胸和中胸勉强带一点棕色。身体的其他部分呈淡绿色,时而有些地方微微发白。这个孱弱的小生命需要洗一个长长的日光浴、泡一个长长的热气澡,以使自己更加强壮。两个小时过去了,蝉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明显的变化。它只靠前爪钩住旧壳,只要稍有风吹,便摇摆得厉害;它仍然孱弱,身体还是绿色。终于,它的颜色开始变了,不断变深,而且很快就完成了。这个过程只需半个小时就够了。我看到一只蝉上午九点悬到树枝上,中午十二点半才飞走。
那张空壳仍然留在那里,除了有一条裂缝,其余均完好无损,并且一直牢牢地挂在树上,即使是秋末的风雨,都未必能把它打落。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甚至在冬天,都可以经常看到一些蝉壳,挂在荆棘上,保持着幼虫蜕变时的姿势。这些壳质地坚硬,使人想到干羊皮,可以作为纪念品保留很长时间。
我们暂时再来看看蝉蜕壳时做的体操吧。尾部是蝉最后一个留在套子里的部分,它首先以尾部为支点,垂直翻一个跟斗,让脑袋朝下。当头和胸在突出物的推动下把胸甲胀裂,完全露出之后,这样的一个跟斗使蝉的翅膀和爪子也获得了自由。接下来该解放跟斗的支点———尾部了。为此,蝉的脊背用尽全力,再次直起身子,把头掉向上方,并用前爪钩住旧壳。这样,它又获得了一个新的支点,可以把尾部从鞘壳中拉出来了。
整个过程中,有两个支撑点:先是尾部,再是前爪尖;有两个主要动作:第一是往下翻跟斗,第二是翻回去,恢复到正常的姿势。这样的运动需要幼虫固定在一根树枝上,头朝上,并且下方有足够的运动空间。如果,我人为地取消这些条件,情况会怎样呢?我们瞧瞧吧。
我用线系住蝉的一条后腿,把它悬在没有气流的试管里。这是一根重垂线,没有什么能改变它的垂直状态。蝉的蜕变需要它处于头朝上的姿势,可现在它却处于头朝下的非常状态,可怜的虫子不停地翻动,竭力挣扎,试图翻过身来,用前爪抓住垂线或者那条被线系住的后腿。有几只蝉做到了,好歹竖起了身子,虽然保持平衡还有点困难,但它们还是自如地在线上固定住,毫无障碍地完成了蜕变。
而其他的则白费力气。线没能抓住,头没有竖起来,蜕变也就无法进行。有几只蝉背上的壳还是裂开了,露出了胀大突起的中胸,但蜕壳却无法再继续下去,于是它们很快就死去了。更为常见的是幼虫的壳还没有出现裂缝,就完好无损地死了。
我又着手进行另一项实验。我把幼虫装进一个广口瓶,在瓶底铺上一层薄沙,使幼虫可以爬行。它爬着,却没法在任何地方直立起来:玻璃瓶壁太滑,使它做不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关在瓶里的幼虫没有蜕变就死了。这样悲惨的结局也有例外:有时,我看到幼虫依靠它难以捉摸的平衡性,就像平常一样,在沙地上蜕变成功。但总的来说,如果不能达到正常或类似正常的姿势,蜕变就不会开始,蝉就会夭折。这是一般的规律。
这个结果似乎告诉我们,蝉有能力对影响它蜕变程序的外力做出反应。一颗蔬菜或一粒豌豆的果实,一旦成熟,就会无一例外地爆开,撒出里面的种子。蝉的幼虫就像包含着种子的果实,而种子就是成虫;幼虫可以控制外壳的开裂,将其推迟到合适的时间,如果外部条件不利,它甚至可以取消蜕变。尽管蜕变前体内的激变一再发出强烈的信号,但只要本能告诉它条件不佳,幼虫就会拼死抵抗,宁死也不裂开。
除了这些在好奇心驱使下所做的悲惨实验,我还从未见过蝉的幼虫这样死去。地洞的周围总能找到一丛荆棘。出土的幼虫爬上去后,只要几分钟,背上的壳就会裂开。如此迅速的破壳过程却给我的研究带来了麻烦。我在附近的小山上发现了一只幼虫。它正要把自己固定在树枝上,却被我逮了个正着。这在我家将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察对象。于是,我把它连同小树枝一起装进锥形纸袋,赶紧回到家里。我只用了一刻钟就到家了。可我的力气白费了:到家时,绿色的蝉儿几乎已经破壳而出。我没有看到想要看的情景。我不得不放弃这种观察方法,转而寄希望于能在家门口几步远的地方侥幸有所发现。
教育家雅克多
 在他那个时代说过:“万物均有联系。”蝉的迅速蜕变使我们联想到一个烹饪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蝉是希腊人高度赞誉的一道佳肴。我没有拜读过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的著作,我这个村夫的书架上没有如此丰富的书籍。不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本权威著作上看到了这件事情。那是马蒂约
在他那个时代说过:“万物均有联系。”蝉的迅速蜕变使我们联想到一个烹饪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蝉是希腊人高度赞誉的一道佳肴。我没有拜读过这位伟大的博物学家的著作,我这个村夫的书架上没有如此丰富的书籍。不过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另一本权威著作上看到了这件事情。那是马蒂约
 写的关于迪约斯科里德
写的关于迪约斯科里德
 的评论。马蒂约是一个优秀的博学者,他应该很了解他所研究的亚里士多德。我对他深信不疑。
的评论。马蒂约是一个优秀的博学者,他应该很了解他所研究的亚里士多德。我对他深信不疑。
他说:“亚里士多德称赞说,蝉在蛴螬挣脱外壳之前食用,鲜美无比。”要知道“蛴螬”,或者说蝉儿之母,是古时候用来指幼虫的表达方式。我们看到,在亚里士多德眼里,蝉儿在挣脱外壳之前味道最为鲜美。
外壳开裂之前这个细节告诉我们,想要得到这份美味,应该在什么时候前去捕捉。不能是在冬天对农作物进行深耕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根本不用担心幼虫会破壳。我们所提醒的注意事项并非毫无用处。捕捉应当在夏天,也就是幼虫出洞的时候进行,那时候,只要认真寻找,就能在地面上见到一只又一只蝉的幼虫。那是注意不让幼虫外壳开裂的真正的、也是唯一的时机,也是赶紧捕捉、准备烹调的时刻:只要再晚几分钟,壳就裂开了。
这道在古代享有盛誉的佳肴,还有那勾人食欲的形容词“美味无比”,它们是否真的名副其实呢?机不可失,我们不妨利用这个机会,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将荣誉赋予这道受亚里士多德盛赞的菜肴。拉伯雷的朋友、知识渊博的隆德勒
 因发明了鱼酱———用烂鱼内脏制成的著名的调料———而声名远扬。如果我们把幼虫外壳这道美餐还给美食家们,岂不也是一件值得夸奖的功劳?
因发明了鱼酱———用烂鱼内脏制成的著名的调料———而声名远扬。如果我们把幼虫外壳这道美餐还给美食家们,岂不也是一件值得夸奖的功劳?
七月的一个早晨,当已经灼人的太阳把蝉的幼虫逼出地洞时,我们全家老幼都开始寻找起来。我们总共五个人,把院子搜了个遍,尤其是小径两边,那里幼虫最多。为了防止外壳开裂,一旦找到幼虫,我就马上把它浸到水里。幼虫窒息后就会停止蜕变。经过了两个小时的仔细搜寻,我们累得满头大汗,可总共只找到四只幼虫,没有更多。它们都被浸在水里,要么死了,要么奄奄一息;管它呢,它们命中注定要被油炸。
烹饪的方法相当简单,目的在于尽量减少这传说中的美味丧失:几滴油、一撮盐、一点洋葱,仅此而已。即使是《乡村厨娘》
 里也不会有比这更简单的菜谱了。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猎手都分享到了这道油炸幼虫。
里也不会有比这更简单的菜谱了。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猎手都分享到了这道油炸幼虫。
大家一致认为,这道菜还是可以吃的。我们的确都有好胃口,而且胃也没有任何偏见。炸幼虫甚至还有一点虾的味道,这种味道在烤蚂蚱串里更加明显。不过,它实在太硬,汁水也太少,吃的时候简直就像在啃干羊皮。这道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的菜,我是不会向任何人推荐了。
诚然,这位伟大的动物历史学家的消息通常都是准确可靠的。它那身为国王的学生从印度———当时这还是一个神秘的国度———为他弄来了令马其顿人的眼睛啧啧称奇的珍禽异兽;马队给他载来了大象、豹子、老虎、犀牛、孔雀,他对它们作了忠实的描述。但是,即便是在马其顿当地,他也只是通过农民才了解了蝉;那些辛勤耕耘的农民在犁地的时候见过蝉的外壳,并且比任何人都早知道日后从这外壳里出来的是蝉。亚里士多德在他浩瀚的工作中,做了一些后来普林尼
 将要做的事,但他比后者更加天真轻信。他听到了乡村的传言,就把它们当做真实的资料记录了下来。
将要做的事,但他比后者更加天真轻信。他听到了乡村的传言,就把它们当做真实的资料记录了下来。
农民们都很狡黠。他们故意把我们口中的科学讥笑为琐事;他们会嘲笑任何在一只微不足道的昆虫前驻足的人;如果我们捡起一块石头,仔细观察,并把它放进口袋,他们就更会放肆地哈哈大笑。希腊的农民更是脾气古怪。他们对城里人说:蝉的幼虫是神的美食,是无与伦比的佳肴,“美味无比”。但是,当他们用夸张的赞美诱惑幼稚的人的时候,却又让他们的贪欲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要做到这一点,首要条件就是:必须在幼虫破壳之前收集到这些美味。
如果你想尝尝这道美味佳肴,那就去搜集出土的幼虫吧。我们五个人,在一块多蝉的地上,花了两个小时,总共才找到四只幼虫。此外,搜寻时要特别小心,不能让幼虫的壳开裂;搜寻的工作可能要花上几天几夜,而蝉的蜕壳却只要几分钟就行了。我敢肯定,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尝过油炸蝉幼虫;我的烹饪结果就是证明。亚里士多德本是出于善意,可他向人们重复的却是一个农民的玩笑。他那神的美食是一场噩梦。
啊!如果我也听信我的农民邻居们所说的一切,就也能收集到好多关于蝉的故事。我就讲一个农民们关于蝉的故事吧,就一个。
您有没有肾衰,有没有因水肿而走路摇摇晃晃?需不需要一贴有效的净化药?所有的乡间药典都会一致向您推荐一种至高无上的药———蝉。夏天,人们把蝉的成虫收集起来,串成一串,在太阳下晒干,小心翼翼地藏在衣橱的一角。如果哪位主妇在七月里没有将蝉儿串起来储藏,她就会觉得自己大意了。
您突然觉得肾有一点轻微发炎吗?或者尿路稍有不畅?赶快服用蝉熬成的汤药。据说,没有什么比这更有效了。曾经有位好心人———我也是后来听人说,才知道此事———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喝了这样一剂泻药,说是为了治疗哪里不舒服;我要向这位好心人道谢。令我惊讶的是,同样的药方竟然也被阿那扎巴
 的老医师们所推崇。迪约斯科里德告诉我们:“蝉,干嚼,对膀胱疼痛有疗效。”自这位药材鼻祖所生活的遥远年代起,普罗旺斯的农民就对蝉的疗效深信不疑;是来自佛塞
的老医师们所推崇。迪约斯科里德告诉我们:“蝉,干嚼,对膀胱疼痛有疗效。”自这位药材鼻祖所生活的遥远年代起,普罗旺斯的农民就对蝉的疗效深信不疑;是来自佛塞
 的希腊人,把蝉和橄榄树、无花果、葡萄一起,展示给他们的。只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迪约斯科里德建议把蝉烤着吃;而现在,人们把它煮烂,熬成药汤喝。
的希腊人,把蝉和橄榄树、无花果、葡萄一起,展示给他们的。只有一件事发生了变化:迪约斯科里德建议把蝉烤着吃;而现在,人们把它煮烂,熬成药汤喝。
有关蝉具有利尿功能的解释听起来相当天真。众所周知,蝉会对前来抓它的人猛撒一泡尿,然后逃走。因此,它应该可以把它的排泄功能传给人吧。迪约斯科里德以及他的同代人可能就是这样想的,而普罗旺斯的农民至今还是这样想的。
哦,善良的人啊!蝉的幼虫为了建气象站,使用尿液来拌和泥浆,如果你们知道了幼虫的这些特长,又会怎么想呢?也许你们会和拉伯雷一样夸张吧?拉伯雷为我们描写了巨人高康大
 ,他坐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从巨大的膀胱里射出洪水般的尿来,淹没了那么多闲逛的巴黎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
,他坐在巴黎圣母院的钟楼上,从巨大的膀胱里射出洪水般的尿来,淹没了那么多闲逛的巴黎人,还不包括妇女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