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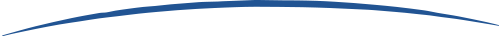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说到中国孩子和美国孩子学画画之关心点的不同,中国孩子总是问老师“我画得像不像”,美国孩子则是问“我画得好不好”。
先说“像不像”。像什么呢?一是像老师的范本,二是像名家或传统的画路。我在电视上见过几个中国孩子比赛水墨画,看笔法都是要写意,但其实全有成规:小鸡是几笔都是几笔,小虾则一群与一群的队形完全一致,葫芦的叶子不仅数目相等并且位置也一样,而白菜的旁边总是配上两朵蘑菇……这哪里还有自己的意,全是别人的实呀!三是像真的。怎样的真呢?倘其写意也循成规,真,料必也只是流于外在的形吧。
再说“好不好”。根据什么说它好不好呢?根据外在的真,只能是像不像。好不好则必牵系着你的心愿,你的神游,神游阻断处你的犹豫和彷徨,以及现实的绝境给你的启示,以及梦想的不灭为你开启的无限可能性。这既是你的劫数也是你的自由,这样的舞蹈你能说它像什么吗?它什么也不像,前面没有什么可以让它像的东西,因而你只有问自己,乃至问天问地:这,好不好?
国画,越看越有些腻了。山水树木花鸟鱼虫,都很像,像真的,像前人,互相像,鉴赏家常也是这样告诉你:此乃袭承哪位大师、哪一门派。西画中这类情况也有。书法中这样的事尤其多,寿字、福字、龙虎二字,写来写去再也弄不出什么新意却还是写来写去,让人看了憋闷,觉得书者与观者的心情都被囚禁。
艺术,原是要在按部就班的实际中开出虚幻,开辟异在,开通自由,技法虽属重要但根本的期待是心魂的可能性。便是写实,也非照相。便是摄影,也并不看重外在的真。一旦艺术,都是要开放遐想与神游,且不宜搭乘已有的专线。
曾经我不大会看画,众人都说好,便追去看。贴近了看,退远了看,看得太快怕人说你干吗来,看得慢了又不知道看什么,看出像来暗自快慰,看着不像便怀疑人家是不是糊弄咱。后来,有一次,忽然之间我被震动了——并非因为那画面所显明的意义,而是因其不拘一格的构想所流露的不甘就范的心情。一俟有了这样的感受,那画面便活跃起来,扩展开去,使你不由得惊叹:原来还有这样的可能!于是你不单看见了一幅画,还看见了画者飞扬的激情,看见了一条渴望着创造的心迹,观者的心情也便跟随着不再拘泥一处,顿觉僵死的实际中处处都蕴藏着希望。
不过,倘奇诡、新异肯定就好,艺术又怕混淆于胡来。贬斥了半天“像”,回头一想,什么都不像行吗?换个角度说,你根据什么说A是艺术,B是创作,而C是胡来?所谓“似与不似之间”,这“之间”若仅是画面上分寸的推敲,结果可能还是成规,或者又是胡来。这“之间”,必是由于心神的突围,才可望走到艺术的位置;可以离形,但不能失神,可以脱离实际沉于梦幻,却不可无所寻觅而单凭着手的自由。这就像爱与性的关系:爱中之性,多么奇诡也是诉说,而无爱之性再怎么像模像样儿也还是排泄。
什么都不像既然也不行,那又该像什么呢?像你的犹豫,像你的绝望,像你的不甘就范的心魂。但心魂的辽阔岂一个“像”字可以捕捉?所以还得是“好不好”;“好不好”是心魂在无可像处的寻觅。
中国观众,对戏剧,对表演,也多以“像不像”来评价。医生必须像医生,警察千万得像警察。可医生和警察,脱了衣裳谁像谁呢?脱了衣裳并且入梦,又是怎么个像法呢?(有一段相声说:梦,有俩人商量着做的吗?)像,唯在外表,心魂却从来多样。心魂,你说他应该像什么?只像他自己不好吗?只像他希望自己所是的那样,不好吗?可见,“像不像”的评价,还是对形的要求,对表层生活的关注,心魂的辽阔与埋藏倒被忽视。
所以中国的舞台上与中国的大街上总是很像。中国的演员,功夫多下在举手投足、一颦一笑的“像”上。中国观众的期待,更是被培养在这个“像”字上。于是,中国的艺术总是以“像”而赢得赞赏。极例是“文革”中的一个舞蹈《喜晒战备粮》:一群女孩儿不过都换了一身干净衣裳,跳到台上去筛一种想象中的谷物。筛来筛去,这我在农村见过,觉得真像,又觉得真没劲——早知如此,给我们村儿的女子们换身衣裳不得了?想来我们村儿的女子们倒更要活泼得多了。还有所谓的根雕,你看去吧,好好的天之造物,非得弄得像龙像凤,像鹰像鹤,偏就不见那根须本身的蓬勃与呼啸。还是一个“像”字作怪。“不肖子孙”所以是斥责,就因其不像祖宗,不按既定方针办。龙与鹤的意思都现成,像就是了,而自然的蓬勃与呼啸是要心魂参与创造的,而心魂一向都被忽视。
像字当头,艺术很容易流于技艺。用笔画,会的人太多,不能标榜特色总归是寂寞,就有人用木片画,用手指或舌头画,用气吹着墨液在纸上走。有个黄色笑话,说古时某才子善用其臀作画,蘸了墨液在纸上只一坐,像什么就不说了,但真是像。玩笑归玩笑,其实用什么画具都不要紧,远古无“荣宝斋”时,岩洞壁画依然动人魂魄。古人无规可循,所画之物也并不求像,但那是心魂的奔突与祈告,其牵魂的力量自难磨灭。我是说,心魂的路途远未走完,未必是工具已经不够使。
外在的“像”与“真”,或也是艺术追求之一种,但若作为艺术的最高鉴定,尴尬的局面在所难免。比如,倘若真就是好,任何黄色的描写就都无由贬斥,任何乌七八糟的东西都能叫艺术,作者只要说一句“这多么真实”,或者“我的生活真的是这样”,你说什么?他反过来还要说你:“遮遮掩掩的你真是那样干吗?虚伪!”是呀,许你满台土语,就不许我通篇脏话?许你引车卖浆惟妙惟肖,就不许我鸾颠凤倒纤毫毕现?许你衣冠楚楚,倒不许我一丝不挂?你真还是我真?哎哎,确也如此——倘去实际中比真,你真比不过他。不过,若只求实际之真,艺术真也是多余。满街都是真,床上床下都是真,看去呗。可艺术何为?艺术是一切,这总说不通吧?那么,艺术之真不同于实际之真,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艺术是假吗?当然也不是。倒是满街的实际,可能有一半是假;床上床下的真,可能藏着假情假意,一丝不挂呢,就真的没有遮掩?而在这真假之间,心魂一旦感受到荒诞,感受到苦闷有如囚徒,便可能开辟另一种存在,寻觅另一种真了。这样的真,以及这样的开辟与寻觅本身,被称为艺术,应该是合适的。
说艺术之真有可能成为伪善的借口,成为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这可信。但因此就将实际之真作为艺术的最高追求,却不能接受。
“艺术源于生活”,我曾以为是一句废话——工农兵学商,可有哪一行不是源于生活吗?后来我明白,这当然不是废话,这话意在消解对实际生活的怀疑。
有位大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他不知道“匡正”也是源于生活?料必他是看出了“源于生活”要么是废话,要么就会囿于实际,使心魂萎缩。
粉饰生活的行为,倒更会推崇实际,拒斥心魂。因为,心魂才是自由的起点和凭证,是对不自由的洞察与抗议,它当然对粉饰不利。所以要强调艺术的不能与实际同流。艺术,乃“于无声处”之“惊雷”,是实际之外的崭新发生。
“匡正”,不单是针对着社会,更是针对着人性。自由,也不仅是对强权的反抗,更是对人性的质疑。文学因而不能止于干预实际生活,而探问心魂的迷茫和意义才更是它的本分。文学的求变无疑是正当,因为生活一直在变。但是,生命中可有什么不变的东西吗?这才是文学一向在询问和寻找的。日新月异的生活,只是为人提供了今非昔比的道具,马车变成汽车,蒲扇换成空调,而其亘古的梦想一直不变,上帝对人的期待一直不变。为使这梦想和期待不致被日益奇诡、奢靡的道具所湮灭,艺术这才出面。上帝就像出题的考官,不断变换生活的题面,看你是否还能从中找出生命的本义。
对于科学,后人不必重复前人,只需接过前人的成就,继往开来。生命的意义却似轮回,每个人都得从头寻找,唯在这寻找中才可能与前贤汇合,唯当走过林莽,走过激流,走过深渊,走过思悟一向的艰途,步上山巅之时你才能说继承。若在山腰止步,登峰之路岂不又被埋没?幸有世世代代不懈的攀登者,如西绪福斯一般重复着这样的攀登,才使梦想照耀了实际,才有信念一直缭绕于生活的上空。
不能把遮掩实际之真的骗术算在艺术之真的头上,就像不能把淫乱归在性欲名下。而实际之真阻断了心魂恣肆的情况,也是常有,比如婚内强奸也可导致生育,但爱情随之荒芜。
实际的真与否,有舆论和法律去调教,比如性骚扰的被处罚,性丑闻的被揭露,再比如拾金不昧的被表彰。但艺术之真是在信仰麾下,并不受实际牵制,它的好与不好就如爱情的成败,唯自作自受。一般来看,掩盖实际之真的骗术,多也依靠实际之假,或以实际的利益为引诱,哪有欺世盗名者希望大家心魂自由的呢?
黄色所以是黄色,只因其囿于器官的实际,心魂被快感淹没,不得伸展。倘非如此,心魂借助肉体而天而地,爱愿借助性欲而酣畅地表达,而虔诚地祈告,又何黄之有?一旦心魂驾驭了实际,或突围,或彷徨,或欢聚,你就自由地写吧,画吧,演吧,字还是那些字,形还是那些形,动作还是那些动作,意味却已大变——爱情之下怎么都是艺术,一黄不染。黄色,其实多么小气,而“金风(爱)玉露(性)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是诗是歌是舞,是神的恩赐呀谁管得着?
其实,对黄色,也无须太多藏禁。那路东西谁都难免想看看,但正因其太过实际,生理书上早都写得明白,看看即入穷途。半遮半掩,倒是撩拨青少年。
我们太看重了白昼,又太忽视着黑夜。生命,至少有一半是在黑夜中呀——夜深人静,心神仍在奔突和浪游。更因为,一个明确走在晴天朗照中的人,很可能正在心魂的黑暗与迷茫中挣扎,黑夜与白昼之比因而更其悬殊。
这迷茫与挣扎,不是源于生活?但更是“匡正”,或“匡正”的可能。这就得把那个“像”字颠来倒去鞭打几回!因为,这黑夜,这迷茫与挣扎,正是由于无可像者和不想再像什么。这是必要的折磨,否则尽是“酷肖子孙”,千年一日将是何等无聊?连白娘子都不忍仙界的寂寞,“千年等一回”来寻这人间的多彩与真情。
不能因为不像,就去谴责一部作品,而要看看那不像的外形是否正因有心魂在奔突,或那不像的传达是否已使心魂震动、惊醒。像,已经太腻人,而不像,可能正为生途开辟着新域。
“艺术高于生活”,似有些高高在上,轻慢了某些平凡的疾苦,让人不爱听。再说,这“高于”的方向和尺度由谁来制定呢?你说你高,我说我比你还高,他说我低,你说他其实更低,这便助长霸道,而霸道正是瞒与骗的基础。那就不如说“艺术异于生活”。“异”是自由,你可异,我亦可异,异与异仍可存异,唯异端的权利不被剥夺是普遍的原则。
不过,“异”主要是说,生理的活着基本相同,而心魂的眺望各有其异,物质的享受必趋实际,而心魂的眺望一向都在实际之外。但是,实际之外可能正是黑夜。黑夜的那边还有黑夜,黑夜的尽头呢?尽头者,必不是无,仍是黑夜,心魂的黑夜。人们习惯说光明在前面引领,可光明的前面正是黑夜的呼唤呀。现成的光明俯拾即是,你要嫌累就避开黑夜,甭排队也能领得一份光明,可那样的光明一定能照亮你的黑夜吗?唯心神的黑夜,才开出生命的广阔,才通向精神的家园,才是要麻烦艺术去照亮的地方。而偏好实际,常常湮灭了它。缺乏对心魂的关注,不仅限制了中国的艺术,也限制着中国人心魂的伸展。
“普遍主义”很像“高于”,都是由一个自以为是的制高点发放通行证,强令排异,要求大家都与它同,此类“普遍”自然是得反对。但要看明白,这并不意味着天下人就没有共通点,天下事就没有普遍性。要活着,要安全,要自由表达,要维护自己独特的思与行……这有谁不愿意吗?因此就得想些办法来维护,这样的维护不需要普遍吗?对“反对普遍主义”之最愚蠢的理解,是以为你有你的实际,我有我的实际,因此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可是,日本鬼子据其实际要侵略你,行吗?村长据其实际想强奸某一村民,也不行吧?所以必得有一种普遍的遵守。
语言也是这样,无论谈恋爱还是谈买卖,总是期望相互能听懂,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就不如各自回家去睡觉。要是你听不懂我的我就骂人,就诉诸强迫,那便是霸道,是要普遍反对的。可是,反抗霸道若也被认为是霸道,事情就有些乱。为免其乱就得有法律,就得有普遍的遵守。然而又有问题:法律由谁来制定?只根据少数人(或国)的利益显然不对吧?所以就得保证所有的人(或国)都能自由发言。
说到保护民族语言的纯洁与独立,以防强势文化对它的侵蚀与泯灭,我倾向赞成,但也有些疑问。疑问之一:这纯洁与独立,只好以民族为单位吗?为什么不更扩大些或更缩小些?疑问之二:民族之间可能有霸道,民族之内就不可能有?民族之间可以恃强凌弱,一村一户中就不会发生同样的事?为什么不干脆说“保护个人的自由发言”呢?
本当是个人发言,关注普遍,不知怎么一弄,常常就变成了集体发言,却只看重一己了。只有个人自由,才有普遍利益,只因有普遍的遵守,才可能保障个人的自由,这道理多么简单。事实上,轻蔑个人自由的人,也都不屑于普遍的遵守,道理也简单:自由一普遍,霸字搁在哪儿?
远来的和尚,原是要欣赏异地风俗,或为人类学等等采集标本,自然是希望着种类的多样,稀有种类尤其希望它保持原态,不见得都有闲心去想这标本中人是否活得煎熬,是否也图自由与发展?他们不想倒也罢了,标本中人若为取悦游僧和学者而甘做标本,倒把自己的愿望废置,把自己必要的变革丢弃,事情岂不荒唐?
前不久,可能是在电视上也可能是在报纸上,见一位导演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问:“有人说您的‘中国特色’其实是迎合外国人的口味。”导演说:“不,因为我表现的是人的普遍情感,所以外国人也能接受。”我便想:什么是普遍情感?这普遍是谁的统计?怎么统计的?其依据和目的都是什么?以及被这统计所排除、所遗漏的那些心魂应当怎样处置?尤其,这普遍怎么又成了特色?是什么人,会认此普遍为特色呢?是不是由市场判定的普遍?是不是由外国口味判定的中国特色?
一个创作者,敢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这里面隐约已经有了一方“父母官”的影子。一个创作者,竟说他表现的是普遍,谦虚得又似过头,这岂非是说自己并无独到之见?一个创作者,至少要自以为有独特的发现,才会有创作的激情吧?普遍的情感满街都是,倘不能从中见出独具的心流,最多也只能算模仿生活。内在的新异已被小心地择出或粗心地忽略,一旦走上舞台和银幕,料必仍只是外在的像。这样的“创作”,我在想,其动力会是什么呢?不免还是想到了“迎合”,迎合市场,迎合“父母官”,迎合一种固有的优势话语,或者迎合别的什么。未必就是迎合大众,倒可能是麻醉大众。大众的心流原本是多么丰富,多么不拘,多么辽远,怎么迎合得过来?唯把他们麻醉到只认得一种戏路,只相信一种思绪配走上舞台或银幕,他们才可以随时随地被迎合。所以我又想,是否正因为这堂而皇之的普遍,万千独具的心流所以被湮灭,以致中国特色倒要由外国人来判定?还有,为什么要以国为单位来配制特色?为什么不让每一缕心魂自然而然地表现其特色呢?
别抱怨摆弄实际之真的所谓艺术总是捉襟见肘吧,那是必然。正因为实际走到了末路,艺术这才发生,若领着艺术再去膜拜实际,岂非鬼打墙?所以,艺术正如爱情,都是不能嫌累的事。心魂之域本无尽头,比如“诗意地栖居”可不是独享逍遥,而是永远地寻觅与投奔,并且总在黑夜中。
要讲真话,勿瞒与骗,这是中国人普遍推崇的品质。可从来,有几人真能做得彻底,真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且莫苛求“言必行”吧。)倒是常听见这样的表白:“有些话我不能讲,但我讲的保证都是真话。”说实在的,能如此也已经令人钦佩。扪心自问,我自己顶多也就这样。但这绝不是说我钦佩我自己,恰恰相反,用陕北话说:我这心里头害麻烦。翻译成北京话就是:糟心。有点儿像吸毒,自个儿也看不起自个儿,又戒不掉。软弱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软弱但还是软弱着,虚伪的自己看不起自己的虚伪却还是“有些话不能讲”——真真岂有此理!
岂有此理就完了吗?钦佩着勇敢者之余,软弱如我者想:岂有此理的深处就怕还藏着另外的道理,未必一副硬骨头就能包打天下。说真话、硬骨头、匕首与投枪,于虚伪自然是良药,但痼疾犹在,久不见轻,大概还是医路的问题。自古就有“文死谏”的倡导,意思也就是硬骨头、讲真话,可这品质世世代代一直都被倡导,或只被倡导,且有日趋金贵之势,岂不令人沮丧?怎么回事?中国人一向推崇的品质,怎么竟成了中国人越来越难得的高风亮节?
说真话有什么错吗?当然没有,还能是说假话不成?但说真话就够了吗?这就又得看看:除了实际之真,心魂之真是否也有表达?是否也能表达?是否也提倡表达?是否这样的表达也被尊重?倘只白昼在表达,生命至少要减半。倘黑夜总就在黑夜中独行,或聋,或哑,或被斥为“不打粮食”,真,岂不是残疾着吗?比如两口子,若互相只言白昼,黑夜之浪动的心流或被视为无用,或被看作邪念,千万得互相藏好,那料必是要憋出毛病的。比如憋出猜疑和防备,猜疑和防备又难免流入白昼,实际之真也就要打折扣了。这还不要紧,只要黑夜健在,娜拉大不了是个出走。但黑夜要是一口气憋死,实际被实际所囚禁,艺术和爱情和一切就都只好由着白昼去豢养、去叫卖了。失去黑夜的白昼,失去匡正的生活,什么假不能炒成真?什么阴暗不能标榜为圣洁?什么荒唐事不能煽得人落泪?于是,什么真也就都可能沦落到“我不能说”了。
听说有一位导演,在反驳别人的批评时说:“不管怎么说,反正我是让观众落了泪。”反驳当然是你的权利,但这样的反驳很无力,让人落泪就一定是好艺术吗?让人哭,让人笑,让人咬牙切齿、捶胸顿足,都太容易,不见得非劳驾艺术不可。而真正的好艺术,真正的心路艰难,未必都有上述效果。
我听一位批评家朋友说过一件事:他去看一出话剧,事先掖了手绢在兜里,预备哭和笑,然而整个演出过程中他哭不出也笑不出,全场唯鸦雀无声。直到剧终,掌声虽也持久,但却犹豫。直到戏散,鱼贯而出的人群仍然没有什么热烈的表示,大家默默地走路,看天,或对视。我那朋友干脆找个没人的地方坐下来发呆。他说这戏真好。他没说真像。他说看戏的人中有说真好的,有说不好的,但没见有谁说真像或者不像。他说,无论说真好的还是说不好的,神情都似有些愕然,加上天黑。他说他在那没人的地方坐了很久,心里仍然是一片愕然,以往的批评手段似乎都要作废,他说他看见了生命本身的疑难。这戏我没看。
我看过一篇报告文学,讲一个叛徒的身世。这人的弟弟是个很有名望的革命者。兄弟俩早年先后参加了革命,说起来他还是弟弟的引路人,弟弟是在他的鼓动下才投身革命的。其实他跟弟弟一样对早年的选择终生无悔,即便是在他屈服于敌人的暴力之时,即便是在他饱受屈辱的后半生中,他也仍于心中默默坚守着当初的信奉。然而弟弟是受人爱戴的人,他却成了叛徒。如此天壤之别,细究因由其实简单:他怕死,怕酷刑的折磨,弟弟不怕。当然,还在于,他不幸被敌人抓去了,弟弟没这么倒霉。就是说,弟弟的不怕未经证实。于是也可以想象另一种可能:被抓去的是弟弟,不是他。这种可能又引出另外两种可能:一是弟弟确实不怕死,也不怕折磨,这样的话世上就会少一个叛徒,多一个可敬的人;二是弟弟也怕,结果呢,叛徒和可敬的人数目不变,只不过兄弟俩倒了个过儿。
谁是叛徒无关紧要,就像谁是哥谁是弟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世上确有哥哥这样的人,确有这样饱受折磨的心。知道世上有这样的人的那天,我也是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呆坐很久,心中全是愕然,以往对叛徒的看法似乎都在动摇。我慢慢地看见,勇猛与可敬之外还有着更为复杂的人生处境。我看见一片蛮荒的旷野,神光甚至也少照耀,唯一颗诉告无处的心随生命的节拍钟表一样地颤抖,永无休止。不管什么原因吧,总归有人处于这样的境地,总归有这样的心魂的绝境,你能看一看就忘了吗?我尤其想起了这样的话:人道主义者是不能使用“个别现象”这种托词的。
这样的事让我不寒而栗。这样的事总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你是他,你怎么办?这问题常使我夜不能寐。一边是屈辱,一边是死亡,你选择什么?一边是生,是永恒的耻辱与惩罚,一边是死,或是酷刑的折磨,甚至是亲人遭连累,我怎样选择?这问题在白昼我不敢回答,在黑夜我暗自祈祷:这样的事千万别让我碰上吧。但我知道这不算回答,这唯使黑夜更加深沉。我又对自己说:倘这事真的轮到我头上,我唯求速死。可我心里又明白,这不是勇敢,也仍然不是回答,这是逃避,想逃开这两难的选择,想逃出这最无人道的处境。因为我还知道,这样的事并不由于某一个人的速死就可以结束。何况敌人不见得就让你速死,敌人要你活着,逼你就范是他们求胜的方法。然而,逼迫你的仅仅是敌人吗?不,这更像合谋,它同时也是敌人的敌人求胜的方法。在求胜的驱动之下,敌对双方一样地轻蔑了人道,践踏和泯灭着人道,那么不管谁胜,得胜的终于会是人道吗?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的敌对双方,到底是因何而敌对?各自所求之胜,究竟有着怎样根本的不同?我的黑夜仍在黑夜中。而且黑夜知道,对这两难之题,是不能用逃避冒充回答的。
对这样的事,和这样的黑夜,我在《务虚笔记》中曾有触及,我试图走到三方当事者的位置,演算各自的心路。
大凡这类事,必具三方当事者:A——或叛徒,或英雄,或谓之“两难选择者”;B——敌人;C——自己人。演算的结果是:大家都害怕处于A的位置。甚至,A的位置所以存在,正由于大家都在躲避它。比如说,B不可以放过A吗?但那样的话,B也就背叛了他的自己人,从而走到了A的位置。再比如,C不可以站出来,替下你所担心的那个可能成为叛徒的人吗?但那样C也就走到了A的位置。可见,A的位置他们都怕——既怕做叛徒,也怕做英雄,否则毫不犹豫地去做英雄就是,叛徒不叛徒的根本不要考虑。是的,都怕,A的位置这才巩固。是的,都怕,但只有A的怕是罪行。原来是这样,他们不过都把一件可怕的事推给了A,把大家的罪行推给了A去承担,然后,一方备下了屠刀、酷刑和株连,一方备下了赞美,或永生的惩罚。
大家心里都知道它的可怕,大家却又一起制造了它,这不荒唐吗?因此,很久以来我就想为这样的叛徒说句话。就算对那两难的选择我仍未找到答案,我也想替他问一问:他到底错在了哪儿?他不该一腔热血而做出了他年轻时的选择吗?他不该接受一项有可能被敌人抓去的工作吗?他一旦被抓住就不该再想活下去吗?或者,他就应该忍受那非人的折磨?就应该置无辜的亲人于不顾,而单去保住自己的名节,或单要保护某些同他一样承诺了责任的“自己人”吗?
我真是找不出像样的回答。但我不由得总是想:有什么理由使一个人处于如此境地?就因为他要反对某种不合理(说到底是不合人道之理)的现实,就应该处于更不人道的境地中吗?
我认真地为这样的事寻找理由,唯一能找到的是:A的屈服不仅危及了C,还可能危及“自己人”的整个事业。然而,倘这事业求胜的方法与敌人求胜的方法并无根本不同,将如何证明和保证它与它所反对的不合理一定就有根本的不同呢?于是我又想起了圣雄甘地的话: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和平,和平本身是一种方法。这话也可引申为: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获得人道,人道本身就是方法。那也就是说:人道存在于方法中,倘方法不人道,又如何树立人道,又怎么能反对不人道?
这真正是一道难题:敌人不会因为你人道,他也就人道。你人道,他很可能乘虚而入,反使其不人道得以巩固。但你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你就也蔑视了人道,你就等于加入了他,反使不人道壮大。仇恨的最大弊端是仇恨的蔓延,压迫的最大遗患是压迫的复制。“自己人”万勿使这难题更难吧。以牙还牙的怪圈如能有一个缺口,那必是更勇敢、更理性、更智慧的人发现的,比如甘地的方法,比如马丁·路德·金的方法。他们的发现,肯定不单是因为骨头硬,更是因为对万千独具心流更加贴近的关怀,对人道更为深彻的思索,对目的更清醒的认识。这样的勇敢,不仅要对着敌人,也要对着自己,不仅靠骨头,更要靠智慧。当然,说到底是因为:不是为了坐江山,而是为了争自由。
电视中正在播放连续剧《太平天国》。洪秀全不勇敢?但他还是要坐江山。杨秀清不勇敢?可他总是借天父之口说自己的话。天国将士不勇敢吗,可为什么万千心流汇为沉默?“天国”看似有其信仰,但人造的神不过是“天王”手中的一张牌。那神曾长了一张人嘴,人嘴倘合王意,王便率众祭拜,人嘴如若不轨,王必率众诛之,而那虚假的信仰一旦揭开,内里仍不过一场权力之争,一切轰轰烈烈立刻没了根基。
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见赵子龙在长坂坡前威风八面,于重重围困中杀进杀出,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不禁为之喝彩。现在却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级的人是谁?多数连姓名也没有,有姓名的也不过是赵子龙枪下的一个活靶。战争当然就是这么残酷,但小说里也不曾对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学传统中的问题。
我常设想,赵子龙枪下的某一无名死者,曾有着怎样的生活,怎样的期待,曾有着怎样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样的时刻得知了他的死讯,或者连他的死讯也从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没回来,好像这人生下来就是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为了给他的亲人留下一个永远的牵挂,就是为了在一部中国名著中留下一行字:只一回合便被斩于马下。这个人,倘其心流也有表达,世间也许就多有一个多才多艺的鲁班,一个勤劳忠厚的董永,抑或一个风流倜傥的贾宝玉(虽然他不可能那么富贵,但他完全可能那么多情)。当然,他不必非得是名人,是个普通人足够。但一个普通人的心流,并非普遍情感就可以概括,倘那样概括,他就仍只是一个王命难违的士兵,一个名将的活靶,一部名著里的道具,其独具的心流便永远还是沉默。
我的一位已故艺术家朋友,生前正做着一件事:用青铜铸造一千个古代士兵的首级,陈于荒野,面向苍天。我因此常想象那样的场面。我因此能看见那些神情各异的容颜。我因此能够听见他们的诉说——一千种无人知晓的心流在天地间浪涌风驰。实际上,他们一代一代在那荒野上聚集,已历数千年。徘徊,等待,直到我这位朋友来了,他们才有可能说话了。真不知苍天何意,竟让我这位朋友猝然而逝,使这件事未及完成。我这位艺术家朋友,名叫:甘少诚。
叛徒(指前述那样的叛徒,单为荣华而出卖朋友的一类此处不论)就正是由普遍情感所概括出的一种符号,千百年中,在世人心里,此类人等都有着同样简化的形象和心流。在小说、戏剧和电影中,他们只要符合了那简化的统一(或普遍),便是“真像”,便在观众中激起简化而且统一的情感,很少有人再去想:这一个人,其处境的艰险,其心路的危难。
恨,其实多么简单,朝他吐唾沫就是,扔石头就是。
《圣经》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看耶稣是怎么说吧:法利赛人抓来一个行淫的妇女,认为按照摩西的法律应该用石头砸死她,他们等待耶稣的决定。耶稣先是在地上写下一行字,众人追问那字的意思,耶稣于是站起来说,你们中谁没有犯过罪,就去用石头砸死她吧。耶稣说完又在地上写字。那些人听罢纷纷离去……
因此,我想,把那个行淫的妇女换成那个叛徒,耶稣的话同样成立:你们中谁不曾躲避过A的位置,就可以朝他吐唾沫、扔石头。如果人们因此而犹豫,而看见了自己的恐惧和畏缩,那便是绝对信仰在拷问相对价值的时刻。那时,普遍情感便重新化作万千独具的心流。那时,万千心流便一同朝向了终极的关怀。于是就有了忏悔,于是忏悔的意义便凸显出来。比如,这忏悔的人群中如果站着B和C,是否在未来,就可以希望不再有A的位置了呢?
众人走后,耶稣问那妇女:没有人留下定你的罪吗?答:没有。耶稣说:那我也就不定你的罪,只是你以后不要再犯。这就是说,罪仍然是罪,不因为它普遍存在就不是罪。只不过耶稣是要强调:罪,既然普遍存在于人的心中,那么,忏悔对于每一个人就都是必要。
有意思的是,当众人要耶稣做决定时,耶稣为什么在地上写字?为什么耶稣说完那些话,又在地上写字?我一直想不透。他是说“字写的法律与心做的忏悔不能同日而语”吗?他是说“字写的简单与心写的复杂不可等量齐观”吗?或者,他是说“字写的语言有可能变成人对人的强暴,唯对万千心流深入的体会才是爱的祈祷”?但也许他是取了另一种角度,说:字,本当从沉默的心中流出。
对于A的位置,对于这位置所提出的问题,我仍不敢说已经有了回答,比这远为复杂的事例还很多。我只是想,所有的实际之真,以及所谓的普遍情感,都不是写作应该止步的地方。文学和艺术,从来都是向着更深处的寻觅,当然是人的心魂深处。而且这样的深处,并不因为曾经到过,今天就无必要。其实,今天,绝对的信仰之光正趋淡薄,日新月异的生活道具正淹没着对生命意义的寻求。上帝的题面一变,人就发昏,原来会做的题也不会了;甚至干脆不做了,既然窗外有着那么多快乐的诱惑。看来,靡非斯特跟上帝的赌博远未结束,而且人们正在到处说着那句可能使魔鬼获胜的话。
插队时,村中有所小学,小学里有个奇怪的孩子,他平时替他爹算工分,加加减减一丝不乱,可你要是给他出一道加减法的应用题,比如说某工厂的产值,或某公园里的树木,或某棵树上的鸟,加来减去他把脚丫子也用上还是算不清。我猜他一定是让工厂呀、公园呀、树和鸟呀给闹乱了,那些玩意儿怎么能算得清?别小看靡非斯特吧,它把生活道具弄得越来越邪乎,于中行走容易找不着北。
我想我还是有必要浪费一句话:舍生取义是应该赞美的,为信仰而献身更是美德。但是,这样的要求务须对着自己,倘以此去强迫他人,其“义”或“信仰”本身就都可疑。
“我不能说”,不单因为惧怕权势,还因为惧怕舆论,惧怕习俗,惧怕知识的霸道。原是一份真切的心之困境,期望着交流与沟通,眺望着新路,却有习俗大惊失色地叫:“黄色!”却有舆论声色俱厉地喊:“叛徒!”却有霸道轻蔑地说:“你看了几本书,也来发言?”于是黑夜为强大的白昼所迫,重回黑夜的孤独。
入夜之时,心神如果不死,如果不甘就范,你去听吧,也许你就能听见如你一样的挣扎还在黑夜中挣扎,如你一样的眺望还在黑夜中眺望。也许你还能听见诗人西川的话:我打开一本书/一个灵魂就苏醒/……/我阅读一个家族的预言/我看到的痛苦并不比痛苦更多/历史仅记录少数人的丰功伟绩/其他人说话汇合为沉默……
你不必非得看过多少本书,但你要看重这沉默,这黑夜,它教会你思想而不单是看书。你可以多看些书,但世上的书从未被哪一个人看完过,而看过很多书却没有思想能力的人却也不少。
中国的电影和戏剧,很少这黑夜的表达,满台上都是模仿白昼,在细巧之处把玩表面之真。旧时闺秀,新潮酷哥,请安、跪拜、作揖、接吻,虽惟妙惟肖却只一副外壳。大家看了说一声“真像”,于是满足,可就在回家的路上也是各具心流,与那白昼的“真”和“像”迥异。黑夜已在白昼插科打诨之际降临,此刻心里正有着另一些事,另一些令心魂不知所从的事,不可捉摸的心流眺望着不可捉摸的前途,困顿与迷茫正与黑夜汇合。然而看样子他们似乎相信,这黑夜与艺术从来吃的是两碗饭,电影、戏剧和杂技唯做些打岔的工作,以使这黑夜不要深沉,或在你耳边嘀咕:黑夜来了,白昼还会远吗?人们习惯于白昼,看不起黑夜:困顿和迷茫怎么能有美呢?怎么能上得舞台和银幕呢?每个人的心流都是独特,有几个人能为你喊一声“真像”?唔,艺术已经认不出黑夜了,黑夜早已离开了它,唯白昼为之叫卖、喝彩。真不知是中国艺术培养了中国观众,还是中国观众造就了中国艺术。
你看那正被抢救的传统京剧,悦目悦耳,是可以怡然自得半躺半仰着听的,它要你忘忧,不要你动心,虽常是夜场但与黑夜无关,它是冬天里的春天、黑夜中的白昼。不是说它不该被抢救,任何历史遗迹都要保护,但那是为了什么呢?看看如今的圆明园,像倒还是有得可像——比如街心花园,但荒芜悲烈的心流早都不见。
夜深人静,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候。其他时间也可以,但上帝总是在你心魂的黑夜中降临。忏悔,不单是忏悔白昼的已明之罪,更是看那暗中奔溢着的心流与神的要求有着怎样的背离。忏悔不是给别人看的,甚至也不是给上帝看的,而是看上帝,仰望他,这仰望逼迫着你诚实。这诚实,不止于对白昼的揭露,也不非得向别人交代问题,难言之隐完全可以藏在肚里,但你不能不对自己坦白,不能不对黑夜坦白,不能不直视你的黑夜:迷茫、曲折、绝途、丑陋和恶念……一切你的心流你都不能回避。因为看不见神的人以为神看不见,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于是神使你看见——神以其完美、浩瀚使你看见自己的残缺与渺小,神以其无穷之动使你看见永恒的跟随,神以其宽容要你悔罪,神以其严厉为你布设无边的黑夜。因此,忏悔,除去低头还有仰望,除知今是而昨非还要询问未来,而这绝非白昼的戏剧可以通达,绝非“像”可能触及,那是黑夜要你同行啊,要你说:是!
这样的忏悔从来是第一人称的。“你要忏悔”——这是神说的话,倘由人说就是病句。如同早晨醒来,不是由自己而是由别人说你做了什么梦,岂不奇怪?忏悔,是个人独对上帝的时刻,就像梦,别人不得参与。好梦成真大家祝贺,坏梦实行,众人当然要反对。但好梦坏梦,止于梦,别人就不能管,别人一管就比坏梦还坏,或正是坏梦的实行。君不见“文革”时的“表忠心”和“狠斗私心一闪念”,其坏何源?就因为人说了神的话。
坏梦实行固然可怕,强制推行好梦,也可怕。诗人顾城的悲剧即属后一种。我不认识顾城,只读过他的诗,后来又知道了他在一个小岛上的故事。无论是他的诗,还是他在那小岛上的生活,都蕴藏着美好的梦想。他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他希望两个女人互相也爱,他希望他们三个互相都爱。这有什么不好吗?至少这是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不可能吗?可不可能是另外的问题,好梦无不期望着实现。我记得他在书中写过,他看着两个女人在阳光下并肩而行,和平如同姐妹,心中顿生无比的感动。这感动绝无虚伪。在这个越来越以经济指标为衡量标准的社会,在这个心魂越来越要相互躲藏的人间,诗人选中那个小岛做其圆梦之地,养鸡为生,过最简朴的生活,唯热烈地供奉他们的爱情,唯热切盼望那超俗的爱情能够长大。这样的梦想不美吗?倘其能够实现,怎么不好?可问题不在这儿。问题是:好梦并不统一,并不由一人制订,若把他人独具的心流强行编入自己的梦想,一切好梦就都要结束。
看顾城的书时,我心里一直盼望着他的梦想能够实现。但这之前我已经知道了那结尾是一次屠杀,因此我每看到一处美丽的地方,都暗暗希望就此打住,停下来,就停在这儿,你为什么不能就停在这儿呢?于是我终于看见,那美丽的梦想后面,还有一颗帝王的心:强制推行,比梦想本身更具诱惑。
B和C具体是谁并不重要。麻烦的是,这样的逻辑几乎到处存在。比如在朋友之间,比如在不尽相同的思想或信仰之间,也常有A、B、C式的矛盾。甚至在孩子们模拟的“战斗”中,A的位置也是那样原原本本。
我记得小时候,在幼儿园玩过一种“骑马打仗”的游戏,一群孩子,一个背上一个,分成两拨,互相“厮杀”,拉扯、冲撞、下绊子,人仰马翻者为败。老师满院子里追着喊:别这样,别这样,看摔坏了!但战斗正未有穷期。这游戏本来很好玩,可不知怎么一来,又有了对战俘的惩罚:弹脑蹦儿,或连人带马归顺敌方。这就又有了叛徒,以及对叛徒更为严厉的惩罚。叛徒一经捉回,便被“游街示众”,被人弹脑蹦儿、拧耳朵(相当于吐唾沫、扔石头)。到后来,天知道怎么这惩罚竟比“战斗”更具诱惑了,无需“骑马打仗”,直接就玩起这惩罚的游戏来。可谁是被惩罚者呢?便涌现出一两个头领,由他们说了算。于是,为免遭惩罚,孩子们便纷纷效忠那一两个头领。然而这游戏要玩下去,不能没有被惩罚者呀?可怕的日子于是到了。我记得从那时起,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尽借口,以期不必去那幼儿园。
不久前,我偶然读到一篇英语童话——我的英语好到一看便知那是英语,妻子把它变成中文:战争结束了,有个年轻号手最后离开战场,回家。他日夜思念着他的未婚妻,路上更是设想着如何同她见面,如何把她娶回家。可是,等他回到家乡,却听说未婚妻已同别人结婚;因为家乡早已流传着他战死沙场的消息。年轻号手痛苦之极,便又离开家乡,四处漂泊。孤独的路上,陪伴他的只有那把小号,他便吹响小号,号声凄婉悲凉。有一天,他走到一个国家,国王听见了他的号声,使人把他唤来,问他:你的号声为什么这样哀伤?号手便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国王。国王听了非常同情他……看到这儿我就要放下了,猜那又是个老掉牙的故事,接下来无非是国王很喜欢这个年轻号手,而他也表现出不俗的才智,于是国王把女儿嫁给了他,最后呢?肯定是他与公主白头偕老,过着幸福的生活。妻子说不,说你往下看:……国王于是请国人都来听这号手讲他自己的故事,并听那号声中的哀伤。日复一日,年轻人不断地讲,人们不断地听,只要那号声一响,人们便来围拢他,默默地听。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号声已不再那么低沉、凄凉。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号声开始变得欢快、嘹亮,变得生气勃勃了。故事就这么结束了。就这么结束了?对,结束了。当意识到它已经结束了的时候,忽然间我热泪盈眶。
我已经五十岁了。一个年至半百的老头子竟为这么一篇写给孩子的故事而泪不自禁,其中的原因一定很多,多到我自己也说不清。不过我一下子就想起了我的幼儿园,想起了那惩罚的游戏。我想,这不同的童年消息,最初是从哪儿出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