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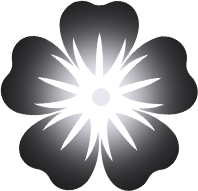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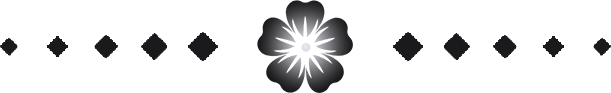
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四八年写作《一九八四》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一九八四》虽在他一九五〇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那么,奥威尔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作家,他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究竟又是怎样的一部作品呢?要解答这个问题,最好是从奥威尔不是什么,或者《一九八四》不是什么说起。这也许对我们正确理解他和他的作品更有帮助。
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一九八三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奥威尔出身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并不宽裕。他父亲供职于印度的英国殖民地政府,作为一个下级官员,无力供养儿子回国进贵族子弟学校上学。奥威尔只是靠成绩优异,才免费进了一所二流的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后来又靠成绩优异考取了奖学金,进了英国最著名的伊顿公学。但是他以一个穷学生的身份,在那里先是受到校长的歧视,稍长后又与那里的贵族子弟格格不入。毕业后他一无上层社会关系,二无家庭经济支援,上不起大学,只好远走缅甸,为帝国警察部队效力,但殖民地下级官员的生活对他来说同样还是格格不入。尽管有这样的背景,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我经受了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加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但是他毕竟受了英国传统的教育,因此从立场上和思想上,多少在开始的时候,是非常非政治性的。例如他写的《缅甸岁月》,背景是殖民地社会,他对英国人和缅甸人都一视同仁,无分轩轾。这使人想起了E·M·福斯特的《印度之行》。福斯特就说过,“大多数印度人,就像大多数英国人一样,都是狗屎。”
这种传统上层子弟教育,用一句庸俗社会学套话来说,在奥威尔身上留下了深深的阶级烙印,这是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Identity)的主要原因。不错,他在学童时代由于家庭经济能力的限制而在势利的圣塞浦里安学校校长的手里饱受凌辱(见他死后出版的《如此欢乐童年》),使他有了心理准备,日后在缅甸见到殖民统治的不公产生反感,而且后来在更大的范围内全身投入地站在受压迫者的一边。但是他毕竟出身中产阶级,而在英国这个阶级界限极为根深蒂固的社会里,要摆脱这个传统在自己身上的束缚是很困难的。奥威尔也不例外,他一直到死都意识到这一点。在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在寄宿学校中的屈辱生活感到极其不愉快。他曾写道,“对一个孩子最残酷的事莫过于把他送到一所富家子弟的学校中去。一个意识到贫穷的孩子由于虚荣而感到痛苦,是成人所不能想象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所受到的心理创伤,在成年的奥威尔身上仍在流血,这在他写的充满不快的回忆的《如此欢乐童年》中可以看出。不止一个评论家认为应该把《如此欢乐童年》与《一九八四》放在一起来读。黎斯就认为,“奥威尔很可能在他当初上的预备学校中找到了他后来所写的大噩梦的第一个显微缩影的胚胎。”奥威尔生前就告诉他的一位友人托斯科·费维尔:“一个不合群的孩子在寄宿学校吃到的苦头可能是英国唯一可以与一个外人在极权主义社会中感到的孤立相比的事。”费维尔在《如此欢乐童年》中观察到了英国寄宿学校生活为《一九八四》提供了一部分声音、景象和气味:“……奥威尔在早年就显露出他对丑陋或敌意的环境特别敏感。这在他描述圣塞浦里安学校生活的令人厌恶一面表现出来。他回忆了他对常常用油腻的盆子端来的馊粥、大浴池里的脏水、硬邦邦的不平的床板、更衣室里的汗臭、到处没有个人隐蔽的地方、不上闩的成排的污秽厕所、厕所门不断开、关的碰撞声、宿舍里用夜壶撒尿的淅沥声这种种印象——他以特有的细腻感觉回忆这一切时,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奥威尔这么描述圣塞浦里安,是作为日后写《一九八四》中惨淡景象试笔的。”
奥威尔背叛自己阶级的努力,在他童年时代寄宿学校中埋下了种子,而在伊顿毕业后因为升不起大学而到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效力,则为这种子的萌芽准备了土壤。他在缅甸呆了五年,这是他成长过程中又一决定性的阶段。他最后决定要脱离帝国警察部队,“我感到我必须洗赎那压得我透不过气来的罪咎……我觉得我不仅仅应该与帝国主义决裂,而且也应该与一切人对人的统治决裂。我希望融合到受压迫的人中间去,成为他们之中的一个,站在他们的一边反对他们的暴君……在这时候,在我看来,没有出息倒是唯一的美德。自我奋斗,哪怕稍有成就,一年能挣上几百镑,我觉得稍有这种想法都是精神丑恶的,是一种欺压行为。”
由于自幼就喜欢写作,因此趁一次回国休假之便,他辞去了在缅甸的帝国警察部队的差使,独自到巴黎找一间廉价的房子,关起门来从事写作。这一时期的摸索并没有为他带来成功,即使他有一个机会,亲身体验一下巴黎(和以后的伦敦)的下层生活。这在开始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是有意识这么做的,比如他在伦敦曾经混在流浪汉里到收容所去度一个周末。奥威尔自己简短地概述了他从缅甸回来后的思想演变:“我尝到过贫困的生活和失败的感觉。这增强了我天生对权威的憎恨,使我第一次充分意识到工人阶级的存在,而在缅甸的工作则使我对帝国主义的性质有了一些认识。但这些经验不足以给我确切的政治方向。”
确实是这样。他尽力接近下层群众,体验他们的生活,但是有一道无形的墙,隔在他与他们之间,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他身上的中产阶级烙印。英国的阶级区分比任何欧洲国家都要等级森严,这种区分看不见,摸不着,然而无处不在,不可逾越。奥威尔由于童年的创伤,对这一弊端极其敏感,对上层阶级有着一种刻骨的仇恨和厌恶。但是他出身于这一阶级的边缘,而且受到这一阶级的教育,因此即使后来在穷困潦倒流浪巴黎和伦敦时期,也使他无法同下层贫苦群众打成一片,虽然他努力这么做了。别的不说,出身和教育养成的说话口音,就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甚至在他病危住院期间,听到隔壁病房探视者的上等阶级口音,还在笔记本中记下他的一段感想:“这是什么口音!一种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沾沾自喜、过分自信的口音,一种深沉、洪亮而带有恶意的口音,你没有看到也可以凭本能感到,他们是一切智慧的思想、细腻的感情、美丽的事物的敌人。怪不得大家都这么憎恨我们。”请注意最后的“我们”一词。奥威尔作了毕生的努力要与自己的阶级决裂,最后还是意识到他属于这个可憎的上层阶级。他曾经说过。“英国人的(阶级)烙印是打在舌头上的。”有一个故事很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他为了体验穷人的生活,曾经伪装酒醉的流浪汉,去辱骂一个警察,想被抓到监狱里去尝一尝与穷人一起过圣诞节的滋味。但是那个警察从他醉酒后的口音,一下就听出了这个身披借来的破烂衣服的醉鬼是一个出身伊顿公学的地道绅士,并没有上钩,而是善意相劝,叫他乖乖地回家去。也许他的侄女的话最能一针见血地说明问题,她对奥威尔的传记作家克立克说:“他的一切疙瘩都来自这个事实:他认为他应该去爱他的同胞,但是他连同他们随便交谈都做不到。”
后来在英格兰北部工业区维冈码头的经验最终树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当时伦敦一家左翼出版社约请他到那里去考察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状况。这次考察和后来的西班牙内战(这在以后再说)用奥威尔自己的话来说,“改变了一切。从此之后,我知道了自己站在哪里。从一九三六年以来,我写的严肃作品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我所了解的那种极权主义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的。”这次为期只有几个星期的工业区考察之行,打开了奥威尔的眼界,使他亲身体验到了社会的不公和人间的苦难达到了什么程度。在这以前,他生活颠沛,对下层社会生活不是没有体会,但这毕竟是个人经历,只有到了英格兰北部工业区后,他的这种体会才有了社会性和阶级性。这种政治上的“顿悟”也许可以用禅宗信徒的大彻大悟来做比喻,也仿佛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听到上帝的启示而皈依基督教——奥威尔的“去维冈码头之路”就是保罗的“大马士革之路”。不过在他身上用这种宗教比喻恐怕是十分不恰当的,尤其是因为奥威尔是一个十足的理性主义者,他对某些社会主义政党的神秘性和盲从性特别反感。做这样的比喻只是说明他的觉悟的即时性、彻底性和不可动摇性而已。
在维冈码头时,奥威尔并没有像一般记者那样仅仅作为一个进行采访的旁观者。《去维冈码头之路》中有一段文字可以扼要说明奥威尔在考察失业者的惨淡生活的旅程中突然面对面看到人间苦难时所得到的闪电般启示:
穿过那尽是钢渣和烟囱,成堆的废铁和发臭的沟渠,靴印交错的泥泞的煤灰小径所构成的丑恶景色,火车把我载走了。时已初春三月,但气候仍极寒冷,到处是发黑的雪堆。我们慢慢地穿过市郊时,一排又一排灰色小破屋在我们面前掠过,它们与堤岸形成直角。在一所房子后面,有一个年轻妇女跪在石块地上,用一条棍子在捅从屋子里接出来的——我想大概是——堵塞了的排水管。我有时间看到她身上的一切:她的麻袋布围裙,她的笨重的木鞋,她的冻红的胳膊。火车经过时,她抬起头来,距离这么近,我几乎看到了她的眼光。她的圆圆的脸十分苍白,这是常见的贫民窟姑娘的憔悴的脸,由于早产、流产和生活操劳,二十五岁的人看上去像四十岁。在我看到的一刹那间,这脸上的表情是我见到的最凄惨绝望的表情。当时这使我想到,我们常说的“他们的感觉同我们的不一样”,还有什么贫民窟里生长的人除了贫民窟不知有别的,这种话是何等的错误。因为我在她脸上看到的表情并不是一头牲口的无知的忍受。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遭遇是什么——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在严寒中跪在贫民窟后院的脏石块上捅一条发臭的排水管,是一种多么不幸的命运。
如果说,维冈之行是偶然的话,去西班牙参加内战则是自觉的行动,他曾向一位编辑友人说:“我要到西班牙去了。”那人问:“为什么?”他答道:“这法西斯主义总得有人去制止它。”他在西班牙作战时间不长,最后以喉部中弹不得不回国治疗和休养。但这短短几个月的战斗,特别是共和政府军方面国际纵队内部派系的猜疑和斗争,不仅没有削弱,倒反而坚定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而且明确了他要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主张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的社会主义,反对一切变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包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即国家社会主义)。当时流行的看法是法西斯主义是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它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而在政府军一边汇集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者中,不乏那种以社会主义为名,实际上为了霸主地位而在敌人的闪电轰炸中,在横飞的子弹中,向自己的同志背后放冷枪的国际阴谋家。一颗法西斯子弹打中了奥威尔的喉部,就在他回国疗伤的途中,还有人一路跟踪到巴塞罗那来追杀。看来这些同一战壕中的同志有兴趣的不是共同保卫共和国抵御法西斯主义敌人,而是消灭有独立思想不跟着指挥棒转的盟友。这伤透了他的心,更加深了他对极权主义的痛恨,不论这种极权主义是以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的。这条道路尽管曲折,却终于使奥威尔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能够写出《一九八四》那样一部二十世纪政治寓言的经典。
从文学写作方法上来讲,奥威尔找到“自性”也是经过了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他从缅甸回来后立志于写作,为此,还有意识地到巴黎和伦敦体验下层生活,但这一时期写的作品并不成功,只有亨利·米勒认为他的初期作品《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因为他经过几年锲而不舍和看来是无望的努力,终于形成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是在黎斯看来,他没有把自己的声音和观点在全书中贯彻始终,这是美中不足。不过瑕不掩瑜,正是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找到了一种新的写作形式,这就是把新闻写作发展成一种艺术,在极其精确和客观的事实报道的外衣下,对现实作了艺术的复原和再现。最后他在《去维冈码头之路》和《向卡塔隆尼亚致敬》两本书以及像《射象》和《绞刑》这样好几篇记述文中,把这种写作新形式提高到了完美的境界。四分之一世纪之后,诺曼·梅勒和杜鲁门·卡波蒂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和笔墨,互相反驳对方自称为“非虚构小说”的鼻祖。他们大概没有读过奥威尔早在他们出道之前在这方面所作的尝试,否则他们就不会闹得如此不可开交了,相反会对自己的大言不惭,感到无地自容。
不过在这以前,奥威尔并没有意识到他是在为日后称作“新新闻写作方法”(New Journalism)这一文学形式开先河。就像他在政治上迟迟没有找到“自性”一样,他在文学上也迟迟没有找到“自性”,或者说,即使像米勒评估的那样,他在《在巴黎和伦敦穷困潦倒的日子》里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声音和观点,但这还不是自觉的和有意识的。证诸他后来接着出版的四部习作《缅甸岁月》、《教士的女儿》、《让盾形花继续飞扬》以及《上来透口气》都是用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写的,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四部作品都是平庸之作,换了别个作家,早该被人遗忘了。但是由于它们是奥威尔写的,在他成名之后,还是有人——至少是评论家——把它们找出来一读,倒不是因为它们的文学价值,而是为了读它们对了解奥威尔的思想和个性发展有所帮助。上面已经提到,奥威尔在《去维冈码头之路》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作品中找到了他艺术上的“自性”,但这是与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分不开的,反过来也可以说,只有他在政治上找到了“自性”以后,他在文学上才找到了“自性”,这最终表现在他的两部政治讽刺和寓言作品《动物农场》和《一九八四》上。可惜天不假年,在贫困中奋斗了一辈子的他,没有能看到自己的成功和享受成功为自己带来的喜悦。然而《一九八四》这部表现二十世纪政治恐怖的极权主义的作品是不会随着极权主义的兴衰而湮没于人类历史中的。
正如汉娜·阿伦特和卡尔·弗雷德里克及布热津斯基早在五十年代分别在前者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后两者的《极权主义、独裁和专制》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极权主义乃是现代专制主义。它从本质上来说与古代或中世纪的专制主义毫无二致,但与这些传统的专制主义不同的,或者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地方是,极权主义掌握了现代政治的统治手段,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生活、舆论工具、艺术创作、历史编纂甚至个人思想和隐私,无不在一个有形和无形的“老大哥”的全面严密控制之下(极权主义的英文“Totalitarianism”意即指此,因此也可译“全面权力主义”),这是中外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所做不到的,更是他们连想也想不到的。作为二十世纪的过来人,我们无需根据个人的经历和体会,一一印证《一九八四》中所做的预言与二十世纪的现实何等相似,但我们不得不惊叹奥威尔的政治洞察力和艺术想象力是何等高超:他没有在任何极权主义国家生活过,他的观察怎么比过来人还要细腻、深刻和真确?是的,他没有这方面实际生活的经验,但是他在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大大超过了当时去参拜过新麦加,被牵了鼻子参观“波将金村庄”,归来后大唱看到了新世界曙光的赞歌的许多国际闻名的大文豪。
奥威尔创作《一九八四》的灵感不是来源于此,而是他参加西班牙内战与其他变种的社会主义者接触,遭到猜疑和排斥,后来回到英国想说一些关于他所见所闻的真话而遭到封杀的经验。他遭到了一道沉默和诽谤的双重厚墙的包围,其他幸存者和目击者也都同样被封上了口,以致摇旗呐喊的应声虫们能够放手改写历史而无人置疑。这样,他直接第一次面对面地接触到极权主义如何制造谎言和改写历史,这被入木三分地反映在温斯顿·史密斯在“真理部”的工作上。这也令人想起了哈罗德·艾萨克在一张照片中他的身影曾被抹去这件事以及更早的他在巴黎、伦敦、纽约各大公立图书馆中遍找文献,就是找不到他要的关于“把蒋介石这一柠檬挤干了扔掉”这一著名发言。在原来发表的报刊上,这一发言都被人撕毁灭迹了。改写和忘却历史的网竟编织得这么无孔不入,只有极权主义才能做到。难怪奥威尔对写过《中午的黑暗》的阿瑟·库斯特勒说:“历史在一九三六年停步了。”库斯特勒颇有同感,连连点头称是。
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奥威尔是一九四八年写完这部政治恐怖寓言小说的,为了表示这种可怕前景的迫在眉睫,他把“四八”颠倒了一下成了“八四”,便有了《一九八四》这一书名。事过境迁,也许这个年份幸而没有言中,但是书中所揭示的极权主义种种恐怖在世界上好几个地方在一九八四年以前就在肆虐了,今天在世界范围内也不能说已经绝迹。二十世纪是个政治恐怖的世纪。二十世纪快要结束了,但政治恐怖仍然阴魂不散,因此《一九八四》在今天仍有价值。是否可以说,对我们来说,只有彻底否定了诸如“文化大革命”这类恐怖的极权主义,才给我们这些多年为社会主义奋斗的人,带来了真正值得向往的社会主义!
董乐山
一九九七年七月酷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