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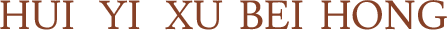

自从徐悲鸿先生逝世以后,国内外有多少他的艺术知音,他遍天下的桃李,他的亲人、朋友,莫不在缅怀着这位代表一个历史时期的杰出画家。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以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来力挽已经积羸将有两三个世纪,陈陈相因、停滞不前的中国绘画。有许多人写过许多文章来纪念他,特别是阐述他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进程中的几个关键时刻,坚持主张以客观生活为艺术创造依据的现实主义。我们经常想起20世纪20年代他同上海颓废派的文人以及20世纪40年代他同北平国民党反动派利用的保守派所进行的有关艺术的论战。这一切都说明了徐悲鸿先生对有悠久历史的中国美术传统的继承,和吸收外来艺术的优点,从而为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开辟了前景,并为繁荣社会主义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中国人民纪念他,他将在中国社会主义艺术的发展上长期起着应有的作用。
这30年来,我和许多其他同志一样写过一些文章来回忆徐悲鸿先生;最近我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化史料》第五辑发表了《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这里我再补充对徐先生的回忆,把我所知道的徐先生的事迹,按照徐先生的性格,力求避免华丽辞藻,如实地记录下来。
徐先生和田汉先生为了艺术革新运动——这是一个带有进步意义的艺术革新运动,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而走到一起来了。在上海,当二三十年代间,有的人打着形形色色的自命“维新”的艺术旗号,在美术方面也有人将西方各种现代流派同思想上的先进混为一谈。但是徐、田两先生则主张艺术要以形式完美为手段,用以达到表达思想的先进为目的。正由于这个艺术观的一致,他们建立了共同奋斗的基地——南国艺术学院。当时所谓“南国精神”,不论在文学上,在戏剧上,在美术上,正如田汉先生所说过的:“……我们在求美、求善之前,先得求真……”1928年春,当南国艺术学院成立不久,美术系被反动势力所砸毁时,他们两人曾有过一次长谈,我相信他们之间,已就各自的艺术观和在艺术活动相互支持上有了默契,这是为此后的一些事实所证实了的。(见拙作《回忆南国社时期的徐悲鸿和田汉》一文)我自己在1930年春去巴黎,对国内的情况了解甚少。1935年我回到南京时,徐先生首先告诉我田汉先生出狱的消息,并要我快去探望刚由他和宗白华先生(当年的南京中央大学哲学教授,现在北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保释出狱的田汉先生。这些细节都见上述《文化史料》第五辑,和1982年出版的廖静文著的《徐悲鸿一生》一书。我深感徐、田两位先辈的情谊是极其深厚的,因为当时在白色恐怖时期,以身家担保的事,即使骨肉之亲尚难免趋避。1953年9月,徐先生刚在北京医院辞世之顷,在侧的几位老友中田先生沉恸独切,这是不无缘由的。徐悲鸿先生从来没有对田汉先生这位诤友在1930年所写的《我们的自己批判》(见1932年《南国月刊》第2卷第1期)中对他的求全责备,流露过一点微词。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地点,处在“左”的压力普遍存在的时期(见《戏剧论丛》1981年第4期第4页陈白尘《中国剧坛的骄傲》一文)。此后南京的营救,武汉的支援,桂林的重逢,尤其是北平解放前夕,田先生冒险密晤徐先生以完成中央交付之重托,亦都足以印证(详见《文化史料》第五辑)。
徐悲鸿先生待人直爽真诚,不以小不舍而弃大义。1948年的年终前后,解放军已指出北平的前途和国民党的去从,问题就看傅作义将军最后的抉择。傅在一次邀宴北平学者名流数十人的席后茶余,向大家提出关于北平“战”、“和”的问题。这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因为当时傅将军还举棋未定,意向未明,而蒋介石还在叫嚣反共到底,在这种情势下说话的人是要担风险的。当时谁也不敢发言,经过长时期的冷场后,徐先生首先发言,他说:“时至今日,傅将军还有什么值得对蒋先生抱幻想的!?……(大意)”徐先生发言之后,在座的才相继纷纷表态,赞成和平解决北平问题。这件事是徐先生参加傅宴后回来,亲自给我讲的,我为之深感欢欣。同时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当徐先生和田先生会晤之后,徐先生坚决保护学校,不使学校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还表达了拒绝南迁的鲜明立场。这是由于党的指示和关怀,使徐先生产生了无限的勇气和力量。
在艺术教育上,徐先生主张对学生要进行严格的基础训练。他要求尊重客观事物,要以一丝不苟的诚实态度来认识客观存在,并加以提炼和提高。他认为要加强造型的表现力,就要删去烦琐的细节,强调塑造形象的统一性。他还认为学生从开始学画,就应当力求刻意勾画;宁方毋圆,宁拙毋巧,要以直线求曲线,以平面求圆面,基本功要做到眼、手、心相协调,“尽精微”以“致广大”。
我由于得到徐先生的支持和鼓励才能赴法学习。到了巴黎,当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找到工作(用以维持生活和参加学习);又由于徐先生预先的安排,有不少在巴黎的老朋友热情地来照顾我,其中有一位名叫张宗禹的,1928年我们曾共同在中央大学徐先生开的夜课旁听过,他收到徐先生的信得知我将到达巴黎,曾给了我许多帮助。我考取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校西蒙教授班,入学时的学费和其他费用,都是由张宗禹先生替我向他人借贷的。我在巴黎生活拮据的日子里,李有行先生曾帮助我找零活干,他和徐先生也属师友之交。除此之外,徐先生还函托了在比利时任公使的谢寿康先生给我关照,由于他的协助,我又考进了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并获得了助学金,从此我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保证了正常的学习。
我还记得徐先生在给我们这些国外学美术的学生的信件中,时常提醒我们要坚持现实主义的治学态度,要向西方美术盛世时期的优秀传统学习,不要被那些资本家豢养的大小画商的巧言令色所迷惑而走上歧途,从而回国后无以交代。
我在法国和比利时所接触到的前辈画家,许多人都知道徐先生的卓越的艺术造诣。他在欧洲所举办的宣传中国艺术的中国画展览会(1932—1933),曾引起当时欧洲的文化界对中国现代绘画的浓烈兴趣。在这些中国现代画家中突出的并为西方各界人士所重视的就是齐白石先生的作品。我回想起在1929年春天,徐先生曾到北平住了两三个月,当时他发觉北平艺术学院的国画教学基本上是掌握在保守派的手里,而他素来主张对陈陈相因,泥古不化的所谓“传统”,要进行改革。他的大胆吸收新的以写生为基础训练的主要教学方向,是不见容于当年画必称“四王”
 ,学必循《芥子园》
,学必循《芥子园》
 的北平艺术学院的。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姚芒父等人,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束装南回了。徐先生在北上之前,为了不让我们的学业由于无人主持而被耽误,就先向我们说:“我这次去北平时间不会长的,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回来。在我走后,你们的功课由上海的张聿光先生和苏州的颜文梁先生暂代,你们要尊敬和听从这两位先生的指教,要特别努力学习,要和我在时一样。”
的北平艺术学院的。尽管还有少数有新意的画家如陈衡恪、姚芒父等人,但他预见到他在北平是孤掌难鸣的。他在北平住了不到三个月就束装南回了。徐先生在北上之前,为了不让我们的学业由于无人主持而被耽误,就先向我们说:“我这次去北平时间不会长的,是去看看,也许不久就回来。在我走后,你们的功课由上海的张聿光先生和苏州的颜文梁先生暂代,你们要尊敬和听从这两位先生的指教,要特别努力学习,要和我在时一样。”
我们做学生的,对徐先生的离去都有依依之情,对张、颜两位先生,持以尊师重道之礼。张、颜两位老师是先后来中大代课的。张先生,在model休息的时候,爱和我们聊天,讲些上海早期美术教育界活动的故事,从中我知道了一些民国初年上海美术界几位先驱者(到现在几乎被人遗忘了的)是如何艰苦经营美术教育的情况。颜先生则总是鼓励我们说大家画得很好……张先生在早些年已经逝世了,颜先生今年91岁,去年中国美协还特派代表到上海给他祝90岁大寿。
当时大家都有共同的疑问,就是徐先生北上时,说“不久就回来”,是真的还是安慰我们的?我只感到时间过得太慢。可竟然,我们翘首北望的徐先生终于回到班上了。由于平时老师对学生的鼓励,学生对老师爱戴,使全班顿时又热烈起来了。大家围绕着徐先生,想听听他北上的情况。徐先生素来是不喜欢说场面话的,开头就说他这次去北平,最大的收获是结识了几位很有艺术才能的画家,他们有坚实的绘画基础,也富有创新的精神,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多才多艺的齐白石先生。
他赞扬齐白石先生在艺术上多方面的成就,他认为齐白石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艺术上的独创性。与此同时,徐先生还带来了齐老的画给我们看。说实在的,我那时才学了不到一年的基础素描,要懂得齐老作品的高明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我来说,这一件意外的事(直到我在十几年后去敦煌莫高窟巡礼临摹,给了我对中国画传统以惊雷似的冲击之前)竟成为我认识和热爱中国绘画的一节“序曲”。
1933年徐先生在西欧各国、苏联举办中国画展,都着重介绍齐白石的作品,从此以后,齐白石终于从被北平的保守派长期鄙视而成为举世闻名的中国当代画坛巨匠。徐先生生前二十多年来始终不渝地关怀齐白石先生和介绍他的作品,协助处理齐白石的生活。1953年9月徐先生不幸逝世,我们都不敢向齐老提起这件事,以免使他受到震动和引起悲恸。那时齐老已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开始的一些时候,他还常问起:“徐先生怎么不来看我?”左右的人都告诉他徐先生因为有事,出门去了,时间一久了,老人也有点将信将疑,过些时,他也不再问了。老人心里是无时不在怀念着徐先生。有一次,那是离老人去世(1957年)不久前,我去他家探望,他一反平日沉默寡言的习惯,忽然对我说:“我一生最知己的朋友,就是徐悲鸿先生!”我们没有说更多的话,但感到黯然神伤,相对无言。
徐先生的感情——对朋友的关怀,对受委屈的人的同情,对因敌寇铁蹄蹂躏而流离失所的千百万同胞的悬念,无时不在他的诗、画、文章、通信中流露着。1938年,他热情满怀义愤填膺地投身到在周总理领导下、郭老主持下的武汉军委政治部三厅的抗战工作。当时田汉是艺术处处长,他们重逢之后,同心同德,一致抗敌。可是当他同政治部主任陈诚晤见时,陈对徐先生反蒋的宿怨未消,给徐先生以冷遇,徐先生拂袖而去。到了重庆,徐先生对我说:“难道我是为了想当一官半职去武汉的?我是要使我的艺术为抗战服务!不过,田先生那儿需要搞美术的青年,可以……”我接着说,我们正想组织几个年轻人去台儿庄战地作画。他说:“这很好,你们早点出发,你们可以到武昌昙华林政治部三厅去找艺术处的田先生,他会给你们帮助的。我已经决定带着自己的作品去南洋办画展,将全部售画款捐献给国内因日寇入侵而流亡的难民。”
我们和徐先生分头奔向各自的目标。徐先生在新州、槟城一带办画展期间,屡次给我写信,对我当时家破人亡的遭遇寄予父兄般的慰勉和同情。与此同时,徐先生自己也经历着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严酷的现实生活。他的思想发展,是从正义感走向痛感社会改革的必要,又进而逐渐认识到共产党人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吾人虽非共产党人,但他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实足钦佩……(大意)”记得这封信是从新加坡寄给我的,时间是在1940年至1941年之间。他的谆谆教导(加上老同学郑君里的规劝),使我在将近一年的目疾痊愈之后,增添了勇气和信心,又背起画箱,提起画笔,由重庆出发,时而去成都、青城,时而去兰州、青海、敦煌等地作画。当我辗转回到重庆时,已是抗战胜利的那一个新年(1945年)。在没有严冬的重庆,我假重庆江苏同乡会举办了三天个人回顾展,展品内容包括近期的西北边地写生创作和30年代初期我在学生时期的大部分作品。这次画展只有三天,其时徐先生因肾脏病卧床数月,新愈身体还衰弱,仍不顾病体不胜疲惫,坚持进城来看我的画展。他虽然清癯,但神采还很好,认真地看了展室所有的画。我劝他不要太累了,他对我说:“这几年你没有把时间浪费了,我虽然病刚好,还是第一次进城,但我决定回去后写一篇短文来介绍这个画展,望你继续努力!”他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使我实在太受感动了。
1940年我的目疾经过诊断是由于过度消耗体力,体质下降,引起视网膜发炎。按医护的要求,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戴黑眼罩,让病目得到休息,而且还要坚持内服药物。这时我虽然不能作画,但住在附近的几位青年画家(其中以李宗津最热情),每天晚上,在城里我新居的一间大屋子里画速写、素描,还和我共研艺术,他们对我的情谊、关心和鼓励,使我难于忘怀。我也是决不向命运屈服的。在那些年月,内忧外患,我们这些艺术青年之间,憎恶、爱好几乎是共同的,都是胸怀坦率,各无城府,彼此间十分融洽。可是好景不长,刚过半年,敌人的空袭把我的住处夷为瓦砾,然而我们之间的友情是炸不毁的!之后,我们各自西东,我去西北,在兰州我和董希文又相逢了。这几年中,我们还常在艺术实践方面互相商榷。1946年初,我从重庆回到上海,首先去看先期到上海的张光宇和小丁(丁聪),在他们的《清明》编辑室里,我们筹划组织上海美术作家协会,用以团结在上海沦陷时期没有“下水”的进步画家,并乘刚复员时期国民党反动势力所策划的“上海美术会”尚未成立之前,举办一个联合美展,把炮打在反动派的前头。这次美展轰动了上海社会。李宗津正赶上参加我们在4月间举办的上海美展。他告诉我他刚从南京来,在南京见到了徐悲鸿先生,徐先生要他打听我回到上海没有,徐先生有事要找我。两三天后,李宗津又回南京去了。6月间,李宗津再次来上海时,带来了徐先生给我的一封手书,并说要注意这封信。我捧读徐先生这封让我回到教学工作的言简意切的信,开始尚有点犹豫。因为在西北诸省的几年中,我觉得过去教书,隘于一隅之地,一旦走出来,眼界放大了,看到了新的生活。当初我和司徒乔(我们对艺术的态度比较一致)先同在西北,后来又同在成都,曾经相约今后再不要当教师。其实在那些年代里,学画必然的出路,就是教书,以为职业画家如何理想,其实也不过是理想而已。(司徒乔在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回来,也和我一样当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我终于为徐先生6月的短笺所触动。这是徐先生的一封对于进步艺术思想、进步艺术教育表态的信,虽然这封信已在1947年2月我于紧急的情况下离开北平去英国的前夕付丙,但我当时曾反复读过几遍,至今虽相隔36年,依然能回忆信中的词句:
作人吾弟:
吾已应教育部之聘,即将前往北平接办(日伪的)北平艺专。余决意将该校办成一所左的学校,并已约叶浅予、庞薰琴、李桦诸先生来校任教。至于教务主任一职,非弟莫属。务希允就,千祈勿却。至盼!
(签名)
我曾一再地想,徐先生的艺术思想已明确地站在进步艺术的一边了,他提名的这几位先生,都是当时就已知名的进步画家,他决意要办一所左的学校,我决不能为了自己的“理想”,忍负徐先生更有远虑的“理想”。第二天我就写了复信,托即将回南京的李宗津面呈徐先生,表示受命北上共襄此举。
1946年7月末,徐先生约同在大后方所拟聘的一些青年画家,经上海取海道北上,到达北平已是8月初了。这时先期到北平的国民党反动力量早已安排好控制北平艺专的阵势(控制训导处和设立三青团),就看以徐大师为首的“离经叛道”的艺术家是否能在他们手掌心中就范,而徐先生要实现他的理想,就必须在自己的阵地上取得优势。为此,他采取以下的措施:首先在原有敌伪时期的学生中,凡学业优良的,因思想进步而被训导处除名的,一律恢复其学籍;再则将原有的教员中,凡落水失节者,一律停聘。在这些问题上徐先生立场是鲜明而坚定的,有一些人反复托情关说,徐先生拒之再三;无奈时,也观其才学批准两三名不占名额的兼任教员。当时有某“教授”,在法国留过学,术业无成,但他却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组织的成员,恃有靠山,多次找徐先生,强词夺理非要当一席教授。徐先生坚持不同意,他竟上告到南京。可是徐先生没有被他吓倒,说这位既无才又无学,靠反动特务组织吃饭的“党棍子”,我们决不能拿教授做“人情”。此人终未得逞。
当我们刚到北平时,就了解到反动派正在策划成立一个“北平美术会”。于是我们又按照在上海的经验,即时成立了“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也和上海一样,是同反动派针锋相对的。我们将计划向徐先生谈了,他立即同意,并答应任名誉会长。协会在组成后借人家的报纸办了自己的期刊。徐先生挥如椽之笔,草拟“论战”文稿。“协会”举办的画展,也得到徐先生的支持。到了解放前夕,“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内部成员,起了泾渭之分,我们就在1948年12月7日,另外组织了“一二七艺术学会”(这是部分进步成员组织成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音乐、舞蹈等方面),在徐先生的直接领导下迎接北平解放。解放初期我们还以这个学会的名义在当时的《进步日报》上,继续办了一年副刊——《进步艺术》。
当我们进入北平艺专之初,训导处那一伙就已感到徐悲鸿先生是不容易推倒的。1946年12月,训导处那一伙人借助学金分配问题,鼓动三青团的打手掀起“倒吴作人”风潮。一个早晨,在校园内,贴满轰我下台的标语,我走进教务处办公室,想了一下,觉得非立刻反攻不可,我即“单枪匹马”地到训导处,并单刀直入地质问训导主任:“这次风潮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指使的?意欲何为?”我还责成其立即叫为首闹事的学生到教务处见我,并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发生这样的事”。他们没有料到我出其不意地反攻,只是唯唯诺诺。我说完就走了。当三青团学生中的两个骨干来到教务处时,我晓以国家发给助学金的意义,并斥责其不法行为,要他们保证以后不再干这一类事。他们悻悻而退,很快就把校园内的标语冲刷干净。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后来训导处的国民党极端反动分子,勾结一些人联名诬告徐悲鸿任用以吴作人为首的“民盟危险分子集团”,并扬言要撤职查办(当时民盟是在被取缔之列,我当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恰在1947年初,英国文化委员会邀请我到英国做为期三个月的考察访问,我即征求徐先生的意见。鉴于当时的斗争十分激烈,他为了保护我,毅然劝我出国访问,他说:“你出国一下,可以姑避其锋,我在这里比你安全些。李宗仁是我当年的老友,傅作义也和我熟识,那些人是不敢随意动我的,过去蒋介石不敢杀害蔡元培,而杀害了杨杏佛。你去吧!你到英国之后再转回来。我有三件事托你替学校办一下:一、在国外给艺专图书馆买一些美术图书及画册;二、邀请在巴黎久居的滑田友回国任教;三、到鲁弗尔宫临摹德拉克洛瓦的名画《但丁游地府》。”徐先生又说:“在你回国路过香港时,专程访问一下我的朋友中华书局舒新城先生,把我寄存在那里的《八十七神仙卷》带回来。”
我于1947年2月离开北平,前往英国,后又转往西欧各地举办画展。徐先生在我出国前所委托的几件事,除因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博物馆正开始整理,一些名画尚未展出,因之临摹优秀名画一事未能如愿外,其他我都照徐先生所交代的完成了。
1948年1月,我又辗转地回到了艺专。徐先生扼要地讲述了过去一年里在北平艺专所发生的许多事,包括艺术思想方面的斗争,政治方面的斗争。他巍然屹立,顶住反动派的攻击、诬告,并揭露他们的阴谋,他据理力争,保护了被反动派迫害的师生。继上一年的“国画论战”之后,徐先生亲自主持了一次规模宏大的“美术联合展览会”,这就是由北平美术作家协会、中国美术学院、北平艺专等三个单位联合举办的画展。这次画展轰动了北平社会。徐先生还收集了反动派的黑文字罪证,累牍盈尺,解放后呈交给来接管艺专的军管会代表——闻名的诗人艾青。党对徐先生在北平与反动派短兵相接的斗争是很了解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关怀下,我国艺术事业得到蓬勃的发展。党和人民非常敬重像徐悲鸿先生这样有极高的艺术造诣,对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事业有不可磨灭的建树,一贯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坚决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的艺术家。特别在反动派威逼利诱下,他冷然对之以浩然正气,不为所动,而在革命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忠心耿耿,挺身而出,怀念及此,令人肃然起敬。
1953年,在第二次文代大会期间,他坚持担当大会执行主席的任务,又参加外事活动,以他多病之身,终以脑溢血不治逝世!他终年刚58岁。正当艺术上、思想上成熟有为的时刻,竟不幸离开了我们!三十年来(经过许多社会变动之后),人民没有忘记他,他给人民留下了艺术硕果。在艺术教育方面的重大收获是满天下的桃李,他们在继承着他可贵的艺术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