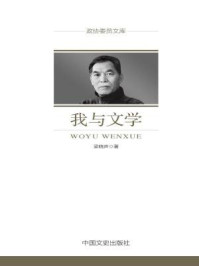这是一个“万里长梦”。梦境历历如真,醒来还如在梦中。但梦毕竟是梦,彻头彻尾完全是梦。
已经是晚饭以后,他们父女两个玩得正酣。锺书怪可怜地大声求救:“娘,娘,阿圆欺我!”
阿圆理直气壮地喊:“Mummy娘!爸爸做坏事!当场拿获!”(我们每个人都有许多称呼,随口叫。)
“做坏事”就是在她屋里捣乱。
我走进阿圆卧房一看究竟。只见她床头枕上垒着高高一叠大辞典,上面放一只四脚朝天的小板凳,凳脚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双沾满尘土的皮鞋——显然是阿圆回家后刚脱下的,一只鞋里塞一个笔筒,里面有阿圆的毛笔、画笔、铅笔、圆珠笔等,另一只鞋里塞一个扫床的笤帚把。沿着枕头是阿圆带回家的大书包。接下是横放着的一本一本大小各式的书,后面拖着我给阿圆的长把“鞋拔”,大概算是尾巴。阿圆站在床和书桌间的夹道里,把爸爸拦在书桌和钢琴之间。阿圆得意地说:“当场拿获!!”
锺书把自己缩得不能再小,紧闭着眼睛说:“我不在这里!”他笑得都站不直了。我隔着他的肚皮,也能看到他肚子里翻滚的笑浪。
阿圆说:“有这种alibi吗?”(注:alibi,不在犯罪现场的证据。)
我忍不住也笑了。三个人都在笑。客厅里电话铃响了几声,我们才听到。
接电话照例是我的事(写回信是锺书的事)。我赶忙去接。没听清是谁打来的,只听到对方找钱锺书去开会。我忙说:“钱锺书还病着呢,我是他的老伴儿,我代他请假吧。”对方不理,只命令说:“明天报到,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有车来接。”
我忙说:“请问在什么地点报到?我可以让司机同志来代他请假。”
对方说:“地点在山上,司机找不到。明天上午九点有车来接。不带包,不带笔记本。上午九点。”电话就挂断了。
锺书和阿圆都已听到我的对答。锺书早一溜烟过来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阿圆也跟出来,挨着爸爸,坐在沙发的扶手上。她学得几句安慰小孩子的顺口溜,每逢爸爸“因病请假”,小儿赖学似的心虚害怕,就用来安慰爸爸:“提勒提勒耳朵,胡噜胡噜毛,我们的爸爸吓不着。”(“爸爸”原作“孩子”。)
我讲明了电话那边传来的话,很抱歉没敢问明开什么会。按说,锺书是八十四岁的老人了,又是大病之后,而且他也不担任什么需他开会的职务。我对锺书说:“明天车来,我代你去报到。”
锺书并不怪我不问问明白。他一声不响地起身到卧房去,自己开了衣柜的门,取出他出门穿的衣服,挂在衣架上,还挑了一条干净手绢,放在衣袋里。他是准备亲自去报到,不需我代表——他也许知道我不能代表。
我和阿圆还只顾捉摸开什么会。锺书没精打采地干完他的晚事(洗洗换换),乖乖地睡了。他向例早睡早起,我晚睡晚起,阿圆晚睡早起。
第二天早上,阿圆老早做了自己的早饭,吃完就到学校上课去。我们两人的早饭总是锺书做的。他烧开了水,泡上浓香的红茶,热了牛奶(我们吃牛奶红茶),煮好老嫩合适的鸡蛋,用烤面包机烤好面包,从冰箱里拿出黄油、果酱等放在桌上。我起床和他一起吃早饭。然后我收拾饭桌,刷锅洗碗,等他穿着整齐,就一同下楼散散步,等候汽车来接。
将近九点,我们同站在楼门口等待。开来一辆大黑汽车,车里出来一个穿制服的司机。他问明钱锺书的身份,就开了车门,让他上车。随即关上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我站在楼门口,眼看着那辆车稳稳地开走了。我不识汽车是什么牌子,也没注意车牌的号码。
我一个人上楼回家。自从去春锺书大病,我陪住医院护理,等到他病愈回家,我脚软头晕,成了风吹能倒的人。近期我才硬朗起来,能独立行走,不再需扶墙摸壁。但是我常常觉得年纪不饶人,我已力不从心。
我家的阿姨是钟点工。她在我家已做了十多年,因家境渐渐宽裕,她辞去别人家的工作,单做我一家。我信任她,把铁门的钥匙也分一个给她拴在腰里。我们住医院,阿圆到学校上课,家里没人,她照样来我家工作。她看情况,间日来或每日来,我都随她。这天她来干完活儿就走了。我焖了饭,捂在暖窝里;切好菜,等锺书回来了下锅炒;汤也炖好了,捂着。
等待是很烦心的。我叫自己别等,且埋头做我的工作。可是,说不等,却是急切的等,书也看不进,一个人在家团团转。快两点了,锺书还没回来。我舀了半碗汤,泡两勺饭,胡乱吃下,躺着胡思乱想。想着想着,忽然动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我怎么能让锺书坐上一辆不知来路的汽车,开往不知哪里去呢?
阿圆老晚才回家。我没吃晚饭,也忘了做。阿姨买来大块嫩牛肉,阿圆会烤,我不会。我想用小火炖一锅好汤,做个罗宋汤,他们两个都爱吃。可是我直在焦虑,什么都忘了,只等阿圆回来为我解惑。
我自己饭量小,又没胃口,锺书老来食量也小,阿圆不在家的日子,我们做晚饭只图省事,吃得很简便。阿圆在家吃晚饭,我只稍稍增加些分量。她劳累一天,回家备课、改卷子,总忙到夜深,常说:“妈妈,我饿饭。”我心里抱歉,记着为她做丰盛的晚饭。可是这一年来,我病病歪歪,全靠阿圆费尽心思,也颇费工夫,为我们两个做好吃的菜,哄我们多吃两口。她常说:“我读食谱,好比我查字典,一个字查三种字典,一个菜看三种食谱。”她已学到不少本领。她买了一只简单的烤箱,又买一只不简单的,精心为我们烤制各式鲜嫩的肉类,然后可怜巴巴地看我们是否欣赏。我勉强吃了,味道确实很好,只是我病中没有胃口(锺书病后可能和我一样)。我怕她失望,总说:“好吃!”她待信不信地感激说:“娘,谢谢你。”或者看到爸爸吃,也说:“爸爸,谢谢你。”我们都笑她傻。她是为了我们的营养。我们吃得勉强,她也没趣,往往剩下很多她也没心思吃。
我这一整天只顾折腾自己,连晚饭都没做。准备午饭用的一点蔬菜、几片平菇、几片薄薄的里脊是不经饱的。那小锅的饭已经让我吃掉半碗了,阿圆又得饿饭。而且她还得为妈妈讲许多道理,叫妈妈别胡思乱想,自惊自扰。
她说:“山上开会说不定要三天。”
“住哪儿呢?毛巾、牙刷都没带。”
她说:“招待的地方都会有的。”还打趣说:“妈妈要报派出所吗?”
我真想报派出所,可是怎么报呢?
阿圆给我愁得也没好生吃晚饭。她明天不必到学校去,可是她有改不完的卷子,备不完的功课。晚上我假装睡了,至少让阿圆能安静工作。好在明天有她在身边,我心上有依傍。可是我一夜没睡。
早起我们俩同做早饭,早饭后她叫我出去散步。我一个人不愿意散步。她洗碗,我烧开水,灌满一个个暖瓶。这向例是锺书的事。我定不下心,只顾发呆,满屋子乱转。电话铃响我也没听到。
电话是阿圆接的。她高兴地喊:“爸爸!!”
我赶紧过来站在旁边。
她说:“嗯……嗯……嗯……嗯……嗯。”都是“嗯”。然后挂上电话。
我着急地问:“怎么说?”
她只对我摆手,忙忙地抢过一片纸,在上面忙忙地写,来不及地写,写的字像天书。
她说:“爸爸有了!我办事去。”她两个手指点着太阳穴说:“别让我混忘了,回来再讲。”
她忙忙地挂着个皮包出门,临走说:“娘,放心。也许我赶不及回来吃饭,别等我,你先吃。”
幸亏是阿圆接的电话,她能记。我使劲儿叫自己放心,只是放不下。我不再胡思乱想,只一门心思等阿圆回来,干脆丢开工作,专心做一顿好饭。
我退休前曾对他们许过愿。我说:“等我退休了,我补课,我还债,给你们一顿一顿烧好吃的菜。”我大半辈子只在抱歉,觉得自己对家务事潦草塞责,没有尽心尽力。他们两个都笑说:“算了吧!”阿圆不客气说,“妈妈的刀工就不行,见了快刀子先害怕,又性急,不耐烦等火候。”锺书说:“为什么就该你做菜呢?你退了,能休吗?”
说实话,我做的菜他们从未嫌过,只要是我做的,他们总叫好。这回,我且一心一意做一顿好饭,叫他们出乎意外。一面又想,我准把什么都烧坏了,或许我做得好,他们都不能准时回来。因为——因为事情往往是别扭的,总和希望或想象的不一致。
我的饭做得真不错,不该做得那么好。我当然失望得很,也着急得很。阿圆叫我别等她,我怎能不等呢。我直等到将近下午四点阿圆才回家,只她一人。她回家脱下皮鞋,换上拖鞋,显然走了不少路,很累了,自己倒杯水喝。我的心直往下沉。
阿圆却很得意地说:“总算给我找着了!地址没错,倒了两次车,一找就找到。可是我排了两个冤枉队,一个队还很长,真冤枉。挨到我,窗口里的那人说:‘你不在这里排,后面。’他就不理我了。‘后面’在哪里呢?我照着爸爸说的地方四面问人,都说不知道。我怕过了办公时间找不到人,忽见后面有一间小屋,里面有个人站在窗口,正要关窗。我抢上去问他:‘古驿道在哪儿?’他说:‘就这儿。’唷!我松了好大一口气。我怕记忘了,再哪儿找去。”
“古驿道?”我皱着眉头摸不着头脑。
“是啊,妈妈,我从头讲给你听。爸爸是报到以后抢时间打来的电话,说是他们都得到什么大会堂去开会,交通工具各式各样,有飞机,有火车,有小汽车,有长途汽车,等等,机票、车票都抢空了,爸爸说,他们要抢早到会,坐在头排,让他们抢去吧,他随便。他选了没人要的一条水道,坐船。爸爸一字一字交待得很清楚,说是‘古驿道’。那个办事处窗口的人说:‘这会儿下班了,下午来吧。’其实离下班还不到五分钟呢,他说下午二时办公。我不敢走远,近处也没有买吃的地方。我就在窗根儿底下找个地方坐等,直等到两点十七八分,那人才打开窗口,看见我在原地等着,倒也有点抱歉。他说:‘你是家属吗?家属只限至亲。’所以家属只你我两个。他给了那边客栈的地址,让咱们到那边去办手续。怎么办,他都细细告诉我了。”
阿圆说:“今天来不及到那边去办手续了,肯定又下班了。妈妈,你急也没用,咱们只好等明天了。”
我热了些肉汤让阿圆先点点饥,自己也喝了两口。我问:“‘那边’在哪儿?”
阿圆说:“我记着呢。还有啰啰嗦嗦许多事,反正我这儿都记下了。”她给我看看自己皮包里的笔记本。她说:“咱们得把现款和银行存单都带上,因为手续一次办完,有余退还,不足呢,半路上不能补办手续。”
我觉得更像绑架案了,只是没敢说,因为阿圆从不糊涂。我重新热了做好的饭,两人食而不知其味地把午饭、晚饭并作一顿吃。
我疑疑惑惑地问:“办多长的手续呀?带多少行李呢?”
阿圆说:“洗换的衣服带两件,日用的东西那边客栈里都有,带了钱就行,要什么都有。”她约略把她记下的啰啰嗦嗦事告诉我,我不甚经心地听着。
阿圆一再对我说:“娘,不要愁,有我呢。咱们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
我无奈说,“我怕爸爸要急坏了——他居然也知道打个电话。也多亏是你接的。我哪里记得清。我现在出门,路都不认识了,车也不会乘了,十足的饭桶了。”
阿圆缩着脖子做了个鬼脸说:“妈妈这只饭桶里,只有几颗米粒儿一勺汤。”我给她说得笑了。她安慰我说:“反正不要紧,我把你安顿在客栈里,你不用认路,不用乘车。我只能来来往往,因为我得上课。”
阿圆细细地看她的笔记本。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手提包,也理出所有的存单,现款留给阿圆。
第二天早餐后,阿圆为我提了手提包,肩上挂着自己的皮包,两人乘一辆出租车,到了老远的一个公交车站。她提着包,护着我,挤上公交车,又走了好老远的路。下车在荒僻的路上又走了一小段路,只见路旁有旧木板做成的一个大牌子,牌子上是小篆体的三个大字:“古驿道”。下面有许多行小字,我没戴眼镜,模模糊糊看到几个似曾见过的地名,如灞陵道、咸阳道等。阿圆眼快,把手一点说:“到了,就是这里。妈妈,你只管找号头,311,就是爸爸的号。”
她牵着我一拐弯走向一个门口。她在门上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按一下,原来是电铃。门上立即开出一个窗口。阿圆出示证件,窗口关上,门就开了。我们走入一家客栈的后门,那后门也随即关上。
客栈是坐北向南的小楼,后门向南。进门就是柜台。
阿圆说:“妈妈,累了吧?”她在柜台近侧找到个坐处,叫妈妈坐下,把手提包放在我身边。她自己就去招呼柜台后面的人办手续。先是查看种种证件,阿圆都带着呢。掌柜的仔细看过,然后拿出几份表格叫她一一填写。她填了又填,然后交费。我暗想,假如是绑匪,可真是官派十足啊。那掌柜的把存单一一登记,一面解释说:“我们这里房屋是简陋些,管理却是新式的;这一路上长亭短亭都已改建成客栈了,是连锁的一条龙。你们领了牌子就不用再交费,每个客栈都供吃、供住、供一切方便。旅客的衣着和日用品都可以在客栈领,记账。旅客离开房间的时候,把自己的东西归置一起,交给柜台。船上的旅客归船上管,你们不得插手。住客栈的过客,得遵守我们客栈的规则。”他拿出印好的一纸警告,一纸规则。
警告是红牌黑字,字很大。
(一)顺着驿道走,没有路的地方,别走。
(二)看不见的地方,别去。
(三)不知道的事,别问。
规则是白纸黑字,也是大字。
(一)太阳落到前舱,立即回客栈。驿道荒僻,晚间大门上闩后,敲门也不开。
(二)每个客栈,都可以休息、方便、进餐,勿错过。
(三)下船后退回原客栈。
掌柜的发给我们各人一个圆牌,上有号码,背面叫我们按上指印,一面郑重叮嘱,出入总带着牌儿,守规则,勿忘警告,尤其是第三条,因为最难管的是嘴巴。
客栈里正为我们开饭,叫我们吃了饭再上路。我心上纳闷,尤其那第三条警告叫人纳闷。不知道的事多着呢,为什么不能问?问了又怎么样?
我用手指点红牌上的第三条故意用肯定的口气向掌柜的说:“不能用一个问字,不能打一个问号。”我这样说,应该不算问。可是掌柜的瞪着眼警告说:“你这话已经在边缘上了,小心!”我忙说:“谢谢,知道了。”
阿圆悄悄地把我的手捏了一捏,也是警告的意思。饭后我从小提包里找出一枚别针,别在手袖上,我往常叫自己记住什么事,就在衣袖上别一枚别针,很有提醒的作用。
柜台的那一侧,有两扇大门。只开着一扇,那就是客栈的前门。前门朝北开。我们走出前门,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那里烟雾迷蒙,五百步外就看不清楚;空气郁塞,叫人透不过气似的。门外是东西向的一道长堤,沙土筑成,相当宽,可容两辆大车。堤岸南北两侧都砌着石板。客栈在路南,水道在路北。客栈的大门上,架着一个新刷的招牌,大书“客栈”二字。道旁两侧都是古老的杨柳。驿道南边的堤下是城市背面的荒郊,杂树丛生,野草滋蔓,爬山虎直爬到驿道旁边的树上。远处也能看到一两簇苍松翠柏,可能是谁家的陵墓。驿道东头好像是个树林子,客栈都笼罩在树林里似的。我们走进临水道的那一岸。堤很高,也很陡,河水静止不流,不见一丝波纹。水面明净,但是云雾蒙蒙的天倒映在水里,好像天地相向,快要合上了。也许这就是令人觉得透不过气的原因。顺着蜿蜒的水道向西看去,只觉得前途很远很远,只是迷迷茫茫,看不分明。水边一顺溜的青青草,引出绵绵远道。
古老的柳树根,把驿道拱坏了。驿道也随着地势时起时伏,石片砌的边缘处,常见塌陷,所以路很难走。河里也不见船只。
阿圆扶着我说,“妈妈小心,看着地下。”
我知道小心,因为我病后刚能独自行走。我步步着实地走,省得阿圆搀扶,她已经够累的了。走着走着——其实并没走多远,就看见岸边停着一叶小舟,赶紧跑去。
船头的岸边,植一竿撑船的长竹篙,船缆在篙上。船很小,倒也有前舱、后舱、船头、船尾;却没有舵,也没有桨。一条跳板,搭在船尾和河岸的沙土地上。驿道边有一道很长的斜坡,通向跳板。
阿圆站定了说:“妈妈,看那只船艄有号码,311,是爸爸的船。”
我也看见了。阿圆先下坡,我走在后面,一面说:“你放心,我走得很稳。”但是阿圆从没见过跳板,不敢走。我先上去,伸手牵着她,她小心翼翼地横着走。两人都上了船。
船很干净,后舱空无一物,前舱铺着一只干净整齐的床,雪白的床单,雪白的枕头,简直像在医院里,锺书侧身卧着,腹部匀匀地一起一伏,睡得很安静。
我们在后舱脱了鞋,轻轻走向床前。只见他紧抿着嘴唇,眼睛里还噙着些泪,脸上有一道泪痕。枕边搭着一方干净的手绢,就是他自己带走的那条,显然已经洗过,因为没一道折痕。船上不见一人。
该有个撑船的艄公,也许还有个洗手绢的艄婆。他们都上岸了?(我只在心里捉摸)
我摸摸他额上温度正常,就用他自己的手绢为他拭去眼泪,一面在他耳边轻唤“锺书,锺书”。阿圆乖乖地挨着我。
他立即睁开眼,眼睛睁得好大。没有了眼镜,可以看到他的眼皮双得很美,只是面容显得十分憔悴。他放心地叫了声“季康,阿圆”,声音很微弱,然后苦着脸,断断续续地诉苦:“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很高很高的不知哪里,然后又把我弄下来,转了好多好多的路,我累得睁不开眼了,又不敢睡,听得船在水里走,这是船上吧?我只愁你们找不到我了。”
阿圆说:“爸爸,我们来了,你放心吧!”
我说:“阿圆带着我,没走一步冤枉路。你睁不开眼,就闭上,放心睡一会儿。”
他疲劳得支持不住,立即闭上眼睛。
我们没个坐处,只好盘膝坐在地上。他从被子侧边伸出半只手,动着指头,让我们握握。阿圆坐在床尾抱着他的脚,他还故意把脚动动。我们仨人又相聚了。不用说话,都觉得心上舒坦。我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床沿上。阿圆抱着爸爸的脚,把脸靠在床尾。虽然是在古驿道上,这也是合家团聚。
我和阿圆环视四周。锺书的眼镜没了,鞋也没了。前舱的四壁好像都是装东西的壁柜,我们不敢打开看。近船头处,放着一个大石礅。大概是镇船的。
阿圆忽然说:“啊呀,糟糕了,妈妈,我今天有课的,全忘了!明天得到学校去一遭。”
我说:“去也来不及了。”
“我从来没旷过课。他们准会来电话。哎,还得补课呢。今晚得回去给系里通个电话。”
阿圆要回去,就剩我一人住客栈了。我往常自以为很独立,这时才觉得自己像一枝爬藤草。可是我也不能拉住阿圆不放。好在手续都已办完,客栈离船不远。
我叹口气说:“你该提早退休,就说爸爸老了,妈妈糊涂了,你负担太重了。你编的教材才出版了上册,还有下册没写呢。”
阿圆说:“妈妈你不懂。一面教,一面才会有新的发现,才能修改添补。出版的那个上册还得大修大改呢——妈妈,你老盼我退休,只怕再过三年五年也退不成。”
我自己惭愧,只有我是个多余的人。我默然。太阳已经越过船身。我轻声说:“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如果爸爸还不醒……”我摸摸袖口的别针,忙止口不问。
“叫醒他。”阿圆有决断,她像爸爸。
锺书好像还在沉沉酣睡。云后一轮血红的太阳,还没照到床头,锺书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们,安慰自己似的念着我们的名字:季康、圆圆。我们忙告诉他,太阳照进前舱,我们就得回客栈。阿圆说:“我每星期会来看你。妈妈每天来陪你。这里很安静。”
锺书说:“都听见了。”他耳朵特灵,他睡着也只是半睡。这时他忽把紧闭的嘴拉成一条直线,扯出一丝淘气的笑,怪有意思地看着我说:“绛,还做梦吗?”
我愣了一下,茫然说:“我这会儿就好像做梦呢。”嘴里这么回答,却知道自己是没有回答。我一时摸不着头脑。
阿圆站起身说:“我们该走了。爸爸,我星期天来看你,妈妈明天就来。”
锺书说:“走吧。”
我说了声:“明天见,好好睡。”我们忙到后舱穿上鞋。我先上跳板,牵着阿圆。她只会横着一步一步过。我们下船,又走上驿道。两人忙忙地赶回客栈,因为路不好走,我又走不快。
到了客栈,阿圆说:“妈妈,我很想陪你,但是我得赶回家打个电话,还得安排补课……妈妈,你一个人了……”她舍不得撇下我。
我认为客栈离船不远,虽然心上没着落,却不忍拖累阿圆。我说:“你放心吧,我走得很稳了。你来不及吃晚饭,干脆赶早回去,再迟就堵车了。”
我们一进客栈的门,大门就上闩。
阿圆说:“娘,你走路小心,宁可慢。”我说:“放心,你早点睡。”她答应了一声,匆匆从后门出去,后门也立即关上。这前后门都把得很紧。
我仍旧坐在楼梯下的小饭桌上,等开晚饭。我要了一份清淡的晚餐,坐着四顾观看。店里有个柜台,还有个大灶,掌柜一人,还有伙计几人,其中有一个女的很和善。我们微笑招呼。我发现柜台对面有个窗口,旁边有一个大转盘,茶水、点心、饭菜都从这个转盘转出去。窗口有东西挡着,我午饭时没看见。我对女人说:“那边忙着呢,我不着急。”那女人就向我解释,外面是南北向的道路上招徕顾客的点心铺,也供茶水,也供便饭。我指指楼上,没敢开口。她说,楼上堆货,管店的也住楼上。没别的客人。
楼上,我的客房连着个盥洗室,很干净。我的手提包已经在客房里了。我走得很累,上床就睡着。
我睡着就变成了一个梦,很轻灵。我想到高处去看看河边的船。转念间,我已在客栈外边路灯的电杆顶上。驿道那边的河看不见,停在河边的船当然也看不见,船上并没有灯火。客栈南边却是好看,闪亮着红灯、绿灯、黄灯、蓝灯各色灯光,是万家灯火的不夜城,是北京。三里河在哪儿呢?转念间我已在家中卧室窗前的柏树顶上,全屋是黑的,阿圆不知在哪条街上,哪辆公交车上。明天我们的女婿要来吃早点的,他知道我们家的事吗?转念间我又到了西石槽阿圆的婆家。屋里几间房都亮着灯。呀!阿圆刚放下电话听筒,过来坐在饭桌前。她婆婆坐在她旁边。我的女婿给阿圆舀了一碗汤,叫她喝汤,一面问:
“我能去看看他们吗?”
“不能,只许妈妈和我两个。”
她婆婆说:“你搬回来住吧。”
阿圆说:“书都在那边呢,那边离学校近。我吃了晚饭就得过那边去。”
我依傍着阿圆,听着他们谈话,然后随阿圆又上车回到三里河。她洗完澡还不睡,备课到夜深。我这个梦虽然轻灵,却是万般无能,我都没法催圆圆早睡。梦也累了。我停在自己床头贴近衣柜的角落里歇着,觉得自己化淡了,化为乌有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的床上,手脚倒是休息过来了。我吃过早饭,忙忙地赶路,指望早些上船陪锺书。昨天走过的路约略记得,可是斜坡下面的船却没有了。
这下子我可慌了。我没想想,船在水里,当然会走的。走多远了呢?身边没个可以商量的人了。一人怯怯地,生怕走急了绊倒了怎么办,又怕错失了河里的船,更怕走慢了赶不上那只船。步步留心地走,留心地找,只见驿道左侧又出现一座客栈,不敢错过,就进去吃饭休息。客栈是一模一样的客栈,只是掌柜和伙计换了人。我带着牌子进去,好似老主顾。我洗了手又复赶路,心上惶惶然。幸好不多远就望见驿道右边的斜坡,311号的船照模照样地停在坡下。我走过跳板上船,在后舱脱鞋,锺书半坐半躺地靠在枕上等我呢。
他问:“阿圆呢?”
“到学校去了。”
我照样盘腿坐在他床前,摸他的脑门子,温度正常,颈间光滑滑的。他枕上还搭着他自己的手绢,显然又洗过了。他神情已很安定,只是面容很憔悴,一下子瘦了很多。
他说:“我等了你好半天了。”
我告诉他走路怕跌,走不快。
我把自己变了梦所看到的阿圆,当作真事一一告诉。他很关心地听着,并不问我怎会知道。他等我已经等累了,疲倦得闭上眼睛。我梦里也累,又走得累,也紧张得累。我也闭上眼,把头枕在他的床边。这样陪着他,心上挺安顿。到应该下船的时候,我起身说,该回去了,他说:“明天见,别着急,走路小心。”我就一步步走回客栈。
但是,我心上有个老大的疙瘩。阿圆是否和我一样糊涂,以为船老停在原处不动?船大概走了一夜,星期天阿圆到哪个客栈来找我呢?
客栈确是“一条龙”,我的手提包已移入另一个客栈的客房。我照模照样又过了一夜,照模照样又变成一个梦,随着阿圆打转,又照模照样,走过了另一个客栈,又找到锺书的船。他照样在等我,我也照样儿陪着他。
一天又一天,我天天在等星期日,却忘了哪天是星期日。有一天,我饭后洗净手,正待出门,忽听得阿圆叫娘,她连挂在肩上的包都没带,我梦里看见她整理好了书包才睡的。我不敢问,只说:“你没带书包。”
她说不用书包,只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小钱包给我看看,拉着我一同上路。我又惊讶,又佩服,不知阿圆怎么找来的,我也不敢问,只说:“我只怕你找不到我们了。”阿圆说:“算得出来呀。”古驿道办事处的人曾给她一张行舟图表,她可以按着日程找。我放下了一桩大心事。
我们一同上了船,锺书见了阿圆很高兴,虽然疲倦,也不闭眼睛,我虽然劳累,也很兴奋,我们又在船上团聚了。
我只在阿圆和我分别时郑重叮嘱,晚上早些睡,勿磨蹭到老晚。阿圆说:“妈妈,梦想为劳,想累了要梦魇的。”去年爸爸动手术,她颈椎痛,老梦魇,现在好了。她说:“妈妈总是性急,咱们只能乖乖地顺着道儿走。”
可是我常想和阿圆设法把锺书驮下船溜回家去。这怎么可能呢!
我的梦不复轻灵,我梦得很劳累,梦都沉重得很。我变了梦,看阿圆忙这忙那,看她吃着晚饭,还有电话打扰,有一次还有两个学生老晚来找她。我看见女婿在我家厨房里,烧开了水,壶上烤着个膏药,揭开了,给阿圆贴在颈后。都是真的吗?她又颈椎痛吗?我不敢当作真事告诉锺书。好在他都不问。
堤上的杨柳开始黄落,渐渐地落成一棵棵秃柳。我每天在驿道上一脚一脚走,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
有一个星期天,三人在船上团聚。锺书已经没有精力半坐半躺,他只平躺着。我发现他的假牙不知几时起已不见了。他日见消瘦,好像老不吃饭的。我摸摸他的脑门子,有点热辣辣的。我摸摸阿圆的脑门子,两人都热辣辣的,我用自己的脑门子去试,他们都是热的。阿圆笑说:“妈妈有点凉,不是我们热。”
可是下一天我看见锺书手背上有一块青紫,好像是用了吊针,皮下流了血。他眼睛也张不开,只捏捏我的手。我握着他的手,他就沉沉地睡,直到太阳照进前舱。他时间观念特强,总会及时睁开眼睛。他向我点点头。我说:“好好睡,明天见。”
他只说:“回去吧。”
阿圆算得很准,她总是到近处的客栈来找我。每星期都来看爸爸,除了几次出差,到厦门,到昆明,到重庆。我总记着她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时刻。她出差时,我梦也不做,借此休息。锺书上过几次吊针,体温又正常,精神又稍好,我们同在船上谈说阿圆。
我说:“她真是‘强爹娘、胜祖宗’。你开会发言还能对付,我每逢开会需要发言,总吓得心怦怦跳,一句也不会说。阿圆呢,总有她独到的见解,也敢说。那几个会,她还是主持人。”
锺书叹口气说:“咱们的圆圆是可造之材,可是……”
阿圆每次回来,总有许多趣事讲给我们听,填满了我不做梦留下的空白。我们经常在船上相聚,她的额头常和锺书的一样热烘烘,她也常常空声空气地咳嗽。我担心说:“你该去看看病,你‘打的’去,‘打的’回。”她说,看过病了,是慢性支气管炎。
她笑着讲她挎着个大书包挤车,同车的一人嫌她,对她说:“大妈,您怎么还不退休?”我说:“挤车来往费时间,时间不是金钱,时间是生命,记着。你来往都‘打的’。”阿圆说:“‘打的’常给堵死在街上,前不能前,退不能退,还不如公交车快。”
我的梦已经变得很沉重,但是圆圆出差回来,我每晚还是跟着她转。我看见我的女婿在我家打电话,安排阿圆做磁共振、做CT。我连夜梦魇。一个晚上,我的女婿在我家连连地打电话,为阿圆托这人,托那人,请代挂专家号。后来总算挂上了。
我疑疑惑惑地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走。柳树一年四季变化最勤。秋风刚一吹,柳叶就开始黄落,随着一阵一阵风,落下一批又一批叶子,冬天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春风还没有吹,柳条上已经发芽,远看着已有绿意;柳树在春风里,就飘荡着嫩绿的长条。然后蒙蒙飞絮,要飞上一两个月。飞絮还没飞完,柳树都已绿叶成荫。然后又一片片黄落,又变成光秃秃的寒柳。我在古驿道上,一脚一脚的,走了一年多。
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圆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圆靠柜台站着。她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她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她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她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她小时候得过指骨节结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她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痛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我的女婿)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一声,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她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她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掉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她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
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锺书,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圆圆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
锺书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圆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圆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圆叫爸爸放心。
锺书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她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
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圆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她休息;现在有了病,她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
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圆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锺书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
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圆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她呢?我得找到她。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重的梦。
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她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圆阿圆,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她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进院门,灯光下看见一座牌坊,原来我走进了一座墓院。不好,我梦魇了。可是一拐弯我看见一所小小的平房,阿圆的小白手在招我。我透过门,透过窗,进了阿圆的病房。只见她平躺在一张铺着白单子的床上,盖着很厚的被子,没有枕头。床看来很硬。屋里有两张床。另一张空床略小,不像病床,大约是陪住的人睡的。有大夫和护士在她旁边忙着,我的女婿已经走了。屋里有两瓶花,还有一束没解开的花,大夫和护士轻声交谈,然后一同走出病房,走进一间办公室。我想跟进去,听听他们怎么说,可是我走不进。我回到阿圆的病房里,阿圆闭着眼乖乖地睡呢。我偎着她,我拍着她,她都不知觉。
我不嫌劳累,又赶到西石槽,听到我女婿和他妈妈在谈话,说幸亏带了那床厚被,他说要为阿圆床头安个电话,还要了一只冰箱。生活护理今晚托清洁工兼顾,已经约定了一个姓刘的大妈。我又回到阿圆那里,她已经睡熟,我劳累得不想动了,停在她床头边消失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床上。我真的能变成一个梦,随着阿圆招我的手,找到了医院里的阿圆吗?有这种事吗?我想阿圆只是我梦里的人。她负痛小步挨向妈妈,靠在妈妈身上,我能感受到她腰间的痛;我也能感觉到她舍不得离开妈妈去住医院,舍不得撇我一人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但是我只抱着她的腰,缓步走到后门,把她交给了女婿。她上车弯腰坐下,一定都很痛很痛,可是她还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手向妈妈挥挥,她是依恋不舍。我的阿圆,我唯一的女儿,永远叫我牵心挂肚的,睡里梦里也甩不掉,所以我就创造了一个梦境,看见了阿圆。该是我做梦吧?我实在拿不定我的梦是虚是实。我不信真能找到她的医院。
我照常到了锺书的船上,他在等我。我握着他的手,手心是烫的。摸摸他的脑门子,也是热烘烘的。锺书是在发烧,阿圆也是在发烧,我确实知道的就这一点。
我以前每天总把阿圆在家的情况告诉他。这回我就把梦中所见的阿圆病房,形容给他听,还说女婿准备为她床头安电话,为她要一只冰箱,等等。锺书从来没问过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他只在古驿道的一只船里,驿道以外,那边家里的事,我当然知道。我好比是在家里,他却已离开了家。我和他讲的,都是那边家里的事。他很关心地听着。
他嘴里不说,心上和我一样惦着阿圆。我每天和他谈梦里所见的阿圆。他尽管发烧,精神很萎弱,但总关切地听。
我每晚做梦,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电话已经安上了,就在床边。她房里的花越来越多。睡在小床上的是刘阿姨,管阿圆叫钱教授,阿圆不准她称教授,她就称钱老师。刘阿姨和钱老师相处得很好。医生护士对钱瑗都很好。她们称她钱瑗。
医院的规格不高,不能和锺书动手术的医院相比。但是小医院里,管理不严,比较乱,也可说很自由。我因为每到阿圆的医院总在晚间,我的女婿已不在那里,我变成的梦,不怕劳累,总来回来回跑,看了这边的圆圆,又到那边去听女婿的谈话。阿圆的情况我知道得还周全。我尽管拿不稳自己是否真的能变成一个梦,是否看到真的阿圆,也许我自己只在梦中,看到的只是我梦中的阿圆。但是我切记着驿站的警告。我不敢向锺书提出任何问题,我只可以向他讲讲他记挂的事,我就把我梦里所看到的,一一讲给锺书听。
我告诉他,阿圆房里有一只大冰箱,因为没有小的了。邻居要借用冰箱,阿圆都让人借用,由此结识了几个朋友。她隔壁住着一个“大款”,是某饭店的经理,入院前刷新了房间,还配备了微波炉和电炉;他的夫人叫小马,天天带来新鲜菜蔬,并为丈夫做晚饭。小马大约是山西人,圆圆常和她讲山西“四清”时期的事,两人很相投。小马常借用阿圆的大冰箱,也常把自己包的饺子送阿圆吃。医院管饭的大师傅待阿圆极好,一次特为她做了一尾鲜鱼,亲自托着送进病房。阿圆吃了半条,剩半条让刘阿姨帮她吃完。阿圆的婆婆叫儿子送来她拿手的“妈咪鸡”,阿圆请小马吃,但他们夫妇只欣赏饺子。小马包的饺子很大,阿圆只能吃两只。医院里能专为她炖鸡汤,每天都给阿圆炖西洋参汤。我女婿为她买了一只很小的电炉,能热一杯牛奶……
我谈到各种吃的东西,注意锺书是否有想吃的意思。他都毫无兴趣。
我又告诉他,阿圆住院后还曾为学校审定过什么教学计划。阿圆天天看半本侦探小说,家里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搜罗了送进医院,连她朋友的侦探小说也送到医院去了。但阿圆不知是否精力减退,又改读菜谱了。我怕她是精力减退了,但是我没有说。也许只是我在担心。我觉得她脸色渐变苍白。
我又告诉锺书,阿圆的朋友真不少,每天病房里都是鲜花。学校的同事、学生不断地去看望。亲戚朋友都去,许多中学的老同学都去看她。我认为她太劳神了,应该少见客人。但是我听西石槽那边说,圆圆觉得人家远道来访不易,她不肯让他们白跑。
我谈到亲戚朋友,注意锺书是否关切。但锺书漠无表情。以前,每当阿圆到船上看望,他总强打精神。自从阿圆住院,他干脆都放松了。他很倦怠,话也懒说,只听我讲,张开眼又闭上。我虽然天天见到他,只觉得他离我很遥远。
阿圆呢?是我的梦找到了她,还是她只在我的梦里?我不知道。她脱了手套向我挥手,让我看到她的手而不是手套。可是我如今只有她为我织的手套与我相亲了。
快过了半年,我听见她和我女婿通电话,她很高兴地说:医院特为她赶制了一个护腰,是量着身体做的;她试过了,很服帖;医生说,等明天做完CT,让她换睡软床,她穿上护腰,可以在床上打滚。
但是阿圆很瘦弱,屋里的大冰箱里塞满了她吃不下而剩下的东西。她正在脱落大把大把的头发。西石槽那边,我只听说她要一只帽子。我都没敢告诉锺书。他刚发过一次高烧,正渐渐退烧,很倦怠。我静静地陪着他,能不说的话,都不说了。我的种种忧虑,自个儿担着,不叫他分担了。
第二晚我又到医院。阿圆戴着个帽子,还睡在硬床上,张着眼睛,不知在想什么。刘阿姨接了电话,说是学校里打来的让她听。阿圆接了话筒说:“是的,嗯……我好着。今天护士、大夫,把我扛出去照CT,完了,说还不行呢。老伟来过了。硬床已经拆了,都换上软床了。可是照完CT,他们又把软床换去,搭上硬床。”她强打欢笑说:“穿了护腰一点儿不舒服,我宁愿不穿护腰,斯斯文文地平躺在硬床上;我不想打滚。”
大夫来问她是否再做一个疗程。阿圆很坚强地说:“做了见好,再做。我受得了。头发掉了会再长出来。”
我听到隔壁那位“大款”和小马的谈话。
男的问:“她知道自己什么病吗?”
女的说:“她自己说,她得的是一种很特殊的结核病,潜伏了几十年又再发,就很厉害,得用重药。她很坚强。真坚强。只是她一直在惦着她的爹妈,说到妈妈就流眼泪。”
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锺书高烧之后剃成一个光头,阿圆帽子底下也是光头。两人的头型和五官都很相像,只不过阿圆的眼皮不双。
锺书高烧退了又渐渐有点精神。我就告诉他阿圆的病情:据医生说,潜伏几十年后又复发的结核病比原先厉害,还得慢慢养;反正她乖乖地躺着休养,休养总是好的。我说:“我看你们两个越看越像。一样的脑袋,一样的脸型。惟独和爸爸的双眼皮不像,但眼神完全像爸爸。可阿圆生了病就变成双眼皮了。”
锺书得意地说:“‘方凳妈妈’第一次见到阿圆就说,她眼睛像爸爸。‘方凳’眼睛尖。”
我的梦很疲劳。真奇怪,疲劳的梦也影响我的身体。我天天拖着疲劳的脚步在古驿道上来来往往。阿圆住院时,杨柳都是光秃秃的,现在,成荫的柳叶已开始黄落。我天天带着自己的影子,踏着落叶,一步一步小心地走,没完地走。
我每晚都在阿圆的病房里。一次,她正和老伟通电话。阿圆强笑着说:“告诉你一个笑话。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妈妈偎着我的脸。我梦里怕是假的。我对自己说,是妖精就是香的,是妈妈就不香。我闻着不香,我说,这是我的妈妈。但是我睁不开眼,看不见她。我使劲儿睁开眼,后来眼睛睁开了——我在做梦。”她放下电话,嘴角抽搐着,闭上眼睛,眼角滴下眼泪。她把听筒交给刘阿姨。刘阿姨接下说:“钱老师今天还要抽肺水,不让多说了。”接下是她代阿圆报告病情。
我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我想到她梦中醒来,看到自己孤零零躺在医院病房里,连梦里的妈妈都没有了。而我的梦是十足无能的,只像个影子。我依偎着她,抚摸着她,她一点不觉得。
我知道梦是富有想象力的。想念得太狠了,就做噩梦。我连夜做噩梦。阿圆渐渐不进饮食。她头顶上吊着一袋紫红色的血,一袋白色的什么蛋白,大夫在她身上打通了什么管子,输送到她身上。刘阿姨不停地用小勺舀着杯里的水,一勺一勺润她的嘴。我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有一晚,我女婿没回家,他也用小勺,一勺一勺地舀着杯子里的清水,润她的嘴。她直闭着眼睛睡。
我不敢做梦了。可是我不敢不做梦。我疲劳得都走不动了。我坐在锺书床前,握着他的手,把脸枕在他的床边。我一再对自己说:“梦是反的,梦是反的。”阿圆住院已超过一年,我太担心了。
我抬头忽见阿圆从斜坡上走来,很轻健。她稳步走过跳板,走入船舱。她温软亲热地叫了一声“娘”,然后挨着我坐下,叫一声“爸爸”。
锺书睁开眼,睁大了眼睛,看着她,看着她,然后对我说:“叫阿圆回去。”
阿圆笑眯眯地说:“我已经好了,我的病完全好了,爸爸……”
锺书仍对我说:“叫阿圆回去,回家去。”
我一手搂着阿圆,一面笑说:“我叫她回三里河去看家。”我心想梦是反的,阿圆回来了,可以陪我来来往往看望爸爸了。
锺书说:“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嗯,回西石槽去,和他们热闹热闹。”
“西石槽究竟也不是她的家。叫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
阿圆清澈的眼睛里,泛出了鲜花一样的微笑。她说:“是的,爸爸,我就回去了。”
太阳已照进船头,我站起身,阿圆也站起身。我说:“该走了,明天见!”
阿圆说:“爸爸,好好休息。”
她先过跳板,我随后也走上斜坡。我仿佛从梦魇中醒来。阿圆病好了!阿圆回来了!
她拉我走上驿道,陪我往回走了几步。她扶着我说:“娘,你曾经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要回去了。爸爸叫我回自己家里去。娘……娘……”
她鲜花般的笑容还在我眼前,她温软亲热的一声声“娘”还在我耳边,但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晃眼她没有了。就在这一瞬间,我也完全省悟了。
我防止跌倒,一手扶住旁边的柳树,四下里观看,一面低声说:“圆圆,阿圆,你走好,带着爸爸妈妈的祝福回去。”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泪来。
我的手撑在树上,我的头枕在手上,胸中的热泪直往上涌,直涌到喉头。我使劲咽住,但是我使的劲儿太大,满腔热泪把胸口挣裂了。只听得噼嗒一声,地下石片上掉落下一堆血肉模糊的东西。迎面的寒风,直往我胸口的窟窿里灌。我痛不可忍,忙蹲下把那血肉模糊的东西揉成一团往胸口里塞;幸亏血很多,把滓杂污物都洗干净了。我一手抓紧裂口,另一手压在上面护着,觉得恶心头晕,生怕倒在驿道上,踉踉跄跄,奔回客栈,跨进门,店家正要上闩。
我站在灯光下,发现自己手上并没有血污,身上并没有裂口。谁也没看见我有任何异乎寻常的地方。我的晚饭,照常在楼梯下的小桌上等着我。
我上楼倒在床上,抱着满腔满腹的痛变了一个痛梦,赶向西山脚下的医院。
阿圆屋里灯亮着,两只床都没有了,清洁工在扫地,正把一堆垃圾扫出门去。我认得一只鞋是阿圆的,她穿着进医院的。
我听到邻室的小马夫妇的话:“走了,睡着去的,这种病都是睡着去的。”
我的梦赶到西石槽。刘阿姨在我女婿家饭间尽头的长柜上坐着淌眼抹泪。我的女婿在自己屋里呆呆地坐着。他妈妈正和一个亲戚细谈阿圆的病,又谈她是怎么去的。她说:钱瑗的病,她本人不知道,驿道上的爹妈当然也不知道。现在,他们也无从通知我们。
我的梦不愿留在那边,虽然精疲力竭,却一意要停到自己的老窝里去,安安静静地歇歇。我的梦又回到三里河寓所,停在我自己的床头上消失了。
我睁眼身在客栈。我的心已结成一个疙疙瘩瘩的硬块,居然还能按规律匀匀地跳动。每跳一跳,就牵扯着肚肠一起痛。阿圆已经不在了,我变了梦也无从找到她;我也疲劳得无力变梦了。
驿道上又飘拂着嫩绿的长条,去年的落叶已经给北风扫净。我赶到锺书的船上,他正在等我。他高烧退尽之后,往往又能稍稍恢复一些。
他问我:“阿圆呢?”
我在他床前盘腿坐下,扶着床说:“她回去了!”
“她什么??”
“你叫她回自己家里去,她回到她自己家里去了。”
锺书很诧异地看着我,他说:“你也看见她了?”
我说:“你也看见了。你叫我对她说,叫她回去。”
锺书着重说:“我看见的不是阿圆,不是实实在在的阿圆,不过我知道她是阿圆。我叫你去对阿圆说,叫她回去吧。”
“你叫阿圆回自己家里去,她笑眯眯地放心了。她眼睛里泛出笑来,满面鲜花一般的笑,我从没看见她笑得这么美。爸爸叫她回去,她可以回去了,她可以放心了。”
锺书凄然看着我说:“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她记挂着爸爸,放不下妈妈。我看她就是不放心,她直在抱歉。”
老人的眼睛是干枯的,只会心上流泪。锺书眼里是灼热的痛和苦,他黯然看着我,我知道他心上也在流泪。我自以为已经结成硬块的心,又张开几只眼睛,潸潸流泪,把胸中那个疙疙瘩瘩的硬块湿润得软和了些,也光滑了些。
我的手是冰冷的。我摸摸他的手,手心很烫,他的脉搏跳得很急促。锺书又发烧了。
我急忙告诉他,阿圆是在沉睡中去的。我把她的病情细细告诉。她腰痛住院,已经是病的末期,幸亏病转入腰椎,只那一节小骨头痛,以后就上下神经断连,她没有痛感了。她只是希望赶紧病好,陪妈妈看望爸爸,忍受了几次治疗。现在她什么病都不怕了,什么都不用着急了,也不用起早贪黑忙个没完没了了。我说,自从生了阿圆,永远牵心挂肚肠,以后就不用牵挂了。
我说是这么说,心上却牵扯得痛。锺书点头,却闭着眼睛。我知道他心上不仅痛惜圆圆,也在可怜我。
我初住客栈,能轻快地变成一个梦。到这时,我的梦已经像沾了泥的杨花,飞不起来。我当初还想三个人同回三里河。自从失去阿圆,我内脏受伤,四肢也乏力,每天一脚一脚在驿道上走,总能走到船上,与锺书相会。他已骨瘦如柴,我也老态龙钟。他没有力量说话,还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忽然想到第一次船上相会时,他问我还做梦不做。我这时明白了。我曾做过一个小梦,怪他一声不响地忽然走了。他现在故意慢慢儿走,让我一程一程送,尽量多聚聚,把一个小梦拉成一个万里长梦。
这我愿意。送一程,说一声再见,又能见到一面。离别拉得长,是增加痛苦还是减少痛苦呢?我算不清。但是我陪他走得愈远,愈怕从此不见。
杨柳又变成嫩绿的长条,又渐渐黄落,驿道上又满地落叶,一棵棵杨柳又都变成光秃秃的寒柳。
那天我走出客栈,忽见门后有个石礅,和锺书船上的一模一样。我心里一惊。谁上船偷了船上的东西?我摸摸衣袖上的别针,没敢问。
我走着走着,看见迎面来了一男一女。我从没有在驿道上遇见什么过客。女的夹着一条跳板,男的拿着一枝长竹篙,分明是锺书船上的。
我拦住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这是船上的东西!”
男女两个理都不理,大踏步地往客栈走去。他们大约就是我从未见过的艄公艄婆。
我一想不好,违反警告了。一迟疑间,那两人已走远。我追不上,追上也无力抢他们的东西。
我往前走去,却找不到惯见的斜坡。一路找去,没有斜坡,也没有船。前面没有路了。我走上一个山坡,拦在面前的是一座乱山。太阳落到山后去了。
我急着往上爬,想寻找河里的船。昏暗中,能看到河的对岸也是山,河里漂荡着一只小船,一会儿给山石挡住,又看不见了。
我眼前一片昏黑,耳里好像能听到哗哗的水声。山里没有路,我在乱石间拼命攀登,想爬向高处,又不敢远离水声。我摸到石头,就双手扳住了往上跨两步;摸到树干,就抱住了歇下喘口气。风很寒冷,但是我穿戴得很厚,又不停地在使劲。一个人在昏黑的乱山里攀登,时间是漫长的。我是否在山石坳处坐过,是否靠着大树背后歇过,我都模糊了。我只记得前一晚下船时,锺书强睁着眼睛招待我;我说:“你倦了,闭上眼,睡吧。”
他说:“绛,好好里(即‘好生过’)。”
我有没有说“明天见”呢?
晨光熹微,背后远处太阳又出来了。我站在乱山顶上,前面是烟雾蒙蒙的一片云海。隔岸的山,比我这边还要高。被两山锁住的一道河流,从两山之间泻出,像瀑布,发出哗哗水声。
我眼看着一叶小舟随着瀑布冲泻出来,一道光似的冲入茫茫云海,变成了一个小点;看着看着,那小点也不见了。
我但愿我能变成一块石头,屹立山头,守望着那个小点。我自己问自己:山上的石头,是不是一个个女人变成的“望夫石”?我实在不想动了,但愿变成一块石头,守望着我已经看不见的小船。
但是我只变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我好劳累地爬上山头,却给风一下子扫落到古驿道上,一路上拍打着驿道往回扫去。我抚摸着一步步走过的驿道,一路上都是离情。
还没到客栈,一阵旋风把我卷入半空。我在空中打转,晕眩得闭上眼睛。我睁开眼睛,我正落在往常变了梦歇宿的三里河卧房的床头。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