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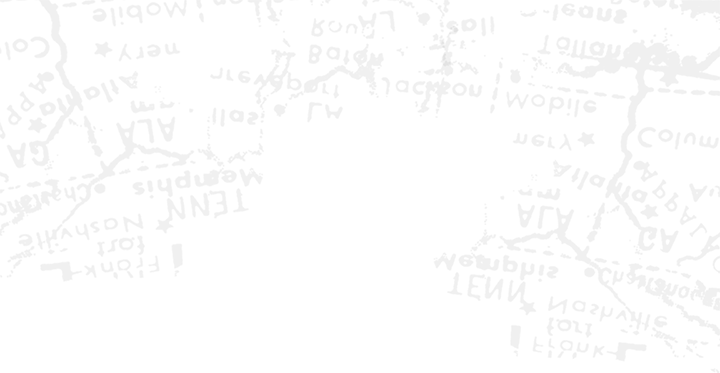


1961年5月14日,星期天,乔治·杰克斯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坐上一辆灰狗长途车,这天正好是母亲节。
他神经紧绷。
玛丽亚·萨默斯坐在他身边。两人总是坐在一起。这渐渐成为了一个惯例,所有人都假设着乔治身边的空位是留给玛丽亚的。
乔治用对话来掩饰自己的紧张。“那么,你怎么看马丁·路德·金?”
金是南方最重要民权组织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主席。前一天晚上,他们在亚特兰大一家黑人开的餐馆里见到了他。
“他是个了不起的家伙。”玛丽亚说。
乔治却没有如此确定。“他说自由之行运动意义重大,可他却没有和我们一起坐车。”
“换位思考。”玛丽亚理智地说,“他是另外一个民权组织的带头人。将军不可能去当别人军队里的脚夫。”
玛丽亚确实冰雪聪明,乔治就没从这个角度看过问题。
乔治几乎要爱上她了。他极其渴望和玛丽亚独处的机会,但他们寄住在一些很有声望的黑人家庭,他们中大部分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允许家中的客房被当作接吻的地方。尽管玛丽亚魅力四射,但她只不过坐在乔治身边和他说笑而已。她从来没有做过表明想要和他超出朋友关系的肢体动作:她没有碰过乔治的胳膊,没有牵着乔治的手和他一起下长途车,更没在集体活动时挨紧过他。玛丽亚从没和乔治调过情。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了,但她很可能还是个处女。
“你和金聊了很长时间。”乔治说。
“如果他不是个牧师的话,我还以为他对我感兴趣呢!”她说。
乔治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就算是牧师,对如此耀眼的玛丽亚动心也并不为怪。他觉得她还不太懂男人。“我和他也聊了一会儿。”
“他对你说了些什么?”
乔治犹豫了。吓着他的正是马丁·路德·金的一席话。他决定告诉玛丽亚:她有权知道。“他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
玛丽亚愣住了:“他真这样说了吗?”
“他确实这样说了。”
现在他们两个都吓坏了。长途汽车缓缓地开出了汽车站。
最初几天,乔治担心自由之行运动太过平静。在公共汽车上,白人乘客丝毫不介意黑人坐在他们的座位上,有时甚至还会和黑人们一起唱歌。当运动的参与者们扯掉车站上“白人专用”及“有色人种专用”的字样时,也没人加以阻拦。一些市镇甚至自行涂掉了这些字样。乔治担心种族隔离主义者想到了绝妙的对策。没有麻烦就意味着没有宣传效果。他们甚至在白人专用的餐厅里得到了上好的服务。每天晚上他们走下长途车,不受干扰地开会,通常是在教堂。开完会后,他们在支持者的家中过夜。但乔治觉得,一旦他们走了以后,那些文字又会被恢复,种族隔离的阴云又将卷土重来。自由之行运动就是在浪费时间。
真是惊人的讽刺。从记事起,乔治就时不时地被表示他是个下等人的言辞激怒和受伤,虽然有时候是间接的表述,但却堂而皇之。他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都聪明,比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白人更有礼貌,穿着更好,但却被整日只知道喝酒或者给汽车加油的愚蠢抑或懒惰的白人看不起。以前每当他走进商店,餐厅,或是外出寻找工作的时候,他就会寻思自己是不是会因为肤色原因而被忽视或者被对方驱赶。他常常为此而感到羞耻。但现在,他却反而为没碰到这种遭遇而感到有几分失望。
与此同时,白宫乱了阵脚。运动开始后的第三天,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乔治亚州立大学发表演讲,表示要加强南方的公民权利。三天以后,他的总统哥哥却与他背道而驰,撤回了对两项民权法案的支持。
种族隔离者会这样赢吗?乔治不禁想。避免直接对抗,然后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并不是这样的。平和的状态维持了仅仅四天。
在运动的第五天,一位成员因为强调自己也有雇人擦鞋的权利而被关进了牢房。
暴力冲突在第六天爆发了。
被打的是学习神学的约翰·路易斯。他在南卡罗来纳洛克山的白人厕所遭到了几个暴徒的袭击。路易斯任由对方踢打没有还手。乔治没有看到冲突场面,这也许是件好事,他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路易斯甘地般的自制力。
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乔治看到了这次冲突的简短报道,但几乎被艾伦·谢泼德
 ——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完全盖过了。这让乔治非常失望。谁会在乎一个被打的黑人呢?他辛酸地想。不到一个月之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刚刚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俄国人在载人航天飞行上胜过了美国人一筹。美国白人能遨游太空,美国黑人却连厕所都不允许进。
——美国第一位进入太空的宇航员,完全盖过了。这让乔治非常失望。谁会在乎一个被打的黑人呢?他辛酸地想。不到一个月之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刚刚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俄国人在载人航天飞行上胜过了美国人一筹。美国白人能遨游太空,美国黑人却连厕所都不允许进。
在亚特兰大走下长途车时,自由之行运动的成员们受到了一些人的热烈欢迎。乔治的热情又恢复了。
但这只是乔治亚州的情况,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阿拉巴马。
“金为什么说我们熬不过阿拉巴马?”玛丽亚问。
“有传言说三K党在伯明翰筹划着什么,”乔治阴沉地说,“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当地的警察呢?”
“警察就是三K党员。”
“那两个人呢?”玛丽亚朝走道另一边后面那排上的两个男人甩了甩头。
乔治回头看了眼坐在那里的两个胖胖的白种男人。“他们怎么了?”
“你没觉得有警察的气息吗?”乔治明白了玛丽亚指的是什么,“你认为他们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吗?”
“他们的衣服很寒酸,不像是联邦调查局出来的人。我猜他们是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逻队的便衣警察。”
乔治大为震撼:“你怎么这么聪明?”
“我妈妈一直逼我吃蔬菜,爸爸又在美国暴徒最为集中的芝加哥当律师,那里可是流氓匪徒之都。”
“那么你觉得他们两个在干什么呢?”
“我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不是来保卫我们的公民权的,你觉得呢?”
乔治望向窗外,看见一个标识牌上写着“欢迎进入阿拉巴马”。他看了看表,这时是下午一点,太阳高挂在湛蓝的天空中。要是死在今天,也算挺美好的。他想。玛丽亚想投身政界或是公益事务。“抗议者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改变世界格局的终将是政府。”玛丽亚说。乔治想了一会儿,不知自己是不是同意这句话。玛丽亚曾经到白宫的新闻办公室应聘,并得到了面试机会,但并没有成功。“华盛顿不雇佣黑人律师,”她愤愤不平地对乔治说,“我也许会去芝加哥,在爸爸的法律事务所工作。”
乔治的过道对面坐着一个穿着大衣,戴着帽子的中年妇女,她的膝盖上放着个白色大手提袋。乔治笑着对她说:“这天气坐车真好!”
“我去伯明翰看女儿。”尽管乔治没问,她还是说道。
“真是太棒了,我是乔治·杰克斯。”
“我是科拉·琼斯。琼斯是夫姓。我女儿的预产期还有一周。”
“是头胎吗?”
“第三个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说你这个外祖母可真是太年轻了。”
女人神情愉快地说:“我四十九岁了。”
“真想不到!”一辆灰狗长途闪着灯从另一个方向开了过来,运动成员所乘的长途车慢慢停了下来。一个白人走到乔治所在这辆车的驾驶座的车窗旁边,乔治听见他对司机说:“安尼斯顿的长途车站聚集了一大群人。”司机对来人说了些话,但乔治没听清。“小心点。”窗边的男子说。
他们所乘的车又出发了。
“一大群人是什么意思?”玛丽亚焦虑地问,“可能是二十几个人,也可能是一千来人;可能是欢迎我们的群众,也可能是充满愤怒的暴徒。他为什么不多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呢?”
乔治觉得玛丽亚刻意用愤怒遮掩着自己的恐惧。
他回想起母亲的话:“我只是怕他们会杀了你。”参加运动的一些人声称自己愿意为自由的事业而选择去死,乔治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成为名烈士。他还有许多事想要去做,比如和玛丽亚睡觉。
不一会儿,他们到了安尼斯顿。它看起来和别的南方小镇别无二致:低矮的房子,棋盘似的街道,又脏又热。路边站满了人,就好像要举行一场游行。许多人都盛装打扮,女人戴着帽子,孩子们梳洗一新,无疑刚去过教堂。“他们是想看到什么?长着角的人吗?”乔治问,“我们终于到这了,伙计们,真正的北方黑人,打扮体面。”尽管只有玛丽亚能听见他的话,但他却像是在对马路两边的围观者发表演说似的。“我们是来这收缴你们的枪,教你们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但首先我想问一问,这里的白人女孩通常在哪儿游泳啊?”
玛丽亚咯咯直笑。“如果听见了你的话,他们肯定不知道你是在开玩笑。”
乔治不是在开玩笑。这和在墓地吹口哨一样,只是在给自己壮胆而已。
长途车开进了车站,里面奇怪地一个人也没有。车站大楼似乎关着并上了锁。乔治觉得这里的气氛非常诡异。
司机打开了长途车的门。
乔治根本没看清暴徒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他们突然之间围住了车。他们都是些白种男人,有的穿着工作服,有的穿着礼拜的西服。他们拿着棒球棍,金属管和长长的铁链,并朝车上大喊。大多数都很幼稚,但乔治也听到了一些诸如“希特勒万岁”之类的充满恨意的口号。
乔治站起身,他的第一直觉就是关上公共汽车的门。但那两个男人,玛丽亚觉得他们像是公路巡警,出手比他更快,他们快步上前关上了车门。也许他们是来保护我们的,乔治心想。但也许他们只是在保护他们自己吧。
乔治朝周围的几扇车窗外望去。外面一个警察都没有。当地警察这么可能不知道有一群武装暴徒聚集在车站上呢?毫无疑问,这里的警察必定和三K党是沆瀣一气的。
没一会儿,暴徒们用携带的武器开始袭击。他们用链条和铁橇敲击着车厢,声音十分刺耳。玻璃窗被砸破了,琼斯夫人惊恐地大叫起来。司机启动汽车,但一名暴徒躺在了车前。乔治觉得司机也许会开车从那人身上轧过去,但他却熄火了。
一块石头穿过了车窗并,玻璃碎了,乔治觉得面颊像被蜜蜂咬了下似的刺痛。他的脸被一块玻璃碴划了道。玛丽亚坐在窗边:她的处境很危险。乔治拉住她的胳膊,把她拽向自己。“蹲在过道里。”他朝玛丽亚大嚷。
一个手指上戴着铜套的男人狞笑着把拳头伸进琼斯夫人身边的车窗。“和我一起趴下来!”玛丽亚把琼斯夫人拉到地上,用肩膀护住年老的夫人。
吼声越来越大。“该死的共产分子!”暴徒们尖叫着,“你们这群懦夫!”
玛丽亚说:“乔治,快猫下腰!”
乔治不想在这群暴徒面前表现懦弱。
噪声突然消失了。对车厢的敲击告一段落,也没有玻璃被打碎了。乔治看见外面有个警察。
也该是时候了。他想。
警察挥着警棍,但和手指上戴有铜套的男人说话很和气。
乔治发现又来了三个警察。他们让人群平静下来,但让乔治气愤的是,他们除此之外什么都没做。好像这群人并没有违法似的。他们和闹事者们闲聊着,看起来像是朋友。
两个公路巡警靠在各自的椅子上,看上去似乎有点不知所措。乔治猜测这两个人原本只是来监视他们的,没想到会成为群体暴力的受害者。他们被迫和自由之行运动的参与者一起自卫。经过了这么一出以后,他们也许会用全新的视角看问题。
长途车发动了。乔治看见一个警察在挡风玻璃前清走暴徒,另一个警察正在指引司机往前开。在车站外,一辆警车在长途车前把它带上了开往城外的路。
乔治的感觉好了些。“我想我们逃过这一劫了。”他说。
玛丽亚站起身,显然没有受伤。她从乔治的西装胸前的口袋里抽出一块手帕,轻轻地帮他擦了擦脸。白色的手帕上立刻染上了红色的血渍。“一条狰狞的小伤口。”玛丽亚说。
“没事,我死不了。”
“不过你不会像以前那么英俊了。”
“我英俊吗?”
“你曾经很英俊,但现在……”
平静没有维持多久。乔治瞥见一长排小货车和轿车跟在长途车后面。他呻吟一声。“我们还没逃过这一劫。”他说。
玛丽亚说:“我们在华盛顿上车前,我记得你跟一个白人小伙子说话。”
“是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约瑟夫·乌戈,你为什么会提到他?”乔治问。
“我想我在车站的人群中看到了那家伙。”
“不可能,他是我们这边的,你一定搞错了。”但乔治记得,乌戈的确来自阿拉巴马。
玛丽亚说:“他有一对凸出的蓝色眼珠。”
“如果他是暴徒之一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一直假借支持民权运动的名义在监视我们。但他不该是那种告密者啊!”
“你确定吗?”
乔治再次看了看身后。
警车在小镇的边界折转,但其他车辆却没有。
车上的暴徒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声音盖过了汽车的引擎声。
在远郊202高速公路一段车辆很少的直道上,两辆车超过了长途车,然后降速下来,迫使长途车司机刹车。长途车司机试图越过这两辆车,但两辆车一左一右卡在车前,挡住了长途车的超车路线。
科拉·琼斯脸色刷白,不停在抖,像抓着救生圈一样紧紧地抓着白色的塑料手提袋。乔治说:“琼斯夫人,很抱歉把你卷进来。”
“我也很抱歉。”她回答道。
前面两辆车最终停在路旁,长途车超越了它们。但噩梦并没有结束,车队仍然紧随在后。没过多久,乔治听见了一声熟悉的炸裂声,长途车的车身开始摇晃起来,乔治意识到轮胎爆了。司机减慢车速,在路边的一个杂货店边停下了。乔治看了看店牌:福赛斯之家。
司机跳下长途车。乔治听见司机咕哝一声:“怎么爆了两个?”接着他走进杂货店,多半是打电话求助去了。
乔治如同弓弦般紧绷,爆一个胎也许是意外,爆两个就是埋伏了。跟在后面的车果然停了下来。穿着礼拜日西服的十几个白人从车上涌了下来。他们大声咒骂着,挥舞着武器,气势汹汹扑面而来。看到他们的脸充满恨意地扭曲着,乔治的腹部收紧了。他总算明白为何母亲提到南方的白人时泛着泪花了。
领头的是先前在汽车站拿着铁橇敲碎车窗玻璃的少年。跟在后面的那个人试图走上客车。那两个白人乘客中的一个站在台阶上方,拿出一把左轮手枪。玛丽亚的猜测没错,这两个人果然是公路管理局的便衣。入侵者往后退去,便衣警察锁上车门。
乔治觉得这也许是个错误。如果运动参与者需要赶紧下车的时候怎么办呢?车外的人开始摇动汽车,像是要把长途车推翻似的。他们一边摇一边高声喊:“杀死黑鬼,杀死黑鬼!”车上的女乘客们尖叫一片。玛丽亚紧抱着乔治。如果不是面临着生命危险,乔治一定会乐坏的。
乔治看见两个穿着制服的公路巡警朝这边走了过来,心中一下子腾起了希望。但让他发怒的是,这两个巡警并没有约束这群暴徒。他看了眼车上的两个便衣:他们的表情充满了恐惧和愚蠢。显然这两个巡警并不认识他们的卧底同事。阿拉巴马高速公路巡警队显然和这些种族主义者一样,毫无组织纪律。乔治焦虑地思考着解救玛丽亚和自己的方法。下车逃跑?躺在地上?还是抢过便衣的枪射杀几个白人呢?这些选择看起来都比什么都不做要糟。
他满怀怒火地看着窗外那两个似乎什么事都没发生的巡警。该死的!他们都是些警察啊!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如果不能维护法律的话,他们为何要穿上这身制服呢?
接着他看见了约瑟夫·乌戈。肯定不会弄错:乔治看见了那对再熟悉不过的凸出的蓝色眼珠。乌戈走到一个巡警身边,对巡警说了些什么。说完后两个人都笑了。
他是个该死的密探!
如果能活着离开这里,乔治心想,我会让这浑蛋后悔的。
外面的人叫嚷着要运动成员下车。乔治听见他们喊:“快下车,让你们这些黑佬的支持者尝尝我们的厉害!”这让乔治觉得留在车上会安全些。
但情势很快发生了改变。
一个暴徒回到他的车旁,打开了后车箱。很快他拿着一个燃烧物跑向了长途车。过来以后,他往破碎的车窗里扔了一团燃烧物。很快燃烧物腾起一团浓烟。但那不仅仅是个烟雾弹,它点燃了座位上的皮革,黑烟很快让乘客透不过气来。一个女人尖叫着问:“前面的空气足一些吗?”
乔治听见外面的人在喊:“烧死那些黑人,把他们都给烤了!”
人们争先恐后想下车。通道里挤满了气喘吁吁的人们。人们都试图从后往前挤,但前面似乎已经被堵上了。乔治大声嚷:“快下车,所有人都得下车!”
在车厢前部有个人喊着回答了他:“门打不开!”
乔治想起带枪的巡警队便衣为了阻止暴徒上车已经锁上了车门。“我们必须从车窗下去!”他大声喊。“跟我一起跳窗!”
他站上椅子,踢掉了车窗上剩下的大部分玻璃。接着他脱下西装,把它包在窗框上,避免窗框上剩下的玻璃碴伤到跳窗的人。
玛丽亚无助地咳嗽着。乔治对她说:“我先跳下去,你跳的时候我接住你。”他弯腰站在窗框上,抓住车座后背以保持平衡,然后跳下了车。他听见自己的衬衫发出撕裂的声音,但没感觉到疼,于是得出了自己没有受伤的结论。他落在路旁的草丛上。暴徒们害怕燃着的长途车会起火爆炸,早就退后了。乔治转过身,对玛丽亚伸出双臂:“像我一样爬出来就行了。”
和乔治的束脚的牛津鞋比起来,玛丽亚穿的女鞋要轻便得多。看见玛丽亚的小脚站在窗框上,乔治为牺牲了那件西装感到有些高兴。玛丽亚比乔治个子矮,但丰硕的体型却比乔治要宽。乔治看见玛丽亚屁股的部位在窗边的一块玻璃上扫过,眉头不禁皱了起来,但是玻璃碴没有刮破玛丽亚的裙子,玛丽亚很快落在了他的双臂之中。
乔治的体格很好,能够轻易地把不太重的玛丽亚托举起来。他把她轻轻地放在地上,但她却不禁跪下,猛吸起空气来。
乔治看了看周围。暴徒们仍然远离着公共汽车,看来不会过来。他往车里看了看。科拉·琼斯站在过道里大声咳嗽着,她来回转着圈,吓得不知道怎样逃出来。“科拉,到这边来。”她听见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把视线投向乔治。“和我们一样跳下窗户就好了。”乔治大声喊,“我会帮你的。”她似乎明白了,仍然紧抓着手提包站上了车座。看见车窗上参差不齐的玻璃碴,她犹豫了一下。她穿着厚外套,但她似乎觉得扎伤比呛死要好,她很快下定了决心,把一只脚放在了窗框上。乔治把手伸过窗户,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抱了下来。琼斯夫人的外套被刮破了,但人并没有受伤。乔治把琼斯夫人放在地上。琼斯夫人蹒跚着,叫嚷着找水喝。
“我们必须离开这辆车!”乔治大声对玛丽亚说,“油箱说不定会爆炸。”但玛丽亚咳个不停,似乎根本动不了。他一只手环在玛利亚脖子上。另一只手放在她的膝盖后面,把她抱了起来。他把玛丽亚抱进杂货店,放在一个和暴徒保持安全距离的地方。他回头看了看,发现车里慢慢变空。车门最终被打开了,那些没有跳下车的人都跌跌撞撞地走下了车。
车上的火势越来越大。最后一个乘客下车的时候,长途车已经变成了一个烤炉。乔治听见有人在叫油箱什么的,暴徒们接起了这声叫喊:“它马上就要炸了!马上就要炸了!”所有人都退得很远,害怕殃及自身。随着沉闷的一声响和突然爆发的火焰,汽车的油箱爆炸了。乔治很确信车上已经没有人了。他思量着:至少现在还没有人死。
爆炸似乎没有满足暴徒对暴力的渴望。他们围在车旁,看着火越烧越大的公交车。
一小群看上去像是当地人的人聚集在杂货店外面,其中有许多在为暴徒而欢呼。但一个年轻的姑娘却和他们不同,她拿着一壶水和几个塑料杯从一幢房子里走出,给琼斯夫人和玛丽亚倒上两杯水,玛丽亚感激地喝下一杯水,然后问姑娘又要了一杯。
一个年轻的白人一副关心的模样走了过来。他长得像只老鼠,前额和下巴向外凸出,长着一副龅牙,棕红色的头发上涂满了发油。“亲爱的,你还好吗?”来人问玛丽亚。但这个人显然别有他图,当玛丽亚要回答他话的时候,他举起一只撬棍,对准玛丽亚的头顶心砸了下来。乔治伸出胳膊挡住撬棍,撬棍硬生生地砸在了他的左手前臂上。这一撬砸得很重,乔治痛苦地惨叫了一声。年轻人再次举起了撬棍,尽管左臂受了伤,但乔治却扛起右臂,撞到对方身上,把对方给撞飞了。
乔治朝玛丽亚转过身,看见又有三个暴徒朝他们逼近,显然他们想为他们贼眉鼠眼的伙伴报仇。乔治以前从来没想过种族分离分子会如此暴力。
乔治很擅长打斗。大学时,他是哈佛大学摔跤队的一员,拿到法学学位时已经是摔跤队的教练了。但眼下的打斗不同于有章可循的比赛。况且,他这时能用的只剩下一只手了。
另一方面,他曾经上过华盛顿贫民区的学校,知道街上的打斗是多么的不择手段。
三个暴徒并排向乔治扑来,于是乔治退到一边。这样不仅能使他们远离玛丽亚,更可以迫使他们站成一列,必须一个个地和乔治对战。
第一个家伙凶狠地向乔治挥舞起铁链。
乔治往后一跳,躲过了舞动的铁链。铁链的冲力使那家伙一时间失去了平衡。趁他蹒跚的刹那,乔治用力往他腿上踢了一脚,把他踢倒在地,手中的铁链掉在地上。
第二个人跨过地上的同伴。乔治上前一步,侧过身,用右肘击打中了对方的脸,希望能使对方的下巴错位。第二个攻击者惨叫一声,倒了下来,手里的撬棒飞了出去。
第三个攻击者突然害怕地停住了脚步。乔治走到他面前,用尽浑身力气打了他的脸一拳。乔治的拳头正好落在他的鼻子上,骨头被击碎,血液飞溅。他痛苦地发出一声尖叫。这是乔治有生以来挥出的最为满意的一拳。让甘地精神见鬼吧。他这样想到。
两声枪响。所有人都停下打斗,朝枪响的地方看。一个穿着制服的州警高举着手里的左轮手枪。“伙计们,散了吧。”他说,“乐子找完了。”
乔治非常愤怒。乐子?警察目击了暴徒们的杀人未遂,却把这叫作乐子?乔治渐渐开始明白,警察的制服在阿拉巴马不代表任何意义。暴徒们回到了各自的车上。乔治愤怒地发现,四个警察根本没有记下任何一个人的车牌号码,更别提盘问他们的名姓了。不过他们估计也都互相认识。约瑟夫·乌戈已经不见了。
长途车的残骸又发生了第二次爆炸,乔治觉得车上必定还有个油箱。但此时已经没人处在危险范围内了。大火自顾自地烧着。有几个人躺在地上,更多的人在吸入了浓烟以后狂吸着空气。其他人因为不同部位受伤而在流血。有些人是活动的参与者,有些是普通的乘客,黑人白人都有。乔治用右手抓住左手的胳膊,把左胳膊贴紧身体,试图不让它移动,因为只要轻微一动就是阵钻心的疼痛。方才与他打斗的四个男人互相搀扶着走回了自己的车。
乔治蹒跚地走到州警身旁。“我们需要一辆救护车,”他说,“也许需要两辆。”
两位州警中年轻的一位瞪了他一眼:“你说什么?”
“这些人需要医疗救治,”乔治说,“叫辆救护车来!”
巡警看上去气疯了。乔治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不该叫白人干这干那。但年长的州警对他的同事说:“算了,算了。”接着,他对乔治说:“孩子,救护车已经叫了。”
没一会儿,一辆小巴大小的救护车开过来了,自由之行行动的参加者们互相扶持着上了救护车。当乔治和玛丽亚走到救护车前时,司机却说:“你们不能上来。”
乔治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你说什么?”
“这是给白人用的,”司机说,“不是黑人。”
“你说的是什么鬼话啊!”
“别顶撞我,小子!”
一个已经上车的白人行动参与者走下车。“你必须把所有人都送到医院,”他对司机说,“白人和黑人都送去。”
“这辆救护车不送黑人。”司机固执地说。
“我们不能不管朋友。”白人行动参与者们开始挨个走下车。
司机惊呆了。如果空车返回医院,他一定会被人奚落的,乔治猜道。
年纪大些的巡警走了过来,他对救护车司机说:“罗伊,最好带上他们。”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司机说。
乔治和玛丽亚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发动以后,乔治回头看了一眼。长途汽车什么也不剩了,只有滚滚的浓烟和熏黑的残骸,以及一排被熏黑的车顶部支架,它们犹如火刑架上被烧死的烈士的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