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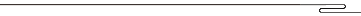
在还未开始这一章的主题之前,我不得不先说几句开场白,来说明一下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有什么样的关系。在之前的一章里我们已经讲过,处在自然环境中的生物是有某种个体变异的。我确实不清楚对于这个论点曾经有过争议。将一群可疑类型称为物种或亚种或者是变种,事实上对于我们的讨论并没有太大的作用。比如,只要承认有些明显的变种存在,那么将不列颠植物里两三百个可疑类型,不管是列入哪一级,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过,只是知道个体变异以及少数的一些明显变种的存在,尽管作为本书的基础是必要的,却很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物种在自然环境中是如何发生的。生物结构中的某一部分对于另一部分还有其对于生活环境所作出的所有巧妙的适应,以及这个生物对于另一个生物的所有看起来顺其自然的适应,是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达到的呢?对于啄木鸟与槲寄生的关系,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那种十分融洽的相互适应关系;对于附着在兽毛抑或是鸟羽上面的那些最下等的寄生物,还有潜水甲虫的构造,以及那些依靠微风飘在风中的具有茸毛的种子等,我们也仅仅是看到了一点点不太明显的适应现象。简单来说,不管在什么地方,不论是生物界里的什么部分,都可以看到这种神奇的适应现象。

啄木鸟独特的攀树、啄树习性,令其与众不同。
接下来,我们还要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那些被称作是初期物种的变种,到最后是怎样发展为一个明确的物种的呢?在绝大多数情况中,物种与物种之间的差别,明显超过了同一物种的变种之间的差别。而构成不同属的物种之间的差异,又比同属物种之间的差异大很多,那么这些种类又是如何出现的呢?所有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论断与问题,应该说,均是从生物的生存斗争中得来的,后面我们会进行更为详尽的讲解。正是因为这样的斗争,不论是如何微小的变异,也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导致了变异的发生,只要对一个物种的个体有积极的意义,那么这个变异就可以让这些个体在与其他生物进行的生存斗争以及与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完好地保存下来,而且这些变异一般都可以遗传给后代。这样,后代们也就得到了较好的生存机会,这是因为一般在所有物种定期产生的许多个体中间,只有少数的个体可以生存下去,现在遗传了变异的个体正是拥有了更好的生存条件。我将每一个有利于生物的细小变异被保存下来的这种现象称作“自然选择”,来区别它与人工选择的关系。不过,斯潘塞先生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最适者生存”,看起来更为准确一些,而且使用起来也更为方便一些。我们已经看到,人类可以利用选择来获得巨大的效益,而且通过累积“自然选择”积攒下来的那些细小并且有用的变异,我们就可以让生物们在我们的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有用。不过,在经历过“自然选择”之后,我们将要看到的,是一种永无止境的神奇力量,它的作用远远地超过了人类的力量所能干涉的范围,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像人类艺术与大自然神奇的作品在做比较,其间存在着的差距,是无法估算出来的。

美国黄石公园的大棱镜泉彩虹般绚烂的颜色来自于蓝藻菌和其他种类的微生物。人们在旁边修筑道路进行观赏,却无法改变,“自然选择”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人类所能干涉的范围。
接下来,我们准备对生存斗争进行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讨论。在我以后的另一本著作中,还会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地进行更多的讨论。老德康多尔和莱尔两位先生之前曾从哲学的角度,向我们说明,所有的生物都暴露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下。对于植物,曼彻斯特区教长赫伯特极有气魄地用自己卓越的才华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很明显这是他拥有着渊博的园艺学知识的缘故。最起码在我看来,只是在口头上承认普遍的生存斗争这个真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当简单易做的事情,不过,如果将这个思想时时刻刻都放在自己的心中,并没有那么容易,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如果不能够在思想中去完完全全地思考这个道理,那么我们就会对包含着分布、繁盛、稀少、绝灭还有变异等诸多事实的自然组成的整体情况出现模糊的认识,也有可能完全将其误解。比如,我们时常看到身边的自然环境向我们展现的是一种明亮而快乐的色彩,我们总能看见很多被剩下的食物,但是我们没有发现甚至是忽略了那些悠然地在我们周围欢唱的鸟儿绝大多数都是以昆虫或植物的种子为食的,这就是在说,它们在觅食的同时常常毁灭一些别的生命。而且,我们也总是忘记或者忽略,那些欢快的鸟儿以及它们生产的蛋,甚至是它们所生产出来的幼鸟又有多少会被其他食肉的鸟以及食肉的兽类所毁灭。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即使现在我们看到的食物是过剩的,并不代表每年的所有季节中都是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