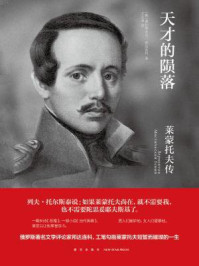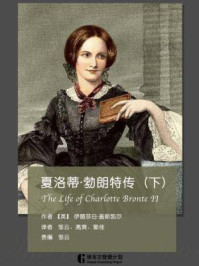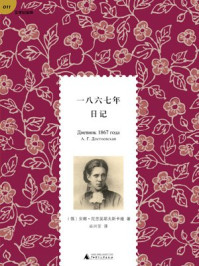本文围绕“争臣”的职责,对阳城在位日久,不问朝政的不负责态度提出了批评,指出圣人贤士应以匡救时弊为己任,“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在其位,谋其政,“居其位,则思死其官”。
【原文】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译文】
有人向我问起谏议大夫阳城:“可以认为这个人是有道德的人吗?他学问渊博,见识也广,又不想出名。学习古人的立身处世的道理,隐居在晋国的边境上。那儿的乡人,有近千人因受到他的道德熏陶而变得品行善良。大臣知道了这件事,就荐举他,天子命他当谏议大夫。大家都觉得荣耀,而阳子却没有得意的表情。他任职已经五年了,看他的品德如同在野时一样。他怎么会因为富贵就改变自己的意志呢?”我回答说:“这就是《易经》中所说的长久地保持一种德操,而不能因事制宜,这是妇人之道,不是大丈夫所遵从的。怎么能够说是有道德的人呢?在《易经·蛊》的‘上九’上说:‘不愿去侍奉王侯,只求自己道德高尚。’《易经·蹇》的‘六二’上说:‘王臣屡次劝谏,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君为国。’这也是因为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实行的道德就不相同。假如像《易经·蛊》的‘上九’所说那样,处在不被重用的地位,却表现出不惜自身的节操;像《易经·蹇》‘六二’所说那样,处于大臣的地位,却将不侍奉天子和诸侯作为高尚的事,那么忧患就要产生,旷废职守的责难就会兴起,这样的志向不能效法,而他的过失也终究不可避免。现在阳子身居官位时间已不短了,对朝政的得失也不是不熟悉了,天子对待他,也够重视的了。可是他没有一句话关系到朝政。他看待朝政的得失,像越国人看待秦国人的胖瘦一样,一点也不在意,在他的心中引不起什么高兴和忧愁。问他的官位,就说是谏议大夫;问他的官俸,就说下大夫的俸禄;问他朝政情况,却说不知道。有道德的人,难道是这样的吗?况且我听说:有官职的人,不能尽职就该辞去;有进言责任的人,不能提出规劝意见就该辞去。阳子能够提出规劝意见吗?能提出规劝意见却不说,和不能提出规劝意见而不辞去,都是错误的。阳子是为了俸禄做官的吗?古人说过:‘做官不是因为贫穷,但是有时是因为贫穷。’说的是那些为俸禄做官的人。应当辞去高位而担任卑贱的职务,放弃富贵而安于贫贱的生活,像当个看门、打更的小吏就可以了。孔子曾当过管粮仓的小吏,曾当过饲养牲畜的小吏,也不敢旷废他的职守。还说‘财物账目相符才行’;‘牛羊顺利成长才行’。像阳子的等级俸禄,不算低下和微薄,这是很清楚的,可是他这样办事,难道是对的吗?”
有人说:“不,并不是这样的。阳子是讨厌毁谤皇上的,厌恶做臣子的因为揭露君主的过失而出名。所以虽然他也规谏和议论,却不让别人知道。《书经》里说:‘你有好计谋好策略,就进去告诉你的君主,然而到外面附和着说,这个计谋这个策略都是我们君主作出的。’阳子的用心,也像是这样的。”我回答说:“如果阳子的用心是这样,那就更是糊涂的了。进去劝谏君主,出来不让人知道,这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该做的。阳子本是平民,隐居于草莽之中,君主赞赏他的品行,提拔到这个位置上。官职既然叫做谏议,实在应当有所作为来奉行他的职守,让天下的人和他们的后代,知道朝廷有直言敢谏的刚正臣子,天子有不滥赏赐和从谏如流的美名。这样就可使山野隐士闻风羡慕,束好衣带,结好头发,主动来到宫阙向主上陈述他们的意见,让我们君主的仁德和尧舜并列,美名光辉至千秋万代。至于《书经》所说的,是大臣宰相的事情,不是阳子所应该做的。而且阳子的用意,不是将使做君主的人厌恶听到自己的过失吗?这是开了君主厌恶听到自己过失的头了。”
有人说:“阳子不求出名而别人都知道他,不求任用而君主任用了他,不得已才出来做官的,保持他的德行而不改变,为什么您要那样厉害地指责他呢?”我说:“自古以来圣人贤士都是不求闻名和任用的,只是怜悯时世不太平,百姓生活不安定,有了道德学问不敢独善其身,一定要用来普救天下,勤奋努力,到死方休。所以夏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孔子回家,坐席未曾坐暖过;墨子回家,烟囱还来不及烧黑,就又出行了。这两位圣人,一位贤人,难道不知道自己过安乐的日子是舒服的吗?实在是畏惧天命而可怜人民穷困啊。上天将道德、智慧和才能授给圣贤,不只是让他自己有余而已,实在是希望他去帮助愚笨的世人。耳目对于人身,耳朵管听,眼睛管看,听清是非,看明安危,而后身体才得到安全。圣人贤人,就好比是世人的耳目;世人,就好比是圣人贤人的身体。再说,阳子如果不贤明,就应当为贤人所役使来奉事他的君主;若是果真贤明,那么本来就应当畏惧天命而怜悯人民的穷苦。怎么可以只图自己闲适安逸呢?”
有人说:“我听说君子不把自己所不要的东西加在别人身上,而且憎恨那种揭发别人的短处却自以为直率的人,像您的议论,直率是够直率了,只怕伤害道德,多费口舌了吧?喜欢直言不讳来揭发别人的过失,这就是国武子在齐国被杀的原因,您大概也听说过吧?”我说:“君子有了官职,就想到以身殉职。没有做官,就想到修饰文辞来阐明道理。我要用言辞来说明道理,不是自命正直而把自己所不要的东西加在别人身上。况且国武子是因为没有遇到善良的人,却喜欢在国乱时直言不讳,所以才会被杀。古书上说:‘只有好人能听从直言规劝。’这是说好人听到规劝的意见才会改正。你告诉我说:‘可以认为阳子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了。’虽然现在还没有达到,难道阳子将来就不能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