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现梦想是你和这个世界更好的接触,我们要接触不同的人群,去寻找梦想实现的可能性。人分三六九等,这不是你可以屈服于梦想的理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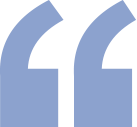
2004年9月27日 星期一 晴
今天,风和日丽,很闷热。我和阿彬一起,经过多项分析排除,最后,不约而同地把目标定在了晋安河畔。那儿人员混乱,莆田的小伙(子)居多,环保意识比较薄弱。
来到那儿才知道,那儿的人不像我们想象中的懒与散漫,他们非常热爱树木花草。有了上次拾垃圾的经验,我们不再怕生,不再怕别人的目光。我们绕着晋安河畔找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瓶瓶罐罐,我们失望极了,但我们没有灰心。我与阿彬从桥头绕到胡同尾,每片草丛,每片树荫,每个可疑的物品,我们都一一翻查。失望、绝望如一池冰水毫不怜悯的(地)泼入体内,汗水和泪水在心中交错。不会有了,已经半个多小时了。我和阿彬几乎(不)抱任何希望了,我真怕再一次失望。
“快来!”阿彬几乎用尽了力气朝我喊。我立刻燃起了希望,在草坪上,一个易拉罐赫然闪现。当时的那种兴奋和快乐是不能用华丽的辞藻来表示(达)的。心中的希望死灰复燃,只是……在草坪上的易拉罐离我们很近,但中间阁(隔)了一道草墙。谁翻?谁也不想翻。我凭着我的敏捷,借助立在草墙后的灯杆,跳进草丛。在拿到易拉罐的那一刻,它仿佛不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易拉罐,而是一颗炽热的心呀!
一角钱,我们来之不易的一角钱,也许伸手就可以,可它是多么来之不易呀!千辛万苦,这钱仿佛是那样热,那样重,有千斤,有万两。
我们在晋安河畔,只捡到了1个易拉罐。我们转回洋下社区时,又惊喜的(地)发现了两个塑料罐。正好有辆收废品的车驶过,我们忙拖住他,费尽口舌,他才边犹豫边无奈地抓出钱包,翻了翻,有零钱!太好了,我和阿彬一人拿了一角,心满意足地回家了。我感受到,水晶宫里的公主长大了,懂得钱的分量了。同时,我也为福州人的环保意识提高备感高兴。
总计:1个易拉罐、2个塑料瓶
合计:2角
分得:1角

我不清楚人们大多是在什么年龄懂得了“世人皆同”是句谎话,但十岁那年,我已经能在日记中写出“河那边的人”这样明显的划分。
似乎没有童话告诉我们人分三六九等,但似乎每个童话又都在告诉我们,人是怎样一种充满阶级性的动物。
豌豆公主即便落难也能被王子发现,是因为五谷不分的贵族生涯给她带来的幼嫩肌肤。
辛德瑞拉之所以受到王子的青睐,是因为她出身于王爵家庭,又有仙女教母心心念念地为她量身定制礼服与水晶鞋。
白雪公主之所以能吐出毒苹果、与王子喜结连理,除了拥有超强的主角光环,究其身份,也是个锦衣玉食的至尊公主。
《城南旧事》的小英子对着蹲在草地里的贼说:“我分不清海和天,我分不清好人和坏人,人太多了,我分不清。”只有笨拙的小孩子才会执着于分清好人与坏人,大人总能用他们自认为正确的准则,去评判、分辨、区别身边的一切人与物。
前文说过,老家附近有一条晋安河。这条河大有来头,值得说说。它早在千年前是条无名小河,时过境迁便成为市区内最长的内河。老家附近的那段,是它中游的一小段死水。
幼年嬉笑怒骂四下撒野时,便听长辈吓唬我们,小孩子不能去那河对面,河对面尽是些魑魅魍魉,小孩子看不得。
我小时候可不是那类敛得住性子的孩子,都说小孩儿看不得,那我便偏要去会会它。于是趁放学后到了河对面,结果好不扫兴。那些来来往往的人,也不过是两枚黑眼珠子配俩鼻窟窿眼儿。
后来到了小学三四年级,懂得看社会新闻版面,才识得“河对岸的东西”是什么。
对面住着两种人:一种被人唤作“妓”,一种被人称作“贼”。
这条街属于几个娱乐区域的交界处,各种灯红酒绿的产业集中。“河那边”是附近地价最便宜的地方,多为房龄极老的房子,自然受到了这些生活边缘人的青睐。
但见识多了,却更加不解。童稚时,读罢《柳如是传》,以为如河东君般顾盼生姿、倜傥自如才能自称为妓。后来发觉“妓”是个贬义词,指自甘堕落的风尘女子,但在形象上至少也该是“腰肢细软身婀娜”。我怎么也不能将那些站立于桥头,黑丝袜里挤出白花花的赘肉,满身葱姜蒜味的中年女人和“妓”这个词产生联系。
童年的初春,柳絮倏地钻进我鼻子,我透过桥头花片子和石狮子的空隙,看到一群女人有着比母亲还要下垂的乳房和暗沉的肌肤,五短身材却穿着比脚脖子还高的高跟鞋。她们谈笑风生地拥在一起,一会儿聊着别家男人的床上本事,一会儿聊起等会儿“做完那事”要顺路买菜回去给自家孩子煮饭吃。那一刹那,她们因过度兴奋而红光满面的脸颊至今烙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成为少女时代对“妓”怀有的文艺想象里,被现实打得最响的一记耳光。
和“妓”一起住在河对岸的,自然还有“贼”。盗夫淫妻,夫妻双双把家还。那时候,我还未曾见过贼,只隐约觉得大概是动画片里凶神恶煞的形象,或者像来往搭起的戏台里的那个白脸高俅。
后来有一阵子,附近自行车盗窃案频发。查来查去就查到了“河对面”的一户人家,社区纠察队破门进去的时候,刚刚睡醒正煮着面的男人一脸愕然。面还没煮熟,在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响声,纠察队就已经冲进自建房的后院里搜出了几辆丢失的自行车,真有点“温酒斩华雄”的意思。
那时候我还小,第二天就在教室里大肆宣传昨天见到了捉小偷的奇闻妙事。大家不相信,纷纷问我,让我描述究竟是怎样的情形,我却一时语塞,不知所措。一来是站得远,对于具体情形确实也没有看出个大概;二来我实在不知道怎样形容一个小偷的脸。
无论是“大小眼、瓢儿嘴、四只眼睛八条腿”还是“奸佞、丑陋、歪瓜裂枣”,都无法对号入座。原来他们也只是满脸刻着“生活”二字的普通人。
可能当你仔细观察每个生命最原始的形貌时,它们都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一样丑陋,也一样具有独特的美丽。
人们总是惯用一个标签去归纳同类的人,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自认为这是方便的手段。就像我曾经在十岁的日记里这样形容“河那边的人”,但在日记的结尾,我们才终于发现,事实并不如我们所料,河那边不仅有荆棘,也有芦苇。
女人为妓,她的破炉在晌午时分也会飘起缕缕炊烟。令人唾弃的贼,或许在某个只属于他的温柔角落,正在为家人撑起一片天。
不要为他人贴标签,更不要随便朝人乱扔石子。每个梦想都给我机会遇见不同的人:走错路的,走对路的;走上坡路的,走下坡路的;走反方向的。或许有些陌生人出现的意义,就是在黑魆魆的途中引火烧身,却用那光亮让你明白,什么是错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