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一个梦想是可以纸上谈兵的。想到梦想立即行动,趁着兴奋感还未完全消磨殆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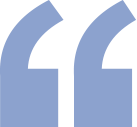
2004年9月24日 星期五 晴
今天,我和王一、阿彬一起捡垃圾。我们用手一点点的(地)把易拉罐从垃圾堆里扒出来。垃圾堆又脏又臭,还有恶心的残渣和骨头。我们细嫩的手很快也变的(得)又脏又臭。我们把扒出来的易拉罐放到一个抬(拾)来的袋子里,虽然很恶心,我们却像珍宝似的搂在怀里,轮流提着。
在学校里,我们共抬(拾)了1个易拉罐与7个塑料瓶。我们在学校里转了又转,转了好久,在确定没有罐子后,才走出学校。我们先向后走,把每个可能有垃圾的地方都一一盘查(翻看)。每个花莆(圃),我们都刨土,观察。路过的行人都看着我们,像是看稀有动物似的,那目光,好像是看不起,又好像是怜悯。有两个男中学生盯着我们,好像看着四处乞讨的乞丐。我们愕然了。
洋下新村最前面的小花莆(圃)臭气熏天。这里,是老鼠、野猫生存的偏僻地方,也是垃圾最多的地方。花莆(圃)里长着长长的野草和一种带刺的花,蚊子数不胜数。我们小心翼翼地踏入草丛,惊起了几只野猫。找到了!在臭烘烘的垃圾山上,有一个瓶子。为了这个瓶子,我们很小心地踏入草丛,把身子俯下来捡。
终于走完了,我们在校外抬(拾)了5个塑料瓶。我们好不容易从巷子里拖回一个(收废品的)叔叔。我们恳求他多给我们两角钱,叔叔显然不愿意,像看着一群小饿鬼一样望着我们。我们可怜巴巴的(地)求他,恨不得跪下来求他。我们缠着叔叔,叔叔心软了,拿出一块钱,我们恳求他多给我们两角钱,当时,我们只有一角零钱(可以找给他)。叔叔收下了,没说什么,便骑车走了。
我们三个卖了9角钱,走遍了附近的铺子,没有一家愿意给一群肮脏的小鬼头换(零)钱。我们跑到王一家,王一的奶奶犹豫了很久才把钱换给我们,我们高兴极了,把钱平分了,忘了累忘了饿。我们为了这些小罐子累的(得)受不了。
疲惫不堪的我一回家便躺在椅子上,再也不想起来了。
总计:1个易拉罐、12个瓶子
合计:9角
分得:3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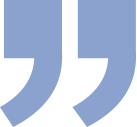
2004年9月24日这一天,我们第一次上街拾垃圾,成了一群在别人眼中臭烘烘的小孩。
这是第一天的日记,我将它完完整整、毫不删减地复制下来。我无从揣摩自己当时的心迹,但它无疑是疲惫却兴奋的。
第一天上街拾荒,我们和每个行业的初学者一样束手无策,甚至连装垃圾的袋子都没准备,顺手在垃圾堆里捡了一个。
经历虽然狼狈,但对于三个年仅十岁的孩子来说已经足够振奋人心。
2004年,电视上正热播一部赚人热泪的电视剧,叫《亲情树》。故事主要讲述的是母亲去世后,大姐独自抚养三个弟妹。有一天,三个孩子为了赚钱去大街小巷拾垃圾,后来被大姐拎回家狠狠揍了一顿。
我们虽年少,但隐约能从电视里知道这是件见不得光的事。阿彬、王一和我,相约要保守这个秘密。
阿彬刚从泉州一个叫永春的地方转学过来,据她说,她住的地方盛产芦柑,却没有公路可以到达,想要见到四轮车的影子,就要先走出村再走出山再雇个小摩托到镇上。在我尚分不清柑子、橘子、橙子的年纪,曾经在大夏天望着英子店里大通铺上的橘子,将其想成阿彬家乡成片的芦柑。小时候看过《橘子红了》,也不知怎么就记住了秀禾和耀辉少爷在橘子园里你侬我侬的模样,于是就以为那橘子树真像剧里那样高高大大的,总幻想能和阿彬奔跑在其中,恣意撒野。后来才知道那是剧组特意千辛万苦摘下来后往高树上挂的,以掩盖橘子树本身矮坨坨的惨状。
阿彬的父亲曾经是个泥瓦匠,读过很多年书,在城里干过很多活儿。后来摔断了腿,每天卧在老家的土坯房里,活生生把阿彬的妈妈给吓走了。他们租在离学校有几条街的地方,离我们家也不近,所以我并不担心阿彬走漏风声。
我贪玩,成绩忽上忽下,没个定数。老师总说:“项瑶啊,脑子是很好用,要是能再努力些就好了。”我属于“赞美藏进耳朵,挨批就装耳聋”的人,往往只听了前半句,就自觉聪明,扬扬得意。而阿彬的成绩是扎扎实实的好,甚至比我还好那么一点点。她说自己在老家总是拿第一,而我虽然摆出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心里却想着:她怎么能这么厉害,回回都考前几名。
他们家只有一间屋子,灶台、马桶、床、书桌都在那间屋里。灶台挨着床,一到回暖天的时候,天穹似盖,将屋子闷得透不过气时,烧起火来整间屋子都烟熏火燎的。“马桶”其实是个小红痰盂,没有管道连接地下,进进出出都要倒马桶刷马桶。
阿彬的父亲终年卧病在床,但穿着很考究。褥子很干净,就算在回潮的日子里,也没什么难闻的气味。他每天都要挣扎着在床上翻几次身,所以并没有长褥疮。我们去阿彬家找她的时候,多半是看见这样的情景:阿彬爸爸斜靠在床上或是拄拐站在墙边,拿着一根小竹鞭,和颜悦色地对我们说“小同学,你们再等等,阿彬做完作业就来”,回头对着阿彬一甩棍子骂:“阿彬,还不快写,没写完不准出去!”
我挺害怕阿彬爸爸的,每次见面都像是老鼠见了猫,飞快地跑掉,生怕那小鞭子落在自己身上。
王一和我一样,是从小学一年级就在这所学校的。她和我住在同一条巷子里,隔在巷头和巷尾。她的脑子比别人慢半拍,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支吾半天也说不清个所以然来。王一虽然叫王一,但甭说拿第一了,从上一年级起她就从没及格过。在五年级之前,我戴着“二道杠”,总和别的“三道杠”“一道杠”玩成一伙,后来“三道杠”“一道杠”都转学走了,因为我俩住得近,就成了共同上下学的玩伴。
在小学生心里,同样坐在教室里的学生早已分了梯队,成人世界里的规矩在这里一样盛行。不同的就是,这梯队并没有显得多么重要,一颗糖、一支铅笔就能将它瞬间瓦解。
王一跟着姥姥和姥爷生活。姥姥老了,有些耳背,不论什么时候都是一脸慈祥地看着我们,偶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币,硬要塞到王一的兜里。休息时她就搬着一张破藤椅,坐在巷子口,边晒太阳边等王一放学。
王一的母亲在远郊的县城做公务员,一周只能回来一次。母亲快要回来的前一天,是王一最紧张的时候。倒不是情感上的紧张,只是小孩子通常都不像父母期望的那般期望父母回来,毕竟父母一回来,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约束。她的父亲在外地做生意,平时见不到几次。小时候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羡慕王一到了有点嫉妒的地步,以至于在这之后,听到媒体报道“留守儿童”这四个字,我还有些不能理解——爸妈不在身边,该是个多么快活自在的事儿啊!
我对王一还是有些不放心,攥紧拳头,恶狠狠地吓唬她:“王一,你千万别和我妈说,否则要你好看!”
“啊?唔……那好吧。”
别看王一平时是闷声不响的,但以她这一触即惊的胆量,说不准哪天被逼问,就说漏嘴了。
曾经看过某部外国作品上形容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说每个孩子都是脆弱的白瓷杯。它没有釉彩,不盛汤水,有些粗心的家长一接过就失手打碎了,有些家长在不经意间就让杯子有了条裂纹还浑然不知,有些父母安了把手小心翼翼呵护着,却因为那把手让它失去了原貌。
有的时候我观察那些最终达成梦想的人,他们的路越走越宽,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合作伙伴。在与他们合作的时候,我会感受到轻松与舒适,他们说的每一句话犹如春风拂面,都给予另一方百分之百的尊重。
那时候我才发现,成功者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不但可以孤军奋战,还可以协同作战;可以单枪匹马,也可以带队同行。
王一和阿彬成了我在拾荒路上最初的伙伴。第一天组队,我们揣着三个钢镚儿,带着一身腐化物的臭气,哼哼唱唱地回了家,结束了拾荒的初体验。
我们总被某些“鸡汤”欺骗,以为化蛹成蝶是生命的必经之途,实则不然。某些成长,就像蝼蛄,从若虫化为成虫,只是形貌与心理顺其自然地发展。我所谓的成长,如同破茧成蝶,彻底放弃原来的外形和样貌。它从具体的某一天某个时刻开始,那一刻的布景能随时在脑海里重建起来,原景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