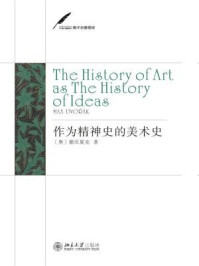对于东北流域史的研究与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长期以来,我一直从事东北地域的田野调查,发现许多人类的遗存遗迹,以及重要的古代军镇、城镇、城市等重要的遗址几乎都分布在流域的左右两岸。特别是东北地区的江、河流域虽然有着漫长的冬季,在寒冷的冬天这些江河的表面都被厚厚的冰层所覆盖,但是在坚硬的冰层下面则依然是江水滔滔、激流滚滚。黑龙江流域就是这样一条流淌在地球寒带的大河。
生活在广袤的黑龙江流域的古代各民族就是依靠这条大河创造了独特的历史与文化。此外,那些作为东北流域发祥地的山脉与山峰也是地下水极其丰富的地域。山有多高,山泉水就会抬升多高。这种特殊的现象使东北古代民族在独立发展过程中为了防御和自身的安全,学会在山顶上修筑坚固的堡垒式的山城。无论是西辽河流域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古族,还是
 貊人、夫余人、高句丽人、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等,他们都学会了寻找在有泉水的山顶上修筑堡垒与坚固的城池。即使在平原地区修筑较大的平原城他们也要寻找靠近江河流域的地方修筑。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后,发现流域对人类的繁衍、民族的迁徙与驻足,以及社会的发展、商业交通、城市的文化的发生与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人类的活动与民族的迁徙,甚至是文化的分布都离不开一条条缓缓流淌的江河及其流域。尤其是人类开始驯服大型动物驱使和依靠他们进行迁徙活动时,就更离不开江河流域的走向。江河流域不仅成为各个民族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后来划分疆界、疆域、境界、边境,以及国境意识的重要依据。
貊人、夫余人、高句丽人、挹娄人、勿吉人、靺鞨人、女真人等,他们都学会了寻找在有泉水的山顶上修筑堡垒与坚固的城池。即使在平原地区修筑较大的平原城他们也要寻找靠近江河流域的地方修筑。我注意到这种现象后,发现流域对人类的繁衍、民族的迁徙与驻足,以及社会的发展、商业交通、城市的文化的发生与繁荣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实人类的活动与民族的迁徙,甚至是文化的分布都离不开一条条缓缓流淌的江河及其流域。尤其是人类开始驯服大型动物驱使和依靠他们进行迁徙活动时,就更离不开江河流域的走向。江河流域不仅成为各个民族生存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成为后来划分疆界、疆域、境界、边境,以及国境意识的重要依据。
中国东北地区历史与文化并非是以现在人们所熟知的行政区划的姿态存在着,而是沿着江河流域或沿海、沿湖的走向分布着。从流域文明的视角来看待东北区域史就是人与水交融的历史,人类的繁衍、民族的迁徙、城市的出现、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变迁无不与流域有着深刻的关系。因此,我认为重新审视东北区域的古代历史与文化,以流域淡化行政区域,以流域打破国界的限制,从流域的角度看待古代中国东北区域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其一,流域文明研究对民族学的意义与价值。
在我国的边疆地区自古以来就生存和繁衍着为数众多的古代民族,事实上,“逐水草而居”不仅是北方草原和西北高山牧场地带的游牧民族生存与生活方式,同时也是绝大多数温带与亚热带民族的生存与生活方式。这一点在西北地区的河西走廊和新疆南疆盆地表现得尤为突出,上述地区气候干旱、雨水稀少,民族群落往往沿河流及绿洲呈带状或星罗棋布般分布。以今伊犁为中心的伊犁河和伊塞克湖流域,由于其宜人的气候和水草丰美、适宜放牧的高山牧场,使这里自古至今都是各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大熔炉。塞种、乌孙、大月氏、突厥、回鹘、葛逻禄、喀喇契丹、察合台、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在这里,共同演绎出绚烂的伊犁河流域文明。在蒙古高原上,匈奴、柔然、高车、突厥、鲜卑、契丹、蒙古等强盛的游牧民族;始终没有离开作为黑龙江流域源头的“三河源之地”,即土拉河、鄂嫩河和克鲁伦河流域,并以此为根据地实现了驰骋欧亚大陆的对外征服与扩张。
流域文明对东北地区古代民族的发生、发展和壮大影响重大。这是因为,东北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狩猎、采集、渔猎、游牧、农耕、冶炼、交通等不同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长期并存和互补。纵观东北古代民族的历史,河流的发源地或汇聚地往往是古代民族繁衍发展的聚居区,而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则构成了东北古代民族自由迁徙的通衢大道。如分布在乌裕尔河与嫩江流域的索离国王子沿嫩江流域南下进入松花江流域上游一带建立了夫余国。索离人的南下又推动了原分布于松花江上游的一部分
 人南下,越过哈达岭和龙岗山脉进入浑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地区。夫余国王子邹牟则沿着与
人南下,越过哈达岭和龙岗山脉进入浑河流域和辽东半岛地区。夫余国王子邹牟则沿着与
 人南下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辽东的浑江流域,并在浑江与富尔江交汇处建立了以纥升骨城(今桓仁五女山城)为王都的高句丽政权。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则是沿着浑江河谷进入鸭绿江上游流域,在狭窄的鸭绿江中游河谷溯江而上抵达今吉林省集安市的鸭绿江畔。东北地区的肃慎-满洲族系的分布也始终没有离开过“三江地区”,尤其是同属于黑龙江流域的牡丹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都成了肃慎民族繁衍壮大的重要区域。从肃慎王城(即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三家子古城)的建立;挹娄人、勿吉人则在乌苏里江流域支流七星河流域建立了王都之所,到渤海国建立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城池的地理位置都没有离开图们江、鸭绿江、东辽河、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女真始祖函普从仆干水之涯迁徙定居在海古勒水,最终依托按出虎水、松花江流域南下逐鹿中原,也都是依托流域而发展壮大起来。在满洲族源神话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顺牡丹江而下,至松花江流域下游的“三姓”之地(即今依兰县),也说明了满洲族更是依托流域而发展的事实。
人南下大致相同的路线进入辽东的浑江流域,并在浑江与富尔江交汇处建立了以纥升骨城(今桓仁五女山城)为王都的高句丽政权。高句丽迁都国内城,则是沿着浑江河谷进入鸭绿江上游流域,在狭窄的鸭绿江中游河谷溯江而上抵达今吉林省集安市的鸭绿江畔。东北地区的肃慎-满洲族系的分布也始终没有离开过“三江地区”,尤其是同属于黑龙江流域的牡丹江流域、松花江流域、乌苏里江流域都成了肃慎民族繁衍壮大的重要区域。从肃慎王城(即今牡丹江流域的宁安三家子古城)的建立;挹娄人、勿吉人则在乌苏里江流域支流七星河流域建立了王都之所,到渤海国建立的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的城池的地理位置都没有离开图们江、鸭绿江、东辽河、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流域。女真始祖函普从仆干水之涯迁徙定居在海古勒水,最终依托按出虎水、松花江流域南下逐鹿中原,也都是依托流域而发展壮大起来。在满洲族源神话中,始祖布库里雍顺乘舟顺牡丹江而下,至松花江流域下游的“三姓”之地(即今依兰县),也说明了满洲族更是依托流域而发展的事实。
其二,流域文明研究对区域史尤其是边疆史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进行区域史与边疆史方面的研究,事实上更能较完整地展现出东北区域的历史与文化,从而避免东北古代历史文化的碎片化和片面化。中国东北的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都是当代的跨国性的河流;其古代民族的历史文化特征显然是一个整体。然而,在当代民族国家疆域的限制下其历史文化特征则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上述东北地区的这些流域无不与蒙古、俄罗斯、朝鲜三国在地域上水道相通,山脉相连,同一条水系的历史与文化被解释成不同的国家历史与文化的现象则成为争论的焦点。总之,流域文明的视角对淡化古代历史与文化的边境意识,保证跨国民族学研究的整体性,促进区域和平发展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边疆地区是区域史视野中一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对于涉及多国的跨国边疆史而言,古代的历史区域发展的形成往往不以当今国际环境的变迁和国境线的走向所决定着,而更多是呈现出区域性和边疆地区的同一性特征。以中国东北为例,当今中国东北疆域的形成是近代以来东亚近代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环境变迁的产物,作为“东北亚内陆”的东北边疆,周边环绕着蒙古国、俄罗斯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东北亚三国。在东北五大流域文明中,黑龙江流域、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以及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的历史文化均具有跨国境的特点,东北边疆的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问题便常常与国家利益、民族问题搅合在一起。研究这一边疆地带的历史文化就不可能回避当代国境线两侧的不同国家的利益与关系。如果一味地从当代的政治地缘角度看待历史问题,就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争论。这种情况一旦受到民族主义情绪的强烈刺激,对其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就变得十分复杂,继而由学术问题转变为牵涉国家利益的政治问题。因此,以流域文明的视角解读边疆史和区域史,有利于相关诸国学者淡化国界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所导致的极端的民族国家认同和族群认同,弱化因疆界划分而产生对历史与文化的阉割,增强整体史观与客观理性地开展跨国境的历史文化研究,避免历史问题现实化、政治化、民族主义化,增强共同拥有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感。
其三,流域文明研究对东北边疆地区和平发展与国际交流意义。
以流域文明的视角展开对东北亚内陆地区跨国的历史文化交流史的研究,这种全新的学术理念对我国与相关周邻国家的彼此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和平共处具有重要意义。流域文明的视野重新整合了跨国区域间的联系,并促进各国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方面进行广泛合作。为当前我国与蒙古、俄罗斯、朝鲜等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借鉴依据。同时,流域文明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中、俄、蒙建立黑龙江流域陆海联运的大通道与经济走廊建设,利用图们江流域、鸭绿江流域打造中朝边境城市的对接,实现中、俄、朝三国大图们江区域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旅游资源开发等诸多领域提供有益的帮助。总之,流域文明的研究会有效促进和推动东北亚区域内陆的国际合作与和平共赢的进一步深化。
其四,流域文明研究对开展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流域文明的角度研究人类学,是对流域范围内人地关系的探讨,更能对流域中各民族交往与融合轨迹的窥探。贵州民族学与人类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宇晓教授指出:“流域是以河流为中心的人-地-水相互作用的自然-社会综合体,以水为纽带,将上中下游和左右岸的自然体和人类群体连接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人类生活世界的本体系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流域作为人类群聚与繁衍的最基本自然单元,多维立体化地展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景象,深刻地反映了人地关系伴随着自然与人为因素改变而产生的波动、对立与调和。有学者已深刻地指出:“流域既是自然资源、人类群体聚散认同、人地关系行为、文化多样性和历史记忆的群集单元,也是物质及能量流动、人口迁移和文化传布的廊道线路,更是人-地-水交叉互动的复合系统,具有面上的区域性、整体性、层次性、复杂性和协同演化特征。因此,以流域为视角,可以更好地将点、线、面三个层次上的研究融为一体,实现人类学的整全观。”
 我国东北“流域”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呈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对松花江流域下游赫哲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其所撰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划时代巨著。该书以松花江下游为自然主线,对赫哲族文化风俗进行研究,展现了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对“流域文明”研究范式的自觉运用和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年代,由张光直教授组织领导的“台湾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则是流域人类学在现代学术视阈下的一次积极实践。到目前为止,流域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根据不同流域而自成体系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民族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研究范式,并为当代流域环境开发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我国东北“流域”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的主体性呈现,始于20世纪3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对松花江流域下游赫哲族进行了实地考察,其所撰写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划时代巨著。该书以松花江下游为自然主线,对赫哲族文化风俗进行研究,展现了中国第一代人类学家对“流域文明”研究范式的自觉运用和意识的觉醒。20世纪70年代,由张光直教授组织领导的“台湾浊水溪与大肚溪流域自然史与文化史科际研究计划”,则是流域人类学在现代学术视阈下的一次积极实践。到目前为止,流域人类学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根据不同流域而自成体系的多样性文明、多样性民族生态和人类社会的重要研究范式,并为当代流域环境开发与治理,提供了新的解决思路。
当然,流域史的研究对于当下理解环境对人类的影响更是极为深刻和刻不容缓的事情。如果当江河枯竭的时候,人们再去注重流域与人类的关系就会导致亡羊补牢的恶果。
总之,流域文明正是在当今区域史与“整体史观”思潮下,最新研究审视区域史所呈现出来的新思考。其创新性与实用性,已经在民族学、人类学、边疆学、环境学、跨国区域社会发展与交流合作等多个学术领域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研究模式,既冲破了固有区域史思维和研究理念对学术发展的制约和禁锢,同时也打破了现实中行政界线和国境线对区域历史文化的阉割和肢解。对淡化界限意识、边境意识缓和国家和民族的情绪对立、消弭民族主义情绪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使我们得以以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态度去尝试重建区域史和边疆史。诚如葛兆光所言:“超越简单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对超国家区域的历史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种相当有意义的研究范式,它使得历史研究更加切合‘移动的历史’本身。”
 人类的繁衍与迁徙是依水而居,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独有模式,即使是农耕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按照流域或水的自然分布而移动着变化着。打破陈旧的窠臼,建立以流域文明为核心的多学科并联、聚合多领域交融的“边疆区域流域学”则成为当下史学界创新的重要议题。
人类的繁衍与迁徙是依水而居,实际上不仅仅是游牧民族有“逐水草而居”的独有模式,即使是农耕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是按照流域或水的自然分布而移动着变化着。打破陈旧的窠臼,建立以流域文明为核心的多学科并联、聚合多领域交融的“边疆区域流域学”则成为当下史学界创新的重要议题。
本书主要是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所发表的与东北流域相关的一些论文,我的妻子王宏北教授帮我完成了论文的汇总和编排工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吴超先生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心血。我的研究生刘佳明、寇博文、王俊铮等同学都为本书出力甚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王禹浪
2016年6月于大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