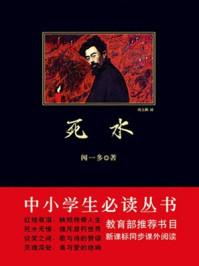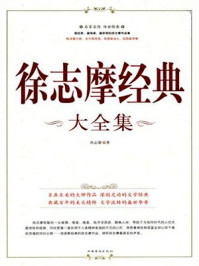|
玫瑰的秘密
叶芝 |
|
本书由新华先锋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凯尔特的曙光
仙军出动
军队从诺克纳里尔骑来,
越过克鲁施纳贝尔的坟墓;
考尔特甩动他燃烧的头发,
尼艾姆叫喊着:“离开,快离开;
掏空你心中世俗的梦幻。
风儿苏醒,叶儿回旋,
我们的脸颊苍白,我们的头发未曾绑起,
我们的心胸剧烈起伏,我们的眼睛闪烁微光,
我们的双臂挥动摇摆,我们的双唇分离张开,
如果任何目光凝视我们这帮冲锋的军队,
我们便会进入他和他的手头之事之间,
我们便会进入他和他的心灵之光之间。”
军队正奔向夜晚和白昼之中;
在哪儿会有这样的心灵之光和手头之事呢?
考尔特甩动他燃烧的头发,
尼艾姆叫喊着:“离开,快离开。”
我就像每个艺术家一样,渴望从这个糟糕愚蠢的世界上的那些美丽、愉快、重要的事物中创造出一个小小的世界,并且通过幻象向任何听从我恳求的同胞展现爱尔兰的面貌。因此,我精确公正地写下了许多我看过的、听过的事情,除了评论的部分,其他没有什么是“出自于我的想象。然而,我却不必苦恼于将我自己的信念同农夫的区分开,而是宁可让我的男人和女人们,精灵和仙人们,不被冒犯地顺其发展,或者用我的理由来为他们作辩护。
一个人听到的和看到的即为生命的丝线,如果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从记忆这个混乱的纺锤中剥离出来,那么任何人都能将它们织入最合他们心意的信念之衫中。我与其他人一样编织着我的衣服,然而我将尝试着保存它的温暖,如果它适合我的话,我将心满意足。
希望和记忆的女儿名为艺术,她建造的住所远离那片绝望的战场,在那片战场上,人们在分叉的树枝上晾挂他们的衣服,于是衣服便成了战斗的旗帜。啊,心爱的希望和记忆的女儿,请在我身边停留一会儿吧!
我按照之前章节的风格添加了许多篇章,并且还会再增加其他的。然而随着一个人的成长,他便失去了某些梦想之轻。他开始用双手抬起生活的重担,他更关心果实而不是花朵,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大的损失。就像之前的章节一样,在这些新的篇章中,除了我自己的评论,没有什么是凭空捏造的。有一两句欺骗性的句子,可能是为了保护一些可怜的讲故事的人与魔鬼、他的信使还有类似东西之间的交流不为他们的邻居所知。再过一小段时间我将会出版一本关于仙人国度的大书,并且将会尝试使那本大书足够系统与博学,从而为这一把失去的梦想之轻请求原谅。
威廉-巴特勒-叶芝
故事的叙述者
书中的许多故事是由一个叫帕蒂-弗林的人告诉我的,他是一个瘦小的有着明亮眼睛的老人,居住在巴利索戴尔村中一个只有一间房还漏雨的小棚屋里。他经常说“在整个斯莱戈郡中,巴利索戴尔村是最为高贵的地方”--他的意思是像仙境一般。其他人承认这是事实,只不过还是仅仅次于德拉姆克里夫村和德拉姆亥尔村。我初次见到他时,他正在烹煮蘑菇。第二次见到他时,他正酣睡于树篱下,睡梦中微笑着。的确,他总是很快乐,虽然我觉得我能够看到他的眼睛里(就像野兔从洞穴中向外张望时的眼睛一样敏锐)有一丝忧郁,隐藏在那快乐之下。那是一种可见的发自纯洁本能的忧郁,存在于所有事物中。
然而在他的生命中有太多的东西压抑着他。他孤独地走过了三十年,他性格古怪,还双耳失聪,当他四处走动时,会被孩子们不断纠缠。可能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不断地提及欢笑和希望。例如,他喜欢讲述圣克伦巴使他的母亲高兴起来的故事。“你今天怎么样,妈妈?”圣人问。“很糟糕。”母亲回答。“希望你明天会更糟糕。”圣人说。第二天圣克伦巴又来了,他们之间几乎是同样的对话。然而第三天母亲说:“好一点了,感谢上帝。”然后圣人回答:“希望你明天会更好。”他也乐于讲述在不停燃烧的火焰中,当士师奖赏好人谴责损失时,是如何在那最后一天同样保持了微笑。他拥有许多独特的视角,这些视角使他保持欢乐或陷入悲伤。我问他有没有见过仙人,他这样回答:“难道他们没有惹怒我吗?”我又问他有没有见过女鬼班西。“我见过,”他说,“在那下面,就在水边,她用手拍打着河水。”
我从一本笔记上复制了帕蒂-弗林的这些叙述,只稍微做了些语句上的改动,那是一本在见他后没多久便几乎塞满了他的故事和言论的笔记。现在我看着这本笔记,充满了悔意,因为末尾的空白页将永远也填不满了。帕蒂-弗林去世了。我的一个朋友送给了他一大瓶威士忌,虽然大部分时候他都是清醒的,然而看到如此多的液体,他便充满了激情。他靠着那瓶威士忌酒过了几天,然后就死了。他的身体因为艰苦的岁月而疲劳不堪,无法承受他年轻时的这种喝法。他是讲故事的好手,他不像普通的传奇作家,他知道怎么借助天堂、地域、炼狱、仙境和尘世,从而使他的故事充满人性。他不是生活在一个缩小的世界上,然而他知道的大千世界不会少于荷马。也许盖尔人应当像他一样寻回古时简单而丰富的想象力。什么是文学?难道不是通过象征和事件来表达情感吗?难道情感的表达不需要通过天堂、地狱、炼狱和仙境吗?--这些都不比这个损毁的尘世少。不仅如此,将天堂、地狱、炼狱和仙境混合在一起,或者甚至将兽头安在人体上,或者将人类的灵魂加在岩石的心脏上,难道这些都不能表达情感吗?让我们继续朝前走吧,故事的讲述者,抓住心灵所渴望的任何猎物,不要害怕。所有事物都存在,所有皆真实,尘世仅仅是我们脚下的一点小小尘埃。
相信与不信
在西方的村庄里,甚至也有一些怀疑家。去年圣诞节时,一个女人告诉我她既不相信有地狱也不相信有魔鬼。她觉得地狱不过是牧师的创造,以使人们保持纯良。她认为魔鬼将不会被允许任意“治罪地球”。“但是存在仙人。”她补充说,“还有小小的矮妖精、水马和跌落的天使。”我还遇见了一个臂上有莫霍克印第安纹身的男人,他也持有恰好相似的相信与不信的观点。然而不管任何人怀疑的是什么东西,人们永远都不会怀疑仙人的存在,因为,就如同那个臂上有莫霍克印第安纹身的男人所说:“他们的存在合情合理。”甚至连官员的头脑也躲不开这一信念。
三年之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小女孩突然失踪了。她那时在格兰戈村当仆人,那个村庄就在本布尔宾向海延伸的山坡底下。一种巨大的兴奋感马上传遍了村庄,因为有谣言说是仙人们带走了她。有人说某个村民为了抓住小女孩同仙人们斗争了很长时间,然而最后仙人们获胜了,那个村民只看到了自己手上的一把扫帚。当地的治安官介入了,马上开始挨家挨户地搜寻,同时建议村民们在她消失的田地里燃烧所有的豚草,因为豚草对于仙人来说是神圣的。他们花了整个晚上的时间来焚烧豚草,同时治安官不停地重复着咒语。第二天早上小女孩找到了,这个故事不胫而走,传遍了整个旷野。她说仙人们骑着仙马,将她带到了很远的地方。最后,她看到了一条大河,那个曾经试图与仙人抢夺她的男人就漂流在上面,藏在一个鸟蛤壳中,那儿便是充满了仙人魔力的混乱而喧嚣的国度。在路上,同行的仙人曾经提到过村庄中许多即将去世的人的名字。
也许治安官是对的。少一些怀疑,去相信一些大部分是非理性的只有小部分是真理的东西,会比出于怀疑的目的去怀疑真理和非理性的东西要来得更妙,因为当我们这么做时,不会突然出现一根蜡烛来指引我们的步伐,在沼泽地中也没有可怜的飞蛾在我们面前飞舞,我们必须摸索着进入那巨大的荒野中,在那里居住着奇形怪状的精灵。总之,如果我们在壁炉中和灵魂中保留一点点火种,张开双手迎接无论好坏的东西来到我们这儿感受温暖,也不管他们是人还是幽灵,并且甚至对着精灵们,也从不发表太过激烈的言论,像是“你们滚吧”,那么我们还会面对如此大的灾难吗?当所有都说了也都做了,我们又怎么会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非理性可能要优于其他人的真理呢?因为它已经在我们的壁炉中和我们的心灵里得到了温暖,正准备好了让真理的野蜂在里面筑巢,酿造它们甜美的蜂蜜。请再次来到这个世界吧,野蜂,野蜂!
凡人的帮助
人们曾在古老的诗篇中听到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人被掳走了去帮助战斗中的神仙们,库赫兰曾经通过帮助女神范德的姐妹和姐妹的丈夫推翻了应许之地上的另一个国家,从而赢得了女神范德的心。我也听说过仙人们甚至不会玩爱尔兰式曲棍球,除非在他们各方都站了一个凡人。而那凡人的身躯,或者用来取代它的什么东西--就像讲故事的人所说的--正在家里睡大觉呢!没有凡人的帮助,他们只是一些影子,甚至连球都不能碰到。一天,我正同一个朋友行走在高威郡的沼泽地上,这时我们看到一个面容严肃的老人正在挖一道沟渠。我的朋友听说这个老人曾经见过某种奇妙的景观。最终我们从他嘴里得到了这个故事。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一天,他正在同大约三十个男人女人和男孩们一起干活。他们劳作的地方在曲尔姆那边,离诺科纳格不是很远。不一会儿,他们三十个人都看到了在大概半英里的距离处有约莫一百五十个仙人。他说,其中两个仙人穿着和我们同时代的黑衣,那两个人之间离了大约有一百码的距离,然而其他人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有的衣服像“连谱号”,有的是方格图案,还有的穿着红色的背心。
他看不清楚他们在干什么,只知道仙人们有可能在打爱尔兰式曲棍球,因为“他们看上去似乎是这样的”。有时候他们会消失,然后--他几乎可以发誓--他们会从那两个黑衣人的身体里钻出来。那两个仙人和真人一般大小,然而其他仙人却很小。他就这样看了大约有半个小时,于是老雇主鞭笞了他们一顿,说:“赶紧,赶紧,否则我们会完不成活儿!”我问那个老雇主有没有看见仙人们。“噢,看见了。”但是雇主不希望他白掏了工钱,因此他让每个人都非常辛苦地干活,再也没有人看到在那些仙人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看到幻象的人
一天晚上,一个年轻人来到我的小屋里拜访我,我们讨论起世界、天堂的起源以及诸如此类的话题。我询问他的生活和所从事的工作。自从上次我们见过面后,他写了许多诗,还画了许多神秘的图案,然而最近他既没写诗也没作画,因为他把全身心都放在了怎样使头脑变得强壮,使自己精力充沛和镇定。他担心艺术家情绪化的生活对他有害,然而他还是很快地背诵了他的诗。他将那些诗存在了记忆中。他的确再也没有写过东西了。那些诗歌中野性的音乐就如同风儿吹过芦苇地。对于我来说,它们是凯尔特人的忧郁中最深处的声音,也是凯尔特人对于这个世界上从未见过的无限事物的渴望中最深处的声音。突然间,我似乎看到他有点热切地盯着周围看。“你看到了什么吗,X先生?”我问。“是一个闪闪发光的长着翅膀的女人,身体被长头发盖住了,正站在门边。”他这样回答,也许是一些类似的话。“那是一些活着的人在想起我们时所产生的影响吗--他们的思维以那种象征符号出现在我们面前?”我问,因为我很了解幻视者的行为和他们讲话的方式。“不是,”他回答说,“因为如果是一个活人的思维,我会在我这活着的身躯里感受到他那生命力的影响,我的心将会猛烈跳动,我的呼吸将会停止。然而那是灵魂,它属于死去的人或者从未出现过的人。”
我问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在一家大商店里做职员,然而他的快乐却时刻在山间漫步,与有点疯癫而不切实际的乡下人交谈,或者劝说古怪而受良心责备的人们将他们隐藏的烦恼交与他照顾关心。还有一个晚上,那时我在他的小屋,有好几个人出现在他的房子里,与他交谈他们的信仰与疑惑。他们沐浴着阳光,就好像那是来自于他心灵的微妙光线。有时在他们交谈时,某种幻象便会进入他的语句。有谣言说他曾经同许多人说到过那些人过往的岁月以及遥远的朋友的真实情况,于是他们便在对于这位奇怪老师的畏惧之情中沉默了。这位老师看上去比男孩大不了多少,然而却比他们之中最年长的更为敏感。
在他背诵给我听的诗句里充满了他的性情和幻想。有时候那些诗句会讲述他经历过的另外不同的生命轨迹,他坚信他曾经在其他世纪中生活过。有时候那些诗句会描述他曾经与之交谈过的人们,并展现那些人的心灵。我告诉他我将会书写一篇关于他的人和事的文章。他同意了,前提是不要提及他的名字,因为他总是希望成为一个“未知、模糊、客观”的人。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大包裹里面全是他的诗,随诗而来的还有这样的说明:“这是你说过的你喜欢的一些诗句的副本。我想我将不会再作诗或绘画了。我正准备进入其他某种生活的循环往复中。我将会固定好我的根和树枝,现在不是我突然长出树叶和花朵的时候。”
所有的诗都竭力尝试在模糊映像织成的网中抓住某种久远且难以触及的情绪。其中有些篇章很好,然而这些篇章通常只是植于他的思想中,很显然,只对他的头脑才有特殊的意义,对于其他人来说却是相反的,那些都不过是一些头脑中的臆想。其他人看到的可能最多只是大量的黄铜色、紫铜色或者失去光彩的银色。在某些地方,他思想的美好之光因他粗枝大叶的写作而模糊了,似乎在那些篇章中,他曾经突然怀疑起写作是否是一个很愚蠢的活儿。他频繁地用绘画来阐述他的诗句,在那些绘画中,某种不太完善的剖析并没有完全掩盖情感的极致美丽。他所相信的仙人们赐予了他许多话题,特别是在这一首诗中:术士托马斯静止不动地坐在曙光中,这时一个年轻美丽的小生物轻轻地依偎在他的影子里,附在他耳边说着悄悄话。他尤为喜欢用修辞来添加强烈的影响:孔雀的翎毛是它们头顶上的神灵,而不只是毛发;幽灵从涡动的火焰中靠近星辰;一个妖精经过时拿着一个彩虹的水晶球--灵魂的象征,它用手半掩着那个球。然而在这大量的比喻中,还有一些温柔的说教,直指人们脆弱的希望。这种精神上的渴望吸引了所有如他一般寻找光明或者哀悼逝去的快乐的人。这些人中有一个尤为特别。一年或者两年前的冬天,这个年轻人大部分晚上的时间都是行走在上山或者下山的路上,同时与一位老农夫交谈着。那位老农夫在大多数人面前沉默寡言,却将心事全都说给了他听。他们都觉得不快乐:X先生是因为头一次认为艺术和诗歌不适合他,而老农夫是因为他的生命陷入了低潮,却没有留下任何成就,没有留下任何希望。他们都是典型的凯尔特人啊!在某种东西从未完全用语言和行为表达出来之时,他们是如此地充满了努力斗争的精神。农夫的脑子里充满了久久不去的悲伤,有一次他爆发了:“上帝拥有天堂--上帝拥有天堂--他却贪求这个世界。”他还曾悲叹,老邻居们都离他而去,所有人都遗忘了他。在每个小屋的火炉边,都曾有一张为他准备的椅子,然而现在他们说:“那个老家伙是谁?”“厄运笼罩了我。”他重复着,然后又开始谈论上帝和天堂。他朝着山峰甩动着臂膀,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只有我自己知道四十年前在那山楂树下发生了什么。”他这样说时,脸上的泪水在月光中闪闪发光。
当我想起X先生时,总会先想到这位老人。他们都在寻觅,一个是通过错乱的语句,另一个是用象征性的图画和隐晦的比喻诗句,来表达某种超越了表达形式的东西。在他们凯尔特人的心底里都蕴藏着大量模糊的奢侈感--如果X先生能原谅我这么说的话。农夫中的幻视者,地主中的决斗者,和整个骚动喧嚣的传说--库赫兰与大海斗争了两天,直到海浪淹过了他,他死了;考尔特猛攻神殿;莪相寻觅了三百年,想要用仙境的所有欢乐来满足他贪得无厌的心灵,却是徒劳无获;两个神秘的人上山下山,用充满梦幻的语句讲述他们灵魂中心的梦幻,以及觉得他们是如此有趣的我--都是那伟大的凯尔特变化无常的幻象的一部分。人们从未发现过这种幻象的意义,任何天使也从未揭示出它的意义。
村庄鬼魂
在这个大城市里,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个世界中如此微小的一部分,我们漂浮在我们自己的少数人群中。在小镇和村庄里,没有所谓的少数人群,因为人口数量还不是足够大。在那里,你必定看得到这整个世界。每个人自己便代表了一个阶级,每一小时都充满了新的挑战。当你经过村头的小酒店时,你便将你最喜爱的奇思怪想留在了身后,因为不会有人来分享你的想法。我们倾听雄辩的讲话,阅读并著书立作,安置好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然而村庄中沉默的人群却一成不变。无论我们如何滔滔不绝,他们手中握着铁铲的感觉还是没有区别:如旧日一样,好时辰和坏时辰循环往复。沉默的人群关心我们并不比关心老马要多,而老马正透过生锈的大门凝视村中的鱼塘。古时的地图绘者在未曾发掘的地域写上:“这里有狮群。”整个村庄的渔夫和挖泥土的工人都与我们大为不同。我们只能写下惟一确定的一条:“这里有鬼魂。”
鬼魂们居住在伦斯特的H村。历史从未以任何形式被这个古老的村庄所毁坏。在这里有弯弯曲曲的小巷,有遍布青草的古老大教堂的墓地,有小冷杉形成的绿色风景,还有停靠了许多渔船的驳岸。在昆虫学的历史记载上,它广为人知,因为往西去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港湾,如果有人在那里连夜观察的话,他将可能在黑夜之边或黎明之始,注意到某种珍稀的飞蛾沿着潮水的边缘扇着翅膀滑过。一百年前,它们被装在一批走私的丝绸和饰带中,从意大利来到了这儿。如果捕蛾者放下他们的捕虫网,去搜寻鬼魂和仙人的故事,以及莉尔丽丝的孩子,那么他将远远不需要这么多耐心。
夜晚,如果一个胆小的人想要靠近这个村庄,那么他需要周全的策略。曾经有人这样抱怨:“以耶稣十字架的名义!我要怎么走才好?如果我取道旦波易山,老伯尼船长可能会注意到我。如果我绕过河流前进,然后攀上台阶,我便会看到第一个无头人,这时还有一个藏在驳岸,第三个就躲在古老墓地的墙根下。如果我往右走上另一条道,斯图尔特夫人就会出现在山坡的大门处,魔鬼他自己则站在医院的小径上。
我不知道他最后面对的是什么样的鬼魂,但我能确定不是医院小径的那个。在霍乱肆虐的时代,那儿立起了一个小屋用来接收病人。当这种需求消失后,小屋被推倒了,然而从那之后,小屋的旧址上突然出现了许多鬼魂、恶魔和仙人。有个来自H村的农夫,名字似乎是帕蒂-B--看名字是个充满力量的人,他是一个禁酒主义者。他的妻子和嫂子惊讶于他的巨大力气,总是猜想如果他喝醉了会做些什么。一天晚上,当他经过医院的小径时,看到了一个东西,起初他以为是温顺的兔子,过了一会儿他发现那是一只白猫。当他靠近后,那个小生物开始慢慢膨胀,变得越来越大。在它膨胀变大时,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在衰退,就好像是被什么吸出了他的身体。于是他掉转了头,跑了。
靠近医院小径的是“仙人之路”。每天晚上,都有仙人们从山上去往海边,从海边回到山上。在路途尽头的海边立着一座小屋。一天晚上,住在那儿的阿尔布纳西夫人敞开了屋门,正等待着她的儿子。她丈夫正酣睡在炉火边,这时一个高个人进来了,坐在了她丈夫边上。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后,夫人问他:“以上帝之名,你是谁?”他站了起来,然后走了出去,说:“永远都不要在这个时辰敞开你的屋门,否则灾难将会降临在你身边。”她叫醒了丈夫,告诉了他这桩奇事。“有一个好人曾经来到我们身边。”丈夫说。
那个人在山坡大门处面对的有可能是斯图尔特夫人。活着的时候,她是新教牧师的妻子。“从未听说过她的鬼魂曾经伤害过人,”村民说,“她不过是在地球上以苦行赎罪。”在她经常出没的地方,离山坡大门的不远处,曾经一度出现过一个更加奇怪的灵魂。它经常出现的地方是一条小道,那是一条从村庄西部的尽头延伸出来的绿色的小窄道。我详细地记录了它的历史--一个典型的小村悲剧。在村庄尽头处的小道旁有一座小屋,里面住着粉刷匠吉姆-蒙哥马利和他的妻子。他们养育了许多孩子。粉刷匠是一个花花公子,与他的邻居相比,他出身于更高的一个阶层。他的妻子是一个高大的女人。某一天,因为酗酒,他被赶出了村里的唱诗班,然后他揍了妻子一顿。妻子的姐姐也像妹妹一样高大强壮,她得知消息后,赶了过来,取下一扇百叶窗--吉姆-蒙哥马利干什么都很灵巧,他在每一扇窗户的外面都装上了百叶窗--然后用百叶窗揍了他一顿。他威胁要起诉她,她回答说如果他真这么做了,她会打断他身体的每一根骨头。她再也没同她妹妹说过一句话,因为她妹妹竟会允许自己被如此瘦弱的男人给揍一顿。吉姆-蒙哥马利变得越来越坏,他的妻子不久便开始吃不饱了。因为内心深处的骄傲,她没有将此事告诉任何一个人。在寒冷的夜晚,她经常会缺少燃烧的炉火。如果有邻居进来了,她会说她刚把火给熄灭了,因为她正要上床睡觉。周围的人经常听见她的丈夫打她的声音,然而她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她变得极其消瘦。最终,在一个星期六,房子里没有任何她和孩子们能果腹的食物了。她再也忍受不了了,只好去牧师那儿要点钱。牧师给了她三十先令。然而,她的丈夫遇到了她,抢走了钱还打了她。她越来越虚弱,被送往了凯莉夫人那儿。凯莉夫人一看到她就说:“我的女人呀,你要死了。”然后又把她送到了牧师和医生那儿。不到一个小时她就死了。她死后,因为吉姆忽视了孩子们,人们把孩子们送往了救济所。孩子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凯莉夫人正走在回家的小道上,这时蒙哥马利夫人的鬼魂出现了,跟随着她。鬼魂一直在她到家后才离开她。她把这件事告诉了R牧师--一个著名的古文物收藏家,然而他却不相信她。这之后又过了几个晚上,凯莉夫人在同样的地方又遇到了鬼魂。她实在是太害怕了,根本不能走完整个回家的路,只好在半路上就停在了邻居家的小屋前,请求他们让她进去。他们回答她说要上床睡觉了。她只好叫出了声:“以上帝的名义让我进去吧,否则我会破门而入的。”他们打开了门,她终于逃离了鬼魂。第二天她又把这事告诉了牧师。这次他相信了,他告诉她说鬼魂会一直跟着她,直到她同它说话。
在小道上,她第三次遇见了鬼魂。她质问鬼魂,为什么要一直跟着她。鬼魂说它必须把它的孩子从救济院带走,因为它从来没有亲人在那里面呆过,还有唱起三支弥撒曲便能够安息它的灵魂。“如果我的丈夫不相信你,”它说,“给他看这个。”然后它用三只手指碰了碰凯莉夫人的手腕。那碰过的地方肿了起来,颜色发暗,然后它便消失了。吉姆一度不能相信他的妻子出现过。“她不会在凯莉夫人前现身的。”他说,“她只出现在受人尊敬的人面前。”最终他被那三个印记说服了,于是孩子们从救济院被带了回来。牧师唱过了弥撒曲,鬼魂必定已经安息了,因为它再也没有出现过。这之后的某一天,吉姆死在了救济院中,死因是极度贫困和过度酗酒。
我知道一些人觉得他们在驳岸处看到过无头鬼魂。有一个人在晚上经过墓地的墙围时,注意到一个女人戴着白色滚边的帽子,爬出了墓地,跟随着他。一直到了他家的门口,那幽灵才离开了他。村民们想象她跟踪他是为了报复她所受到的某些冤屈。“等我死了我会缠着你。”是一句很受欢迎的威胁的话。那个人的妻子曾经被吓得半死,因为她觉得她看到过一只像狗的恶魔。
这些都是旷野中的幽灵,他们中更恋家的群体则聚集在室内,就如同南檐下的燕子一样多。
一天晚上,有一位诺兰夫人正在家里照看她奄奄一息的孩子。突然,她听到了一阵敲门声。她没有开门,因为她害怕会是一些非人类的东西在外边。敲门声停止了。过了一会儿,先是前门,接着是后门都突然打开了,然后又关上了。她的丈夫走过去想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发现两扇门都是闩着的。然后孩子死了。这时门又像开始一样打开了又关上了。诺兰夫人想起来她忘了按照习俗打开门窗,让灵魂离开。这些奇怪的开开合合以及敲门声都是来自于那些照顾濒死之人的幽灵的警告和提醒。
屋里的鬼魂通常都是无害而具有善意的生物。我们要尽可能地容忍它们的存在。它们带给与之一起生活的人们好运。我记得有两个孩子同他们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一起睡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那个房间里有一个鬼魂。他们在都柏林街上售卖鲱鱼,并不怎么在意鬼魂的存在,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睡在鬼魂出没的房间里时,鲱鱼总是能很容易地就被卖出去。
在西部村庄的鬼魂预言家中有我的一些熟人。康诺特的传说与伦斯特的有很大的不同。这些H村庄中的灵魂有一种阴郁的、切合实际的行事方式。他们宣告死亡、完成某种义务、报复冤屈、甚至结算他们的账单--就像某一天渔夫的女儿做的--然后便急急忙忙地赶去休息了。他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派的合乎秩序的。只有恶魔而不是鬼魂会将它们自己装扮成白猫或黑狗。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是贫穷、热心的渔人,他们在鬼魂的行为中发现了令人陶醉的恐惧感。在西方的传说中,他们的行为有着古怪的优美之感和难以理解的奢华。讲述这些故事的人生活在荒凉而优美的景色中,生活在飘满了奇异白云的天空下。他们是农夫和劳工,还不时地捕几条小鱼。他们不会太过害怕幽灵以至于不能感受到幽灵的行为中充满着艺术和幽默感的愉悦。鬼魂同他们分享古怪的欢乐。在一个西方小镇上,被废弃的码头上冒出了青草。当一个不信者大胆地睡在闹鬼的房子里时,那里的鬼魂便会充满了精力。有人告诉我,它们将他扔出了窗外,连床也扔了出去。在临近的村子里,这种生物会使用最为奇怪的伪装。一位老绅士装成大白兔抢走了他自家花园里的卷心菜;一个邪恶的船长变成鹬在屋墙的灰浆里生活了数年,制造出最为恐怖的噪音。在墙被推倒后,他才被赶了出来。跳出那固体灰浆后,这只鹬尖叫着匆匆地走了。
尘土合上海伦的双目
I
我最近到过有一小片房子的地方,就在高威郡的基尔泰坦大庄园里,那里还不足以称为村庄,它的名字--巴利里,为整个西爱尔兰所知。在那里有一座古老的方形城堡,里面生活着农夫和他的妻子,还有一座住着他们女儿和女婿的小屋和一个住着年迈的磨坊主的小磨坊,古老的白蜡树在小河和巨大的石阶上投下了碧绿的影子。去年我到过那儿两三次,同磨坊主交谈比蒂-厄丽以及她的言语--“在巴利里的两个磨轮之间存在着拯救所有罪恶的良药”。比蒂-厄丽是一个一些年前生活在克莱尔郡的聪明女人。我还要问他或者其他人:她说的是不是流水间的苔藓,或者是其他的什么植物。这个夏天,我到了那儿,在秋天到来前我还会再去一次,这是因为玛丽-惠妮斯,这个死于六十年前的美丽女人,在燃烧的炉火边的谈话中始终是一个奇迹。我们的双脚总是停留于有过忧伤的美丽的土壤上,从而让我们懂得忧伤并不属于整个世界。一位老人领着我走出了磨坊和城堡一小段距离,然后往下走上了一条漫长狭窄的小道,那条小道几乎被黑刺苺丛和黑刺李灌木丛给掩盖了。然后他说:“这就是那房子小小的古老基石,大部分都被拿去修建了墙壁。山羊啃食了路上的这些灌木丛,于是它们生长得弯弯曲曲,再也长不高了。他们说她是爱尔兰岛上最美丽的女孩,她的皮肤就像飘落的雪花。”--他可能是想说堆积的雪花--“在她的脸颊上泛着红晕。她有五个英俊的兄弟,但是现在都去世了。”我向他提及了一首爱尔兰诗歌--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拉夫特里为她所作的。诗歌里有这样一句话:“在巴利里有一个坚固的酒窖。”他说的那个坚固的酒窖是一个巨大的洞穴,河流经过那儿时,水位便下落了。他将我带到了一个很深的水塘边,在那里一只水獭从灰色的大块石头下快速地窜过。他告诉我清晨时分会有许多鱼儿从深黑的水中冒出来,“品尝从山上流下来的新鲜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