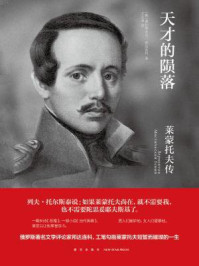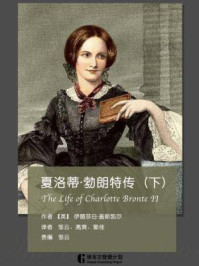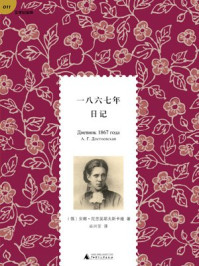当时间不再因为衰老而流失,我们是否可以让感情主宰了时间?
当我们忆起一段情,一个人的时候,岁月便像是遥遥而来的马车,我们挥一挥手,轻声说一句:走吧。
于是,这驾车便带着我们进入朦胧的回忆中。
如此,岁月便也折返。
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酉时,按照公历推算应是1897年1月15日。酉时,按照现今时间来计算大致是下午五点到七点之间,此刻正是夕阳沉落,余晖流彩,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第四进院子的楼上。这一年,父亲徐申如二十五岁,母亲钱慕英二十三岁。
出生一事,原本可说是母难,也可说是独属于一个人的节日。
生命便因此开始,如上天不经意点了一个墨点,于是这个墨点游走在尘世间,曲曲折折,迂迂回回,直到末了,那墨点又被一张新的宣纸覆盖上去,一切如初。
徐申如是娶了二房太太,才得了一个儿子,所以徐志摩一出生便成了家里的掌上瑰宝,举家呵护。
天时、地利、人和,徐志摩是一样都没缺,一样都没少。他出生在富贵家庭,父亲徐申如继承独营酱园业,在此祖业外又合股开办钱庄、丝厂、绸缎店、火力发电厂,家产营业面宽广,地域也延伸到了泸杭两地。若是此刻的徐志摩只是富家子弟,将来子承父业、娶妻生子尽享天伦,倒也算此生完满。然而有个趣闻成了先兆,注定了他一生不如想象中平凡。
按照江南旧俗,周岁又称为“晬盘之喜”,是要用一只红漆木盘盛上剑、笔墨、算盘等物,说是以物测人,比如,若是抓住了剑,那婴儿将来可能从军;若是抓住了笔墨,那婴儿将来可能从文;若是抓住了算盘,那婴儿将来可能是账房先生……
所以,“晬盘”又称为“试儿”。
徐志摩的“试儿”拿些了什么我们已无从得知,却说在试儿时突然闯进来一名叫志恢的和尚,通过摸骨算命,对徐申如说,此儿将来必成大器。
自古以来人们往往喜欢通过占卜、看相等来预知未来,算命的人便常往好里说,虽说真假难辨,但也将信念植入人心,久而久之,是多了一份成功的可能。
这摸骨算命是有个传说:清朝有个大官叫张之洞,相当于现在的省长,他来湖北主事,见满街的算命先生,就觉得这应是本地落后的根源,于是便想取缔。但他是读书人,知道要以理服人,就微服私访在街上找到一个瞎子,让他摸骨。那瞎子刚从脚摸到肩膀,就一掌将他推开,骂道:“一身狗骨头,还来算什么命。”张之洞大喜,心想:这算让我找到灭你们这行的把柄了吧,我堂堂一品大员,你吃了雄心豹子胆竟敢说我一身狗骨头。但他仍耐着性子说:“先生你好歹把我摸完嘛。”那先生骂骂咧咧地说道:“你难道是狗骨镶龙头不成?”边说边摸,刚摸到顶,扑通就跪下了,嘴里叫着:“大人饶命,大人是狗骨镶龙头,必定是诸侯。”张之洞哑然,不得不服气而去。
这摸骨算命一行才留了下来。
似有惊世之才的人都会有一种将来必得成才的预感,在年少时要立下一些豪言壮语,如张爱玲写过《我的天才梦》: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徐志摩也写过相似的话,他在《猛虎集》的序言中写道: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在二十四岁以前我对于诗的兴味远不如我对于相对论或民约论的兴味。我父亲送我出洋留学是要我将来进“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个中国的Hamilton(哈米尔顿)!在二十四岁以前,诗,不论新旧,于我是完全没有相干。
作家们的写作似乎总会有一个追溯的过程,越是写得深越要追溯到他的童年,一旦达到了那种境界,便是返璞归真,让天性占了大多数。雨果也曾说过:没有一个不幸的童年对于作家而言是种损失。此话,虽不能一言以蔽之,但也可瞧见童年对于写作者的影响之深。
纵观徐志摩的写作历程,最初虽不是理想之路,可他拥有的天赋却未被浪费。童年时,徐志摩勤奋好学的性格,对他日后的写作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为一栋雄伟的文学大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徐志摩的童年,正逢中国新旧学制交替之时,科举虽已废除,地方上的新式学堂尚未开办,大多数官富家还是有家塾。徐志摩五岁入家塾,开蒙,业师孙荫轩先生。这位孙荫轩是本县青云镇上的一个秀才。徐志摩应该是文星庇护,开蒙不久,便识了很多字,言语中也颇具文采。
不过,读书终究是枯燥的,尤其业师还是一位秀才,教书死板,教的之乎者也让人昏昏欲睡。徐志摩便常会走神,望着窗外,其实窗外并没有什么奇美之景,他不过是想借此来逃离这枯燥的读书生活。塾师往往在这个时候会用那把楠木戒尺,重落桌面,将他惊醒。那飘出去的魂猛然被拉了回来,呼吸骤停,心神慌乱。后来,他乘着塾师不在,偷了那把戒尺,投进了水井里。当塾师当面质问他时,他却说:“我见了这根戒尺怕,脑子发胀,读不进书。”
在家塾里读书的情景,徐志摩曾在《雨后虹》里写道:但在白天天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可怜的“读书官官”们,还照常临帖习字,高喊着“黄鸟黄鸟”,“不亦说乎”;虽则手里一把大蒲扇,不住地扇动,满鬓满腋的汗,依旧蒸炉似的透发,先生亦还照常抽他的大烟,哼他的“清平乐府”。
徐志摩六到十一岁复从师查桐轸。这位先生,说来有趣,从不洗澡也不洗头,不修边幅,恐是要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但生活中,周身常散发出难忍的酸臭味。徐志摩是向父亲抱怨过此事,不过他有学问,徐志摩的父亲便也默许下来。
后来徐志摩在一次自我检讨中也提到了这位查先生:查先生这个人明明是因懒惰而散漫,别人却赞美他是落拓不羁,我的父母都是勤勉而能自励的人,我这个儿子何以懒散成这个样子,莫不是查桐荪先生的遗教?
童年的徐志摩,常如破石而出的顽猴,贪玩、好动、活泼。本是要恭恭敬敬读书,恪守礼教,却因他的性格有了冲突。如一副淡远宁静却略有枯燥的水墨画,忽而被染色的笔着了一笔,那日日乏味至极的生活却也亮了起来。
徐志摩的母亲胆小,深怕这样的性格会让徐志摩闯了祸,便常用一些传说或者预言来恐吓他,一如现在的家长管教孩子失灵时常用的把戏。
“别哭,妖怪专咬爱哭小孩子的脚趾头!”
“别跑远了,街上的瞎子会抱走小人!”
“再吵,吵醒了熊婆婆晚上就来了!”
这样颟顸的字句难免成为孩童清池之心的一点污浊,让人心生耿介。
黄昏之时,群鸟绕着夕阳的余晖,在一片赤金之色中盘旋,发出呼呼的响声,徐志摩常在这时如一只疲惫的猫儿蜷缩在祖母的臂弯里,听祖母讲故事。那是夏天,祖母最怕热,一手揽着徐志摩,一手摇着蒲扇,趁着乘凉的机会,她便给徐志摩讲些“牵牛织女”、“哪吒脑海”、“夸父逐日”这类代代相传却又回之有味的古老故事。
祖母有事或者倦了的时候,徐志摩便会去找家里的老佣人家麟,年岁与苦难滴入他的生命,融成一片海洋。家麟会讲很多故事,徐志摩一旦去找他,他就会立刻放下手里的活给这位小少爷讲起故事来。因为书是没有读过的,所以他讲起故事来也是信马由缰,那故事便也活了起来。
他是把一整部《岳飞传》都讲完了。
后来徐志摩的小说《家德》便是以家麟为原型创作的,虽然后经陆小曼之口说,徐志摩是缺了创作小说的那一份灵气,却也可以窥见岁月深处家麟的音容笑貌。
徐志摩是这样写过:我们最喜欢听他讲岳传里的岳老爷。岳老爷出世,岳老爷归天,东窗事发,莫须有三字构成冤狱,岳雷上坟,诛仙镇八大槌--唷,那热闹就不用提了。他讲得我们笑,他讲得我们哭,他讲得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得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
说到徐志摩的童年,自然要提及他的功课。
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科举制度这条腐朽的铁链终于轰然崩落。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徐志摩进入了废除科举后的硖石镇第一所学堂--开智学堂。此时的徐志摩正如脱笼之鸟逃离了家塾的禁锢生活。
学堂除了开设国文、数学、英文之外,还有音乐、体育、自修诸课。这对于徐志摩而言自然是新鲜的,恰新学堂又设在硖石镇的西山之麓上。西山之上有亭、寺、泉,原本已经丰美的山麓又添了这些趣味之地,如绢帛之上又钉上了几颗华美的宝石,对于生性活泼的徐志摩来说,再合适不过了。
徐志摩的国文老师张仲梧非常欣赏徐志摩的才华,常把他的文章当做范文向学生宣读。徐志摩行文如流水,常是一气呵成,妙语连珠,难怪会引得张仲梧欣赏。徐志摩不仅国文成绩好,其他科目成绩也是出类拔萃,学堂里的学生都称他为“两脚书橱”,一是他功课好,二是他听闻多,在其他学生眼里倒也配得上“渊博”二字。
徐志摩写过一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语言驾驭能力已颇具火候,古文基础扎实,那时的他不过是十三岁的少年。
且引出几句来看看:夫禄山甫叛,而河北二十四郡,望风瓦解,其势不可谓不盛,其锋不可谓不锐,乘胜渡河,鼓行而西,岂有以壮健勇猛之师,骤变而为赢弱顽皮之卒哉?其匿精锐以示弱,是冒顿饵汉高之奸谋也。若以为可败而轻之,适足以中其计耳,其不丧师辱国者鲜矣!
1911年春天,徐志摩从开智学堂毕业,与其表兄沈叔薇一起考入杭州府中学堂。
此间,徐志摩结识了郁达夫,两人在府中学堂求学期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那时,徐志摩与郁达夫不过都是青葱年岁。这个年纪,或呼朋引伴,或三五成群,或拉帮结伙,或两人独酌,皆是在他人身上寻找自己的影子。
郁达夫虽然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才,但转学到了新的环境,还是难免有些惶恐与战战兢兢,加之性格内向,很多时候只是蜷缩在教室一角,默默读书。而徐志摩与表兄两人却很活泼。
郁达夫心如静水,徐志摩则如砾石一般,落了进去。
郁达夫心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
两人之间真正结缘还是来自于“文”,那时的国文老师常常把郁达夫与徐志摩的文章作为范文向全班宣读。于是,志同道合,两人成了好友。
郁达夫佩服徐志摩洋洋洒洒的行文。徐志摩曾在《校刊》上发表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颇得那时的郁达夫欣赏。
我想,古时有“文人相轻”一说,大致是因为要相博出名,但如果彼此在同一时刻,既获得对方的欣赏又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可谓皆大欢喜。
前些日子,好友C向我诉苦,说一起玩了那么多年的好友,十年的交情,只因一点小事忽然陌生了起来,心生感慨。
我问她,当初是为何在一起?
她答,大概是那时无人可说话,无人可作伴。
感情便是这样,尤其是友情,不以时间的长度来衡量,也不以金钱的施与受来衡量,不过是,我看你是这一路的人,那便携手走下去。若是此路没人,恰好遇到一陌生人,走了很久,还是要散,更可悲的是散去了,不过依旧是陌生人。
至交,是骨子里的相随。
昨夜恰巧读书读到:白发为新,倾盖如故。我感慨,这是一语中的。
1915年春,惊蛰之后,万物苏醒,一片青翠。
张嘉璈在府中读了徐志摩所写的那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大为赞赏,便找到了当时府中学堂的校长张萍青。
张嘉璈说是要来巡学,实则是为小妹张幼仪物色夫婿来的。张萍青又将徐志摩的成绩册写作文拿给张嘉璈看。张嘉璈瞧见徐志摩这么优秀,心中甚是欢喜。
张嘉璈又问张萍青校长:“这徐章垿家里状况如何?”
张萍青回道:“家境殷富,祖业根基牢实,若与之结亲那定是入了宝盖鸾骖。”
张嘉璈会心地点了点头。
爱情的来临,不是一场盛夏骤至的暴雨,让人措手不及。爱情是一场有预兆的雷雨,年少时的懵懂,接触时的悸动,都是爱情的前兆。
可爱情是需要酝酿的,年少时不知什么是爱,错把责任、义务、报恩、父命当做了爱。
旧式的婚姻,大多是这样。
如一条长路,每人速度不一,正好有一扇爱的门,便在父母的推搡下,仓促迈入此门。
一直很喜欢李白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
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
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
……
在府中上学的徐志摩与张幼仪订婚了,那年,徐志摩十六岁,张幼仪十三岁,正是两小无猜的年纪。
那时合婚是要将两人的生辰八字拿给相命人看的。张幼仪在家里排行第二,按照旧俗,是要等到大姐出嫁了,她才能嫁。但大姐的命数不佳,嫁早了克夫,必须等到二十五岁才能嫁,因此张幼仪是要先嫁了。
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八字起初是不合的,后来父母听了相命人的意见,改大了两岁,这才促成了一桩“佳缘”。
那时的婚姻,夫妻要等到洞房花烛夜才能见面。而对于彼此相貌的了解,都是通过媒人相递照片。他们彼此先看了对方的照片,张幼仪瞧着徐志摩大眼挺鼻,生得一派俊俏相,心里欢喜。而徐志摩则不然,他见张幼仪梳着齐耳短发,一副敦厚良实的模样,心想这肯定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女子,眼里没有丝毫灵气,也没顾忌媒人的面子,硬硬撂下一句:“土包子。”
写至此,恰有人问我,什么是一见钟情与日久生情?
我想,这两者虽然都生出了情,但实质却不一样。一见钟情,所生的必然是男女之间炽热无比的爱情。日久生情,则大概是一种相互依存,一种习惯,类似于亲情。
若是有人信了日久生情,似乎就少了那一份爱情该有的猛料。
人生中岔路口很多,可有几个岔路口,一旦过去了,便是一番新的人生景象。婚嫁便是其中之一。
我想,徐志摩与张幼仪结婚必也是一番新的人生。
徐志摩在1925年曾写过《去罢》:去罢,人间,去罢!
我独立在高山的峰上;
去罢,人间,去罢!
我面对着无极的穹苍。
去罢,青年,去罢!
与幽谷的香草同埋;
去罢,青年,去罢!
悲哀付与暮天的群鸦。
去罢,梦乡,去罢!
我把幻景的玉杯摔破;
去罢,梦乡,去罢!
我笑受山风与海涛之贺。
去罢,种种,去罢!
当前有插天的高峰;
去罢,一切,去罢!
当前有无穷的无穷!
这十几年后的诗句,倒真应了之前的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