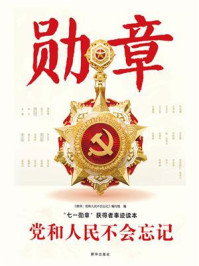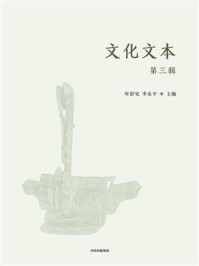四、义以为上与孔颜之乐
群己关系本质上并不仅仅具有抽象的道德意义,它同时指向具体的利益。如何以普遍的规范来协调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这一问题在儒学中即展开为义利之辩。义与宜相通,含有应当之意,引申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当然之则),利则泛指利益、功效等。从价值观上看,义利之辩首先涉及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的定位。广而言之,义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理性的要求,而利则往往落实于感性需要的满足,因而义利关系又内在地关联着理欲关系,正是通过对道德的内在价值、利益中的公私关系、人的理性品格与族类本质等方面的规定,孔子奠基的儒家价值观获得了更具体的内涵。
孔子贵仁,而仁与义又有内在联系。与注重仁道原则相应,孔子将义提到了重要地位。按照孔子的看法,义作为道德规范,本身便具有至上的性质:“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在此,“质”、“上”便是指一种内在的价值。正由于义有自身的内在价值,故不必到道德领域之外去寻找义所以存在的根据。孔子所理解的外部根据,主要便是指利,既然义有自身的内在价值而无须求诸外部根据,那么,结论自然便是不必喻于利,当孔子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时,突出的也是这一点。不过,应当注意的是,如后文将要指出的,孔子把“喻于利”作为小人的品格而加以贬抑,并不意味着绝对地排斥利,而主要着重于将利从义之中剔除出去。换言之,他强调的是义作为当然之则,只有略去一切外部因素(包括利),才能使自身的价值得到净化。
根据义以为上的观点,孔子认为,行为的价值主要取决于行为本身,而无关乎行为的结果。如果行为本身合乎义,则即使行为不能达到实际的功效或利益,它同样可以具有善的价值。孔子的学生子路曾以行道(推行道)为例,对此作了阐释: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微子》)这一看法可以看作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挥。按孔门的理解,君子的特点便在于虽然意识到“道”无法实现,却仍然努力推行道,因为他们把推行道这一行为本身看作是“义”的体现。一般而论,所谓行为之合乎义,首先是指行为之动机的正当性。这样,以行为本身来评判行为之价值,便相应地意味着以行为的动机来评判行为。在这里,孔子及其门人赋予行为本身及行为之动机以绝对的价值,将“义”(当然之则)理解为一种无条件的道德命令,并把履行道德规范(“行义”)本身当作行为的目的,从而把道德评价归结为不涉及行为结果的过程。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义以为上”说的逻辑推论:既然义有自身的价值而无须利(道德之外的因素)之介入,那么,行为的价值相应地也取决于行为本身,而与行为所产生的结果无关。
孔门的如上看法在某种意义上接近于康德的见解。在康德看来,真正的道德行为总是有其自身的价值,这种行为之所以为善,并不在于它能导致功利的结果,而主要在于它合乎道德律令的要求。换言之,只有当人们仅仅根据绝对命令的要求去从事某一行为,而完全不考虑这种行为是否能带来实际的利益,该行为才具有道德(善)的性质。孔子以“行其义”为行为之内在理由,而将行义是否能带来成功这一问题置于视野之外,这与康德的道德哲学多少有相通之处。康德在伦理学上具有义务论的倾向,当孔子以“行其义”为首要的关注之点时,似乎也表现出类似的特点。从伦理学上看,道德行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总是具有二重性:从其起源、作用来看,它乃是以社会的现实关系为基础,带有工具的性质(表现为满足人的合理需要、调节人际关系、维系社会稳定的手段),但同时,作为人的尊严、人的理性力量的体现,道德又有其内在的价值,并相应地具有超功利、超工具性的一面;前者赋予道德以现实性的品格,后者则体现了道德的崇高性。义务论强调道德的价值即在道德自身,突出的正是道德的内在价值。就中国思想史而言,孔子在义利之辩上的贡献,首先也正在于把道德行为与一般功利的行为区别开来,并使之得到提升,从而将道德的崇高性(超功利性)这一面以强化的形式展现出来。孔子对义的如上强化与提升,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中国文化的道德自觉,并使人是目的这一仁道原则获得了更具体的内涵。当然,孔子由此而完全否定道德的现实功利基础,则又表现了义务论价值观的抽象性。孔子在义利关系上的所见与所蔽,为尔后的儒家价值观定下了基本的格局:对道德内在价值的注重与忽视道德的功利基础,构成了儒家区别于其他学派的显著特点,而儒家义利观的合理性与片面性,亦同时蕴含于此。
义的规定主要涉及道德的价值基础,与这一问题相关,义利之辩还涉及另一问题,即怎样调节利。如前所述,君子不喻利,主要是强调道德原则(义)之成立并不依赖于利,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全忽略利。否定利是道德之价值基础与绝对地摒弃利,在逻辑上并不等价。事实上,孔子绝非完全弃功绝利。如他到卫国,并非仅仅关心那里的道德风尚如何,相反,倒是开口便盛赞该地人口众多。当他的学生问他“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即明确地回答:“富之。”(《子路》)“庶”、“富”在广义上属于利的范畴,以上所表现的,显然是对实际功利的肯定。在孔子看来,功利的追求并不是一种绝对的恶,从社会范围来看是如此,就个人而言也是这样:“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言不及利、摒弃正当的功利活动,以致贫贱交加,这不仅不足取,而且是一种应当否定的价值取向:“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正是基于如上的看法,孔子一再要求:“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尧曰》)当然,肯定利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并不表明可以无条件地追求利。那么,如何对利加以适当地调节?这一问题的解决,再一次涉及义与利的关系。按孔子之见,尽管义无须以利为根据,但利的调节却离不开义。如果不合乎义,则虽有利而不足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一旦仅仅以利本身为出发点,而不以义去约束利,则往往将导致不良的行为后果:“放于利而行,则多怨。”(《里仁》)所谓放于利而行,便是指一味地追求个人之利,而如此行事的结果,则是引起普遍的不满(多怨),后者显然是一种不利的结果。换言之,以利为行为的至上原则,常常将走向其初衷的反面(不利)。正是在此意义上,孔子认为:“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惟有以义制约利,才能避免这一归宿。
一般而论,利首先与个人或特殊集团相联系,而个人(或特殊集团)之利往往并不彼此一致,因此,如果片面地以利作为行为的惟一原则,总是不可避免地将导致社会成员在利益关系上的冲突。相对于利而言,义则超越了个人的特殊利益,具有普遍性的特点:它所体现的,乃是普遍的公利,惟其如此,才能对特殊的利益关系起某种调节作用。这样,义与利的关系在一定意义上便表现为特殊之利(个人之利)与普遍之利的关系,而以义调节利,则相应地并不是为了消解利,而是旨在达到普遍的公利;孔子从“大事不成”这一功利角度反对执著于“小利”,实际上便体现了如上思路。也正由于义体现了普遍的公利,孔子一再要求“见利思义”(《宪问》)、“见得思义”(《季氏》)。这种看法在某种意义上将义(道德原则)之价值与公利联系起来,因而不同于康德仅仅从当然之则本身之中寻找道德规范的价值。孔子的如上看法对其义务论倾向也多少有所限制,它使孔子的义务论带有某种温和的色彩。
孔子以义制利的主张同时又是其群己之辩的具体化,注重义的规范功能与强调群体原则在理论上彼此相契,义在一定意义上即是群体之利的体现。这种看法注意到了道德原则(义)在维护普遍的整体之利中的作用,并通过为利的追求规定一个合理的限度而避免了利益冲突的激化。与“义以为上”的命题一样,“见得思义”的要求所凸显的,乃是人的族类(社会)本质,它使人超越了个体的利益之争而真正地意识到了社会整体之利的重要意义。历史地看,人的道德自觉的尺度之一,便是由单纯追求个体之利进而确认族类(社会整体)的利益,这种确认实质上构成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必要前提,孔子所开创的儒学在某种意义上便反映了如上的自觉。
不过,孔子在强调以义规范利的同时,又潜含着一种倾向,即突出普遍的整体之利(公利):在“见利思义”、“见得思义”的价值原则中,义所代表的整体之利,似乎被提到了至上的地位,这种倾向如果进一步发展,往往将导致以义抑制利,并相应地忽视个体之利,在尔后的儒家思想特别是正统儒学那里,我们不难看到这一点。
义作为整体之利的确认与人的族类特征之体现,总是以理性要求的形式出现;利在广义上以需要的满足为内容,而这种需要首先表现为感性的物质需要,这样,义与利的关系往往进而展开为理性要求与感性需要的关系。与容忍合理之利相联系,孔子对感性的物质需要并不简单地加以贬斥。《论语》中曾记载,孔子平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乡党》)。食所满足的,是人最基本的感性需要,“食不厌精”表现了孔子对这种需要的肯定。不过,尽管孔子并不怀疑感性需要的正当性,但却反对沉溺于此。在他看来,合理的态度是“欲而不贪”(《尧曰》)。欲表现的是感性的要求,而贪则是无限制地追求感性欲望的满足。感性欲望本身无可厚非,但一旦超过了适当的度,则将转向反面。要避免这种状况,便必须以理性的要求对感性欲望加以节制。
与肯定义以为上相联系,孔子更为关注理性的要求。在孔子看来,感性的欲求固然不应当忽略,但相对而言,理性要求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此,人首先应当实现理性的要求: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道在此指广义的社会理想(包括道德理想),谋道所体现的,即是理性的追求。在感性欲求(“谋食”)与理性追求(“谋道”)两者之间,后者显然具有优先地位。当然,不谋食并不是指完全摒弃感性欲望,而是使物质需要从属于理性的追求。一旦志于道,则即使处于艰苦的生活境遇,也可以达到精神上的愉悦。孔子曾这样称赞其弟子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这种人生态度,也同样表现为孔子自己的道德追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此处所描述的乐,也就是后来儒家(特别是宋明新儒学)常常提到的“孔颜之乐”,它的核心即是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孔颜的这种境界将精神的升华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强调幸福不仅仅取决于感性欲望的实现程度,从而进一步凸显了人不同于一般生物的本质特征。在理性对感性的超越中,人作为道德主体的内在价值也得到了更为具体的展示。
不过,应当看到,孔门的如上境界同时又蕴含着理与欲之间的某种紧张。在谋道不谋食、安贫而乐道的价值取向中,人的感性需要尽管没有被否定,但却被理解为一种从属的因素;理性似乎可以在感性之外甚至先于感性而得到发展。这种理性优先的观点,显然未能真正达到存在与本质、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它在理论上埋下了以人的理性本质抑制人的感性存在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