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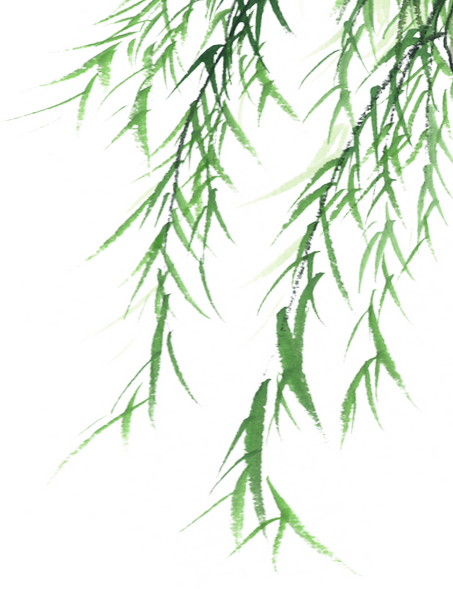
村里难得有个在战场立了功回来的, 大郎这个最平常的大头兵也成了稀罕人物, 一圈的汉子围着大郎问东问西:“什么南蛮子长得什么样儿?在军营里吃什么?长官威武不威武?那个什么校尉大人是多大的官儿?有没有县太爷的官大等等。”有些可笑, 却也无可厚非, 百姓的眼中, 县太爷就是顶大的官儿了。
说到这个, 碧青不禁想起上次那位杜知县, 一看就是世家子弟, 外放到间河县这样的地方, 估计就镀金,做出点儿政绩也好升迁。
虽说心思缜密,可为人却不坏, 碧青其实知道,想拿那十两奖银并不容易, 若照着程序走,到自己手里, 恐怕连一半都剩不下, 雁过拔毛是官场默认的规矩, 就算当官的抬了手, 还有下头的酷吏呢, 不盘剥老百姓指着那点儿俸禄,稀粥都喝不上。
碧青领这份情, 却并不觉得占了多大的便宜,皇上重农桑, 才设立了这个奖银制度, 自己不过得了十两银子,而对于杜知县却是最亮眼的政绩,可以想见,吏部今年的考评册上,间河县县令会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更是升迁的本钱,当官的嘴里口口声声为民做主,有几个是真的,即便喊得再响,若不为着头上的乌纱帽,恐怕天下人也不会如此趋之若鹜了。
就连王大郎这么个目不识丁的村汉,不也想着有一天能封侯拜相吗,瞧他在乡亲们羡慕的目光中一碗酒一碗酒的往下灌就知道,心里一定爽死了。
作为男人,无论世家公子还是乡野村汉,没机会还罢了,若有机会,没有不想出人头地的,碧青能理解王大郎的心态,但不敢苟同,就算王大郎得了高人调教指点,摸到了当官的门,可出身在这儿摆着也难如登天。
更何况,这还不是最大的硬伤,最大的硬伤是他目不识丁,没听说哪个当官不认识字的,哪怕最底层的那些小吏,至少也识几个字,大郎这样的文盲要是当了官,岂不成了大笑话,这就是命,谁也没辙。
想起这男人对自己呼来喝去的态度,碧青忽然失去了偷看的兴趣,这男人是自己名义上的丈夫,却距离她心目中的丈夫相距太远,可以说是天与地的差别。
碧青并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多有出息,但也绝不是王大郎这样把媳妇儿看成物件儿的男人,即使在这个男权社会,她也希望自己能跟丈夫拥有对等的地位,这才是夫妻。
可在王大郎眼里,女人除了那事儿就是生孩子,从他的目光里,碧青能清楚感觉到这种对自己的轻视。
碧青不知道怎么改变这种境况,王大郎回来是目前为止最大的变数,也是最大的危机,她喜欢何氏跟二郎,把她们看成了家人,可让她接受这头蛮牛当自己的丈夫,实在不乐意。
桃花娘见碧青有些怏怏不乐,以为累着了,忙道:“男人家都贪酒,不定要喝到多会儿呢,你先家去歇着吧,剩下的事儿就甭管了。”碧青巴不得呢,客气几句走了。
瞧着她出了院子,一边儿的王根儿婆娘啧啧两声道:“不服气不行啊,这人就是命,大郎这媳妇儿刚嫁过来的时候,还说这辈子就是守寡的命呢,谁想人大郎家来了,还立了军功,谋了个正经的兵差,这往后说不定就能当官,这个一口袋黍米换回来冲喜的媳妇儿,若是当了官夫人,祖上得烧了多少高香啊,早知道大郎能出息,当年他家找媒人说我家三丫头,我就应了。”
桃花娘不爱听了,哼一声道:“早干什么去了,这会儿后悔晚了,再说,就你那家那三丫头,跟人大郎媳妇儿能比吗,别一口一个冲喜的,你们谁家媳妇儿有大郎媳妇儿的本事,王家之前可都快揭不开锅了,再瞧瞧现在,人家那日子过得,比你们哪家差了。”
王根儿家的被桃花娘几句话呛回来,嘟囔道:“咱不就是说闲话吗。”
桃花娘道:“有背后说闲话的功夫,把自己的日子过红火了,比什么都强。”
王根儿家的不言声了,旁边二柱子娘低声道:“咱们也就眼红些,可真有睡不着觉的呢,你们刚没瞧见王青山两口子,在院外边的墙根儿站着,冻得唧唧索索的也不敢进来,趁着人家没顶家的男人,可没少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如今大郎家来了,估摸觉都睡不着了。”
桃花娘道:“乡里乡亲的,瞧着孤儿寡母正该拉一把,他两口子倒变着法儿的欺负人,这才是活该呢。”
碧青一出了王富贵家的院门,就瞅见墙边儿的王青山两口子,两口子见她出来,互相推了一把,最后还是王青山的婆娘走了过来,勉强露出个比哭还难看的笑脸:“那个,大郎媳妇儿,以往都是婶子的不是,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头去。”一边说着一边儿瞧碧青的脸色,战战兢兢,怕的脸都白了。
碧青却笑了:“过去的事都过去了,婶子就别提了,再提可就远了,我婆婆前儿还念叨婶子,说婶子鞋上的好,大郎的好几双鞋都是婶子帮着上的,最是牢靠,让我得闲儿跟婶子好好学学呢。”
王青山的婆娘一愣,再也没想到,会是这么个结果,从知道王大郎回来,两口子就怕的不行,越想之前的事儿越怕,生怕王大郎打上门来,要给他娘兄弟出气。
两口子来王富贵家,也是想寻个机会认错,不敢进去找王大郎,就在院外头等着碧青,计量着妇道人家总好说话些,却没想到人家根本不计较,还客客气气的拉着她说家常,就算王青山的婆娘是村里有名的泼妇,望着碧青笑吟吟的脸,也羞愧难当。
拉了两句家常,碧青搓了搓手道:“今儿可是冷,叔跟婶子快进去吧,别冻着了,家里的鸡鸭还没喂呢,我得回去瞧瞧。”撂下话走了。
王青山的婆娘直愣愣瞧着碧青的身影越来越远,半天方低声道:“当家的,大郎媳妇儿这是啥意思?”
王青山老脸通红,瓮声瓮气的道:“当初我就说,人家孤儿寡母的不易,乡里乡亲的,别落得不好,你偏不听,明明不占理儿还弄到里长跟前来,小肚鸡肠的让人笑话,你瞧瞧人大郎媳妇儿多大度,要我说,赶紧给大郎娘赔礼去,我瞧大郎媳妇儿是个厚道人,不会难为咱家的,往后可得厚道着些,老人的话对,这一分厚道一份福啊。”
当初王青山两口子耍刁欺负人的时候,碧青也生气,恨不能把王青山的婆娘揍一顿解气,心里却也知道,打一顿不是解决问题的法子,一个村里头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真闹的太僵,往后可怎么处,传扬出去,自己家没准还落个仗势欺人倚强凌弱的恶名,本来占理的事也弄成不占理了,欺负人的王青山家反而成了苦主。
傻子才干这样的事儿呢,倒不如大度些揭过去,庄稼人实诚,心里都有把秤,谁好谁坏,比谁都清楚,比起被王青山两口子占的那点儿小便宜,得一个好名声,可比什么都强。
果然,进了院没一会儿,王青山的婆娘就来了,不由分说拽着她婆婆就走了,碧青忍不住点点头,这王青山家的泼妇倒也不算太傻。
二郎也不在家,估摸跟着王小三跑出去玩了,两个半大小子正淘气,到了一块儿就没个闲着的时候。
碧青进了灶房,从瓮里舀了小半瓢麦糠,兑上切得碎碎的番薯藤,倒在鸭食盆子里,这二十只鸭子可是给家里立下了汗马功劳,墙根儿那满满一大坛子鸭蛋,过几天就能吃了。
碧青还特意留了些种蛋,想过了年多孵些小鸭子,鸡蛋也留了,明年的鸡窝还得重新盖大些,鸭舍也得盖一个,或者,可以垒个猪圈,耕牛那样的大牲口,碧青就不想了,守着王富贵家呢,若是用牲口,借来使就是了,牛可贵着呢。
倒是小猪仔能养几头,桃花娘前几个月就跟自己说了,要买小猪仔就去她家挑,她家的种猪壮,小猪仔也结实,养上一年,到年底一宰,过年就不愁肉吃了。
碧青正想着在哪儿垒猪圈呢,忽的身后门一响,一股子酒气冲过来,碧青还没回过神来,就被大郎按在了麦草里,男人粗重的呼吸裹着酒气,熏的碧青有些蒙。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发现蛮牛一手按着自己,另一只手竟伸到自己腰上,要解她的裤子,明明白白要霸王硬上弓。
碧青这个后悔就别提了,早知道刚才不跟王青山家的装大度了,也省的那泼妇把她婆婆拉走,这会儿自己想叫都没人,刚看蛮牛不醉死不罢休的样儿,谁想到他这么快就跑回来了。
要是让这禽兽解了裤子,碧青相信,他不会管自己死活,没准还更兴奋,现代时,不就有很多男人有恋童癖吗,自己这个德行没准正符合了男人的恶趣味。
更何况,人都说,兵营三年母猪赛貂蝉,自己好歹比母猪强吧,真落到那种结果,自己也太悲惨了。
开始激烈挣扎,对着蛮牛又踢又咬,可碧青很快发现,自己所有的挣扎对付这个浑身都是力气的蛮牛根本没用,好比蚍蜉撼树,都不是一个级别上的。
踢腿被他抓住,打他,挠他,这厮皮糙肉厚,跟挠痒痒差不多,张嘴咬吧,自己牙根儿都咬酸了,蛮牛连点儿反应都没有,从他越发粗重的呼吸来看,反而更兴奋起来。
碧青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这头蛮牛根本就没想放过自己,而且,只要他想,自己根本就反抗不了。
碧青颓然放弃挣扎,眼泪决堤而出,从没有一刻,让她觉得如此绝望,哪怕在沈家村快饿死的时候,她都没这么绝望过,她闭上眼,等着最不堪的结果,感觉腰带松了,一双粗劣的大手从腰上探了进去,碧青浑身抖的如同寒风中的树叶,紧紧咬着唇,都快咬出血来了。碧青还没真正恨过什么人,可这一刻她恨这个男人,非常恨。
就在碧青绝望的时候,男人的手忽然抽了出来,耳边传来男人不满的声音:“哭什么,你是我媳妇儿,我是你男人。”
这男人直白的让碧青恨不能踹死他,碧青猛地睁开眼,抖着声音道:“王大郎,我是你媳妇儿,可我也是人,而且,我还不到十三呢。”说着恨恨瞪着他。
王大郎却理直气壮的说:“我也没想干那事儿,我就想摸摸,在军营待了五年,好不容易家来,摸摸媳妇儿怎么了。”
碧青气的险些晕过去,这什么逻辑啊,尼玛,摸摸,她不信他摸完了之后就能老老实实的,这就是一头发情的禽兽。
面对这样的禽兽,也得讲一下策略,碧青吸了两口气,略冷静了一些,脑子转了转,终于想到一个解决方法,极力忍着怒气,尽量用商量的语气道:“王大郎,你要是实在憋不住,就去找别人,你不是立功了吗,肯定有赏钱,拿着赏钱去城里的花楼,想找多少女人都成,我保证不吭声儿,也不跟娘说。”
碧青以为自己的提议,算是一个两全其美的主意,既彰显了自己的贤良大度,又解决了蛮牛的根本问题,不想蛮牛听了之后,瓮声瓮气的道:“有媳妇儿做什么花那冤枉钱。”
一句话碧青一口血险些喷出来,跟这头牛讲理根本是白费口舌,忽瞥见墙上挂着的镰刀,抬手摘下来,抵在自己的脖子上:“不想我死,就离我远点儿。”
碧青话音没落,胳膊一疼,镰刀就掉在了地上,男人捏着她是手腕子低吼:“不就摸了一下,至于寻死吗。”
见碧青狠狠瞪着他,大郎也有些挠头,本来还想收拾这丫头一顿,让她别总防贼似的防着自家,可没想到这丫头瞧着弱巴巴,却是这么个硬性子,只得退一步:“我不摸还不成吗。”嘴里说着,一低头眼睛却直了。
碧青刚要松口气,见他直勾勾盯着自己,顺着目光一看,恨不能一镰刀阉了他,简直是个色胚,刚一阵挣扎,自己棉袄的前襟扯开了些许,急忙掩上,防贼似的放着他。
大郎心里琢磨,他媳妇儿的脖子都这么白,那身子……一想早晚是自己的,心里就痒痒,可看见小媳妇儿那副宁死不屈的表情,只能把口水吞进肚子里,也放开了碧青。
手腕子的力道一送,碧青急忙跑了出去,刚跑出去,迎面正好撞见她婆婆何氏,碧青委屈的不行,终于看见亲人了,一头扎在何氏怀里呜呜的哭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