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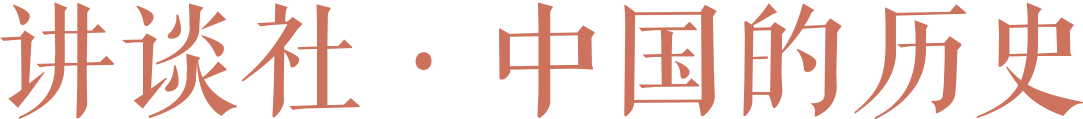
从神话到历史 神话时代 夏王朝

中国也是王朝国家。对一个继承了王位正统的王朝而言,连接历代王朝的历史,为前代王朝修订正史成为传统。二十四史就是这样的正史。如前所述,最早的正史是西汉司马迁编纂的《史记》。
中国自汉代以来均以这些正史为中心的文献记载为依据,儒学家之间盛行以考据正史为主的训诂学。清朝末期,欧美列强的势力波及中国,清王朝被迫敞开了国门。正逢欧洲列强先后达成产业革命、争相扩大殖民地统治之时,在他们眼中,中国和印度等国被贴上了落后专制的标签。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即以当时亚洲专制国家的存在为背景,从亚洲的立场来看,这也是一种包含歧视的历史认识。
在这样的政治状况之下,1919年中国爆发了众所周知的群众爱国运动——五四运动。这场运动直接起因于反对日本侵略政策的抗议活动,而在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也指在此之前就已开始的文化启蒙运动。这是一场以打倒旧式家族制度及儒教陈规、学习西欧近代思想的新文化运动。
乘着这场运动的潮流,历史学当然也不得不面临着向现代学问体系即科学体系发展的动向。其结果是,诞生了怀疑文献记载真实性的疑古派。
疑古派的代表首推创立了“古史辨”学派的学者顾颉刚。顾颉刚率先采用西欧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解说历史,从此迎来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黎明。对《史记》中《夏本纪》和《殷本纪》记载的夏王朝和商王朝是否真实存在而产生疑问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距今约一百年前的清朝末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他的食客刘铁云发现了甲骨文,这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大事件。其中罗振玉、王国维等沿袭清朝考证学传统的学者对甲骨文的解读尤具重要意义。
甲骨文中有“殷”字,成为殷商确实存在的证据之一。这可说是近代历史学上的一个重大成果。王国维还解明了甲骨文中商王的名字,并确定这些名字与历史记载的谱系基本一致。
但是要证实商王朝确实存在,必须以商朝遗址的发现为证据。当时龙骨还只是一种珍贵中药,于是人们开始寻找龙骨即甲骨文的出土之处。
清朝在日清战争中败北之后,加上义和团运动的打击,内忧外患,终于爆发了辛亥革命,清朝走向灭亡。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促进现代化而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是傅斯年。
傅斯年得知甲骨出自河南省安阳小屯,立即任用刚刚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李济,组成了安阳考察队。
在此之前,受聘于中国政府,在地质研究所任职的瑞典人安特生(J. G. Andersson)注意到已在学会公开的龙齿,并于1926年在北京郊外周口店的石灰岩采石场发现了人类的化石。化石埋藏于五十万年前的地层,被命名为北京猿人。
当时,荷兰人杜布瓦(Dubois,E.)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发现了人类化石,他认为这是比属于古人的尼安德特人更早的猿人化石,但当时学界对猿人是否扩散至亚洲尚存疑问。北京猿人的发现更证实了杜布瓦的观点,说明早期猿人(南猿)在非洲出现后,经过进化的晚期猿人很早就已扩散至亚洲。对于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的人类进化的多系统学说,上述发现都成为极其重要的根据。

9 仰韶文化船型彩陶壶
安特生于1921年在辽宁锦西沙锅屯遗址发现了彩陶。同年,又在河南渑池仰韶村发现了彩陶。这些彩陶类似于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彩陶,由此得以确证中国也存在过新石器时代。同时安特生极其重视中国彩陶与西亚的关系。他因此继续在甘肃考察,把在当地发现的彩陶命名为甘肃彩陶,并认为中国的彩陶源于西亚。
另外,1924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和德日进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发现彩陶,1923年桑志华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武灵水洞沟发现了后期旧石器。
在丝绸之路一带,瑞典的地理学家斯文·赫定、英国的东方学家马克·斯坦因、法国的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人进行了探险。敦煌文书被带到海外也是这个时期,即1900—1920年代。
日本人开始前往中国大陆考察也是这个时期。以京都帝国大学的滨田耕作教授、东京帝国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的马衡教授为中心组成的东亚考古学会于1927年开展了首次大陆考察,即在今辽宁省碧流河河口附近的貔子窝遗址开展的考察。
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后,在满洲即今中国东北部一带大举扩张势力,考古学者们也在这里正式开始发掘考察。
据说滨田耕作对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逃亡至日本的罗振玉带来的殷墟出土文物格外重视,他最初期望的是对殷墟的考察。然而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了殷墟的发掘考察,所以滨田耕作不得不放弃了这个愿望。
其后,东亚考古学会的发掘开始以当时的满洲尤其是辽东半岛为中心展开,发掘对象主要包括牧羊城遗址、南山里的汉代遗址、营城子汉墓、羊头洼遗址等。另外,桑志华和德日进在赤峰发现的彩陶也引起了滨田耕作的兴趣。1935年,他考察了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确认了彩陶文化与青铜器时代两种文化的存在。红山后遗址的彩陶文化现在被认为是中国东北部的特殊的新石器文化即红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
滨田耕作的上述业绩作为与侵略行为相呼应的殖民地考古学,当然应该受到批判,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可以算是该地区现代考古学的开拓者,而且在发掘考察后不久即印行了大量的发掘考察报告,其勤力治学的精神值得尊敬。这些考察是现代考古学开拓期的考察,虽然其中包括考察精度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在发掘考察报告中所做出考古学基本评价,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提供基础资料,其学术意义至今尚存。
其后,从太平洋战争开战前夕的1941年至1942年,由日本学术振兴会在辽东半岛进行了一系列史前时代的遗址考察,范围包括四平山积石冢、老铁山积石冢、文家屯贝冢、上马石贝冢等。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这些考察成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考察的最后一幕。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傅斯年尝试从科学的角度证明《史记·殷本纪》中所记载的殷商的存在。1928年,他指派董作宾到据传出土了甲骨文的河南省安阳小屯进行先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小屯极可能就是殷墟的所在地。
傅斯年决定凭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对殷墟进行正式的发掘考察。其后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受命担任考察队长。李济曾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专攻现代考古学,他召集董作宾等年轻有为的学者组成考察队。成员包括郭宝钧、梁思永、吴金鼎、高去寻、石璋如、夏鼐等。殷墟的正式考察于1929年开始,除去1930年对山东省济南章丘市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考察之外,得以持续进行了共十五次,直到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
在此期间,于小屯发现了宗庙遗址及大量的甲骨文。于侯家庄发现了王陵及祭祀坑,考古调查取得卓著成果,并证明了安阳即殷墟所在地。发掘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从安阳搬运至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南京。
1937年爆发了中日战争,随着战事不断激化以及日占区的扩大,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迫于事态危急,不得不步步后退,最终退至重庆。
在这次撤退中,安阳殷墟的文物与故宫文物一起被撤离南京博物院,不得不随同历史语言研究所向湖南长沙、云南昆明、四川李庄等地转移。在此期间,研究所的学者们的研究得以勉强维持,但在殷墟发掘的文物却不能轻易打开。
这一时期成为甲骨文的受难期。中央研究院转移期间,关于出土甲骨的正式报告已接近出版阶段,然而因战争的影响,出版两度受挫。直到发掘考察之后约二十年,经第三次筹划才得以出版了正式的考察报告。受害的还不只是出版的延迟,作为《小屯》乙篇出版的H127坑出土的甲骨在发掘出土时形状完好,却因在战争中转移而受损,变成一堆无法复原的碎片,导致其资料价值大大降低。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中国大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军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开始了全面内战。以陕西延安为据点的共产党军队首先解放了中国东北部,占据有利形势,并逐步南下。国民党军队被共产党军队围困孤立,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仓皇逃往台湾,并在该地保住了残余势力。
这时故宫文物与殷墟文物被一同转移至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终于得以在台北南港安顿下来。现今故宫博物院分为北京与台北两地,原因即在于此。
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于1949年在北京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些曾参加安阳考古调查的青年学者此时不得不面临人生道路的一大抉择。与历史语言研究所一道撤退至台湾的有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人,留在中国大陆的则有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人。李济后来成为台湾大学教授,致力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建设。张光直即毕业于此,他后来前往美国,成为哈佛大学教授,将中国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发扬至国际学界。
另一方面,留在大陆的郭宝钧、梁思永、夏鼐等学者加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再度展开大陆的考古调查。安阳也在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再度开始时隔十三年之久的发掘考察,并获得武官村大墓和祭祀坑等发掘成果。1959年,在安阳开设了进行调查事务的工作站,长期派驻研究者在此进行发掘考察和研究。当今中国大陆的考古调查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以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导的形式获得了显著的成果。
早在建国前,本书将要论及的新石器时代的著名遗址就已经为尚处在草创期的中国考古学界所周知。其中之一即成为红山文化名称来由的红山后遗址。另外,1928年发现的山东省龙山镇城子崖遗址也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吴金鼎等学者于1930年和1931年分两次进行了考古调查。城子崖遗址正是龙山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饶有兴味的是,在城子崖遗址的这两次调查中发现的文物现收藏于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浙江省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的六处黑陶文化遗址进行了试行发掘,这是以绚烂豪华的玉器文化闻名于世的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
如前所述,在1920年代,安特生发现了彩陶文化的遗址。其一是1921年发现的河南省渑池县的仰韶遗址。这里成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遗址。其二是由安特生发现的甘肃彩陶。如此看来,关于今天广为人知的各地新石器时代文化,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仰韶文化、甘肃彩陶文化、红山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主要文化的标志性遗址都已得到发掘考察。
在这些文化当中,作为彩陶文化的仰韶文化和作为黑陶文化的龙山文化被认为是源于不同系统的民族,即有名的夷夏东西说。这是由傅斯年在当时提出的观点。然而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的差异并非出于民族的差异,而是出于年代的差异。这个观点要等到建国后于1959年进行的河南省陕县庙底沟遗址发掘之后才得以明确证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各地的考察与发掘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当时称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进行。该研究所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1950年。第一任所长是郑振铎,之后由尹达以及曾在英国学习近代考古学的夏鼐担任领导,苏秉琦、王仲殊、徐苹芳、安志敏等为其中佼佼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即发现了除殷墟之外存在的商代中期遗址琉璃阁遗址。另外还在固围村遗址对三座战国时期的魏国墓葬进行了发掘考察。1954年在洛阳设置了工作站,其后又设立了西安研究室和安阳工作站,长期持续地开展了有组织的考古调查。可以说所有这些考古调查呈现的是国家级工程的形态。
在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即后来的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是培育年轻学者的基地。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正式成立于1952年,负责人是苏秉琦、俞伟超、宿白、邹衡、严文明等。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就这样,以学术机关与教育机关为两轮,新生中国的考古学研究走向了发展之路。
仅就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来看,在建国后不久的1954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导下进行了西安半坡遗址的考古调查,成功实现了对整个聚落的全面发掘考察。之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夕,北首岭遗址、安阳后岗遗址、山西省西阴村遗址、甘肃省临夏姬家川遗址等,在当今考古学史上意义重大的遗址都得到发掘考察。同样,北京大学的学者们也对成为中原陶器编年标准的洛阳王湾遗址,以及有着多人合葬墓的元君庙仰韶墓地等进行了发掘考察。
1966年至1971年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在中国社会留下巨大创痕。此期间内,也是整个国家的社会机能趋于麻痹的空白期间。考古学研究也受到影响,研究被迫中断。该领域的主要学术杂志《考古》、《文物》及《考古学报》都被迫停刊。另外,考古学调查也不得不中断,但其间仍进行了如1968年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与夫人窦绾的合葬墓即满城汉墓的发掘考察,以及1969年北京的元大都的发掘考察。
从群众运动转化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逐渐平息,自1972年起,各主要学术杂志也得以复刊。同年,殷墟及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再度开始。在殷墟孝民屯遗址成功地保存了商代车马的完整形态。在二里头遗址,一号宫殿基址得到全面发掘,其全貌得以公之于世。此后考古学研究及发掘考察得以在全国全面恢复,考察与研究活动也日渐兴盛起来。

随着“文化大革命”导致的社会逐渐平复,考古学研究再度恢复了活力。1972年中国相继与美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恢复邦交,中国逐步开始对外开放。特别是1978年12月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路线实施以后,伴随巨大的路线转变,中国的经济增长开始加速。
在此时期,与从前的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为中心进行的发掘考察不同,各地博物馆及大学逐渐开始进行自主的考察研究。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地方的文物考古研究所从博物馆独立出来,成为独自进行发掘考察的专门研究机关。
各地发掘考察的进展虽说始于七十年代后半期,其发展其实与改革开放路线同轨而行,到了八十年代初期,除了之前的三大学术杂志,各地也开始发行地方考古学的专业学术杂志。1980年,陕西省的《考古与文物》、河南省的《中原文物》、湖北省的《江汉考古》分别创刊。1981年创刊的杂志则有黑龙江省的《黑龙江文物丛刊》(后改称为《北方文物》)、江西省的《农业考古》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内蒙古文物考古》。
其后,至八十年代后半期,又有陕西省的《文博》、辽宁省的《辽海文物学刊》、河南省的《华夏考古》、江苏省的《东南文化》、江西省的《南方文物》、四川省的《四川文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新疆文物》、河北省的《文物春秋》、山西省的《文物季刊》(后改称为《文物世界》)等。
随着各地出版活动的活跃,加上发掘考察报告迅速增多,之前极其有限的考古资料得以飞速增多。同时,以这些丰富的资料为背景的研究活动也日益深化,而且具备了在考察后把成果及资料尽早与其他学者分享的学术环境。自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开始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上述活动得到更进一步充实。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不仅对国内的学者,也对海外学者予以共享,从信息公开的意义上来看,这也可说是学术研究的一大进展。
1990年代,改革开放路线为中国的经济带来飞跃性发展。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各地的城市化,同时也在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与工业化落后的内陆地区造成了经济上的差距。各省之间的经济差距又导致了预算的差距。
1970年代后半至1980年代期间在各地成立的考古研究所和文物考古研究所也难免受到经济状况的影响。有享受着丰厚的考察研究费用的大城市的研究所,也有连少量考察费也难以负担的地方级研究所。经济差距自然也导致了各地考古学的研究进展的差距。
经济的发展还引发了急速的国土开发,对濒临破坏的遗址的紧急发掘也随之急剧增多。这也是当今考古调查的一个特征。这种事态使得考古资料数量大增,另一方面的现状是,越发旺盛的发掘考察报告等信息普及也引发了考古资料信息泛滥的现象。这与日本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相当类似,这些问题正日渐成为当前的课题。
中国当代社会正急剧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城市,现代建筑使市容焕然一新,社会生活也随之改变。尤其是闹市区出现的快餐店,其景象与日本甚至美国并无二致,这也是近年来的变化之一。
朝着IT社会的转变日渐迅速,城区的网吧随处可见。然而遗迹参观考察所到之处的农村地区或荒野一如往年般寂静,令人难以想象这是同一国度的景象。这样的社会变化也对大学的机构组织带来影响。近似日本的所谓大学院大学(研究生院)的制度,中国也已开始采用。
例如北京大学的考古学系,相当于日本的考古学部。所设专业有:按时代划分的旧石器、新石器——商周、汉——唐专业,以及古文字、陶瓷器、博物馆学、考古科学等。其组织庞大,拥有师资三四十名。这般规模已是日本所没有的专业大型的考古学教育机构。1998年,又新设为兼有文物保护与古代建筑专业的专业考古学教育机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又称中国文物博物馆学院)。
考古文博院在1999年和2000年又分别开设了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和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其作用类似于日本的文部科学省主导的COE(Center of Excellence)制度,是为建成高级教育研究机构而设的制度,并享有特别预算。另外,吉林大学考古系也利用该制度申请并获准成立了吉林大学边疆考古学研究中心。开展边境地区的考古学及体质人类学研究,并积极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
另外,在1996—2000年,为科学断定夏商周年代而展开了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这是一项国家级工程。所谓夏商周三代,即中国最初的王朝夏朝、因殷墟甲骨文而得以确定的商朝以及灭亡商朝后建立了封建国家的周朝所存在的年代。
这三个朝代的历史均记载于《史记》,然而其年代只有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以后的纪年得以确认。之前的年代只能以相对的年代关系来把握。
因此,关于商纣王灭于周武王的确切年代,人们只能从文献记录以及古代天文现象的关系来进行考证,进而总结各种观点得出公元前十一世纪左右这个年代。而年代更加久远的商朝的成立时期,或是商朝盘庚迁都的年代,还有传说中的王朝夏朝的成立年代等等,都还包裹于谜团之中,尚无决定性的证据来确定其年代。
为解决这些问题,就要综合考古学、历史学、天文学、文物科学的力量,以求得出最为接近实际年代。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
作为这项研究计划的一环,学者们在周朝初期的都城周原进行了发掘考察,并获得了新的考察成果。2004年,周原被认为很可能就是周王陵,这可算是该项研究的一个进展。但是目前对该处是否确实是周王陵尚无定论。在此之前周王陵一直不为人知,如果周原真的是周王陵所在地的话,这将是跨越三千年时间的伟大发现。周原王陵位于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附近。今后的发掘考察值得期待。
夏商周三代断代工程是在中国在经济发展取得成效后,为加强民族意识,把古代中国定位为先进文明而进行的。就像汉代至唐代,都曾把炎帝、伏羲、女娲从传说中发掘出来,作为史实来进行考证一样,其目的在于确定本民族的祖先,肯定其先进性和文明性。同时这也是一种国家战略,为的是对中国文明作为领先世界的四大文明之一的事实从科学的角度加以证实。中国的大国意识,也鲜明地反映在当前的这种历史观之中。

如前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随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本学者曾在以中国东北部为中心的地带直接参与了发掘考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这些考察活动为当地确立了正规的考古学调查的基础。日本学者们之所以在当时就对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寄予关心,是因为流传至日本列岛的多种文化的源头都来自上述地区。就像欧洲社会为了到西亚寻求自身文明的源头,而在当地开展了殖民主义式的考察,我们不能否认,日本的考古学考察在当时也是站在政治支配的立场上进行的。
战后,日本学者被逐出大陆考察的领域,其后,五十年间无法进行在大陆的考察。在此期间,丧失了中国大陆这块考察田野的考古学者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距离大陆最近的对马、壹岐以及北海道东部的发掘考察。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两国间的直接交往几乎是不可能的。《考古》、《文物》、《考古学报》等主要学术杂志成为在日本唯一可用的中国考古学基本资料。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7年,经中国科学院邀请,以东京大学的原田淑人教授为团长,驹井和爱、水野清一等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著名学者组成的代表团在战后首次访问了中国。代表团一行经香港由陆路进入广州,参观考察了南京、北京、敦煌、西安、洛阳等地,然后又经香港回到日本。在今天这样的迂回路线几乎是无法想象的。代表团成员们在访问中亲眼看到,新中国成立伊始,就已拥有充实的考古学资料,同时举国上下积极保护文物古迹的情景也令代表团成员感动不已。
代表团中最年轻的成员是冈崎敬,其次是樋口隆康,两人当时还是三十出头的青年。后来樋口隆康成为京都大学教授,冈崎敬成为九州大学教授,他们堪称战后日本中国考古学的带头人。对这些学者而言,日本的中国考古学虽然拥有战前的积累,但无法直接到当地考察并接触文物的情况无疑有一种隔靴搔痒般的遗憾。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间的正式往来得以实现。然而当初学者的交流却并不容易。直到后来才逐渐可以直接接触中国的相关资料。
1978年12月以后,中国转向改革开放路线,中日两国间的学者交流才如同大坝决堤一般活跃起来。1979年,第一个日本考古学者获准到中国留学,其后每年都有年轻学者前往中国留学,得以直接学习中国考古学。
同时,八十年代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路线之后,也迎来了各地大显身手的时代。各地诞生了以区域为单位的考古学学术杂志,研究资料的公开变得丰富且迅速。在日本,以中国考古学为专业的学生开始增多也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国考古学不再是七十年代以前那种遥不可及的状态。我也是在这种形势下走入这个领域的学子之一。我于八十年代正式开始学习中国考古学,并前往中国留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樋口隆康、冈崎敬两位前辈看来,形势的变化一定令他们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中日间学术交流于八十年代正式展开。而双方的交流得到更快速的发展则应该说是在1991年2月,考古涉外工作管理办法修订之后。由于这项办法的修订,在与中国学者共同研究的先决条件下,外国学者也可以获准在中国大地上参加发掘考察。这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的一环。目的在于学习海外先进的考古学、科学保存的技术,以提高中国考古学的学术水平。接下来是我参与共同发掘的一些体会。

中国迄今为止与海外学者进行的共同研究中,其对象国主要是美国和日本。中国与日本的联合发掘考察始于1995年。详情将在后文中加以说明。在此先把中日共同发掘的主要的遗址名列举如下。
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浙江省普安桥遗址、内蒙古自治区岱海遗址群、四川省宝墩遗址、湖南省城头山遗址等。商周时代的遗址则有属于二里岗文化的都城遗址,即河南省府城遗址。汉代以后的遗址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交河故城城南区古坟群车师国时代墓,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北周田弘墓,唐代史道洛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尼雅遗址、陕西省汉长安城桂宫二号遗址等。
在与美国联合发掘考察中,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主要有:山东省两城镇遗址、江西省吊桶环遗址、仙人洞遗址。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代的遗址有:河南省商丘遗址群、四川省的中坝制盐遗址等。另外美国还积极参与了山东省两城镇遗址周边、河南省二里头地区、河南省安阳周边、山西省垣曲周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地区等遗址的分布调查,并积极开展研究,利用计算机的地理信息系统实施了空间分析,从遗址分布的时代变迁入手,对区域历史的发展流向进行了大致调查。
由于美国的学术风格以及之前学术积累较之日本相对薄弱,与美国的共同调查通常不立刻开展发掘考察,而是从绵密的遗址分布调查开始,在充分把握调查成果之后,才开始进行发掘考察。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考察重点置于初期的遗址分布调查。实际上,通过全面开展遗址分布调查,发现了大量不为人知的遗址,并且,从这些调查成果中得出了许多为前人所忽视的历史性的新观点。由此我们也认识到,这种绵密的调查在中国大陆是非常必要的。
在中国由于遗址分布已得到确认,使之成为被忽视的研究领域,然而对共存于东亚的日本学者,我认为这是一个必须的视点。
我参加的中日联合发掘考察有三处:湖北省阴湘城遗址、江苏省草鞋山遗址和内蒙古岱海遗址群。在阴湘城遗址,我们发掘了新石器时代的巨大城垣。在草鞋山遗址,我得以参加了东亚最古老的水田遗址的发掘工作。而在岱海遗址群,我们在气候变动显著的长城地区以时间为轴线明确了环境与遗址的关系。
参加上述联合发掘考察之前,我曾在自1990年起的三年时间里,体验了与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联合考察。这三年的考察是在外国人被许可参加发掘考察之前的事。所以,我接触的是遗址的测量调查、遗址参观以及文物调查等工作。但这是首次获得国家文物局正式许可的联合考察,为此,整个考察团队都深感自豪以及责任重大。日方考察团的团长是大手前大学的秋山进午教授,中方团长是当时辽宁省文化厅的副厅长郭大顺先生。
第一年度我们进行了测量调查的遗址包括:属于二里头文化并行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辽西凌源县城子山遗址、同为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的阜新县南梁遗址。第二年度,我们测量调查的遗址有:位于辽东半岛,属于商代并行期的积石冢即大连市王山头积石冢。第三年度,我们对属于辽东支石墓墓地群的凤城县东山大石盖墓进行了测量调查。

10 使用光波测距仪进行实测的情形

中国考古学界的学者们似乎很少亲自使用测图板和照准仪(平面测量工具)进行简单的平面测量,也不太操作光波测距仪(total station)等测量器具。对我们所做的单调的调查,中方学者们看起来仍抱有一些怀疑。我还记得日方学者一边尽力说明遗址的测量工作对考古学者获取信息有何意义,一边在初冬凛冽的寒风中实施调查的情形。
这些测量调查的意义详细记录在了共同发表的考察报告书中。我想,这些记录可以表明,即使不进行发掘,从基础的调查中也可以获取各种各样的信息。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经过测量调查之后,从中获得的信息也促生了新的假说,进而想加以验证也是人之常情。望着我们测量过的遗址,我们不禁开始盼望能在该处设立考察区域,通过发掘来判明假说的真伪。
1995年春,首次参加在中国的发掘考察终于得以实现,这是我一直以来期盼的机会。那是在湖北省荆州市阴湘城遗址的发掘考察。经福冈市主办的文化研讨会派遣,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冈村秀典副教授已在前一年访问了该遗址,经过交涉,终于使发掘考察得以实现。这次发掘考察由福冈市文化研讨会主办,由福冈市教育委员会与湖北省江陵县博物馆共同参与。日方考察队的队长为冈村秀典,中方负责人由江陵县博物馆的副馆长新石器时代专家张绪球先生担任。
在中国进行联合考察和共同发掘时最常遇到的是住宿问题。对我们而言,简易的住宿环境并不成为问题,然而中方把我们当客人招待,尽力为我们避免简陋的待遇。为了选择适当的住宿条件,住处大多选在宾馆酒店,但是遗址附近很少有这样的住处。毋宁说保存完好的遗址大多位于郊外,遗址与宾馆的距离往往较为遥远。这与欧美人在遗址附近搭帐篷住宿,以实用为优先的考察大不相同。我曾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经历过与俄罗斯学者的联合考察。在遗址附近搭建帐篷,在河水中洗澡可谓家常便饭。然而在中国这是不被容许的行为。也许因为事关治安和饮食的安全问题,所以难以实现。
中国学者们平时并不讲究饮食,在接待外国学者时,却一定要准备相当规格的饭菜。这也关系着中国人的面子。中国人时常意识到面子问题。我们面对各项交涉时,也不得不考虑到面子问题,这可说是外国考察的宿命,唯有入乡随俗。阴湘城的发掘考察之时,从我们的住处到遗址需要近一个小时车程外加四十分钟的步行才能抵达。1995年夏天至1997年夏天在内蒙古岱海附近进行发掘考察时,我们住在工作站改装而成的住宿设施之中,即便如此,仍需在车上颠簸两个小时才能抵达考察现场。
在联合考察的过程中,对遗址和出土文物的记录方法,双方产生了分歧。日本人对这些问题的要求极为繁琐。或许是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导致的不同,日本学者们觉得没有制成精确的图纸图面就不能算作正规的考察。
中方的调查采用的是沿用英国考古学传统的探方考察法。首先以5米见方为一格挖掘探方,也就是说首先设置好坐标网格后再开始发掘。这样的探方呈网格状分布,网格状的探方间留有隔梁,隔梁对把握遗址的层位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这样的方法在日本也经常使用,但问题在于测量的基准坐标。即便是看上去规整如棋盘的探方,实际上只是依靠大致的丈量挖掘而成,当遗址位于倾斜地形之上,间隔距离即为斜线距离,虽然肉眼看不出误差,但实际测量后,往往达不到5米见方的规格。

11 探方发掘法 以5米见方为一个格,做网状发掘,隔梁用于观察地层
在以往的考察中,这些探方或网格被作为与实测用纸的网格同等的实测基准。然而如前所述,这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误差。在日本,这样的情况通常使用经纬仪或光波测距仪来进行实测,并用在地表设置基准桩的办法来确定精确的基准坐标。这样的作业方式对九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考古学者们来说还很陌生,或者是因为拥有这类仪器的研究单位还不多。在辽宁省与中方共同实行测量调查时也是这样的情况,我们不得不从这种测量的意义以及以探方为基准产生的误差开始进行充分的说明。
阴湘城遗址是面积广大的新石器时代城址。我们在发掘考察之前在该处制作了精确的地形测量图,使土垒及其外侧的环壕的复原成为可能。
关于各处发掘考察的具体情况,与在日本的考察同样,我们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令人忘却烦恼和疲劳的要数收工之后的餐食。各项考察为了节约经费,往往直接雇佣当地人为我们做饭。我们因此得以品尝到当地的家常风味。在阴湘城和草鞋山进行发掘考察的时候,主食的大米都是籼米。对于吃惯了粳米的日本人来说,应该说是并不合口味,但是用蒸笼现蒸出来的香喷喷的米饭实在非常可口。
中国各地的口味千差万别。较之草鞋山口味清淡的饭菜,阴湘城则多用辣椒作调料,味道偏辛辣,而内蒙古的菜式则有豪放的华北之风,总之各具特色。从食物素材来看,阴湘城位于长江流域,餐桌上常有河鱼的菜式。对那些遗址中发现的鱼的种类,之前只能从文献中得知。而今通过品尝当地的饮食,使我对那些鱼的形态有了直接的了解。
当然,我们在内蒙古也得到了羊肉的款待。从如何宰羊到羊肉的各种做法,我们都得到了学习的机会。与此同时,我们也目睹了考察地附近的居民生活习俗的差异。考察中通过与在当地临时雇用的老百姓的实际接触,我们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以及日常生活的情形。另外,参观附近民居也使我们看到,阴湘城所在的长江中游地区与华北内蒙古在村落形态以及住房空间上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我想,这些差异上溯到史前时代,也是必然存在的。
从另一方面来看,草鞋山是位于大城市附近的近郊农村,近年迅速富裕起来,虽留有旧时水乡的遗韵,却让人切实感受到农村的巨大变化。对于农村留存下来的各种民俗,应加紧记录和采访调查。我作为一个外国人,也不禁为之感到焦虑。目前因为三峡大坝的建设,附近居民的迁移已经开始。全国各地的考古学者被集中到这里,展开紧急发掘考察,并对考古学资料进行记录,然而民俗调查却受到忽视。长年居住于此的居民们的风俗和生活习惯及技艺正急速转向荒废,令人不禁担心这些民俗资料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就消失在时间的长河之中。
2000年以后,中日联合考察逐渐转向低潮。若要开展联合考察,必须得到文物局(相当于日本的文化厅)的许可。以目前的状况,想要获得联合考察的许可,其难度较当初可说是增大了许多。其原因包含一定的政治因素,但主要是因为随着中国学者研究水准的提高,与外国共同开展研究本身也逐渐丧失了魅力。加之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关领域已发展到了不需要寻求外国经济支援的阶段。
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另一种意义上也为中国考古学界带来了巨大的激励。与日本的经济高度成长期类似,随着各地的开发不断加速,紧急发掘也急速增多,同时关于这类发掘成果的出版物也迅猛增加。以往那种不成熟的印刷技术也得到改善,带有大量豪华彩色图版的学术报告也变得毫不稀奇。而且价格昂贵,在现阶段想要收集所有的相关出版物,以学者个人的财力已难以负担。
在此情况之下,学问的发展引发了学问的细分化。像过去那样,把中国考古学笼统地看作外国考古学,对其进行网罗所有时代的体系研究,或是涵盖旧石器时代到历史时代,或是就贸易陶瓷展开全领域研究的时代已经走向尾声。而在中国国内,各地的研究交流还不够充分。能够横跨各地掌握整体资料的学者在中国仅限于极少数的学术权威。另外各地研究者的观点也存在分歧,各地之间甚至有就遗址、文物的年代久远及珍贵程度进行竞争的现象。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作为一名外国考古学者,要想对史前时代进行通史性质并网罗全域的综合研究,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本书仍将对中国的史前时代做出综述。我也想凭着自己参加中日联合发掘考察的经验以及在实地对文物和遗址的观察,来执笔论述,而结果究竟如何呢?
在下一章,将探讨中国大陆农业社会如何诞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