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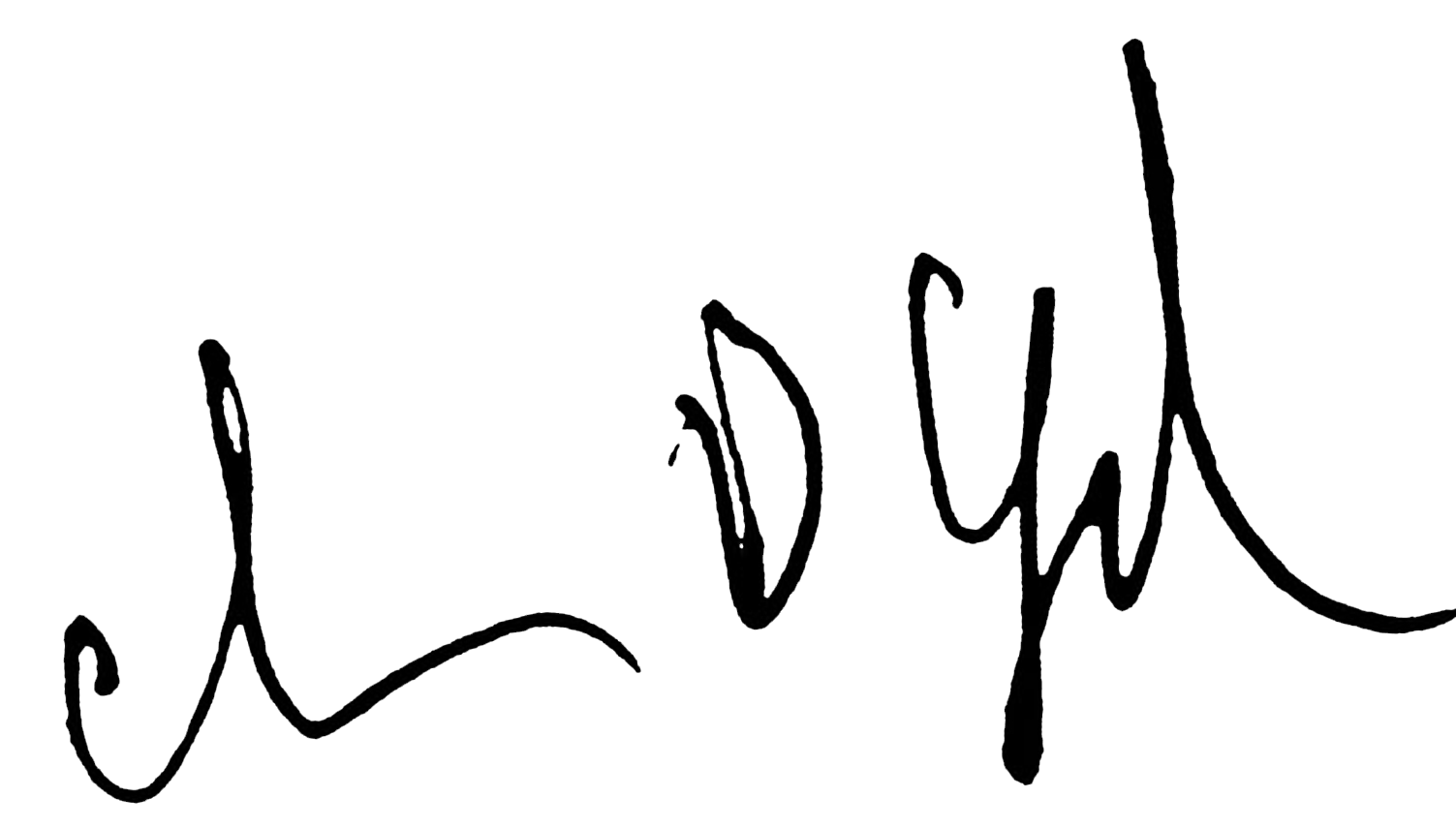
四个星期后,在位于贝克街7号的办公室内,布雷尔坐在他的书桌前面。时间是下午4点钟,而他正焦急地等候路·莎乐美小姐的到来。
对他来说,在他的工作时间内会有这样一段空档,相当不寻常。然而,想要见到路·莎乐美的渴望,让他迅速打发了之前的三位病人。全部都是无关痛痒的小病,他没花什么精神就解决了。
头两位患者都是60多岁的男士,两位皆为相同的病症所苦:严重的气喘。多年来,布雷尔一直治疗着他们的慢性肺气肿。这种病在寒冷、潮湿的天气下,会成为益发严重的支气管炎,如果继续发展下去,会导致剧烈的肺部并发症。布雷尔为这两位病人的咳嗽,开了以下处方:吗啡(复方吐根散,一天三次,每次五粒),还有低剂量的祛痰药品(吐根)、汽态吸入剂与芥子膏。虽然有些医生嘲笑芥子膏,但布雷尔相信它的药效,并常将它纳入药方,尤其是今年,大约有半数维也纳人被呼吸疾病击倒的时候。这座城市已有三个星期得不到阳光的造访,有的只是无情刺骨的绵绵细雨。
第三个病人,皇太子鲁道夫家中的仆人,是个精神不安定的麻脸年轻人,喉咙不舒服,害羞到布雷尔必须专横地命令他宽衣,以便做进一步的检查。诊断结果是扁桃腺炎。尽管擅长以剪刀及镊子迅速切除扁桃腺,但布雷尔还是判定这些扁桃腺没有成熟到可以摘除的时候。因此,他开了一帖凉贴纱布、一份氯酸钾漱口药水以及蒸馏水喷雾吸入剂。由于这已经是这位病人在这个冬天第三次的喉咙不适,布雷尔还建议他每天洗冷水澡,来强化皮肤的抵抗力。
在等待的时间,他拿起了三天前收到的莎乐美的来信。鲁莽依旧,一如先前的短笺,她声称她会在今天下午4点钟抵达他的办公室。布雷尔的鼻翼扩张着:“她告诉我她要抵达的时间,她已下了诏书。她授予我的荣誉是——”
不过他很快就控制住自己:“别太认真了。见她又怎样呢?莎乐美怎么会知道,星期三碰巧就是见她的最佳时间呢?在忙碌的生活中,见她会带来什么意义呢?”
“她对我来说……”布雷尔思考着这样的声调:正是相同的志得意满与狂妄自大,让他厌恶他的医学同僚,像是比尔儒斯以及较年长的施尼茨勒,还有他许多声名显赫的病人,像是勃拉姆斯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在他所亲近的熟人当中,其中大部分同时是他的病人,他最喜欢的特质是像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的朴实内敛。也许安东永远无法成为勃拉姆斯那样的作曲家,但是他至少不会自吹自擂。
至于熟人们的下一代,那群桀骜不驯的年轻人,布雷尔乐于有他们的陪伴——年轻的雨果·沃尔夫(Hugo Wolf)、古斯塔夫·马勒(Gustav Mahler)、泰迪·赫泽尔(Teddie Herzl)以及最少见的医学院学生亚瑟·施尼茨勒(Arthur Schnitzler)。他认同他们,当其他长辈不在场时,他会在热门课堂上说些辛辣的话语来取悦他们。譬如,上周在贝尔综合医院,他发表声明说:“是的是的,维也纳人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的上帝名为‘礼仪’。”这话逗乐了那群簇拥在他身边的年轻人。
布雷尔以科学家的精神,在仅仅几分钟之内,轻易地切换到另一种精神状态——从傲慢到谦逊。多么有趣的现象!布雷尔心想,有可能复制这个现象吗?
当下,布雷尔在想象中进行了一项实验。首先,他试着将自己沉浸到一切他所痛恨的、维也纳人那种浮夸的人格面貌。借由自我膨胀并无声地咕哝着“她好大的胆子!”斜眯着眼并蹙紧前额,反击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借此,他重新体验到自己的生气与愤怒。然后,呼气、放松,他放弃所有这些想法,再重新进入自己之中,进入一种可以自我解嘲的心理状态,可以嘲笑自己的荒唐与局促不安。
他注意到这些心理状态,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情绪色彩:志得意满的那种有着鲜明的棱角——那种恶意暴躁,跟傲慢孤独比起来,其实是不相上下。相反,另一种心理状态却让人感觉到融洽、柔和以及受到肯定。
布雷尔想到,这些是明确的、可被区别的情绪,它们同时也是有所节制的情绪。然而,那些更为强烈的情绪又如何呢?酝酿它们的心理状态又如何呢?是否有控制这些强烈情绪的方法?难道这不会导引出一种有效的心理学疗法吗?
他搜索着自己的经验,他最不稳定的心理状态,都与女人有关。有的时候,他感觉到坚强又安心——像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候,自己正安坐在诊疗室的堡垒中。这种时候,他会看到女人的真实面貌:她们面对着日常生活中无尽的急迫问题,她们是奋斗着的、有野心的生物。他还会看到她们胸部的真实面貌:成串的乳房细胞,漂浮在脂肪的池塘内。他知道她们月经的渗出量与痛经的问题,他还知道她们的坐骨神经痛以及各式各样不正常的突起——膀胱与子宫脱垂、隆起的蓝色痔疮与静脉曲张。
当然,布雷尔还有其他时候——销魂的时候。当他被女人给掳获时,当她们变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时。当她们的胸部鼓胀成强有力的奇妙球体时,他被巨大的渴望所征服,他只想要跟她们亲热,这种心理状态非但势不可挡,还负载有颠覆人生的可能。在他对贝莎的诊疗中,这种心理状态差点让他赔尽了一切。
攸关一切的只是观点而已——转换心理结构的观点。如果他可以教导病人在意志上做到这点,他可能真的会成为莎乐美小姐所寻找的对象,即医治绝望的医生。
他的沉思被外面办公室大门的开关声打断。布雷尔稍微等了一下,以免显得过分急切,之后,他步入候诊室来问候路·莎乐美。她全身湿漉漉的,维也纳的纷飞细雨变成倾盆滂沱。在他帮她脱下湿答答的大衣之前,她自己已把它褪下,并递给他的护士兼前台人员贝克太太。
布雷尔招呼莎乐美小姐进入他的办公室,看着她迈向一个厚重的黑皮弹簧座椅之后,他在她隔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他忍不住评论道:“依我看,你比较喜欢自己料理事情。难道这样不会剥夺了男人为你服务的乐趣吗?”
“你我都知道,某些男人所提供的服务,对女性的健康不见得有好处!”
“你未来的先生会需要再教育。早年养成的习惯,可不是如此容易就被去除的。”
“结婚?不了,我可不要!我告诉过你。噢,或许一种兼职的婚姻可以,那或许适合我,但是不能有太多的束缚。”
看着这位大胆又美丽的访客,布雷尔看得出兼职婚姻这个想法的吸引力。布雷尔很难提醒自己说,她只有自己一半的年纪。她穿了一件简单的黑色长洋装,纽扣一直高高扣到脖子,围在肩膀上的,是一个有着狐狸般小巧的脸与脚的软皮毛。奇怪,布雷尔想着,在冷冽的威尼斯,她把皮毛大衣抛在一边,但是在这暖气过强的办公室里,她却紧抓着它不放。不追究这些了,现在是谈正事的时候。
“嗯,小姐,”他说,“让我们开始处理你朋友的疾病这件事。”
“是绝望,而不是疾病。我有几个建议,可以与你分享吗?”
她的傲慢无礼难道没有止境吗?他气愤地怀疑着。她说话的口气,仿佛她是我的同事。她把自己当成一个医疗中心的负责人,我是一个有着30年经验的医生,而她不过是一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学生。
冷静下来,约瑟夫!他告诫着自己。她还很年轻,她并不崇拜维也纳的上帝——礼仪。除此之外,她比我更清楚这位尼采教授。她极有智慧,而且可能有某些重要的事情要说。天知道我对治疗绝望一点概念也没有,我连我自己的绝望都治不好。
他镇定地回答说:“好的,小姐,请说。”
“我今天早上见过舍弟耶拿,我向他提到你利用催眠术来帮助安娜·欧,借以唤起她每一个症状的原始心理。我记得你在威尼斯告诉我说,这种对症状起源的发现,能够因为某种原因,让症状消失不见。让我感到好奇的是这个‘某种原因’是如何做到的。找一个我们都比较空闲的时候,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它明确的机制以及这种去除症状的机制在知识上的源起。”
布雷尔摇了摇头。“那并不是一种经验上的观察。就算我们花上所有时间来谈论,只怕我也没有办法提供你所想要的那种精确性。不过你的建议是——”
“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不要在尼采身上尝试这种催眠方法。这在他身上是不会成功的!他的心志、他的智慧是一种奇迹——这个世界的奇观之一,你会自己亲眼看到。但他实在是,让我借用他最喜欢的句子,人性的,太人性的,他也有自己人性的盲点。”
路·莎乐美现在脱下了她的毛皮大衣,缓慢地起身,走过办公室把它放在布雷尔的沙发上。她浏览了一下挂在墙上镶框的证书,调整其中稍微有点倾斜的一个,然后再次坐下,双腿交叠。
“尼采对权力的话题极其敏感。任何让他感到可能把他的权力拱手让人的程序,他都拒绝参与。他醉心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希腊哲学,尤其是阿哥尼斯观念——关于一个人只能透过竞争来启发天赋的信念。对于任何放弃竞争并声称自己是个利他主义者的人,他会彻底地怀疑他们的动机。他的观念启蒙于叔本华(Schopenhauer)。他相信没有人会有帮助他人的欲望,帮助他人仅仅是为了支配他人,并借此来增加他们自身的权力。有少数几次,当他感到把他的权力让渡给他人时,他感到不知所措,并且以震怒收场。这事在理查德·瓦格纳的身上发生过。我相信同样的事,现在发生在我身上了。”
“发生在你身上?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真的在某种程度上,对尼采教授深沉的绝望负有责任吗?”
“他认为我有。这就是为何我的第二个建议是不要让你跟我产生关联。你看起来不明所以,为了让你了解,我必须告诉你,我跟尼采关系上的一切事情。我会巨细靡遗并一五一十地回答你所有的问题,这并不容易。我把自己置于你的掌握之中,但是,我说的话必须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当然,这点你大可放心,小姐。”他回答说,既因她的坦率而惊讶,亦因与如此开放的人交谈而感到气象一新。
“呃,那么……我第一次碰到尼采大约是在八个月以前,在4月。”
贝克太太敲敲门并端了咖啡进来。布雷尔坐在路·莎乐美的旁边,而不是他惯常在书桌后面的位置。如果贝克太太曾对此感到任何诧异的话,在神情上她并没有透露出半点异样。她一言不发地放下一个托盘,上面摆有瓷器、汤匙与装满咖啡的闪亮银壶,然后迅速离去。布雷尔在路·莎乐美继续说明的时候倒了咖啡。
“我在去年因为健康状况而离开俄罗斯,呼吸方面的疾病,现在已经大为改善了。我先是住在苏黎世,跟随比德曼(Biederman)研习神学,同时与诗人戈特弗里德·金克尔(Gottfried Kinkel)一同工作——我想我不曾向你提过,我是一个胸怀大志的诗人。当我与我的母亲在今年上半年搬到罗马的时候,金克尔为我提供了一封给玛威达·迈森堡(Malwidavon Meysenburg)的推荐信。你知道她吧?她撰写了一个唯心论者的回忆录。”
布雷尔点点头。他很熟悉玛威达·迈森堡的作品,她对女性权利、激进的政治改革以及因材施教的主张。他对其近期反唯物论的论述不太敢苟同,他认为那套理论是伪科学主张。
路·莎乐美继续着:“所以我去了玛威达的文艺沙龙,并且在那里遇见了一位迷人又才华横溢的哲学家保罗·雷(Paul Ree),我跟他变得相当熟稔。雷多年前听过尼采在巴塞尔的课,两人从此开始了亲近的友谊。我可以看出雷对尼采的景仰超过对所有其他人的景仰。雷很快就有了这样一种念头,如果他跟我是朋友,那么尼采跟我一定也可以成为朋友。保罗·雷,但是,医生,”她脸上的红潮仅仅一闪而过,不过已足以让布雷尔注意到,而他反映在脸上的神色,已足够让她察觉到他的关注,“让我称他为保罗吧,因为那是我称呼他的方式,今天我们没有注重社交细节的时间。我与保罗非常亲近,不过我永远不会把自己作为他或任何人在婚姻上的祭品!”
“不过,”她无奈地继续说下去,“我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去解释我脸上不由自主的短暂脸红吧。我们是不是唯一会感到困窘的动物呢?”
词穷之余,布雷尔只能设法点了点头。有片刻,在医疗设备的环绕之下,他感到自己比他们上一次谈话时更有力量。但现在暴露在她的魅力之下,他感到自己的力量正悄悄消失。她对她自己面红耳赤的解说很了不起:在他一生中,他从未听过任何人,更别说是这样一个女子,能如此坦率地谈到男女交往之事,而她只有21岁而已!
“保罗深信尼采跟我会发展出持久的友谊,”路·莎乐美说下去,“他认为尼采与我完美得适合彼此。他要我成为尼采的学生、门徒以及生存的依据。他想要尼采作我的老师、我天长地久的宗师。”
他们的谈话被轻微的叩门声打断。布雷尔起身开门,贝克太太大声地耳语说,有一位新的病人刚刚进门。布雷尔再度坐下并向路·莎乐美保证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因为,未曾预约的病人总会有久等的心理准备,同时催促她继续说下去。
“嗯,”她继续说着,“保罗安排了在圣彼得大教堂会面,对我们这不敬的三位一体来说——这是我们稍后替我们自己所取的名字,不过尼采常常把它称为‘毕达哥拉斯式的关系’——圣彼得大教堂是最难以想象的会面地点。”
布雷尔发现自己盯着的是他访客的胸部,而不是她的脸。他怀疑着,我这样做有多久了?她注意到了吗?有其他女人注意到我这样做吗?他想象自己抓起扫帚,把所有跟性有关的念头一扫而空。他将注意力更为集中在她的双眼与她的话语上。
“我立刻就被尼采所吸引。他在外表上不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男人——中等高度,拥有温和的声音与不露情感的双眼,与其说他的眼睛是看着外界,不如说是往内看,仿佛他在保护着什么内在的宝藏一般。我当时并不知道他已经失明到3/4的程度。然而,他有某种格外引人注目的东西。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各是从怎样的星辰朝彼此坠落而到达此处来的?’”
“然后我们三个开始谈天说地。那是多让人惊讶的谈话啊!有一刻,保罗对尼采与我之间的友谊或师生之谊的愿望,似乎获得了充分的实现。在知性上,我们是完美的契合。我们融入彼此的心智当中——他说我们有孪生兄妹的大脑。哦,他大声朗读他最新著作中的珠玑之言,他为我的诗定律,他告诉我,他准备在接下来的10年当中为这个世界提供些什么——他坚信,他的健康所容许的时间,绝不超过10年。”
“很快地,保罗、尼采与我决定,我们应该住在一起,三人行。我们着手计划在维也纳或巴黎,一起度过冬天。”
三人行!布雷尔清清喉咙,在他的椅子上不安地挪动着。他看到她朝着他的狼狈浅笑。难道她是如此明察秋毫吗?这个女人会成为怎样的一位诊断专家啊!她曾经考虑过以医学为业吗?她可能成为我的学生吗?我的门徒?我的同事?在诊疗室里、在实验室里、在我身旁工作?这个幻想非常有力量,有真正的力量。但是,她的言语马上让布雷尔摆脱了这个幻想。
“是的,我知道这个世界不会赞同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住在一起,纯洁地。”她在“纯洁”上优美地加重了语调——强到足以让事情为之矫正,然而又柔和到足以规避了非难。“不过,我们是自由思想的观念论者,不认同社会所强加的限制。我们相信,我们有创造出我们本身道德系统的能力。”
由于布雷尔没有做出反应,他的访客第一次流露出不确定要如何进行下去的神色。
“我应该继续吗?我们有时间吗?我冒犯到你了吗?”
“请继续,亲爱的小姐。首先,就时间而言,我已经把这段时间留给你。”他伸手从书桌拿起他的行事历,指着1882年11月22日星期三这一天,潦草写就的大大L.S.。“你可以看出我在这个下午没有安排其他事情。其次,你并没有冒犯我。相反,我钦佩你的直爽、你的直截了当。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如此真诚地谈话!生活将会更丰富与更真实!”
不多做任何解释就接受了他的恭维,路·莎乐美为自己倒了更多咖啡,并继续讲她的故事。“首先,我应该表明我与尼采的关系虽然亲密,但是很短暂。我们只碰了四次面,而且几乎总是在我的母亲、保罗的母亲或者是尼采妹妹的监督之下。事实上,尼采跟我极少独自散步或交谈。”
“我们这不敬的三位一体,在知性上的蜜月期同样很短暂。裂痕出现了,然后是浪漫与色欲的感觉。或许它们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或许我应该为疏于辨认出它们而负责。”她边说边颤抖着,仿佛想要摆脱这个责任一般。
“接近我们第一次会面的终了时,尼采逐渐对我的纯洁三人行的计划感到不安,认为这个世界还不能接受它,并且要求我把我们的计划保密。他尤其在意他的家庭: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的母亲或妹妹都绝对不能知道我们的事。如此保守!我既惊讶又失望,并且怀疑我是否被他果敢的言辞、自由思想的宣言所误导。”
“之后不久,尼采达到一个甚至更强硬的立场——他那种在居住上的安排,将对我会有社交上的危险,或许甚至是毁灭性的影响。他说,为了保护我起见,他已经决定要提议结婚,并且要求保罗传达他求婚的意图。你可以想象这把保罗逼到了什么位置吗?但是出自对朋友的忠诚,或者说忠实,但有点冷漠的忠诚,保罗转告了我尼采的求婚。”
“这让你大感惊讶吗?”布雷尔问道。
“非常惊讶!特别是在我们只碰过一次面时!它同时搅乱了我的思绪。尼采是一个很好的人,并且有种高贵、强大、非凡的风采。我不否认,布雷尔医生,我被他强烈地吸引着,但不是那种罗曼蒂克的吸引。或许他感受到我对他的着迷,因此不相信我对婚姻与浪漫恋情的声明是真的。”
一阵突兀的狂风在窗子上弄出来的吱嘎声,把布雷尔的注意力分散了一会儿。他突然感到脖子与肩膀的僵硬,他已经如此专注地倾听了好几分钟而没有移动过。病人偶尔会跟他谈到私人的问题,但是从未像今天这样。以往的病人从来不是面对面的,从来不是如此勇于面对现实。贝莎曾经揭露了许多,不过总是在一种“恍惚”的心理状态下。路·莎乐美“清醒”得很,并且即使是在描述久远的事件,仍会创造出相当亲密的刹那,那会让布雷尔感觉他们就像是恋人般地交谈着。不难理解,尼采何以仅在一次会面后,就向她求婚。
“然后呢,小姐?”
“然后我决定在我们下一次碰面时要坦白以告。但事实证明,这是没有必要的。尼采迅速理解到,他对婚姻的看法就如我一般排斥。两星期后在奥尔塔,当我再次见到他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我千万别把他的求婚放在心上。然后,他恳求我加入他对完美关系的追求——那种热情的、纯洁的、知性的与精神上的完美关系的追求。”
“我们三个重修旧好。尼采对我们的三人行是如此兴致勃勃,有一天下午在卢塞恩,他坚持我们要为此合影——我们不敬的三位一体唯一的一张相片。”
在她递给布雷尔的照片当中,两个男人在一辆两轮马车前并列;她则屈膝坐在里面,挥舞着一支小皮鞭。“在前面那个有着短髭的男人,凝视着上方的那个——那是尼采,”她有点兴奋地说,“另一个是保罗。”
布雷尔仔细端详着这张相片。这两个男人让他感到不安,这两位可怜又受到束缚的杰出人物啊,被这位美丽的年轻女子与她小巧的皮鞭所主宰。
“你觉得我的马匹怎么样,布雷尔医生?”
目前为止,这是她第一次偏离正题,而此时,布雷尔突然想起她才不过是一个21岁的女孩。他感到不舒服,他不喜欢在这个美丽的生物上看到一点瑕疵。他的内心深处同情着那两个受到奴役的男人——他的兄弟们,他肯定自己会是他们其中之一。
他的访客一定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布雷尔察觉到她急忙地继续她的叙述。
“我们又见了两次面,在妥腾堡,大概三个月以前,先是和尼采的妹妹,然后是保罗的母亲。但是尼采持续写信给我。这儿是封回信,对我先前告诉他我是如何被他的书《曙光》所打动,这是他的回应。”
布雷尔飞快读了她递交的这封短信。
我亲爱的路:
我也是,我也有我的黎明时刻,这些时刻不是虚构的图画!以前我认为不可能的事,现在对我来说有了可能,为我终极的快乐与苦痛找到一个朋友,如今是可能的了,就像是灿烂金黄色的可能性,在我未来生命的地平线上升起。每当想到我亲爱的路,她无惧、丰富的灵魂时,我就为之悸动。
F.N.
布雷尔保持缄默。他现在对尼采的神往,感到愈发的强烈。曙光!去发现金黄色的可能性,去爱一个丰富、无惧的灵魂!布雷尔觉得,每个人都需要一生至少一次的追求。
“在同一段期间内,”莎乐美继续着,“保罗开始写来情感同样炽烈的信件。除了尽我所能的努力斡旋之外,我们三位一体之间的紧张,开始上升到令人惊慌的地步。保罗与尼采之间的情谊迅速崩解。在给我的信件中,他俩开始诋毁对方。”
“这是当然的啊,”布雷尔插嘴说,“难道这在你的意料之外吗?两位热情的男子与同一位女子有着亲密的关系?”
“或许我太过天真了。我以为我们三个可以共享一种心灵生活,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严肃的哲学工作。”
显然为布雷尔的问题所困扰,她站起来,略为伸展一下四肢,漫步走向窗边,在途中停下来端详着他桌子上的某些物品——一套文艺复兴时期的青铜研钵与捣锤、一幅迷你埃及丧葬图、一个内耳半规管的精巧木制模型。
“或许我太顽固,”她说,看着窗外,“不过我依然很难相信我们的三人行是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成功,只要尼采可憎的妹妹没在一边作梗。尼采邀请我与他和伊丽莎白在妥腾堡共度夏日,那是图林根的一个小村庄。她先跟我在拜罗伊特会合,我们在那里碰到了瓦格纳,并且出席了一场《帕西法尔》的演出。然后我们一起旅行去妥腾堡。”
“你为何说她可憎呢,小姐?”
“伊丽莎白是一个爱挑拨离间、心胸狭窄、不诚实又反犹太人的傻瓜。当我失言告诉她保罗是犹太人的时候,她费尽心机让瓦格纳的整个圈子得知这一点,以确定保罗永远不可能在拜罗伊特受到欢迎。”
布雷尔放下他的咖啡杯。虽然路·莎乐美起先哄骗他进入了爱情、艺术与哲学,那些甜蜜又无害的领域,但她现在的字眼惊醒他回到现实当中,回到反犹太主义存在着的丑恶世界。这天早上,他才读到了《新自由报》中的一篇报道,说的是兄弟会的年轻人混进大学、闯入课堂、叫嚣着“犹太人滚蛋!”并且强迫所有犹太人离开讲堂——任何反抗的人,都会被他们拳打脚踢。
“我也是犹太人,我认为我有必要知道,尼采教授是否支持他妹妹的反犹太观点?”
“我知道你是犹太人,耶拿告诉过我。重要的是,你得知道,尼采只关心真理,他痛恨带有偏见的谎言——一切的偏见,他憎恨他妹妹的反犹太主义。伯纳德·福斯特(Bernard Forster),一个激进的反犹太分子,经常拜访他妹妹,尼采对此不仅惊讶,而且厌恶。他的妹妹,伊丽莎白……”
现在她说话的速度加快,音调提高了八度。布雷尔看得出来她知道自己正在岔离正题,但是她无法阻止自己。
“布雷尔医生,伊丽莎白极为讨厌。她叫我娼妇,她对尼采说谎,她跟尼采说我向每个人炫耀那张照片,还说我对旁人说尼采有多喜爱我的皮鞭的滋味。她始终在说谎!她是个危险的女人。记得我说的这句话,终有一天,她会对尼采造成极大的伤害!”
她在说这些话的时候紧紧握住一把椅子的椅背,然后,她坐了下来,较为镇定地继续说下去,“就如你能想象的,在妥腾堡与尼采及他的妹妹共度的那三个星期很复杂,我与他独处的时刻是高尚的。我们有美好的散步时光,深谈一切话题。有时候,他可以一天说上10个小时!我怀疑以往是否曾经有过,两个人之间出现这样一种哲学上的开放。我们谈论善与恶的相对性,谈论为了过道德的生活,而将自己从一般道德规范中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谈论一种自由思想家的宗教。尼采说的没错,我们有孪生子的头脑——我们可以只说半句话、半个句子、仅仅比个手势,就对彼此传达了如此多的信息。然而这种快乐被毁掉了!因为我们一直都在他恶魔般妹妹的监视之下——我可以看出来她一直在注意听着,不停地在误解与图谋着什么。”
“告诉我,伊丽莎白为什么会中伤你?”
“因为她在为她的一生抗争。她是气量狭小、精神贫乏的女人,她无法承受把她的兄弟输给另一个女人,她了解尼采现在是而且永远都是她生命重要性的唯一来源。”
她瞄一下她的表,再瞥一眼紧闭的大门。
“我有点担心时间,所以我会加快速度。上个月,不顾伊丽莎白的反对,保罗、尼采与我在莱比锡跟保罗的母亲待了三个星期,我们再次拥有相当严肃的哲学讨论,特别是关于宗教信仰的发展。我们在两个星期前分手,当时尼采依然相信,整个春天,我们三个会一起住在巴黎。但我知道,那是永远不会实现的了。他妹妹已经成功地毒化了他的心灵,要他与我对立,最近他寄来的信中,充满了绝望、怨恨,对保罗和我的怨恨。”
“而现在,今天,莎乐美小姐,情势的发展如何?”
“所有的事情都恶化了,保罗与尼采已经成为敌人。保罗每次读到尼采写给我的信就越加愤怒,当他听到我对尼采有任何温柔的情感时,也会一样愤怒。”
“保罗看你的信?”
“是的,为何不呢?我们的友谊很深,我想我永远会与他非常亲近。我们彼此之间没有秘密,我们甚至阅读彼此的日记。保罗曾经恳求我与尼采绝交,我最终勉为其难地同意了,并且写信给尼采,表示我将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但是,我们的三人行是永远不可能的。我告诉他,太多的痛苦、太多毁灭性的影响来自他的妹妹、他的母亲以及他跟保罗间的争吵。”
“而他的反应是?”
“疯狂!令人恐惧的疯狂!他尽写些疯狂的信,有时候是侮辱或威胁,有时候是深沉的绝望。噢,看看上个星期我收到的这些段落。”
她拿出两封信来,这些信从外表上就显露出焦躁的气息:不协调的潦草书写,许多句子被删除,或在底下画了好几道线。布雷尔斜瞄着她圈起来的段落,但是无法辨识出几个字来,就把它们递还给她。
“我忘了,”她说,“我忘了他的字迹有多难阅读。让我解读写给保罗跟我两个人的这封:‘不要让我暴怒的自大狂,或受到伤害的虚荣心太过打扰你们——如果那一天,我刚好因为一时的冲动而了结了我自己的生命,在那个了结里,不会有任何值得担忧的事情。我对你们还真的是心存幻想啊……我对现况所做出的这些合理观点,是在绝望中产生的,在我服用了巨大剂量的鸦片之后——’”
她突然停下来,“这应该足以让你对他的绝望有点概念了。目前我在保罗家位于巴伐利亚的房子已经待了好几个星期,我所有的邮件都寄到那儿去。为了避免我痛苦,保罗毁掉了尼采大部分的来信,但这封单单寄给我的,逃过了一劫,‘如果我现在把你从我心中驱逐,这对你的整个存在来说,是种极为严苛的否定……你造成了损耗,你带来了伤害——不只是对我,还伤害到所有爱我的人,这把剑就悬在你的头上。’”
她抬头看着布雷尔:“医生,现在,你可以了解我为何如此强烈地建议,不要让你自己跟我扯上任何关系了吗?”
布雷尔深吸了一口雪茄。虽然他被路·莎乐美引起了好奇心,并且对她所摊开的戏剧性事件感到着迷,但他却深感为难。同意涉入是明智之举吗?真是一团糟啊!何等原始有力的关系:那不敬的三位一体、尼采与保罗破裂的友谊、尼采与妹妹之间的强力联结,还有尼采妹妹与路·莎乐美之间的互相憎恨。我得当心,布雷尔对自己说,要把这些交加的雷电置之度外。此中最具爆炸性的,当然是尼采对路·莎乐美不顾一切的爱,那爱现在已变成了恨。然而,回头已经太迟了。布雷尔曾经对自己承诺过,这承诺也在威尼斯爽快地告诉过她,“我从未拒绝治疗病人”。
他转回到路·莎乐美这边,“莎乐美小姐,这些信帮助我了解了你的警告。我想,你对你朋友的担心是正确的,他的稳定似乎只是反复,而自杀的确有可能。不过,既然现在你对尼采教授只有些微的影响力,你又如何说服他来见我呢?”
“没错,这是个问题,我对此考虑了很久。我的名字现在对他来说就是毒药,我一定得间接施力。这意味着,他必须永远、永远不知道我安排了一场与你的会面。你一定不能让他知道!不过你现在愿意见他了吗?”
她放下杯子,极为专注地看着布雷尔,使得他必须迅速地回答说:“当然,小姐。就如同我在威尼斯跟你说过的,‘我从未拒绝治疗病人’。”
听了这些话,路·莎乐美脸上绽开了微笑。哎,她的压力比他所以为的要大得多。
“有了这样的保证,布雷尔医生,在尼采不知道我介入的情况下,我将开始着手把尼采带到你办公室来的计划。他的行为现在是如此混乱,我确信他所有的朋友都警觉到了,并且乐意见到任何合理计划的出现。在我明天回柏林的路上,我会在巴塞尔停留,向弗朗茨·奥弗贝克(Franz Overbeck)提出我们的计划,他是尼采终生的朋友。你作为一位主治医师的声誉会对我们有所帮助。我相信奥弗贝克教授可以说服尼采,就他的健康状况来找你求诊。如果我成功了,你将会收到我的信。”
她以飞快的速度,把尼采的信放回皮包里,站起来,整整长裙,从长沙发上拿起狐狸皮毛大衣,伸手紧紧握住布雷尔的手。“而现在,我亲爱的布雷尔医生——”
在她把另一只手放在他手上时,布雷尔的脉搏加速。他想着,别像个呆子一样,但这个指望,在她双手热情地环绕之下放弃了。他真想告诉她,他是如何喜爱她对他的触碰。或许她知道吧,因为她在说话时,还把他的手保留在她的双手内。
“希望就这件事,我们能保持频繁的联系。不只是因为我对尼采有着深沉的情感,还因为我得为他的某些痛苦负责,即使是无心之过。还有其他事情,我也期望你我能成为朋友。我有许多缺点,如你亲眼所见,我很冲动,我会吓到你,我是个不受传统规范的人。但是我也有长处,对于判断一个人是否有高贵的灵魂,我有绝佳的眼光。而当我发现了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我很不情愿失去他。所以我们会通信?”
她松开了他的手,大步走向门口,然后突如其来停住。她伸手从她的皮包里抽出两本小书。
“噢,布雷尔医生,我差点忘了。我想你应该要有尼采最新出版的两本书,它们会领着你洞察他的心灵。但是他绝对不能知道你见过这两本书,他会起疑,因为他的书太少有人买了。”
再一次,她碰触了布雷尔的手臂。“还有一点,虽说现在的读者如此之少,尼采深信他的声誉终究会到来。他有一次告诉我,不久的未来是属于他的。因此,别让任何人知道你在帮助他,别对任何人透露他的姓名。如果你这样做,并且被他发现了,他会认为那是一种严重的背叛。你的病人(安娜·欧)那不是她的真名,对吧?你用了一个假名?”
布雷尔点头。
“那么,我建议你对尼采做同样的事情。再会了,布雷尔医生。”她伸出了她的手。
“再会,小姐。”布雷尔说,他弯下腰来并把他的双唇印在上面。
她离开后,他关上门,在把书放到书桌上之前,他浏览了平装的薄薄两册小书,并且注意到它们奇特的标题——《快乐的科学》以及《人性的,太人性的》。他走到窗边以捕捉对路·莎乐美的最后一瞥。她撑着雨伞,迅速步下台阶,头也不回地进入一辆等候的小型出租马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