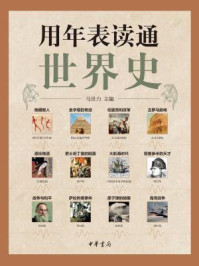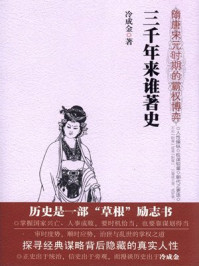在我看来,百年言论史是从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开始的。王韬卒于1897年,在王韬去世的那一年,梁启超主笔的上海《时务报》已经风行一时。但是王韬本身,还没有构成一个时代。那是中国百年言论史的萌芽时期,在这个萌芽时期,王韬在香港执笔论政,呼唤改良,呼唤变法,直接启蒙和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这些后来变法维新的主角,但是由于他的报纸远在香港,虽然经常被上海的一些报纸转载,如外国人办的《申报》,但他的影响还不足以构成一个时代,真正在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可以构成一个时代的在我看来是“梁启超时代”,甚至可以把梁启超的名字作为时代来命名。
梁启超,严格地说,他办的第一本杂志是1895年在北京创办的《万国公报》,但是这个杂志的名字和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一本很有名的杂志重名。后来,因为版权问题,美国人提出重名问题,就像原来的《读者文摘》和美国的《读者文摘》重名,官司打输了,改成《读者》一样,当年梁启超他们也是主动改成了《中外纪闻》。这个杂志为期很短,办了不到1年,而且销量有限,每期印3000份,免费赠阅,对象是达官贵人,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沿门丐阅”之时——那是要和邸报一起免费赠阅的。
到了1896年,“梁启超时代”正式拉开序幕,梁启超、汪康年这些中国转型时期第一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其实这是一本杂志,一本旬刊,10天一期,正是通过这本杂志,变法维新的声音成了时代的最强音。24岁的梁启超以他的言论登上了历史大舞台,影响之大,一时甚至盖过了他的老师康有为。但是由于汪康年与康梁之间的矛盾,1897年梁启超离开上海《时务报》,到了湖南时务学堂当教师去了。当然,做教师他也有成绩,教出了像蔡锷、范源濂这样第一流的知识分子。蔡锷这个人,虽然是个军人,但却是个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只有他拿着枪说出了“为国民争人格”这样的话。
梁启超在《时务报》到《新民丛报》之间还办过《清议报》,后面还办了《国风报》《政论》杂志,还有辛亥革命后办《庸言》杂志。在他一生中,至少与22家报刊有密切的联系,其中,10种以上的报刊是他亲自参与的,7种是他亲自主编的。影响最广、最深的是他在日本创办的《新民丛报》《新民丛报》与《时务报》一样,也是一本杂志,而非报纸,是一本月刊,《新民丛报》从1902年到1907年,只生存了5年,但是它的影响之大,远不是时间所能涵盖的。在《新民丛报》停刊之后,人们还把《新民丛报》的旧杂志拿来,当作自己启蒙的材料。包括很多与梁启超在政治立场上并不一致的人,很多倾向革命而非改良的人,比如辛亥革命时期非常活跃的湖南人,同盟会的元老,谭人凤先生。据他回忆,当年之所以要走上反对满清政府的道路,要走上革命的道路,并不是因为受了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影响,而是读了梁启超编的那些杂志,看了《新民丛报》《时务报》,心中觉得有一股不平之气,有一种对文明世界的向往,所以他要走出来,就这样走到了革命之路。
梁启超的影响不只是对一代人,包括毛泽东、邹韬奋、王芸生在内,中国几代的历史人物都曾经受到过梁启超的影响。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那些文字,被人们称为“新民体”。那么,他到底有什么魅力打动了千千万万的中国读书人?用梁启超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他的文章笔锋常带感情,别有一种魔力。但是,我觉得,仅仅用文字上的感染力来谈论梁启超对一个时代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梁启超对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最大的影响还是那三个字:开风气。梁启超在一首诗中说过“但开风气不为师,十年之后当知我”,他觉得自己走在时代的前面,他所提出的东西人家往往要10年以后才能理解。
我把“梁启超时代”大致界定为从他创办《时务报》到《新民丛报》停刊这10年间。这10年是“梁启超时代”的黄金时代,是它的最高潮,从1907年《新民丛报》停刊以后,梁启超的时代就在走下坡,新的人物、新的报刊在崛起。包括上海租界里出现了于右任先生创办的三个“民”报,三张报纸,前后延续——《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后来那张直接呼唤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的著名报纸——《民立报》。
但是梁启超的影响始终存在,1912年12月梁启超回到中国,马上创办了《庸言》杂志,发行量很快超过1万份,在当时的中国,民智未开,受教育的人口相当少,一份新办的杂志,销量可以超过1万份,这不是我们今天一般的杂志所能想象的。现在国内读书界比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像《书屋》杂志,发行量也不过2万5千份。那么在90多年前,民国初年,梁启超在国外流亡了16年之后回国,一创办杂志,发行量就能突破1万份,这在当时无疑是个很大的发行量。
到了1915年,当袁世凯黄袍加身要称帝的时候,正是这位在言论史上已经逐渐落幕的梁启超先生,写下了雄篇巨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这篇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大,震撼之巨,我们今天的人已经无法想象了,当袁世凯得知梁启超写了一篇文章反对他,他马上派人给梁启超送去20万元大洋,就是跟梁启超谈判,能不能不发这篇文章,不发,就20万,以后还可以再加,钱没有问题,只要不发文章就行。当然,梁启超断然拒绝了。这件事,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在天津的租界里商量的时候说,蔡锷,你是军界大有力量的人,你跟我不一样,梁启超只是一介书生,对我来说,袁世凯要做皇帝,我就要堂堂正正地反对他,否则的话,中国的读书人最后一点气骨都没有了,你不一样,你有力量,你要韬光养晦,不要让袁世凯看出你有异心,以风花雪月来掩饰自己,寻找机会,回到云南去,用武力反对袁世凯。梁启超的这篇文章很快就在报纸杂志上发表,上海的老牌报纸,外国人办的《申报》——这时候已归入史量才名下,就分两次转载了这篇长达一两万字的文章,一时举国上下争相传阅。这是梁启超在言论史上最后的辉煌之一。
在袁世凯皇帝梦破灭,一命呜呼之后,梁启超本来打算退出言论界,退出政界,一门心思地去从事他的教育事业,他和很多记者,包括给他女儿的信中都一再表示他要从此退出政界,退出报界,他要一门心思地去做老师,去办教育,他认为教育是根本的救国之计。但是时代的问题由不得一个读书人自己去想象,就在他想要去做教师的时候,中国又发生了变局,张勋拥废帝溥仪复辟了,当时整个中国知识分子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复辟的——仍然还是梁启超,他写下了反对复辟的通电,他说,我,一介书生,手无寸铁,我今天所能做的,就是把我的观点堂堂地亮出来,我相信,凡是有一点人气的人,都会像我一样做。事实证明,张勋复辟只维持了12天,比袁世凯的83天皇帝梦还要短得多,从那之后,在中华大地上,无论你拥有百万雄兵,还是拥有多如牛毛的中统、军统、蓝衣社、白衣社,要想戴上有形的皇冠,称孤道寡,几乎已经没有机会了。
梁启超在把中国从一个专制皇权社会带入一个共和社会的过程中,他的言论所产生的影响,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是无比巨大的。但是梁启超并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
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他曾经几度介入政治,做了官,从了政,当过熊希龄人才内阁的司法总长,当过币制局总裁,后来当过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当然,他当官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年,在他的一生中,2年不过是个零头而已。但是,这2年给他带来的负面伤害远远超过了他10几年的流亡生涯。
一个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到底以什么样的形式推动社会进步,做他更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的例子是很鲜明的。从本质上说,梁启超是一个论政的人,而不是一个从政的人。他自己也对女儿说,在政治舞台上做政客,对自己的心灵伤害得太厉害。官场上的错综复杂,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读书人所能面对的。梁启超在和袁世凯、段祺瑞这些军阀打交道的过程中,深感心力交瘁,无法适应。这两年时间把他变得如同垂暮老人一样,他后来一门心思做他的学术,做他的老师,支持办报,就是对那两年政客生涯带给他伤害的反思。在袁世凯、段祺瑞这些旧官僚旧军阀的身上,充满了几千年专制主义带给他们的权谋之道与纵横捭阖的伎俩。这些东西,恰恰是梁启超作为一个政论家,一个言论史上著名的知识分子,所深恶痛绝的。但是,当他回头反思,想重新去从事言论事业时,已是力不从心了——他的身体状况与精力已经不允许了,梁启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我前面说他的时代从1907年就开始走下坡了,之所以还能延续到1917年,是因为他在前面的影响巨大,余波所及,还有10年。这个时代,我把他看作百年言论史上第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代——“梁启超时代”。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只有10年,从1896年到1907年,余波所及,影响到了1917年,一直到张勋复辟的时候,他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梁启超的一生中,有三次扮演了历史的主角。第一次在百日维新这场和平的政治改革中,他利用《时务报》这个平台,发挥他在思想言论方面的影响。第二次是在反对袁世凯称帝中,他在《大中华》杂志上首先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第三次是在反对张勋复辟中,他第一个站出来发表通电,后来亲自参加了段祺瑞的马厂誓师,打垮了张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当中能三次介入重大历史事件,后两次并且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是十分罕见的。
言论史上“梁启超时代”过去了,接下来的第二个时代我把它称为“《新青年》时代”——用一本杂志来命名。
“《新青年》时代”的到来是意想不到的,1915年,当时袁世凯的马仔们正紧锣密鼓地为袁氏把总统的名字换成皇帝做准备。比如“筹安六君子”“十三太保”这些人,包括严复、刘师培这样的大学问家,胡瑛、李燮和、孙毓筠这些身上都有光环的老革命党人都纷纷落入袁世凯的彀中,为他称帝鸣锣开道。在这样一个恶劣的形势下,在上海,一本毫不起眼的杂志,没有人想到它以后会影响到中国历史进程的《青年》杂志,破土而出了。
办这本杂志的人,我们都知道是陈独秀先生。陈独秀在办这本杂志以前,已经在言论史上留下了一些算不上深的脚印。他曾经介入过“《苏报》案”之后创办的一张报纸——《国民日日报》——在上海与章士钊一起办的;在安徽,他曾经办过《安徽俗话报》,他是有过办报办刊经验的知识分子;也是参加过诸如暗杀团、岳王会这样一些地下革命密谋组织的资深革命党人。辛亥革命之后,他曾经出任过安徽都督柏文蔚的秘书长。既有丰富的革命阅历,又有第一手的办报办刊经验。1915年,陈独秀选择了办杂志这条道路,创办了《青年》杂志,在《青年》杂志的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下了《敬告青年》一文,开宗明义提出科学与人权就好像车船两边的两个轮子,没有它们,社会是不会向前的。
从第二卷开始,他把杂志改名为《新青年》,并且把科学与人权扩大为后来大家所熟知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从此以后,他就打着“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两面大旗,集中当时中国最富有前瞻性、最有活力的一批知识分子,比如易白沙、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鲁迅、周作人兄弟、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这样一大批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在《新青年》上发表他们的言论,有些言论之激进,让我们今天看来都可能会心惊肉跳。比如说,鲁迅讲的“不读中国书”,钱玄同讲的“废除汉字”等,都是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正是以这样一种决绝的、不容讨论的姿态,陈独秀以他强有力的个性,推动了《新青年》杂志,推动了新文化运动。
当然,在这背后,我们不能不提到蔡元培先生,他在1916年接受了北洋政府的任命,成为北大校长,他延请陈独秀担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新青年》的大本营从上海转移到了北京,这些情况改变了新文化运动的格局。在陈和《新青年》影响下,新文化运动风生水起,山鸣谷应,仅1919年全国就出现了几百种新办的杂志,创办这些杂志的都是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人。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机遇,《新青年》杂志在袁世凯还要当皇帝,张勋还要拥溥仪复辟的情况下,居然在思想文化领域打开了一块新天地,重塑了中国近代史。
在《新青年》以前,无论是王韬办报还是整个“梁启超时代”,言论史的重点始终是围绕着政治,除了政治还是政治。梁启超耿耿于怀的是中国的变法,是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的立宪。到了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的时候,就不是以政治为中心了,他的目光看得更远,放得更大。《新青年》有一句话叫“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而是把目光主要锁定在思想文化,伦理道德的变革上,叫作“伦理的觉悟是最后觉悟之觉悟”。他们猛烈地向孔家店开火,向儒家文化,向小脚、贞节牌坊、宗法礼教制度开火。
在《新青年》杂志风行中国的那个年代,儒家文化、读经运动到底应该如何去看待,当时在《新青年》杂志的作者眼里可以说这是一个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胡适、鲁迅、傅斯年他们对读经的态度,当年是很明确的。现在再面对这些问题时,我们反而失去了方向感。当年什么人倡导读经?要么就是拖着辫子的、过时的人物,像康有为、前清的遗老遗少们;要么就是手里拿枪的军人,像湖南军阀何键是赞成读经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也是赞成读经的,可以说,如何面对读经运动,在“五四”时期,《新青年》所朝向努力的方向,就是要推倒几千年来以旧文化、旧道德、旧伦理、文言文为核心的整个价值标准,引入以法兰西文明中自由、平等、博爱为核心的新文化、新价值、新观念。
陈独秀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一本小小的杂志,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风气。影响所及,到了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施复亮当年就在一师读书,还有当时在浙江甲种工业学校读书的夏衍,他们办的那些杂志,像《钱江》《双十》《之江》,都是一些油印的期刊,这些杂志在当时的中国不是孤立的,可以说是遍地开花,整个形成了山鸣谷呼应的局面。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没有遇到太大的阻力,就这样过来了。
在“《新青年》时代”中,影响最大的人物,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三个人——他自己、胡适、蔡元培;当时的鲁迅已经发表了《狂人日记》,已经写下了《热风随感录》,还有许多小杂文。但是就当时的影响而论,“五四”时期鲁迅的影响还是不够。
“《新青年》时代”的黄金时代从1915年到1919年,只有短短的4年,马上就开始走下坡了,但是,《新青年》的流风余韵一直影响到了1924年创办的两本杂志,《语丝》和《现代评论》,这是两本截然相反的杂志。其实这两本杂志所标榜的东西实质上并无太大的差异,但是由于当事人相互之间的纠葛,这两本杂志始终是对立的。《语丝》杂志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林语堂;《现代评论》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王世杰、胡适、陈西滢等,这两本杂志其实代表了《新青年》分裂后两种不同的路径,一路以鲁迅为标志,渐渐往左翼走了;另一路就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保持中性、客观地介入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道路。以后我们还会讲到“《大公报》时代”中胡适派的影响,而鲁迅的影响在《语丝》之后,其实主要是往左翼转了。“《新青年》时代”的主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政治的,它的影响主要是思想的影响,文化的影响,价值观的影响。它对社会的影响是更加深远的。
现在有一些人想抹杀“五四”的功绩,想抹杀《新青年》的价值,重新进行评估,甚至把我们此后的民族灾难都归结为“五四”激烈的反传统。其实,这没有找到病根。尽管“五四”表现出了激烈的反传统姿态,但是“五四”骨子里还是立,而不是破,主要是引进新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破坏旧的价值尺度。要立起一个新的价值尺度,在当时守旧的中国,必须表现出一种决绝的姿态,必须要有像吴虞这样的老英雄,对孔夫子以来的中国传统进行一番比较激进的清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激进的反传统,可是如果我们仔细地推敲一下,“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新青年》杂志的核心人物,哪一个不是贯通中西的人物?胡适一生最重视的东西不就是整理国故吗?直到他的晚年,他所致力的不就是《水经注》的研究吗?他们对典籍的研究是我们难以望其项背的。
当然他们对西方文明也有很深的了解,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留学背景,在学习了西方的文化,吸收了西方的观念之后,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放弃传统,以胡适为例,他终其一生没有娶小老婆,也没有换过妻子,他的妻子就是当年他母亲给他订下的那个,说他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这是蒋介石给他的盖棺论定。鲁迅身上也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并不像他自己所说的打翻了一切“三坟五典”“百宋千元”,从鲁迅的句式、文笔上看,他更多的滋养依然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在魏晋时代可以找到渊源。鲁迅的文风,鲁迅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我们如果去看魏晋时期的作品,比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那种臧否人物的写法,在鲁迅的笔下都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鲁迅最欣赏的人物不就是阮籍、嵇康吗?他表面上说不读中国书,但是他学术上做得最好的几本书,像《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都是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在我看来,“《新青年》时代”的主要知识分子留给后人的影响,主要是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价值尺度,多元的价值尺度,一种不以单一标准衡量世界的价值尺度。假如说,只能用一种既定的价值尺度去衡量一切,答案事先已经设定了,那么就无法探察到世界本身的复杂性、多元性。多元性只有用多元的尺度才能衡量出真相,而不可能用一元的尺度来衡量。
所以《新青年》的主要贡献就在于它提供了全新的价值尺度。说陈独秀是“三千年来第一人”,我认为是客观的,陈独秀之前三千年来的价值尺度,看待世界的标准,都是已经设定好的,都是在中国文明的轴心时代、诸子百家时代设定好的。到了陈独秀时代开始,才撇开了跟权力有关的东西;撇开了政治;撇开了种种表面的东西,抓到了文明的内核,自由的内核。
“五四”的本质就是自由,“五四”是建立在百花齐放的基础上的,《新青年》最大的功绩就是迎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后来的整个新文学,学术、思想界的活跃,包括马克思主义,唯物、唯心,不同的流派,都滋生于“《新青年》时代”之后的分化。在分化之后,不同的流派,不同的思考,引入不同的新观念,来自西方的东西——叔本华的、尼采的、柏格森的、罗素的,都出现了,包括唯物辩证法,包括形形色色的新哲学、新思潮,都是在那个时代引入的。所以我觉得在“梁启超时代”之后,我们言论史上的“《新青年》时代”主要不是政治言论,而是文化言论,文明言论。但是,这个时代很快被陈独秀本人所抛弃了,他要往另一条路走,走到组党实践的路上去了,这与我们谈论的话题就没有关系了。所以我们百年言论史上的第三个时代就不是由陈独秀来扮演主角了。
百年言论史上的第三个时代我想用一家报纸来给它命名,叫作“《大公报》时代”,这是百年言论史上最成熟的一个时代,也是延续时间最长、最具有包容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肇始于1926年9月1日,9月1日这个日子在百年言论史上特别重要。《观察》周刊创刊也是9月1日;我们过去的记者节也是9月1日。新记《大公报》的复刊就是在1926年9月1日,《大公报》是一张1902年创刊的老报纸,到了1925年已经关门大吉了,因为它跟政治上失势的安福系军阀有很深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办不下去了。
1926年,有三个人合作重新开办了这家报纸,他们接办之初就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标准,就是有名的四“不”方针——不党、不卖、不私、不盲。这四个“不”在言论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是第一次这样鲜明地亮出了报纸的方针。这三个人,一个叫吴鼎昌,他后来做了国民党的官以后,主动辞去了《大公报》董事长的职务,离开了《大公报》,他在言论史上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提他,因为是他出了5万元银元,《大公报》才办起来。第二个人是《大公报》长期的总经理胡政之先生,他是一个报业的全才,能书善言,而且善于经营,真正的报业全才,长袖善舞之辈。第三个人是以一支笔名动当世的张季鸾,我曾经提出过一个问题:鲁迅还是张季鸾?就是说在他们生活的那个年代,张季鸾的影响大还是鲁迅的影响大?我的答案是张季鸾的影响要比鲁迅大,我们现在来看肯定是鲁迅大,因为鲁迅的影响在身后,鲁迅的影响是一种文学的影响,是思想史上的影响。而在当时,20年代到30年代的中国,1926到1936的中国,鲁迅在上海的租界写他的《且介亭杂文》,写他的《准风月谈》《伪自由书》。在那个时候,他的影响根本无法与《大公报》社评,与《大公报》动辄发行10万份的影响相比。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像张季鸾这样言论史上的代表人物就逐渐为人们所淡忘了;而鲁迅作为文学家、思想家,他的言论,他的影响,在后面被逐渐放大。这就形成了今昔的一个反差。
我们再说这三个人,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个人联袂唱了一台大戏。1926年他们在天津,用5万块钱,其中1万块把这家已经倒闭的报纸接过来,然后就开张了,他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如果失败也无非是把这4万块钱赔光了关门大吉。结果没有想到的是,一年下来不仅实现了收支平衡,而且声誉鹊起,整个中国言论史的格局也被改变了。
从那以后,我把这个时代叫作“《大公报》时代”。这个时代的核心尺度就是《大公报》的“四不”,就是坚持自己独立的标准来评判世间事务,到1931年,《大公报》已经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民间的一些政治力量,他们在判断时局的时候都得看《大公报》是怎么说的,《大公报》的新闻是怎么报道的,《大公报》的评论是怎么写的。
胡适说了一番话,《大公报》为什么成功,成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他认为中国的言论界还是在一个成长时期,还是一个矮人,矮人国里的巨无霸为什么成功?胡适有两句话:一是登载了确实的消息,二是发表了负责任的评论。这两句话抓住了《大公报》之所以成功的关键的两个奥秘。前一句登载确实的消息,很明白,报纸当然要报道确实的消息,第二句话,“发表了负责任的评论”就大有文章,什么是“负责任的评论”?“负责任的评论”就是不仅要对自己负责,对报馆负责,还要对社会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大众负责,对国家和民族负责,这就是负责任的评论。
在负责任的背后,是《大公报》自己独立的评判。它不是依附于蒋介石政权的。不是蒋介石说一,马上跟着说二,顺着杆子往上爬的。尽管后来蒋介石与张季鸾有很好的私交,蒋介石把张季鸾看成是国士,张季鸾也有报恩的思想,但是一直到1941年张季鸾去世的那一年,张季鸾和《大公报》始终没有和国民党政府发生过一分钱的关系。就是说没有拿过蒋介石一分钱,至多只是吃过几顿饭(请客往往也不是单独请张季鸾,而是请了很多人)。据说有一次蒋介石请客,文臣武将济济一堂,结果人们发现,最主要的客人,竟然是一个穿着布衫,患着肺结核的老头,就是张季鸾,所以举国都对他刮目相看。他是少数几个可以不经通报直接进入蒋介石办公室的人。
但是并不会因此《大公报》就完全听命于蒋介石,私交是私交,公私分得很清楚。
在重大的问题上,比如“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公报》的社评马上指着国民党政府骂得狗血喷头,认为国家民族到了这一步,国民政府的达官贵人们无论如何自责也无以谢天下,文字非常的严厉,不断地向国民政府呼吁,要开放舆论,要倾听民众的声音。甚至还发表了范长江非常同情红军的文章——《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上午蒋介石在中央全会上侃侃而谈,到了下午,《大公报》从上海运到南京,那些参加会议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一看,跟蒋介石上午讲的完全不一样。国民党并不是没有新闻检查,稿子是要事先看过的,但是胡政之说我们不送检查,宁可冒着风险先登出来。为了这件事,蒋介石与张季鸾几乎红了脸,但是事后张季鸾和胡政之并没有找范长江谈话,也没有认为范长江给他们捅了篓子。
再比如说,萧乾,《大公报》的名记者,当年他进《大公报》时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他进《大公报》是去办副刊的,胡政之说,你来办副刊,我全交给你了,你只要办得喜闻乐见、有读者就行了,他曾经发表当时的剧作家李健吾的一个独幕剧,剧本里有抗日的内容。报纸登出来之前,萧乾留了个心眼,他把所有的“日”字都改成“×”,当然读者一看就明白,日本人也明白,于是,日本领事馆马上在上海的租界法庭里起诉,最后,张季鸾、胡政之去法庭上应诉(萧乾只是打工的,当然是老板应诉),但是,他们俩从来没有责怪过萧乾,说你给我们惹了麻烦,你让我们当了被告了。结果,官司打赢了,因为剧本里没有出现“日”字,说“×”就是“日”字那是日本人自己的引申。赢了之后,两位老板来夸奖萧乾,说这个“×”打得好,没这个“×”,我们就输了。
我们从另外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大公报》的独立品格。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规定报纸凡是称共产党一定要称“匪”,但是《大公报》从来不买账,他们的版面上称共产党的军队为红军,这在当时是非常犯忌的一件大事,毛泽东对此心存感念。40年代,《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跟其他一些报纸的记者前去延安访问,毛泽东设宴招待他们,唯独把《大公报》的记者当作座上嘉宾,给予了最好的礼遇,他说了一句感人的话:“只有你们《大公报》把我们当人。”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大公报》对于各方面的态度,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对于日本人的态度,都有自己独立的尺度,都坚持了自己的标准。这样的《大公报》,发行量自然是节节攀高,成为举国舆论的重镇。
在言论史上,《大公报》还有一个特点,是民间报纸和学院派知识分子、其他各界人士结合论政的最好类型。它在1934年开设“星期评论”这个栏目,每个周末由报馆之外的知识分子来执笔评论。从胡适开始,有200多位来自各方面的人物,包括像竺可桢这样的自然科学家,包括梁漱溟等,在15年间他们先后写了七八百篇星期评论,这大概是与知识界结合得最好的一家报纸。这个特征标志着一家报纸要评论时事,监督政府,介入社会,仅仅靠报馆本身的力量是不够的,还要借助社会的力量,借助那些本身就有影响的知识精英的力量,把报纸和全国的知识精英结合在一起,共同发出声音,发挥影响力。这里面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办《大公报》的这几个人,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都是留日学生,后来请来参与写“星期评论”的最早的作者,像胡适、傅斯年、翁文灏、丁文江等各个领域的知识精英们大多是留学欧美归来的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结合也是一个最佳的结合,标志着留学日本的知识分子与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在言论上的一种结盟。
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大公报》历经抗战,直到战后,在中国始终保持着最大的影响力。当然,“《大公报》时代”不仅仅只是《大公报》一家报纸,还有其他一些优秀报刊,比如《新民报》,鼎盛时期有五地八版,发行量10几万份,还有成舍我的“世界报系”,徐铸成主笔的《文汇报》等等这些报纸,当然还有胡适他们办的《新月》《独立评论》这些杂志在内,它们共同构成了“《大公报》时代”。
百年言论史的第四个时代严格地讲它还构不成一个时代,但它是百年言论史上的绝响,我称之为“百年绝响”,可以勉强叫它为“《观察》周刊时代”。《观察》周刊是储安平1946年9月1日在上海创办的,是一本完全民间性质的周刊。在那个时代,办周刊是一种时髦,比如说,左翼倾向的有《群众》《文萃》《周论》《民主》,还有民盟办的周刊,昆明,重庆,其他地方也有;第三条道路的有《新路》《世纪评论》《天下一家》《周论》等,一系列的周刊都是在抗战胜利之后出现的。所以,《观察》的诞生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这是当时的一个风潮。在一个急剧变动的大时代里,他们考虑到如果用日报的形式来评论社会深度不够;月刊又太慢,所以就选择了周刊模式,能既深入又比较及时地报道、评论。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时代称为“周刊时代”,或者“《观察》时代”。
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征,左、中、右各种倾向的知识分子纷纷登上论政舞台,包括朱自清先生——我们熟知的朱自清先生,是写《荷塘月色》的,一个温文尔雅的唯美主义散文作家,或是写《经典常谈》的古典文学家。但实际上,朱自清先生早在20年代就十分关心社会,“三·一八”事件他就在现场,后来写下了《三·一八屠杀记》,详细记录了那些青年学生是如何被杀害的;40年代,他在贫病交加中,不断地发表社会评论,参与了许多北京知识分子集体签名,为人权呼号,为反对内战呼号,为国家的政治前途呼号,包括西南联大十教授给蒋介石、毛泽东写公开信,包括晚年因为国民党查封中国民主同盟和48位教授联名发表抗议。他们始终不仅仅局限于学院,他们的目光始终看到了围墙之外的世界,看到了祖国的苦难,体会到了民族的痛苦的脉搏。
一句话,他们的笔是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经典常谈》之外,在那些优美的散文之外,朱自清还有执笔论政的一面。包括像钱钟书、宗白华这些在书斋里面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知识分子也曾经都是《观察》的特约撰稿人,像贺麟这样的哲学家,任鸿隽这样的自然科学家,陈衡哲这样的历史学家,朱光潜这样的美学家,他们在专业之余,关怀的就是国事民生,并经常把自己的这种关心写下来。周刊之所以能风行一时,和他们这些人当时的选择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百年言论史,多少风雨坎坷,几代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挥洒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邵飘萍死了,林白水死了,史量才死了,他们的热血铸就了一部可以歌哭、可以回望、可以缅怀的百年言论史,铸就了永恒的文人论政传统。在朱自清、朱光潜这些几乎不问政治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同样看到了他们关怀社会,与大众共命运、同呼吸的一面。在许多寒冷的长夜里,我常常为中国曾经拥有过这样的知识分子而感到无比温暖,无比骄傲,为我们这个古老民族曾经有过这样的一段历史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