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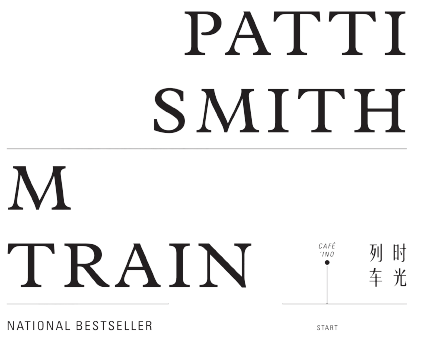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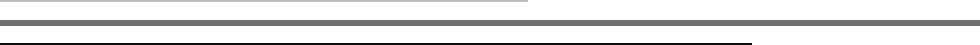
我爬上阶梯,进到我只有一个天窗的房间里,一张工作桌,一张床,我弟弟的海军旗,他亲手捆好的,窗边的角落里搁了一张小扶手椅,上面披盖着旧的亚麻布。我脱下外套,该干活儿了。我有张很好的书桌,但还是比较喜欢在床上工作,像一首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诗里,那个逐渐康复起来的病人。一具用好几个枕头撑起来的乐观主义僵尸,制造几页梦游者才种得出来的果实——有的还不太熟,有的又熟过了头。偶尔我就直接把稿子打进我轻薄的笔记本电脑里,同时有点愧疚地抬头瞄一下书架上那台使用老式色带的打字机,旁边还有另一台过时的Brother牌文字处理器。难以消除的忠诚使我无法抛弃它们中的任何一个。然后还有大堆的笔记本,召唤我用内容来把它们填满——告解、揭露、同一个段落没完没了的重写变奏,以及一堆兴之所至、滔滔不绝潦草记下、事后却怎么也看不懂的餐巾纸。干涸的墨水瓶,结痂的笔尖,笔本身早就找不到了的备用笔芯,没有铅笔芯的自动铅笔。作家所留下的残骸瓦砾。

罗贝托·波拉尼奥的椅子,布拉内斯,西班牙
我没过感恩节,拖着浑身的不自在经历了十二月,沉湎于时间延长、程度也加剧的孤寂心境之中,却很可惜没有结晶成为任何值得一提的作品。每天早上,我把猫群喂了,默默地将自己的东西收一收,然后走几步路横过第六大道到伊诺咖啡馆,坐进我平常盘踞的角落那一桌里,喝咖啡,假装写点东西,或者真的就热诚地写起来,写出来的成果却都差不多一样的不成气候。我尽量避免参加各式活动,还强势地做了安排,让自己能够一个人过节。圣诞夜,我帮爱猫准备了浓香猫薄荷的玩具老鼠,自己没想清楚要去哪儿,就出门走进这个空荡荡的夜里,最后踏进了一家靠近切尔西旅馆的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晚场的《龙文身的女孩》。我在街角的熟食店买了票、大杯的黑咖啡和一袋有机爆米花,然后走进电影院,在后排把东西放好坐定。观众席里只有我跟其他二十多个都市浪人,舒舒服服地远离这个世界,自成一格地过起我们心旷神怡的佳节假期,不用什么礼物,不用圣婴耶稣,不用金箔拉花彩带,不用槲寄生,只有一种完全自由的感觉。我喜欢这部电影的外观。之前我已经看过没有字幕的瑞典版,但是没读过原著小说,所以这么一来我可以把情节给拼凑起来,同时尽情陶醉于萧索的瑞典风光之中。
我过了半夜才回到家。相对起来,这一晚天气还算暖和,我最主要的感觉是平静,这种平静慢慢汇聚成一种想回到家钻进自己被窝里的欲望。在我住的那条街上,空空荡荡,没有什么看得出来的圣诞节的痕迹,只有一点零星的拉花彩带挂在打湿的树叶上。我跟摊在沙发上的几只猫说了晚安,走上楼梯回到自己的房间,其中那只小个的、金字塔色皮毛的阿比西尼亚猫开罗,尾随着我上楼。我打开一个上了锁的玻璃柜,小心翼翼地取出包得好好的法兰德斯制的耶稣诞生彩像,里面有圣母玛丽亚与圣约瑟,两头牛,和躺在摇篮里的圣婴,我将它们全部摆在我书架的最上层。过去的两百年光阴,给这些骨制的雕塑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太遗憾了,我心里想,这些牛做得那么传神,却只有圣诞节期间才能被拿出来展示一下,真是可惜了。我祝圣婴生日快乐,然后把床上的书和纸张都挪开,刷了牙,床罩折下来,让开罗睡在我的肚子上。
新年前夜也差不多是同样故事的重演,没有什么特别的解决之道。当几千名饮酒狂欢的民众在时代广场大肆买醉之际,我正在全力对付一首打算要在新年伊始抢先完成的诗,为了向伟大的智利作家罗贝托·波拉尼奥致敬,沉吟之间,那只阿比西尼亚小猫就在地板上围着我的脚步转圈圈。在读他的《护身符》一书时,我注意到其中有一段提及百牲祭——古时候大规模屠杀百头公牛的隆重献祭。我于是决定要为他写一首百牲祭——一首百行的诗,以表达对他把短暂的宝贵余生用于勉力完成巨著《2666》的谢意。如果老天能够多给他几年的时间,继续活着,跟他的孩子多点时间相处,往下再写几部小说,那该有多好。因为《2666》的设定是似乎能够一直不断地写下去,只要他还有意愿写。这么美好的波拉尼奥,却命薄如此,在写作巅峰的五十岁年纪,就这么英年早逝,实在太可惜、太让人抱不平了。不管怎样,失去了他,本该写出来的作品就这么没了,使得我们无缘得窥一个世界的奥秘。
一年中的最后几个小时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流逝,我写了又重写,然后大声地朗诵出声。但是到了时代广场的大球落下来时,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小心写了一百零一行,而且无法决定到底要牺牲掉哪一行。我又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漫不经心地盘算着,要来屠杀书架上那两头俯视圣婴的、闪闪发亮的骨制牛的同类。这个仪式虽然只是字面上的,然而有差吗?我的牛只是用骨头雕刻的,然而有差吗?经过几分钟来回的反复思考,我暂时把我的百牲祭给放到一边,用笔记本电脑切换模式来看部电影。在看《马太福音》的过程中,我注意到帕索里尼片中的年轻玛丽亚的样子非常像跟她差不多年轻时的克里斯汀·斯图尔特。我把画面暂停,去泡了一杯雀巢速溶咖啡,随便套了件连帽衫,走到外头坐在门廊下。气温很冷但天空清朗。几个有点醉意,也许是从新泽西来的年轻人大声问我:
——操,现在什么时候了?
——该去吐一吐的时候了,我回答。
——别在她面前说这个字,她整晚搞的都是这个字。
她光着脚丫,红头发,穿一件亮片迷你裙。
——她怎么没穿外套?要不要我找一件毛衣给她?
——她不要紧。
——好吧,新年快乐。
——已经跨年了吗?
——对呀,大概四十八分钟前。
他们快步地转过街角消失了,留下一颗泄气的银色气球在人行道上滚来滚去。我走过去把它捡回来。
——差不多也就这样了,我大声地自言自语道。
雪。下得几乎有我靴子这么高的雪。我披上我的黑外套和针织帽,像个尽职的邮差一样,步履维艰地穿越第六大道,把自己例行运送到伊诺咖啡的橘色雨篷前。给波拉尼奥的百行诗还是煞费苦心地改了一遍又一遍,平常只有早上窝在那儿,这天却顺理成章地坐到了下午。我点了白豆汤,杂粮面包蘸橄榄油,又续杯更多的黑咖啡。我重新算了算百行诗的行数,现在变成缺三行。有九十七条线索可以下手,但就是找不到头绪,只能暂时先放一边了。

我应该离开这里,我在想,离开这个城市。但我要去哪里,才能摆脱掉身上这股似乎怎么样也振作不起来的无精打采呢?它就像是被内心不安所驱策的十几岁曲棍球选手身上,老背着的那个大帆布袋。如果离开,那我每天早上要怎么继续窝在我的小角落里呢?每晚深夜又要怎么拿着难以控制的遥控器一台一台地转呢?那个遥控器太难用了,每次都要按好几下才能有反应。
——我已经帮你换电池了,我语带恳求地说,妈的你倒是给我转台呀。
——你不是本来应该要工作的吗?
——我在看我的犯罪剧集,我毫无愧色地自言自语,这可是要紧的事。昨天的诗人是今天的侦探。他们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要嗅出这第一百行诗,侦破一个案子,然后精疲力竭拖着脚步走向日落尽头。这些节目娱乐我也支撑着我。林登和霍尔德。戈伦和埃姆斯。霍拉肖·凯恩
 。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学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为他们的失败痛心,而且每一集播完了很久,还在想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首播还是回放。
。我跟他们走在一起,学着他们的行为举止,为他们的失败痛心,而且每一集播完了很久,还在想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不管是首播还是回放。
手上这个小小的遥控器居然可以如此目中无人!或许我实在应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自己会跟没有生命的东西说起话来。不过,因为这玩意从小就在我清醒的生活之中扮演某种角色,都习惯了,不觉得有什么问题。让我困扰的反而是,为什么每年一月我都会染上春倦症。为什么我脑子里的皱褶好像蒙上了一层花粉。我叹着气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一检视着珍视的物品,确认它们并没有被吸到什么东西都硬生生消失不见的半次元空间里去。那是些超越袜子或眼镜这种日用层面的东西:凯文·席尔兹的EBow1,一张弗雷德睡眼惺忪的快照,一只缅甸的献钵,以及我女儿亲手用黏土捏的一只奇形怪状的长颈鹿。我在我父亲的椅子前定格了好一会儿。

当年我父亲用这张椅子坐在他的书桌前,历经几十年,开立支票,填表报税,或是狂热地研究赛马的让分投注技巧。一沓一沓的《电讯晨报》堆在墙边。他用一本绒布包面的日记簿,在上面记满了想象中下注的输赢,存放在左手边的抽屉里。家里没有人敢去动这个本子。他下注是根据什么,从来都不肯说,但是持之以恒,苦心研究。他不是那种会赌钱的人,实际上,也没有余钱可以下注。他就是一个工厂的男人,怀抱着数学层面的好奇心,从预测赛马中寻找乐趣,希望能探索出其中的制胜模式,由或然率入手,来开启人生意义的大门。
那时从旁观察之下,我对父亲颇为佩服,他似乎就这样轻易地遂其所愿,和我们的家居生活隔了开来。他为人慈祥,而且心胸宽阔,具有一种内在的优雅,使得他跟我们家的左邻右舍都不太一样。但是他对邻居从来都不会摆出一副优越的态度。他就是一个行事正派、脚踏实地的男人。年轻的时候有跑步的习惯,各项运动都很擅长,平衡感也优于一般人。二次大战的时候,他曾被派驻到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的丛林里。虽然他反对暴力,当时还是忠于国家、奋勇作战,但投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让他很伤心,对我们这个物质至上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残忍和软弱唏嘘不已。
我父亲工作时上的是夜班。他白天睡觉,我们还在学校的时候他就得离家去上工,然后要到很晚我们都睡了,他才会下班回家。周末我们会体贴地不去打扰他,毕竟他平常能够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太少了。他会坐在最喜欢的椅子上,《圣经》摊开放腿上,看电视转播棒球。他常常会把《圣经》里的一些篇章大声念出来,希望能够引起我们的讨论。他也会不时提醒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存疑。一年当中有大半年,他都穿着一件黑色的汗衫,深色的旧裤子卷在小腿肚和皮拖鞋之间。他脚上一定都会有这双拖鞋,因为妺妹、弟弟和我会存上一整年的零钱,每年帮他买一双新的当做圣诞礼物。到了晚年,他特别热衷于喂鸟,不管天气如何,鸟都会很捧场,只要他一叫就会来,降落到他的肩膀上。
他过世的时候,我继承了他的书桌和椅子。书桌里有个雪茄盒子,装着一些注销的支票、指甲刀、一只坏掉的Timex手表,和一张发黄的剪报,上面是1959年,我在一个国家安全海报竞赛里得到三等奖时的灿烂笑容。那个盒子我始终还是放在右边最上面的抽屉里。那张被我妈没头没脑地贴满了鲜艳玫瑰花贴纸的结实椅子,现在还靠在我床脚对面的墙上。坐垫上的一个香烟烧痕使得这把椅子更有历经沧桑之感。我伸出指头去抚触那个烧痕,脑海中浮现出他的骆驼牌无滤嘴香烟的软包装。约翰·韦恩也是抽这个牌子的烟,包装上的图案是毛色金黄的单峰骆驼和棕榈树剪影,唤起异国风味与法国外籍军团的印象。
你应该坐到我上面来,他那把椅子敦促着我,但我就是提不起劲坐上去。以前我们都不准坐到爸爸的书桌前,所以他这把椅子我现在也不拿来坐,只是摆在身旁。前几年我去波拉尼奥在西班牙南部海滨小镇布拉内斯的家里参观时,曾经坐过一次他的椅子。我当时就后悔了。我之前对着他的椅子拍了四张照片,椅子的样式很简单,但波拉尼奥不管怎么颠沛流离,搬到哪里都把它带着,他相信这张椅子的魔力。这是他写作的椅子。我当时是不是觉得,坐上那张椅子就可以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作家?在自我告诫的战栗之下,我把装裱相框上的灰抹掉,里面框着的,正是那张椅子的宝丽来照片。
我下楼去抱了两整箱的东西回到卧室,把里面的东西倒在床上。该来看看刚过去这年的最后一批邮件了。首先筛检淘汰掉诸如朱庇特海滩分时享用的度假房、专门给老年人设计的生财之道等小册子,还有彩色精印的厚厚一沓资料,教我怎么把累积的飞行里数兑现成各种诱人礼物,全都原封不动送去回收筒,一想到要砍掉多少树木才能折腾出这堆没人拜托他们生产的废物,自然也不免有点罪恶感。除了这个,当然也有一些好的广告目录,介绍19世纪的德文手稿、垮掉一代的纪念文物,甚至于一卷一卷的比利时中古亚麻布,这些目录则堆在厕所旁边,以备未来消遣。我无所事事地经过我的咖啡机,它像个蜷缩着的和尚,安坐在我放瓷杯的金属柜上。我拍拍它的头,避免和一旁的打字机和遥控器有眼神交流,我突然发觉,有些没生命的东西就是比其他东西要亲切得多。

云移翳日,一道乳白色的光从天窗渗透下来,洒进我的房间。隐隐约约,我感觉到自己被召唤着。有个什么东西正在召唤我,所以我一动也不动,就像《谋杀》片头里的侦探莎拉·林登,在黄昏的沼泽边上。我慢慢地向前走到书桌,把桌面抬起来。我并不常打开这个桌面,因为里面的珍贵物品保存着不堪回首的往事。不过很庆幸,我不必往里面看,我的手对里面所放置的每一件东西的大小、材质和位置都了如指掌。从一件我小时候穿过的裙子下面,我取出一个小小的金属盒子,盒子上有一些小孔。我打开之前,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因为我一直怀抱着某种不理性的恐惧,觉得里面神圣的收藏一旦突然受到外面涌进来的空气冲击,就会烟消瓦解消失无踪。但是还好,一切都原封未动。四根小鱼钩,三根羽毛假饵,还有一根假饵是紫色半透明橡胶材质的,看起来像一颗Juicy Fruit或者Swedish Fish牌软糖,形状则像一个带着螺旋形尾巴的逗点。
——哈啰,小鬈毛!我低声唤着,一瞬间跟着高兴起来。
我用指尖轻轻敲着它,感受到重温旧梦的暖意,在北密歇根安湖上,划着船和弗雷德一起钓鱼的时光浮现脑海。弗雷德教我怎么抛钓线,还给了我一根便携型的Shakespeare牌钓竿,分解开来的各部零件,可以很妥帖地像一束箭般,装进箭筒一样的携行盒里。弗雷德抛起钓线动作优美、耐性十足,身边总是备妥火力充沛的假饵、鱼饵和铅坠。我则使用我的抛射杆,携行盒里还装着小鬈毛——我的秘密帮手。我的小假饵!我怎么会忘记我们共度的那些具有先见之明的甜蜜时光呢?当我把钓线抛进深不可测的湖水里,它总是称职地跳着探戈,勾引滑溜的鲈鱼上钩,好让我之后去了鳞煎给弗雷德吃。
如今国王已然驾崩,本日停止渔业活动。
我把小鬈毛好好放回桌子里,重新提起精神来处理我的邮件——账单、请愿书、逾期的典礼邀请函、开庭日近在眼前的陪审通知。接着,我迅速地挑出一封吸引我注意的邮件——是一个普通的牛皮纸信封,上面盖着封蜡,显示着缩写前缀CDC。我快步走向一个锁着的柜子,选了一把细骨柄的拆信刀,这是打开来自大陆漂移社(Continental Drift Club)所寄来的珍贵信件的唯一正确方式。信封里装着一张红色的卡片,印着黑色的数字二十三,还有一纸手写的邀请函,请我一月中旬在柏林举办的半年大会上发言,内容不拘。
看到这封邀请函,我兴奋满满,但时间所剩不多,发信的时间已经是几个星期前。我把桌子清了清,连忙给他们写了个即将赴会的回复,接着满桌子到处找邮票,抓上我的针织帽和外套,把回信丢进邮筒。然后我越过第六大道,又去了伊诺咖啡馆。时间是近晚的下午,店里都没有人。我坐到我的老位置上,本来打算拟一份这趟旅程要带的物品清单,结果却沉湎于白日梦,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好多年前到过的不来梅、雷克雅未克、耶拿,还有很快将会再度前往的柏林,在那里又可以见到大陆漂移社的好朋友们。
1980年代由一位丹麦的气象学者创立的CDC,是地球科学团体分支出来的一个立意不甚明确的社团组织。成员有二十七个人,散居世界各地,他们誓言要致力于
让人类整体的记忆长存
,特别是有关于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的事迹,他是世界上最早提出大陆漂移理论的先驱。这个组织每两年开一次大会,全体会员都要参加,对内部规程予以审酌,表决经援某些申请CDC补助的实地考察,对组织所支持的推荐书单也投注相应的热情。这一切都是为了跟魏格纳身后以他为名的另一个世界组织,设立于德国下萨克森州城市不来梅港
 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圈与海洋研究中心”并肩奋斗共同努力。
的“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极圈与海洋研究中心”并肩奋斗共同努力。
我之所以取得CDC的会员资格其实纯属偶然。大致来说,这个组织的成员是以数学家、地质学家和神学家居多,成员在组织中不是用原来的名字,而是被赋予一个号码。当年我给魏格纳研究中心写过几封信,托他们寻找一位继承他遗物的后人,想得到允许去拍摄这位伟大探险家生前穿过的长靴。其中一封信被转到大陆漂移社的秘书手上,通了几封信之后,他们邀请我去参加2005年在不来梅召开的大会。那一年正好是魏格纳125岁冥诞,也是他逝世75周年。我出席了他们的座谈会,还在“City 46”参加了纪录片《冰上研究与探险》的特别放映,片中用到了魏格纳1929和1930年探险考察时拍摄的珍贵片段。之后又跟他们一起去不来梅港附近,对魏格纳研究中心的设施做了一次私人访问。我很清楚我并不符合他们的入会标准,但我猜想经过一些考虑之后他们接纳我,是因为有感于我丰沛的浪漫热情。2006年我变成正式成员,被授予的号码是二十三。
2007年我们在雷克雅未克开会,那是冰岛最大的城市。那一年有些会员计划在会后继续前往格陵兰,进行一次CDC的独立探险考察,所以开会的时候都显得异常兴奋。他们组成了一支搜索队,希望能找到1931年魏格纳的弟弟库尔特为了纪念兄长而安厝的十字架。十字架由几根铁棍搭建,二十多英尺高,用来标示他的长眠之所,大约在距离伊斯米特营区西边一百二十英里处,那是他的探险伙伴最后一次看到他的地方。不过在那个时候,十字架确切的位置还没人知道。我当时真希望自己也能去,因为我也知道这个大十字架的事迹,如果能够找到,肯定可以拍出非常棒的照片,可惜我的身体条件没办法承受那样严酷的考验。但我还是待在冰岛,因为组织中的十八号,是一个身体强健的冰岛国际象棋大师,他出乎意料地请我代替他去主持一场在当地被高度期待的国际象棋比赛。如果我帮他这个忙,那他就可以参加搜索队去深入格陵兰了。这么一来我可以得到博格旅馆的三晚住宿,还能获准拍摄1972年博比·菲舍尔和鲍里斯·斯帕斯基对弈时用过的棋桌,它平时都被闲置在当地政府机关的地下室里。鉴于我对国际象棋的热爱完全只在审美层次,我对受命观棋这个任务有点缺乏自信。不过有机会去拍摄现代国际象棋界的圣杯,倒是足够补偿不能去格陵兰的遗憾了。

隔天下午,我带着宝丽来相机抵达的时候,那张棋桌正悄悄地被搬往棋赛大厅。它外观很不起眼,但上面有两大棋王的签名。结果发现我的任务很简单,参加棋赛的都是一些青少年,而我只要露个面就好了。最后胜出的选手是一位十三岁的金发少女。拍完合照之后,我有十五分钟可以拍那张棋桌,可惜当时灯火通明,完全不适合照相。大伙的合照拍得比较好,还登上了当地的早报;那张有名的棋桌也在大家的前方一起入镜。吃过了早餐,我跟一位老友到乡间转了转,骑上了粗壮的冰岛小马。友人骑的是匹白马,我骑的是黑马,和国际象棋里的马一样。
我回来的时候,接到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自称是博比·菲舍尔的保镖。他受命来安排我跟菲舍尔先生在博格旅馆餐厅的半夜私下会面。我可以带我自己的保镖,但是不可以提起跟国际象棋有关的话题。我答应了这场会面,然后走到广场对面的夜店Club NASA去找他们的首席技师,是一个我信得过的家伙,名字叫斯基尔斯,来充当我的临时保镖。
博比·菲舍尔半夜时分穿着一件深色的连帽派克大衣来到旅馆。斯基尔斯也穿了一件连帽派克大衣。博比的保镖比我们所有人都高。他跟斯基尔斯一起等在餐厅外面,博比选了一个角落里的餐桌,我们面对面坐下来。他马上就开始测试我,讲起一连串令人不快、甚至极端惹人反感的话题,说着说着就演变成偏执妄想、怀疑事情别有用心的大声嚷嚷。
——你这根本是在浪费时间,我说,我也能跟你一样难搞,只是针对的事情不同。
他坐在那里不再说话,盯着我看,然后终于把风帽给脱了下来。
——你会不会唱巴迪·霍利的什么歌?他问我。
接下来几个小时我们就坐在那里唱歌。有时候是他或我独唱,有时候是两人齐唱,歌词大概能记得起一半吧!期间他还想用假音唱《大女孩别哭》的和声,他的保镖有点紧张地跑了进来。
——没什么事吧,先生?
——没事,博比说。
——我好像听到有什么奇怪的声音。
——是我在唱歌。
——唱歌?
——对呀,唱歌。
这就是我跟博比·菲舍尔碰面时的情况,20世纪最伟大的国际象棋手之一。黎明曙光将出之前,他竖起风帽出门离去。我留在餐厅里,直到旅馆的工作人员上班,开始准备起自助早餐的各式菜色。我坐在他的空位对面,想象着大陆漂移社的成员们这时应该还在睡梦中,或者是因为太期待而情绪亢奋辗转难眠。再过几个小时他们就会起床,开始往冰天雪地的格陵兰内陆前进,去寻找当年竖立大十字架的往事陈迹。当厚重的窗帘被拉开,早晨的阳光涌进小小餐厅的那一刻,我忽然想到,毫无疑问,有时候我们的梦想就是会被现实所遮翳。

野牛,动物园,柏林